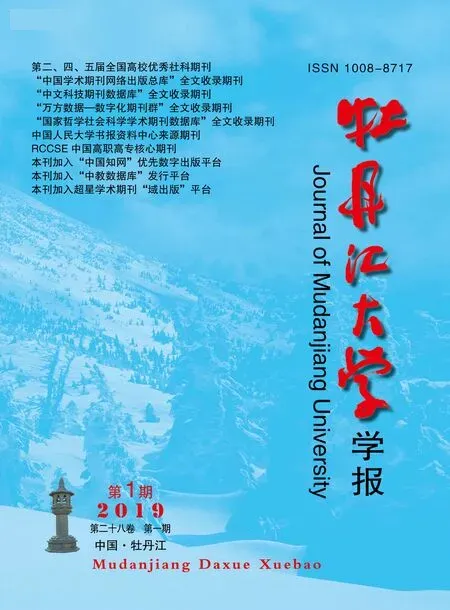从存在符号学视角解读《中国佬》中华裔的边缘生存
2019-12-30王素佳王绍平
王素佳 王绍平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
一、引言
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是美国当代主要作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备受瞩目,其主要作品《女勇士:一个女孩在群鬼间的生活忆往》(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1976)、《中国佬》(China Men,1980)、《孙行者:他的即兴 曲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1989)以及《第五部和平之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2003)享誉文坛。著名学者张敬钰教授在接受单德兴访谈时指出:“汤亭亭的《女勇士》是美国大学校园中,在世的美国作家的作品中最常被采用作教材的。”[1]315
汤亭亭的《中国佬》(China Men)发表于1980年,这部将自传因素与中西方文学典故和“小说化”的历史融合在一起的作品,讲述了四代华人移民的历史。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族裔文学研究的持续升温,对于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有的研究通过描述《中国佬》中呈现的中国传统故事、西方传统故事及红色中国形象等探讨读者反映;[3]85卡拉·纽鲍尔通过照片等记忆资料,着重阐释记忆与过去在《中国佬》中的重要性。[4]17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对《中国佬》研究虽然2000年后起步,但研究视角多样。陈晔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华裔的离散身份建构——以汤亭亭小说<女勇士>和<中国佬>为例》一文中,从斯图亚特·霍尔的“差异理论”入手分析两部作品中华裔群体的身份建构问题。[5]167刘心莲在《中国神话重写与美国华裔人的身份迷失》一文中,从中国神话、传说以及民间故事的改写这一角度,探讨华裔美国人的性别和文化身份的迷失。[6]168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出,从塔拉斯蒂的存在符号学角度探讨华裔群体在美国的边缘生存,至今鲜有论述。
汤亭亭在创作《中国佬》时,以自身家族几代男性生活经历为原型,将四代华裔美国人的历史事实以文字的方式记录成册,再现了整个华裔在美国的艰辛生存历程。对他们来说,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处于流散和无可皈依的状态。“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到哪里去?”这样的疑问充斥在每一个华裔的心里。因此,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塔拉斯蒂的存在符号学理论,从“否定”——身份迷失到“肯定”——身份建构这两项超越行动,来分析《中国佬》中华人在美国从备受歧视到逐渐被接受的历程,再现华裔在美国的边缘生存状态。
二、存在符号学简述
当代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通过对各种生活符号的破译向人们表明,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并非一个由纯粹事实构成的经验世界,而是一个由各种符号形成的意义世界。[7]137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人生的存在需要用符号来证明。20世纪初,索绪尔和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合力创建了符号学。随后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C.W. Morris)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7]135埃罗·塔拉斯蒂将这种动态的、时间的、流动不止的世界模态化,试图进行这样一种尝试。2000 年,他出版了《存在符号学》,作者将之称为新符号学(Neo-semiotics)。[8]21
存在符号学或新符号学是一种不同于以皮尔士、格雷马斯、西比奥克等为代表的经典符号学家的理论。[9]182塔拉斯蒂认为,“存在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形成之前的状态,是“前符号”,是对符号的一种动态研究。“在那儿,一切事物处于运动之中,没有稳定的、井然有序的或固定不变的事物。”[10]18“存在的符号时刻是在符号形成之前或之后的时刻,因为符号的生命不会停下来,它们总是处于形成的状态。”[10]7在存在符号学理论中,符号重新焕发生命,主体重新得到思考,全新的概念亦被带进了符号学理论,比如超越。[8]22主体进行超越的行动在《中国佬》中的几代华人移民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集中表现出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主体,不断地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摸索前进,超越自身。主体在塔拉斯蒂的“此在——存在”这一模式的观念基础是:存在是一种“becoming”的超越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这一主体必须首先在客观符号中找到自身,即“此在”,然后以“存在”为目标,不断地运动,向其靠近。[10]18华裔离开家乡故土,向“美丽的国家”迈进,就像是一个个存在的符号漂浮在空中,不停地移动,进行着主体的超越。
三、存在主体的边缘生存——超越行动
存在符号学认为,“每个人都有对于自己和他人变得有意义、富有意义的欲望和被理解的欲望。”[10]8追求主体存在的意义起源于主体对自己现状及所存在的世界的不满足,主体要想达到超越必须要通过“否定”和“肯定”运动。对华裔而言,无论是被迫出走他乡,亦或是主动出国深造,他们自离开中国文化起,就开始面向未知世界进行自我身份的“否定”及自我身份的“肯定”之旅。那么,这两项行动是如何来演绎完成这一历程呢?
第一种是否定,主体认识到自身存在所处环境的空虚和虚无,主体朝向“虚无”进行飞跃,这构成了第一次超越行为,即“否定”[10]18。对于华裔群体而言,在经历无尽的饥荒、赋税及征兵后,他们试图离开中国文化这一领域,去追寻更加自由、美好的生活,这就是否定的开始。“他们在空中漂浮,寻找可安顿的居所,凸显的美国文化域成为了他们的目的地,于是符号飘落下来,他们进入了美国文化域,在其边缘生存定居。”[14]182汤亭亭在《中国佬》中陈述了华裔离开中国并奔赴美国的原因,阐明了推动华裔进行“否定”运动的因素。凶残的战场,冷酷的服兵役制度,迫使中国男性不得不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逃过征兵。作品中的母亲为了让父亲避免上战场想尽了荒谬的办法,甚至不惜搞坏了父亲的身体。此外,“另一个必须要离开中国的原因是赋税”。[12]279由于地主军阀对农民大肆的掠夺,使得许多人家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亲人来抵押债款,这种严苛的赋税政策使大部分人无法继续承担,只好出逃到“和平的国家、自由的国家和美丽的国家去。”[12]37服兵役、赋税还有无止境的饥荒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了不安,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要离开中国这个母体去未知世界探寻。
接下来,符号进行超越的第二次行动——肯定。通过肯定,通过远距离扫描,了解它们穿过前一层面的不足,好像它们是根据更深层面的参考框架做出的承诺。正是在这种分离与返回的过程中,符号转换为连续的运动;它们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对象,而是以全新的方式自由塑形。[10]30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主体找到了存在的理由,而且,对于专注于它的主体辐射出一种新的意义。这个时候,主体感受到了生命的“充实”。[10]11对出走他乡的华裔群体而言,他们迈出此在的动力是充足的。带着美好的期许,那些离开妻儿的中国男人一踏上美国的国土,似乎就感受到了来自这个“美丽的国家”深深的“善意”——天使岛上非人类般的盘问刁难,种植园中像牲畜一样干活的“奴隶劳动营”,用生命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人劳工们——这样拿着生命的赌注在生存环境恶劣的他乡,艰难地在边缘地带生存。“别多管闲事,像牛一样干活儿。种植园上有条规矩,就是干活儿的时候互不说话。”[12]98这荒诞的规矩剥夺了曾祖父等早期华人移民的话语权,他们干比别人更多的活,赚比别人更少的钱,甚至还莫须有的被禁语,这一系列对华工的折磨不得不让他们对自己的存在产生怀疑。美好的期许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噩梦的不断延续。在这个华裔被视为“怪物”的国家里,他们追寻到最后,发现了他者的有色眼光,不是“自己是谁”的问题,而是“他者是谁”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探索这个由他者构成的此在,并对此进行颠覆和反思。
《中国佬》中有很多人像曾祖父一样,选择最终回到中国去,比如宾叔。他们虽因种种原因选择回归家乡,但此次的回归一定是以全新的方式和思想回归。与之相对,像高公、少傻等选择继续留在美国的华裔,他们终其一生都待在这个国家里奋斗、工作,在美国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所以,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他们都不是绝对的排斥和接受,而是希望通过两种文化的融合,构建自己独特的身份,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成为真正的“符号自我”。
四、结语
在《中国佬》中,汤亭亭用语言和故事来还原历史上缺失的真实事迹,为长期得不到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华裔群体正名。因此,《中国佬》不再仅仅是一部自传式的家族史,而是一部华裔美国人的移民文化史,是一次通往华裔群体的心灵之旅。在这个旅程中,他们不断地进行“否定”再“否定”,直到经历了“肯定”之后,追寻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汤亭亭用笔记录和书写着华裔主体与“家”这一客体断裂后的焦虑和追寻的存在足迹。因此,对华裔群体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存在过程,经历过后才能完成华裔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超越之旅,实现华裔属性与美国属性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