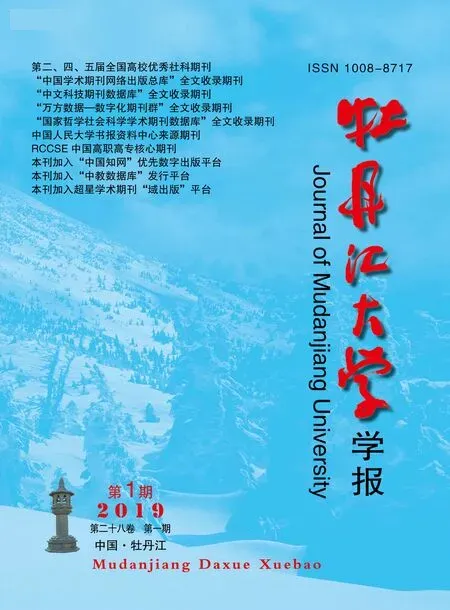论我国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性怀疑”规则的理论困境与完善进路
2019-12-30夏军营
夏 军 营
(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一、中国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性怀疑”新内涵
“排除合理怀疑”,其设计初衷并非保护被追诉人,而是慰藉审判员的灵魂。[1]在基督教的神学教义之中,如果审判员在作出对被告人的判决之时,不存在“合理怀疑”,那么审判员的灵魂便不会受到鞭挞,良心也不需要自责。[2]可见,“排除合理怀疑”之所以存在,纯粹是为了让裁判者独自去承受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尽管这项规则运行已久,但是在中外法学界从未给与“排除合理怀疑”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能够机械的将“排除合理怀疑”定性为原义上的法律术语,它应当是法律观念、诉讼理念、意识形态等各综合性因素互融且互斥的结果,代表一套具有多元性的、内涵丰富的法理念、法制度和法经验。[3]对于衡平法系的国家来说,通常通过“确定性”来对排除合理性怀疑加以解释。以美国为例子,在1990年的凯歌案件,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对排除合理怀疑作出了解释,他们认识这种合理的怀疑不是恣意的怀疑,是建立在事实与证据基础之上的怀疑,而且决不能超过社会一般人的一般观念。[4]在1994年的维克托案件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又赋予了“确定性”更为详细的内涵。“确定性”就是头脑中决定的“盖然性”,对于一个社会一般人来言,当他面对重要的选择和决定之时,头脑中是否打消掉犹豫,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如果决定的作出者没有丝毫的踌躇,就认为排除了合理怀疑。
反观我国,“排除合理怀疑”制度一直被人广泛提及,却从未真正的研究和推广。甚至在第一部刑诉法出台到2012年新刑诉法诞生这漫长的时间之内,还存在着拒绝和接受的激烈争论,直到2012年新刑诉法给出了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是,法律制度上的高标准却并没有在实践中做到严要求,存在着刑事证明标准降格适用的现象。[5]原因在于,尽管刑事诉讼法条文给予了“排除合理怀疑”一席之地,但是现实司法实践却没有该制度的生存空间。虽然存在了条文的规定,但是却没有给与其具体可操作的内涵,甚至由于专有名词的超抽象性而不能为社会一般人所理解。笔者认为应当给与“排除合理怀疑”基本的内涵,使其可以成为可把握、可操作、可理解的具体规则,而非形同虚设、泛泛而谈的法律装饰。既然如此,如何理解中国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呢?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认为我国传统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客观标准,那么“排除合理怀疑”就是与之对应的主观证明标准。笔者认为,尽管卡尔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中给出了学术研究类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刻意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主观证明标准,去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证明标准相对立,难免有学术研究过度类型化之嫌。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本身就具有主观相结合的天然性,而非人工雕琢的后天类型化。“排除合理怀疑”从主观层面来看,是指法官内心的确信程度;而从客观方面来看,它又是通过事实与证据的综合印证得出来的确定性,并非不切实际的纯粹主观猜测,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因此,中国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与事实基础之上的主观印证标准,并非纯粹的主观证明标准。
二、我国“排除合理怀疑”制度适用的理论困境
法律移植当然要考虑不同法系之间司法环境的“异质性”。我国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的舶来品,应当在移植的过程之中审慎的分析中国司法环境的现状。因此,笔者通过我国和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司法环境的对比,发现我国“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运行的理论困境。
(一)法律思维的桎梏
西方人崇尚自由与法治,而在自然的正义价值观之中,程序正义的精神渐渐被延伸出来,并且得到推崇。英国人法律思维的模式是规则优先,程序优先。他们认为时间具有着一维性,犯罪事实已经发生,不可能被回放和复制,任何调查都不可能还原绝对的客观真实。因此,绝对的客观真实从人类认识规律角度来看,是绝对不可能通过侦查行为查清。而在美国更是如此,1995年轰动整个世界的辛普森杀妻案,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推向了整个世界,激起了司法界与学术界的轩然大波。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程序正义精神的扩展与延伸。只要是程序是正义的,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就应当是正义的,就算这个结果从实体法来讲是错误的也应当具有对世效力,为所有人所尊重。在我国的传统法律思维之中,一个刑事案件发生之后,没有人会关心规则和程序是如何规定甚至是如何执行的,民众只关心绝对的客观真实有没有被查清,“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才是至上真理。而在司法实际的过程之中,公检法除了自身带有“实事求是”的客观属性,更为致命的是还要发挥求和维稳的作用,防止发生民愤、民怨事件的发生,因此,更容易受到民意的裹挟。案件真正流转到法院,交予法官审理的时候,法官已经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根本无法就案件事实和证据本身,完成高水准的排除合理怀疑。
(二)诉讼构造的异化
意大利在1930年刑事诉讼之中,诉讼构造就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预审法官权力极度膨胀,不仅挤压掉了司法警察的侦查权力,而且严重压缩了检察院的起诉权,成为了横跨侦诉审三方的主导角色。因此,在1988年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之中,意大利高度削减了预审法官的权力,从绝对的纠问式诉讼构造转向了当事人对抗主义模式。[6]因此,尽管意大利是大陆法系国家,但是其“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有着充分的对抗制诉讼构造的土壤。而美国更是当事人对抗主义模式的代表,侦诉审三方相互独立,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庭审阶段更加是注重庭审的实质化,法官只负责法律审,大小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因此,美国刑事案件的“排除合理怀疑”不是单独的个体的排除合理怀疑,而是集体的群众的排除合理怀疑,这就大大降低了个体法官判断的偶然性。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却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一方面,我国侦诉审之间的纵向诉讼构造是典型的“流水线”模式,三机关配合为主,制约为辅,同时侦查居于侦诉审三者的主导位置。[7]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旦提起公诉,无论是检察院还是法院都不会轻易否定掉公安机关的成果,这必然导致案件的判决结果倾向于有罪而不是无罪。另一方面,我国的横向诉讼构造更类似于“倒三角形”,法院和检察院平等的居于上层顶点,而被告人被孤立在最下面的角点。法官与检察官都有着积极发现事实真相的客观真实义务,因此,法官更不可能做到理论上的排除合理怀疑。
(三)制度设计的阙如
“排除合理怀疑”不是一个孤立适用的刑事诉讼规则,需要相应制度设计的配套。从刑事司法原则来看,英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起诉便宜主义原则。检察官拥有巨大的裁量权,大部分案件都是通过辩诉交易的形式解决掉的。在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只有很少一部分案件进入到陪审团的审判。这充分体现了英国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是尽快妥善的解决刑事纠纷,而非一味的追求查明事实真相,追究刑事责任。而我国的起诉法定主义,发现犯罪就要追究犯罪。刑事案件达到法律规定的条件,公安机关必须侦查,检察院必须起诉,法院更可能做出有罪判决,那么法官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排除合理怀疑。从陪审员的实质作用来看,美国刑事诉讼的事实证明要经过大小陪审团的双重认定,特别是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认定主体的量呈现多元化,是检验排除合理怀疑质量的重要一个标准。相比之下,我国的排除合理怀疑由法官个体单独适用,即便是新修正的《陪审员法》已然出台,但是短期内依然难以改变陪审员参而不审的形式主义作业模式。除此之外,从机构设置来看,意大利刑事司法为了防止法官的预断,不仅设置了预审法官,同时还设置了双重卷宗制度。而我国1996年刑法曾经一度采用复印件主义,校正了79刑诉法的全案移送的弊端,但是在2012年新刑诉法出台之后,不仅没有选择呼声很高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反而调转方向,恢复了79年的全案移送。法官在正式庭审之前,已然在心中有了案件的结果,庭审更容易流于形式,那么,就更不可能去排除合理怀疑。
三、我国“排除合理怀疑”制度的完善进路
(一)革新法律观念
“排除合理怀疑”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刑事案件的证明问题设计的实务性规则,更能反映出整个司法环境所展现出来的法律理念与法律精神。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以法治为原则,而法治必然是程序之治和规则之治。[8]笔者认为,真正阻碍排除合理性怀疑适用的从根本上来说是整个国民的法律素养。法律应当被尊重,才能具备其应用的权威。时空具有一维性,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能被完全回放。而刑事司法要做的事情是,尽最大可能还原事实真相,而非一味的追求客观事实。这种法律理念的变化,一方面责在司法人员。正是由于传统上侦诉审之间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关系,导致法官在运用排除合理怀疑过程之中,不仅受到强客观义务的限制,同时还受到侦、诉机关的影响,无法完全独立的作出法律判断。因此,只有通过制定相关的业绩考核规则,才能鼓励或者限制法官的无为而判。另一方面,革新法律观念,重在国民。只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崇尚法律,那么就不会轻易产生民意裹挟法律的案件。司法改革过程之中最难改变的往往不是法律规则与制度,而正是国民的法律思维与法律观念。我国国民正是缺乏这种规则意识和程序意识,才会在很多场合作出出格的法律否定性评价行为。矫正法律观念就是要通过普法活动,让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辐射多元人群。只有为法官营造出良好的官民双维度司法环境,法官才可能真正的在刑事审判过程之中,排除任何干扰,高标准的适用排除合理性怀疑规则。
(二)再造诉讼结构
刑事诉讼的构造不仅反映了侦诉审三方在刑事诉讼之中的法律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加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的立法理念。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出现了严重的异化,侦诉审三方并没有体现出三权分立的监督与制约,更多的是进行流水线作业,机械的加工处理刑事案件。纵向刑事诉讼构造的严重畸形,导致了冤家错案的发生,比如呼格吉勒图案件。横向诉讼构造的异化更是使得被告人处于完全不利的位置,这也使得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之中发挥极为有效的作用。从我国的刑事司法时间来看,我国刑事案件代理律师能够将提起公诉案件辩护为无罪的概率特别低,更多的只是从重罪改成罪轻。而且近几年,随着刑事案件的数量不断的加速增长,我国刑事司法越来越倾向于效率主义。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陆续出台,在这些简易化刑事诉讼程序之中,法官更难做到每个案件都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构造更应该响应 “以审判为中心”的精神,要从侦查中心走向审判为中心,要以庭审为中心,与此相对应的是横向诉讼构造与纵向诉讼构造的重构。从刑事诉讼运行的整个过程来看,侦查与起诉绝不是办理刑事案件的重点阶段,只有审判是最终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审判为中心,就是要减少侦诉审三家长期办案遗留下来的熟人圈子、人情关系,防止侦诉乱审的发生。而从审判的整个过程来看,法官真正做出判断的阶段应当是在法庭,绝对不应该在庭审之前。因此,法律调查与法庭辩护阶段必须是精益求精的阶段,不能过于简化。
(三)创新制度设计
排除合理性怀疑规则的实际适用效果,离不开相应合理的配套制度。尽管我国现阶段的公诉原则是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起诉便宜主义为辅,但是实际司法实践几乎不存在便宜主义的空间。司法公务人员超强的发现真实的客观义务,难免会导致侦诉审三方在办案过程之中的速侦、速审的局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打”的刑事司法政策就导致了一大批案件超速结案,事后很多案件被证明是冤家错案。因此,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的逐步过渡是世界司法的潮流,一方面不仅可以约束公权力的滥用,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也可以迎合刑事诉讼繁简分流的趋势,缓解办案的压力。此外,既然将排除合理性怀疑纳入到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之中,就应该真正的防止法官的预断。从目前来看,设置预审法官的方法显然在员额制背景下缺乏实际可行性,但是全案移动的卷宗制度绝对可以进行改善,不应该再走回头路。尽管暂时无法借鉴纯粹的日本的“起诉状一本主义”,但是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学习意大利的“双重卷宗制度”,检察院要制作两份卷宗制度,一份留给检察官,一份送交至法官。检察官卷宗可以包含侦察机关通过侦查得到的一切证据,但是法官卷宗只能够包括起诉书等相关的材料以及证据保全得来的部分证据,除此之外再也不能纳入更多材料。最后,尽管我国人民陪审员法已经出台,但是陪审员参而不审的形式主义依然是个顽疾。每个陪审员应当是以此为责任,而并非以此为工作,走形式领份子钱。因此,在人民陪审员法制定的陪审员奖惩规则之外,仍有必要增加与法官相同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一旦案件出现了误判与错判,不作为的陪审员同样要承担连带责任,与有效辩护相对应的当然要存在有效陪审。真正做到是审判组所有成员的“排除合理怀疑”,而并非是法官一个人的“排除合理怀疑”,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适用主体的擅断与恣意。
四、结语
“排除合理怀疑”是一项伟大的刑事司法发明,它在域外刑事司法领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新刑诉法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中,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包容性。但是,法律移植应当全面考虑制度与环境的斥引性。只有通过中外刑事司法环境对比,找出我国司法环境对“排除合理怀疑”适用的理论困境与潜在阻力,才能不断的修正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