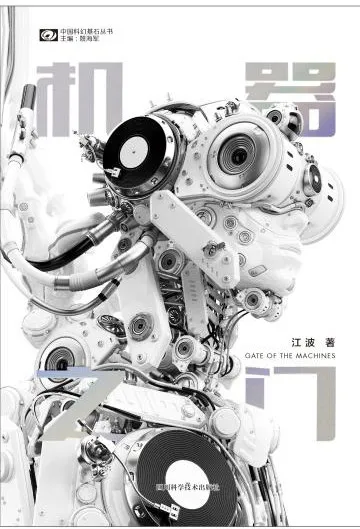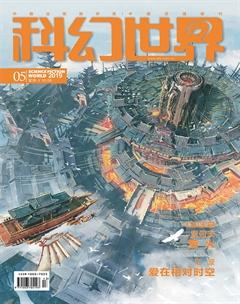热爱是最好的导师
2019-12-29江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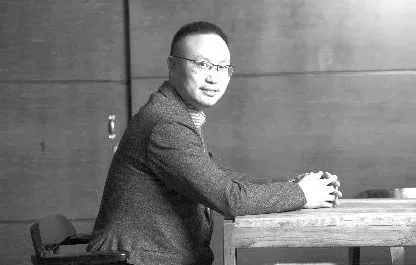
我算是资深科幻小说读者吧,从小学就开始看,那时候看的东西其实很杂,但我特别喜欢科幻小说。奇怪的是,我不记得小时候自己看过《科幻世界》,按理说,那时候喜欢看《奥秘》《飞碟探索》的孩子,应该也喜欢看《科幻世界》才对。然而,我真的不记得自己看过,这或许是记忆的错失吧。
进入大学,到了大三,我和《科幻世界》有了第一次间接接触。那时我的两位同学孙静和郭进,张罗着把清华科幻协会搞了起来,那是1998年。这或许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有科幻协会。然后,1999年的时候,《科幻世界》杂志社在清华大学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写了一篇上万字的小说《历史》,得了三等奖。这算是第一次和《科幻世界》发生关联。
在学校的日子,我总会写一些虚构类的作品,其中有两篇,自己觉得还颇满意,分别是《清华爱情故事》和《悟空传奇》,前者是校园爱情故事,后者是神魔小说,都获得了一些来自水木BBS的赞誉,《清华爱情故事》还被收到一本叫作《雕刻西风的木匠》的小说集里,占据了小半本的规模。自己的作品能印成铅字,让我颇为得意,稿费大概拿了三千多,当即花了两千请同学们吃了一顿日本料理。
那时,我也写了一些科幻小说,今天翻出来看,短篇居多,其中一篇稿子,写到了十万字,最后坑了,要是一直写下去,也算是科幻长篇了,而且是少年乌托邦类型(差一点儿填补一项空白……:))。短篇的稿子,都曾经向《科幻世界》投过稿,那还是从稿纸寄信到e-mail寄信过渡的时代,但不管是寄出的信还是发出的e-mail都如泥牛入海,茫茫不见踪迹。
我在BBS上曾经试图寻求和《科幻世界》联系。期间有两件有趣的事:一件是我把大刘当作了刘维佳,冒昧地给他写了封信,还写错了他的名字,把“刘慈欣”写成了“刘欣慈”。回想起来,以这种方式和如今的“中国科幻第一人”发生初次接触,有点儿奇妙的感觉;第二件是当时在BBS上有个有名的ID,看其发言貌似资深科幻评论家的样子,显得牛气冲天,我忘了此公是私信还是在版上回复我的,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写科幻是一件很苦、很不容易的事,让我放弃幻想,不要再往这个偏门上走。我当然没有听他的,因为写科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的过程,我完全不觉得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很幸运,把写科幻当作一种享受,容易不容易,辛苦不辛苦,那其实都不重要。
当然,如果一直没能够发表,可能等我离开清华大学之后,就和科幻分手了。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3年,临近毕业,我在实验室接到了电话。电话是刘维佳从编辑部打来的,告知我《最后的游戏》一文被决定录用了。那真是一个幸福满满的时刻,我就差在实验室里放声高歌了。《最后的游戏》这一篇科幻处女作,入围了倪匡科幻奖的决赛圈,但是最后没有得奖,但能够在《科幻世界》上发表,是我的幸运。这是一个重要的激励,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得以一直写下去,不知不觉到今天已经十六年了。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刘维佳,则一直是我的责编。这就是缘分哪!
2003年之后,我开始工作,在外企上班。外企在中国,相对比较闲适,我也继续保持着写科幻小说的业余爱好,大约每年发表一到两篇,一直持续到2010年。
为什么要把2010年拿出来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科幻世界》的笔会。在此之前,我对笔会没有什么兴趣,成都在很远的地方,飞机太贵,火车太慢,我根本没有任何想法要跑到那儿去加入一群陌生人,进行一场讨论。换言之,在2010年之前,虽然我每年不断发表科幻小说,但从来没有接触科幻圈,对圈内的人,仅限于知道一些名字,一直没有打过照面。直到2010年,《时空追缉》这篇小说拿了银河奖的杰作奖,这就是我去成都参加笔会的原因。
然而去了之后,拿奖就不再是原因了。
笔会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我遇到了许多之前只闻其名的人,经历了许多有趣的谈话,这让我感觉有点儿恍惚,像是被人从日常生活中突然剥离,放入一个角度迥异的世界里(这个感悟似乎是和陈楸帆交流时提到的,不过已经记不清是他的话,还是我的话)。我突然明白了笔会的价值所在。有些事,不亲身经历感悟,恐怕是无法理解的。
那时,我已经开始创作《银河之心》的第一部,写了大约十五万字。碰巧,《科幻世界》安排我和大刘住同一个标间,于是就有了一次夜谈。靠在床头,喝着啤酒,从琐碎人间聊到海阔天空。我记得以前刘维佳和我聊过一次创作,他说的是《地火》中的一个细节很令人印象深刻,并且说大刘是有阅历的人。我当时不以为意,直至这次喝酒聊天,我才理解这种阅历是怎么回事。在文学的框架内,好的科幻作者,无论其作品多么空灵飘忽,能够打动人的东西,必然源自现实生活。人类的基本情感千万年没有变化,哪怕在科幻的框架内也一样。阅历,是理解人类的唯一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显然做得远远不够。
然而至少字数是够了。大刘听到我已经写了十五万字,说这已经就是一个长篇了,很积极地鼓励我写下去。从笔会回来后,我继续创作《银河之心》,最后在2012年出版了第一部,二十七万字。
提到长篇小说的出版,就不得不提姚海军老师。写作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在开始写《银河之心》这个长篇之前,我写了几个较长的中篇,其中两篇被姚老师选中,刊载在《星云VII》这本书上。《星云VII》有其他作者的作品,但主打的是我的两个中篇,所以封面上的作者也就放了我的名字。这是一个巨大的鼓励,看到一本书的作者署名处填着我的姓名,这激励我再进一步,写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书。
2016年,《银河之心》三部曲完成了。其中姚老师多有鼓励和支持,也不一一赘言。
回到2010年的笔会。
笔会之后,我开始逐渐认识各位老师,听说他们的各种八卦,也了解到《科幻世界》的各种不容易,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幻世界》是全中国唯一能发表科幻小说的地方,可以说,杨潇社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把整个中国科幻扛在肩上,让中国的科幻之火在最困难的时刻没有断绝。了解得越多,我对于《科幻世界》也就有了越深刻的印象,它不仅仅是一个发表的平台,更是中国科幻的一个具体象征。在过去、现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谈到中国科幻,不谈及《科幻世界》,你简直就没法谈。
不过之后我个人和《科幻世界》之间的往来,就变得比较平淡,大概事物的精彩,都在于转变之中。常态化,也就是不再有什么故事。写稿、投稿、打回或者发表、写长篇、出版……这些就是我和《科幻世界》的日常。
这种平淡,直到2018年的笔会。
这一年笔会,我突然发现,到场的都是年轻人,而我成了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于是我戏言,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要争取成为不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变化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蓦然惊醒的时候,已经换了人间。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为谁停留,对我如此,对《科幻世界》,也是如此吧。
只祝愿将来春光明媚,繁花遍野,在科幻这方天地里,《科幻世界》持续不断地推出好作品,发掘新鲜血液。我相信,将来还会有很多年轻人,经由《科幻世界》而踏上科幻创作之路,正如我当初一样。
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祝《科幻世界》四十周年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