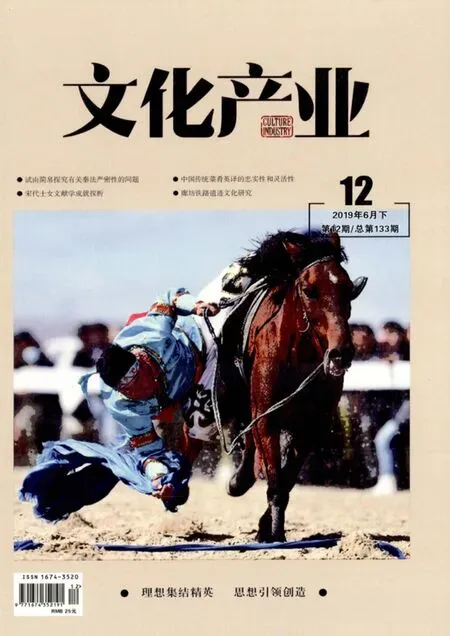试由简帛探究有关秦法严密性的问题
2019-12-27何海涛
◎何海涛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陕西 西安 710061)
一、前言
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焉)[1]。
自秦孝公五年(公元前356)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国力大增,由边陲蛮夷蜕变成四海霸主,商鞅所秉持“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2]的法家思想以及其所立的各项法律条文是秦成长崛起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秦国及后来的秦朝法律(以下统称秦法)一脉相承,秦法形成于秦称王以前,很可能是在商鞅时期制订的原文,其中所蕴含的严密性绚烂璀璨,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试由近几十年来我国各地出土的秦代简牍帛书,探究秦法的严密性及其有关问题。
根据秦汉史料记载,法律基本上可以分为律、令、制、诏四种。律就是由封建国家正式颁布的成文法;而令、制、诏都是以皇帝名义临时发布的命令或指示。在专制制度下,皇帝的令、制、诏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如果令、制、诏与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定相矛盾时,则以令、制、诏为准。从秦简中可以看到,秦朝的法律,除了律、令、制、诏之外,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以及有关规定审理案件程序的司法文书,都是秦律的组成部分,和法律具有同样的效力,这也就造就了秦法的严密性。以下将对秦法严密性的表现、作用、源由、意义等各方面问题展开进行论述。
二、秦法的作用与意义
(一)控制公共秩序
在秦统一之前,六国的浮浪人口远多于秦国。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人口数量把控严密,控制言谈游说之士,打击投机取巧之民,把社会各阶层都置于官府控制之下,想方设法驱民于农,因此其浮浪人口的生存空间远远小于六国。这些只要看看《史记·货殖列传》对各地风俗的描述就不难理解:那些挖坟掘墓、好勇斗狠、投机取巧,为了富贵不择手段等事情大都发生在六国,而秦国绝少,原因就在于社会控制的差别。出土文献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据,云梦秦简《日书》甲种云:“结日,作事不成……以寄人,寄人必夺主室”“毋以辛酉入寄者,入寄者必代居其室。己巳入寄者,不出岁亦寄焉。入客,戊辰、己巳、辛西、辛卯、己未、庚午,虚四彻不可入,客、寓人及臣妾,必代居室”“墨(晦)日,利坏垣、彻屋、出寄者,毋歌”;《日书》乙种云:“阁罗之日,利以说孟(盟)诈(诅)、弃疾、凿宇、葬,吉。而遇(寓)人,人必夺其室”“凡五五巳不可入寄者,不出三岁必代焉”“毋以戊辰、己巳入寄者,入之所寄之”“丁、癸不……巳、未、卯、亥、壬戌、庚申、己亥、壬寅,不可以入臣安及寄者,有咎主”“毋以戊辰,己巳入寄人,寄人反寄之。辛卯、卯、癸卯,入寄之,必代当家”,简文中的寄人就是寄居别人家的浮浪人口,“入寄”和“寓人”指接受浮浪人员并长期生活在自己家中。上述“寄人”“入寄”“寓人”等反映的主要是楚国的现象,也非楚地独然,《魏户律》《奔命律》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可见六国浮浪人口问题都很严重[3]。秦的社会公共秩序远胜于六国,刘邦在约法三章时也曾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可见秦法之严密,对于社会公共秩序的控制已十分奏效。
(二)建立法律诉讼程序与侦破案件规范
据《封诊式》记载:“男子某有鞫,辞曰:‘士五(伍),居某里。’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可(何),可(何)罪赦,或覆问毋(无)有,遣识者以律封守,当腾,腾皆为报”,该规定主要是为了官员能够快速摸清原告、被告的各种情况及以往案底,使官员对双方有个大概了解。“诘之有(又)尽听书其解辞,有(又)视其它毋(无)解者以复诘之”降低了错判误判的风险,有利于官员更好地了解案件详细经过;“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为官员把握询问的“度”提供了依据;“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这一规定减少了屈打成招的可能;“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治(笞)讯某”加快了查案的效率。以上这些办案方法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新上任的官员也可以迅速掌握,因而此法也多为后世所用。万荣指出,秦及汉初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判决术语“论”具有终审意义,含义包括定罪与量刑,可解释为“论处”;“当”指郡守、廷尉所作没有定审意义的判决意见,“报”特指对疑狱“议审"的批复[4]。在举告阶段,“辞”“言”的使用是对“告劾”的补充,一是申辩自己的权利,二是举报可疑的人和事[5]。由此也可以看出秦代诉讼程序规则的严密与科学。
在查封作案现场或没收财产时应当记录详细,如以“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为例,记录有“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蓋,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花板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对现场情况的记录小到门窗崭新程度,大至人畜数量年龄都应照实如数记载;之后应“幾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甲党(倘)有它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无)它当封者。’”即询问当地里典和邻居,再“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侍(待)令”,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人并规定监管时间及方法,这个查封记录对被查封财物的种类、数量、特征以及参加查封的四邻证人都有详细明确的记载,和我们现代办理案件的查封记录的各项要求基本一致。
在《封诊式》中还记载了一件案情“令史某爰书:与牢隸臣某即甲、丙妻、女诊丙。丙死(屍)縣其室东内中北廦权,南乡(嚮),以枲索大如大指,旋通繫颈,旋终在项。索上终权,再周结索,馀末袤二尺。头上去权二尺,足不傅地二寸,头北(背)傅廦,舌出齐唇吻,下遗矢弱(溺),污两却。解索,其口鼻气出渭(喟)然。索(椒)鬱,不周项二寸。它度毋(无)兵刃木索。权大一圍,袤三尺,西去堪二尺,堪上可道终索。地坚,不可智(知)人。索袤丈。衣络单襦、各一,践□”,这段文字对死者的尸体情况、束绳情况及屋内环境均做了详细记录,并且对死者上吊的行动轨迹做了第一印象猜测,为之后的查案提供思路,“即令甲、女载丙死(屍)诣廷”说明县廷中拥有专门的停尸房;在下文中秦简即对这一方法进行概论总结:在官员勘测死者时“诊必先谨审视其,当独抵死(屍)所,即视索终,终所党有通,乃视舌出不出,头足去络所及地各几可(何),遗矢弱(溺)不(也)?乃解索,视口鼻渭(喟)然不(也)?及视索鬱之状”对检查死者所采用的步骤进行阐述,极具可操作性;接下来又要进行深度检查,分类说明,“道索终所试脱头;能脱,乃□其衣,尽视其身、头发中及篡。舌不出,口鼻不渭(喟)然,索不鬱,索终急不能脱,□死難审(也)”运用这一经验即可作出判断,但如果“節(即)死久,口鼻或不能渭(喟)然者。自杀者必先有故”,这样即可判断出死者为自杀,那么就应当“问其同居,以合(答)其故。”
对于盗窃案的勘测在秦简中也有所记载:“爰书:某里士五(伍)乙告曰:‘自宵臧(藏)乙复(複)衣一乙房内中,闭其户,乙独与妻丙晦堂上。今旦起啟户取衣,人已穴房内,(彻)内中,衣不得,不智(知)穴者可(何)人、人数,毋(无)它亡(也),来告。’”这一段话说明了平民立案时应当讲清前因后果、地点时间等等有关信息;“即令令史某往诊,求其。令史某爰书:与乡□□隶臣某即乙、典丁诊乙房内”证明查案时各方官吏均要到场,为侦察提供思路;记载说“房内在其大内东,比大内,南乡(嚮)有户。内后有小堂”,对失主家中房屋情况进行记载,有助于以后随时随地进行侦察;接着对盗洞情况进行记录:“内中央有新穴,穴(彻)内中”对其位置进行记载,“穴下齐小堂,上高二尺三寸,下广二尺五寸,上如猪窦状”对其尺寸进行记录,“其所以埱者类旁凿,广□寸大半寸”对挖凿工具推测,“其穴壤在小堂上,直穴播壤,柀(破)入内中。内中及穴中外壤上有(膝)、手,(膝)、手各六所。外壤秦綦履四所,袤尺二寸。其前稠綦袤四寸,其中央稀者五寸,其(踵)稠者三寸。其履类故履”对盗贼情况进行有关记录,“内北有垣,垣高七尺,垣北即巷(也)。垣北去小堂北唇丈,垣东去内五步,其上有新小坏,坏直中外,类足之之,皆不可为广袤。小堂下及垣外地坚,不可。不智(知)人数及之所”对房屋地段进行记录,便于日后判断,又记录了房中的情况“内中有竹,在内东北,东、北去廦各四尺,高一尺”,对证人进行查问得到了如下回答:“乙曰:‘□衣中央。’讯乙、丙,皆言曰:‘乙以迺二月为此衣,五十尺,帛里,丝絮五斤(装),缪缯五尺缘及殿(纯)。不智(知)者可(何)人及蚤(早)莫(暮),毋(无)意(也)。’讯丁、乙伍人士五(伍)□,曰:‘见乙有复(複)衣,缪缘及殿(纯),新(也)。不智(知)其里□可(何)物及亡状。’以此直(值)衣贾(价)”,由此可以得到失主确实丢失衣物的事实与其丢失衣物的纹饰、材料、尺寸等情况,有助于日后追寻。
秦法还规定了“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即前期都官应抄写当地通用的法律,后期“岁雠辟律于御史”,即每年都要到御史处去核对刑律,保证了在信息并不畅通的时代,信息难以传达的边疆地区刑律的正确性。
秦代根据定性量刑的原则,对于不同情节的罪犯,会判不同的刑期。如盗一钱以上的就要判刑,盗一百钱以上到六百六十钱的要判为“隶臣”,盗六百六十钱以上到一千钱的要“黥为城旦”。除了盗钱外,盗牛的要“完城旦”;与人斗殴,把对方捆缚起来,拔掉须发眉毛的要“完城旦”;斩人发结的要“完为城旦”;用针、钵、锥刺伤了人的要“黥为城旦”;撕裂了别人耳朵的“皆当耐”,咬掉了别人鼻子、耳朵、手指、嘴唇的“皆当耐”[6]。由此可见,秦代执法时对如何定性量刑是有严格规定的,刑量大小都是以盗窃财物数量和斗殴伤人的情节轻重为依据,有着明确的标准[7]。
(三)管理国家财政和基础经济活动
秦汉时期,各项业务都有一定的工作效率标准,对其中比较重要的工作都要进行定期考核,并据考核结果奖勤罚懒惩有过[8]。《效率》有载:“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又“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赀一盾。半石不正,八两以上;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朱(铢)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黄金衡赢(累)不正,半朱(铢)厂「以」上,赀各一盾。”[9]即允许误差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脂、攻闲大車一辆(两),用膠一兩、脂二锤。攻闲其扁解,以數分膠以之。为车不劳称议脂之”即对车辆用胶量进行规定。
有关百姓狩猎采集活动也有一定的禁令“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秦本是游牧渔猎民族,从事渔猎为其根本,因而才诞生了这几条律令,同时这也是我国最早记载并明确用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森林保护条例。
秦法对生产资料也是极为重视、倍加保护的,“公器不久刻者,官啬夫赀一盾。”即官有器物不加标注,罚啬夫一盾;“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为旱〈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即优秀者赐酒肉、免更役、赐资劳,低劣者斥啬夫、罚资劳、笞三十,牛每瘦一寸即鞭笞主事者十下,极为严格;对官有的牛马也是如此,“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牛马生病要及时上报,“其入之其弗亟而令败者,令以其未败直(值)赏(偿)之。其小隶臣疾死者,告其□□之”牛马病死需要赔偿,“其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其大厩、中厩、宫厩马牛(也),以其筋、革、角及其贾(价)钱效,其人诣其官。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县诊而杂买(卖)其肉,即入其筋、革、角,及(索)入其贾(价)钱。钱少律者,令其人备之而告官,官告马牛县出之。”无病的牛马如果死亡其处理办法也有相应规定,“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一课,卒岁,十牛以上而三分一死;不盈十牛以下,及受服牛者卒岁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内史课县,大(太)仓课都官及受服者。□□。”意思是说每年由内史考核,若牛马死亡过多,主管牛的吏、饲牛的徒、令、丞均会获罪。简文“作伪,假(略)人符传及让(攘)人符传者,皆与阑人门同罪”是说:伪造符傅,掠夺他人符传以及偷盗他人符傅者,均与擅自闯入禁苑之人同罪,亦即一并处以斩刑[10]。
在对仓库的管理方面有这样的记载:“有实官县料者,各有衡石羸(纍)、斗甬(桶),期。计其官,毋(假)百姓。不用者,正之如用者”对有关的度量衡进行统一,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夹(狭)必等”,杜绝外借,保准其精准无误。又“有实官高其垣墙。它垣属焉者,独高其置刍廥及仓茅盖者”“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是县入之,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封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饩)人”对粮仓建造标准进行规定,“令人勿(近)舍。非其官人(也),毋敢舍焉。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儆)”“毋敢以火入臧(藏)府、书府中。吏已收臧(藏),官啬夫及吏夜更行官。毋火,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节(即)新为吏舍,毋依臧(藏)府、书府”两文规定了看守章程,“见之粟积,义积之,勿令败”提供了谷物出虫的解决方法,“有不从令而亡、有败、失火,官吏有重罪,大啬夫、丞任之”“籍之曰:‘其廥禾若干石,仓啬夫某、佐某、史某、禀人某。’”明确责任主体,实行连坐。
在有关官府财政支出问题上有如下简文记载:“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僕,少半斗”“不更以下到谋人,粺米一斗,酱半升,采(菜)羹,刍各半石。宦奄如不更。”“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无)爵者,及卜、史、司御、寺、府,(粝)米一斗,有采(菜)羹,盐廿二分升二”三条简文证明了秦法对各级官吏所分配的口粮也有明确规定,《内史杂》记载“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上会九月内史”,即要求地方财政部门定期报账,“城旦舂,公食當責者,石卅錢。”意思是服城旦舂劳役的人若是吃官府的饭每石收三十钱。
(四)管理和控制官僚系统
里耶简5-31有“课乡上”,《校释》注“课,考核、考课”,又简8-2198有“廷主课发”,可知“主课”为掌管考课的官员,推测“课者”可能是接受考课的人。里耶秦简中记载了一条完整的漆课规范:漆课。得钱过程四分一,赐令、丞、令史、官啬夫、吏各襦,徒人酒一斗、肉少半斗;过四分一到四分二,赐襦、绔,徒酒二斗、肉泰半斗;过四分二,赐衣,徒酒三斗、肉一斗;得钱不及程四分一以下,赀一盾,笞徒人五十;通四分一到四分二,赀一甲,笞徒百;过四分二,赀二甲,笞徒百五十。
“程”即标准,由上所见,“课”的重点在于衡量官吏超过、不及标准的程度,以之来赏、罚相关的官吏,因此必先订立标准。秦法还规定:“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官啬夫節(即)不存,令君子毋(无)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防止了权力的缺失、错位、滥用、误用。
(五)管理信息和文书
有关官方文书也有诸多准则,如秦法规定:“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即口说无凭需立字据。“令县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书者,方之以书;毋(无)方者乃用版。其县山之多者,以缠书;毋(无)者以蒲、蔺以枲萷之。各以其〈穫〉时多积之。”即对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进行规定。在里耶秦简中,有“迁陵承主”一职,这一官职就是在简牍后面所称的“迁陵守丞”,二者所指是同一人,这种“守丞”与“丞”指同一人的情况是由文书的行文格式造成的[11]。不仅如此,在许多秦简简末都有书手的名字,如毛手,静手等,有利于责任的追查[12]。由上述律令可见,秦对于邮书管理制度极其严密,在寄发、运行、签收、考核环节均有法律约束,与现代物流业管理基本无异。
(六)控制意识形态及宗教习俗
秦在占领新地区后往往要实行徙民,如《史记·秦本纪》载:“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禳。”二十七年,“(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13];甚至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对六国故地进行人口迁移,巩固了其统治地位秩序,但由于列国与秦法律制度的不同,如楚国与秦相比,郡县化、“齐民”化过程难以顺利前进[14],导致了六国在控制意识形态及宗教习俗方面与秦相距甚远,这也是秦能够一统宇内的一大助力棒。
南郡守腾发布《语书》是晓喻属下各县、道要加强法治,用法律手段“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虽然类似的秦律早就已经在南郡公布,但是由于过去的官吏没有认真执行,淫佚之风依然如故,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南郡守决定要做三件事:一是重新公布秦律,“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二是官吏要执行法律,人民要奉公守法,凡有冒犯法令的,县令、丞要检举揭发,否则便是养匠奸恶的不忠之臣;三是派人巡行视察各地,对触犯刑律的人要予以惩处,失职的官吏也要给予处分,没有及时检举罪犯的县令、丞是失职,要上报受审[15]。其目的是普及法律,并运用法律手段来改变当地原本淫僻的恶习。
根据现代考古资料表明,秦人葬式主要是屈肢葬。在关中采用一种弯曲特甚(股骨与胫骨夹角约在40°左右)的屈肢葬。从战国晚期到秦代,一些秦人或其后裔到了六国旧地,还保留着这种葬式,只是屈肢的程度较为舒缓[16]。睡虎地秦墓墓主喜作为南郡某县衙中担任执法的刀笔吏正是采用这种葬式,这对六国旧地的平民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而且秦简《日书》作为民间择日用书出土于楚国故地也是很好的例证。在秦统一前后,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可能趋于一致,民间信仰和心理认同亦渐趋一致[17],这也为秦的统一与巩固统治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北京大学藏秦简《祓除》,其首简简文记:
睪(皋)!敢=播=美=黍=(敢播美黍。敢播美黍,)葵行与=(舆舆)。敢播美稷,葵行翼=(翼翼)。上请司命、司犮(祓)。(04-124)
整理者认为其中的“舆舆”和“翼翼”,都是“称美祝祷者所奉献的谷物丰盛的样子”。但其前文已说,“‘敢播美黍、敢播美稷’,是祠祝前播撒谷物、招请神灵的仪式”[18]。据初步考证,简牍可能出土自湖北孝感或荆州地区,在楚国故地能堂而皇之地写在简牍上的祈祷仪式,必定是秦地风俗,可见秦法对六国故地思想文化控制之严密。
(七)管理和开发劳动力资源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云:“‘发伪书,弗智(知),赀二甲。’今咸阳发伪传,弗智(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今当独咸阳坐以赀,且它县当尽赀?威阳及它县发弗智(知)者当皆赀。可(何)谓;‘布吏’?诣符传于吏,是谓‘布吏’。”《封诊式 迁子》爰书又云:“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汉初有专门的《津关令》,可能也是继承秦制而来的。如《二年律令 津关令》云:“丞相上备塞都尉书,请为夹鸡河置关,诸漕上下河中者,皆发传,及令河北县为亭,与夹谿关相直。阑出入、越之,及吏(五二三)卒主者,皆比越塞阑关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日:可。(五二四)[19]”均证明了持“传”出入各地,否则当赀财产,其目的就是要更好地掌握人口流动情况,从上文浮浪人口问题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来秦国远胜于六国。
“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僕、养”,即隶臣有技艺可作工匠的,不要叫他做给人赶车、烹炊的劳役,人在其为不能屈才,法律赋予了“半自由人”以“自由人”的民事权力能力[20],体现出对其技术的重视和保护。
从云梦睡虎地秦简还可以证明刑徒是有刑期的。例如:“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为隶臣,勿刑,行其耐,有(又)般(系)城旦六岁”。葆子作案后还没有定罪,他们又去诬告别人,应当判他们为隶臣,先不施行肉刑,剃去须鬓,拘系服城旦劳役六年。又如“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鬼薪,勿刑,行其耐,有(又)般(系)城旦六岁。”这是指葆子作案后应该判为鬼薪,又去诬告别人,罪上加罪,改判为服役六年的城旦。假如认为隶臣、鬼薪统统是无期徒刑,在加重惩处时,却改为刑期六年,岂不是成了宽大处理,从轻发落吗?还有“司寇不足,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为城旦司寇。”意思是城旦已经劳作三年以上的可以减刑为城旦司寇。“人奴妾般(系)城旦春,贡(贷)衣食公,日未备而死者,出其衣食。[21]”意思是私人奴妾在押服役期间由公家供给衣食,劳作期限未满死亡,注销衣食费,不必偿还。这两条简文都是城旦有刑期的很好证据,刑徒刑期一旦结束,也能够迅速从事生产,保证其农业、手工业等产业劳动力充足。
(八)确定个人及家庭事务准则
秦法对个人及家庭事务,特别是婚姻制度做出了规定,针对“男子‘多妻’观与女子‘贞节’观”“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离婚制度”三方面制定法律规范。如对于“女子大夫亡”,或与他人“相夫妻”,依秦律规定“当黥城旦春”,即规定妻子首先必须要忠于丈夫。结合上文可以得出,妻子不但无“弃夫”的权利,而且被弃之妻还要处以“赀二甲”的财产刑,承担家庭破裂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臣强与主奸,可(何)论?比殴主。斗折脊项骨,可(何)论?比折支(肢)。”若男奴强奸主人,应当怎样处罚?应按殴打主人之罪论处。若因为斗殴断了颈项骨,应当怎样处罚?应该按折断四肢论处。因为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丈夫殴打妻子的家庭暴力层出不穷,因而秦法也对此制定了相关刑罚规定,表面上是在帮妇女并维护了妇女权益,但从本质上来讲,由被惩罚对象应受处罚来看,该处罚程度与妇女遭遇是不相对应的。但若妻子事先告发丈夫,那么妻子就免遭处罚,而且妻子陪嫁来的奴婢、财物等也不会被没收。《法律答问》有云:“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即妻子若未事先揭发丈夫那妻子不仅连坐没收为奴并处罚,她陪嫁来的奴婢、财物也应被没收;如果是妻子犯罪那妻子的财务应被没收。《法律答问》有言:“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且畀夫?畀夫。”即为若妻子有罪被收为奴,其陪嫁的奴婢、财物等应当被没收,还是给丈夫?应该给丈夫。丈夫不但不会因妻子连累自己,还会得到奴婢、财物等。
“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智(知),为收。”丈夫若盗窃一千钱,妻子藏匿三百钱,妻子受何处罚?妻子若知晓盗窃并藏钱,应该与盗三百钱同罪,若不知情,不需上交。“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可(何)以论妻?非前谋殹(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夫盗二百钱,妻所匿百一十,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以百一十为盗;弗智(知),为守臧(赃)。”即丈夫若盗三百钱并告诉妻子,夫妻共用赃款,妻子应受何刑罚?无预谋则无须上交;若是有预谋,夫妻同罪;丈夫盗二百钱,妻子藏匿一百一十钱,妻若知内情则与盗一百一十钱同罪,若不知情则为守赃。“削(宵)盗,臧(赃)直(值)百十,其妻、子智(知),与食肉,当同罪。”即一人夤夜盗窃得百十钱,若妻、子知晓,还与此人共用,则妻、子同等论处。从以上三条简文不难得出:若妻子知晓夫君或邻居、朋友进行偷窃并隐瞒分赃,那么秦法有相关刑法惩妻;如果妻子对此不知,则秦法将宽松待妻[22],表明了女子对其家庭与社会是应负责任的。
(九)垄断及重新组织社会地位体系
秦代社会中,赘婿地位低下,与公猪地位无差,秦法规定:赘婿不得为官,三代之后才许其为官,但仍需注明此人是赘婿之后,这导致部分人无法为官的现实。在《史记·陈涉世家》有言“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索隐:“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今力役凡在闾左者尽发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23]”秦代富强与贫弱两类人是分开住的,这就导致了两极分化、贫富不均且差距不断增大。而据云梦秦简载:“旞火延燔里门,当赀一盾”“越里中之与它里界者,坦为院”的记事,秦似是把“里”编制为最基层统治组织,以追求直辖统治,这些律令不同程度地导致了社会阶级体系固定化。
(十)管理军队
睡虎地秦墓墓主喜在17岁时依照秦法向政府申报了自己的年龄,当时叫作“傅籍”,意思就是喜真正成为一名可以为国效力的壮丁。秦实行征兵制,喜分别在始皇三年、四年和十三年从军打仗,可见从17岁至60岁,只要国家需要,所有适龄男子都必须要随时准备奔赴战场。军粮由国家发放,每人每月在40斤左右,但冬夏衣物是要自备的,在睡虎地4号墓出土了两封家书,黑夫与惊在写给大哥衷的信中都向家中要了钱财和衣物:“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钱衣,愿母幸遣钱五、六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
即使是在重大对外战争之时,秦对于士兵的征发仍然是较为合理的,秦对兵徭之役的慎重表现在:一般情况下尽量征发非农业人口以免影响农时[24]。南郡郡守腾重新颁布的法律条文是有其侧重的,例如突出了勘验财物账目的经济法律《效律》,并规定度量衡一定要保证精确。军队所用的皮革、武器、铠衣一定要妥善管理。又有《秦律杂抄》所引的与军事有关的十一种秦律: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勤供应及战后奖惩等,由以上得见这次的秦律是为适应对外统一战争的需要[25]。
三、秦法严密性下的优缺点
(一)秦法严密性下的人性化
秦法虽然严密,但也有其人性化的一面。如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劳役时“居赀赎责(债)欲代者,耆弱相当,许之。”即同意他人替代此人劳动偿还。“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责(债)而莫见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即若一家中两人均在劳役,允许两人轮流倒班劳动。“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即以劳役抵债赀赎债务的人在播种和管理禾苗的时节可以回家农作二十天。“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即允许百姓用奴隶或牲畜抵押代替劳役。“居赀赎责(债)者,或欲籍(藉)人与并居之,许之,毋除(徭)戍。其日未备而柀入钱者,许之。”即允许此人借助他人同服徭役。“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或赎(迁),欲入钱者,日八钱。”即百姓可以通过戍边五年来替家中隶妾赎免。
在“工人程”方面,“新工初工事,一岁半红(功),其后岁赋红(功)与故等。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能先期成学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书而上内史。”表明对新工的奖励,“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即在冬季劳作放宽标准,三天收取夏季两天的产品。在对待针织刺绣行业“隶妾及女子用箴(针)为缗它物,女子一人当男子一人”,男子女子一视同仁。
除此之外,邬文玲据秦简资料指出,赦免措施在统一之前的秦国是一种常态化的做法,具有相应的制度,涉及的对象广泛,秦王政时期也多次颁布过赦令[26]。
(二)秦法严密性下的遗漏缺失
秦法虽然严密,但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依然屡禁不止,上文中提到秦法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这样的规定,其目的就是阻止战国以来十分普遍的自由农民逃亡问题,即使是后来进行了编户齐民,但统治阶级对农民逃亡现象依然无能为力,走私行为屡禁不止。盗窃在秦国也很普遍,彼时夫盗妻藏、夫妻盗钱共用和全家共盗现象经常发生。据史料载:秦代官员也不是铁面无私的法家理想人物,经常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律令于不顾。当时官员、平民、罪犯及奴隶中那些对律令有所了解的人,都利用自己的相关知识在法律流程中为自己谋福利,利用政府颁布的法令与国家机器本身进行对抗[27]。以上导致了法律权威与效能的不断弱化,这对秦的统治可以说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毁灭性打击。
四、秦法与其他律法的比较
(一)与列国法律的比较
秦法所具有的严密性并非商鞅首创,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法律的共同特点。
如楚法:文王所制定的《仆区之法》中有“盗所隐器,与盗同罪。”这与后来的秦法连坐制如出一辙。康王时,蔡国大夫声子来楚和楚国令尹子木会面,谈及楚晋政务及人才优劣,声子言说:“楚多淫刑,故诸大夫获罪惧诛常逃死于四方,成为别国谋主,转而侵害楚国。”这也是楚国最大弊陋之一。后世史家言及楚国政务时都指明楚法律苛严,不但臣民动辄就会触禁受罚,甚至令尹等重臣也是如此,《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论》有“少自愤事,旋即诛死”之语。平王时,楚国令尹子常杀奸臣费无极与鄢将师后被“尽灭其族”,还有平王杀斗成然且“灭其族”的记载。肢解之刑,是极刑之尤极者,悼王去世后,有文献说吴起是遭车裂而死。肢解又称磔刑,《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产金,凡私采者,“得而辄辜磔于市”。楚国当时已拥有极为完整的司法诉讼程序:司法部门受理案件后,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审理案件。在此期限内司法部门官员必须要将所接收的案件进行审理,否则视为渎职,而且原告方在期限内拥有督促官员审理案件之权;官员若审理不当或判决有误,被告方亦可在此期限内提请申诉。包山楚简中的“受期”一简,即为执法官员因渎职而受控告的记录。审理案件时官员必须要“听狱”,就是听取争讼双方的申述,包山楚简131、136简有载:“执事人诅阴人宣相。苛冒、舒逊、舒腥、舒庆之狱于阴之正,思听之。”接着记载了舒氏父于和宣、苛二人两方言辞,以此作为听狱的实证;官员还需要听取提供证据的非当事证人的证词。按楚法云:“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包山楚137号简记“执事人为之盟证、凡二百人十一人。”得见证人之多;结案时需按律定罪,就是依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案件作出合理的判决,称之为“断狱”。《周礼·地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包山楚简131-139简中的舒庆杀人案因为迟迟未断而惊动楚王,遂左尹以王命告汤公命“为之断”[28]。结合上文对秦法与楚法诉讼程序的叙述,可以看出二者在查问步骤、证人数量等方面是有许多相同点的,并且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秦法,秦法也正是因此而不断发展,愈加严密科学。
再如齐法,《管子·揆度》就主张“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29]。秦代统治阶级接受这一主张,并且形成法律,如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土以下刑为城且”[30]。
又如赵法:“重刑轻罪”就是轻罪重罚,此原则早在春秋时期赵简子开拓疆土发展赵氏基业时就被统治阶层高度重视。据《韩非子·内储说左上》记载:贤臣董阏于前往赵氏新领地任郡守时,行石邑山中,见涧深峭如墙,因问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痴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人涧之必死也,人则莫之犯也,何为不治哉!”其重刑主义得到了赵简子认可并身体力行,据《说苑·君道篇》记载:赵简子与栾激游,将沈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来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晋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因此宠臣栾激便身负“进吾过而黜吾善”之罪而沉河。对于溜须拍马之小人,赵简子并非简单地疏远罢黜,而采用极其残酷的法律消灭他,小人在侧必闭塞上听,使贤人望而却步的道理浅显易懂,正在谋发展求人才的赵简子当然难以容忍这种小人在侧,重刑加身定是大势使然[31]。可是后来赵武灵王因舐犊之情而捐弃国法,上行下效,之后大臣徇私枉法也一发不可收拾。《史记·吕不韦列传》载有:赵王欲杀秦质子子楚,子楚与吕不韦商议后遂以黄金六百斤贿赂守卫,才得逃奔秦国,子楚之妻赵姬及其子嬴政也被藏匿,得脱此难。战国末期赵国法律之松懈及人民对法律的蔑视程度已到了令后人惊讶的程度。
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并“改法为律”[32]。但之后“商君虽死,秦法未败”,在商鞅死后除秦国秦惠文王仍坚持商君之法外,其他各国均选择放弃变法,这也直接导致了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强弱变化。
(二)与西汉法律的比较
西汉统治者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对法律进行了简化宽松的改革。在“严”这方面,西汉时期“…有法,父母妻子与其身同罪。”说明丈夫犯法,父母妻子连坐,而据《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在这里指一家有罪,什伍皆相连坐罪[33]。《汉书·刑法志》载“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时期废除肉刑、载宣帝诏“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34],将部分酷刑与连坐制废除。从“密”上来看,刘邦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35]这实际上是对秦法的高度简化,给予百姓以更大的自由性。
但西汉统治者还是吸取了秦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通过和出土的秦律相比较,发现西汉并不是有选择地继承秦朝的法律体系,而是在原样照搬的基础上做了微小改动。汉律替换了一些秦律中的法律术语,如用“奴婢”替换“臣妾”,用“罚”替“赀”。西汉中央政府为了满足特定政治需要,对相关秦律进行了调整:如秦二十等爵中最高的“列侯”,在汉代可以拥有自己的侯国封地,并且被要求在自己的封地生活。秦代只有“列侯”可以世袭,到了汉朝较低级别的爵位也可以被继承[36]。但上文说到的秦国存在私自解释法律的问题,直至西汉时期依然没有得到根除,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第18个案例中就记载了一件直接谋反案例。
五、结语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37],秦法开法治时代之先河,结束礼治时代,使古代中国从“一准乎礼”步入“一准乎法”。
秦法起到了监督农业生产、牛马饲养、铁器管理的作用,将先进生产经验技术,如土地播种量、田猎活动方法等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还保证国家各项赋税收入,管理粮仓府库,规定并指导官营手工业运转,管控货币流通,管理市场交易,循役征发戍卒,兴建重大工程,进行刑徒监管,任免官吏职务和军功爵位赏赐,保障了社会稳定和平。而根据以往判案成例来审理案件,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表明封建秩序者绝不会让法律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当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或者虽有明文规定但不能满足某种需要时,执法者就可以不依法律而以判例办案,这有利于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所以法律解释和依判例办案,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法律形式。
秦法所蕴含的严密性是基于对外统一战争下的,当秦统一六国后,以战时状态治理国家,不合时宜,而且秦法主要还是为了保障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控制剥削。
“事皆决于法”的依法治国理念,“学法令”“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普法教育要求,“刑礼并用,以刑为主”的法治、德治并用原则,“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平等公平意识以及《关市律》等民法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均为当今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借鉴意义。“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如何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如何使我国法律不会形同具文,靠的就是法治,“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历史性一跃的关键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最后倒计时,“第一个百年”目标胜利在望,“第二个百年”目标日渐接近,这就需要法治护航指引,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