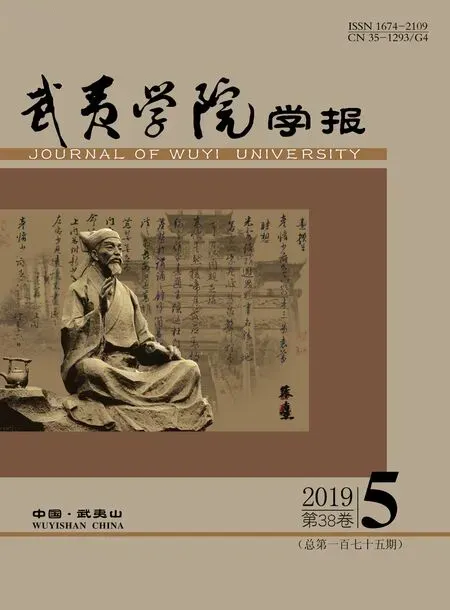朱子哲学体系中的道家、道教思想渊源
2019-12-27肖溱
肖 溱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汇集前代发展成就乃至别出一体,是儒学集大成者,也是秦汉之后少数能够被官方称为圣人之人。他的理学体系,不仅在宋朝备受关注,对后朝的影响也十分深远,甚至一度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不仅如此,朱熹的哲学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重要影响,比如朝鲜和日本就曾先后引入朱熹的哲学体系,甚至两国一度把其确立为统治思想。同样,东南亚地区也深受朱熹哲学体系的影响。到了近代,朱熹哲学体系还传入欧美,引发欧洲学者的广泛关注。从这一角度来看,朱熹哲学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哲学领域的重要财富,更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学说对其他很多国家贡献了文化力量。而当代对朱熹理学的研究,又多注意道家、道教思想对其的影响。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黄老学说开始不断丰富发展,在历朝历代都极受推崇。事实上,朱熹虽然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理学也是儒家学说在宋代的传承与发展。但就朱熹的哲学体系而言,它的形成吸纳了很多道家、道教的理论主张,因此理学又称道学,是研究儒家经典义理的学说。
一、儒道结合下的大背景
(一)儒与道在时代洪流中的亲密关系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教思想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三者鼎足而立,既互相论战,又互相渗透,互相学习,从而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流。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以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为理论发端,并结合战国以来朝野盛行的神仙方术而形成。从道教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地位来看,这一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即使是现在也在积极的发展中。老子作为道家的创始人,著有著名的《道德经》,其身世后世多有神化。从现实角度讲,其哲学主张以“道”为核心,“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于是,“道”成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道家的哲学体系;庄子作为其继任者,又进一步发展了道家哲学体系,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道家思想流传到汉代末期,为张陵等方士吸收,创立了五斗米教,是为道教之发端。
另一方面,佛教自传入我国之后发展出了和印度原生佛教不太一样的形态,尤其是在禅宗诞生之后,这种本土化的佛教形式迅速在士大夫阶层逐渐流行起来,在唐代时就已经处于非常兴盛的状态,宗派众多。至宋时南北宗禅确立,其体系之完整与学说之发达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就使得很多唐宋时期的名家作品都具备着一定的“禅意”。
由于释、道两家学说在文化领域的盛行,着眼于世俗统治的儒家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要对这两类学说提起重视,甚至可以将两者的理论化为己用,以进一步发展儒家学说。由此,“三教合一”的口号被儒生们提了出来,如唐代学者杜光庭就曾说道:“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名,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也不以至道为尊,也不以众教为异,也不以儒宗为别。”[1]
但以朱熹所在的宋朝来说,对释、道两家的吸收是不平衡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政局。自中唐之后,政治局势日益动荡不安,中原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借古文运动恢复儒家道统的努力被打断,一直到宋建立初期,儒家依旧相对式微,而释、道则相对兴盛,这就使得这两家学说成为欲振兴儒学的大学者们重点吸收的对象。但纵观宋之一朝,无论对辽对金,对外战争屡屡失利,俯首纳贡成为寻常之事,南宋甚至只能偏安一隅、苟延残喘,这使得当时朝野上下的爱国热忱与民族情绪大为高涨,致使学者们对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学说比较排斥,而对同为本土文化的道家、道教学说则青睐有加。朱熹就曾说,“老氏见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2],“老庄于义理灭绝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2]等褒扬道门而贬低佛门之语。由此可见,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在对这二者的吸收过程中,往往更加重视道家、道教学说。
(二)儒道奉行的共同经典——《周易》
许地山曾说:“道家思想底渊源也与儒家一样同出于《易》。”[3]《周易》并不能单纯地说是属于儒家或是道教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二者思想都有。汉代初立,国力衰微,文景二帝奉行黄老之学,甚至将道家思想奉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并依“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实行休养生息的国家政策,在两任皇帝在位期间重新积累了国家财富,这才为汉武帝时期的崛起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周易》也被儒家纳入奉行经典之一,后来独尊儒术之后也没有改变。那一时期的儒生也热衷于为周易做释义,也就诞生了《象传》等经典文本。另一方面,道教的雏形在汉代末期出现,《周易》由于具备卜筮功能而广泛地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也被道教自然而然地奉为经典,成为道教重要的思想来源与宗教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是“两教一典”,但儒家与道教对《周易》的认知与运用是不尽相同的:儒家更侧重于符合儒家思想模式的诸多义理;道教则更加重视象数命理。
但即使有这些差异,儒家与道教奉行共同的经典依然为两者之间创造了更多的思想相通之处,这也就为北宋儒道结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朱熹作为宋代大儒,其思想多受道教影响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道教对朱熹哲学体系构建的影响
道教思想对朱熹哲学体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对道教思想的接纳既有受大环境的被动影响也有个人的主动接纳,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朱熹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整理与评价;朱熹对道家、道教思想的吸收与运用。
(一)朱熹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整理与评价
1.独特的道教史观
朱熹对道家、道教的历史发展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与现代学者通常将道家作为学派、道教作为宗教去区别看待不同,他并没有把道家与道教完全区别开来分别论述发展历程,而是把道家作为道教的发端。但这并不代表朱熹不明白二者之间的差异。
朱熹的学生曾对此感到迷惑:“道家之说,云出于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莫是张角术?”[2]朱熹答道:“是张陵……米贼是也。”[2]可见朱熹对道家和道教之间的差别和源流有着清楚的认识,明白后世道教其实源于张陵的五斗米道,而并非是老子学说的直系产物。但朱熹又为何在道教史观上把二者融为一炉呢?
对此朱熹是这样解释:“老氏初只是清静无为。清静无为,却带得长生不死。后来却只说得长生不死一项。如今恰成个巫祝,专只理会厌禳祈祷。这自经两节变了。”[2]可见朱熹认为从先秦的学问流派道家到宋代的宗教道教也并非是一脉相承,而是经历了两次“节变”的。第一个“节变”是从老子的清静无为理论到专讲长生,消减了文化、理念,倒是多了神秘色彩。而从专讲长生不死到厌禳祈祷又是第二个“节变”,哲理文化没有了,全变成了宗教仪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朱熹是完全把老子哲学作为道教的源头之一的。
但这也并不是道教的唯一源头,道教的两次“节变”实际上都有道家思想以外的因素参与。一方面是方士,比如前面提到的创建了五斗米道的张陵,其作为寻仙问道、开鼎炼药这些传统迷信活动的行动者,在道教第一次“节变”中将道家思想神秘主义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佛教,佛教实际上在道教的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很多道教人士在佛教中借鉴了很多宗教仪式、偶像体系、名词符咒等,简单地说就是佛教完整、严密的宗教体系教导了道教作为一个宗教要如何去蛊惑人心并进一步神秘化。朱熹在一段批评宋代道士的文本中就曾提到:“今极卑陋是道士……禅家已是九分乱道了。”[2]“佛经本是远方外国来,故语言差异,有很多差异字,人却理会不得;他便撰许多符咒,千般万样教人理会不得……”[2]虽是批评、抨击之语,但佛教对道教发展的影响可见一斑。
2.对老庄的评价
对于老子和庄子这两个在道家、道教极为重要的人物方面,朱熹首先认为应当老庄分立。当时世人往往将老庄合在一起论述,普遍认为老子与庄子思想上一脉相承、不分彼此。朱熹虽然也经常老庄连用认为二者虽然都是道家,但还是认为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在朱熹看来道教历史从老子到庄子开始进入了一种狂放无状的路子,老子旁观后犹有忽然跳出来的发用,到庄子则只剩下冷眼旁观了,甚至于连旁观也懒得去了。”[4]
在对二者的评价上,朱熹整体上持赞赏态度。对于老子,他说:“今观老子,自有许多话说,人如何不爱?”[2]从一名儒家学者的角度上,朱熹对老子思想中相关于社会现实并且与儒家内核相吻合的部分比较重视,比如他在反对兵刑方面曾这样论述:“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者,莫过于兵刑,临阵时胡乱,错杀了几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详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2]可见朱熹对老子思想的赞同、吸收主要集中在儒家可用的部分。另一方面,朱熹认为老子虽然提倡“清静无为”但却并不是真的“无为”,而是以无为求有为。“他所有的隐忍、柔弱、谦恭,其目的就是把自己置于静的境界,其心最安,如此才能识破万事,做到‘因而为’,立足于不败之地。”[5]
对庄子,朱熹对他的评价更在老子之上,这在他常称庄老而非老庄上就可以体现,他还曾说:“老子极老攘,庄子较平易。”[2]他对庄子的评价甚至超越了儒道之间道统的藩篱,认为“庄子不知他何传授,却自见道体,盖孟子之后,荀卿诸公皆不能及……”[2]可见庄子在朱熹心中之地位。同时朱熹对庄子的才华也赞赏,认为庄子把道家思想带到了一种狂放无状的路上,而这不仅影响了道家与道教的发展方向,甚至成为了佛教的本土产物——禅宗的真正思想内核。
3.对道家、道教典籍的评价
朱熹早年多学释道二家学问,对双方典籍多有涉猎,但在24岁与李侗相遇后,他逐渐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在31岁重遇李侗之后彻底确立了以儒家为思想发展的主要方向,并对道家、道教思想多有批判。但即使如此,在他晚年之时依然对道家、道教的两部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就是《阴符经》与《周易参同契》,足见这两部典籍在朱熹看来有着特殊的价值。
朱熹对《阴符经》评价颇高,他认为此书“然非深于道者,不能作也”[6]。因此他曾对《阴符经》做了深入的考据探究,并拟写了大量释义文献,以帮助儒生对其进行运用,如《阴符经考异》等。总的来说,朱熹对其中的哲理方面特别赞赏,这一部分的内容也对朱熹哲学体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易参同契》这本书对朱熹来说就更是特殊,甚至有人认为朱熹因此书差点去当了道士。此说虽是夸张,但它从侧面表现了朱熹的重视。朱熹对《周易参同契》的研究可以说更加的深入而久远。他接触此书的时间其实远在晚年之前,对它的研究也开始得很早,只是当他晚年年老体衰之后研究的热情更加高涨,其原因在于《周易参同契》讲解的是道教徒修炼的方法。朱熹修身养性的功夫多源于道家、道教,对这样一本书自然更是重视。
(二)朱熹哲学体系对道家、道教思想的吸收与运用
1.朱熹天理思想对道家、道教理论的吸收与化用
朱熹的哲学体系核心与标志是“理”或者说“天理”,在他看来“理”是宇宙的本体,既是“自上推而下来”的理——气物的出发点,又是“自下推而上去”的物—— — 气—— — 理的归宿。[4]二程已提出“天理”,这是朱子“天理”的直接源头。但朱熹这一思想应该是受到了道家、道教理论的不少启发,尤其是《阴符经》。
《阴符经》开篇即讲:“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心,万化生乎身。天性,人心;人心,机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6]可见其提倡将道家、道教所认为的宇宙核心——天道客观化、外在化,使其成为人可以探究并遵循的法则,掌握这个法则并依照修炼便可以成为圣人。朱熹对这一理论推崇备至,认为其“虽六经之言无以加”。极大地启发了朱熹建立儒家自己的天地法则、世间至理——天理,并将这一理念客观化、外在化,以天理为核心去反映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将天理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同时他也并没有否认道的概念,而是将道与理相联系并对道进行了儒家角度的解释。他说:“道即理之谓”“若论道之常存……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由此可见,他认为对理与道之间基本上是等同关系。道已经成为百家共有的哲学理论基础。
同时,朱熹在吸收道家理论后进一步对道的属性做了阐释。首先,他认为“盖道无不包”[2]“夫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粟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厘差者”[7]既是说道便是代表着宇宙万物的全体。其次,他认为道虽代表宇宙万物全体,但又和宇宙万物不同,再深究便是万物运行的法则规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本无体……那无声无臭便是道。”[2]形而上的理论法则便是道,形而下的万物形态便是器。
由上可见,朱熹哲学体系的理论核心——理的确立,实际上是大量吸收道家、道教思想之后的结果,这些思想极大丰富、完善了朱熹理学的思想架构,提升了儒学的思想层次,基本改变了当时儒生多注重寻章摘句却在思想上无所建树的现状。
2.朱熹心性论对道家、道教理论的吸收与运用
北宋初年的道士张伯端提出“欲神者,气禀之性也,元神乃先天之性也。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8]。这是二程、张载等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直接理论来源。朱熹继承了这个理论。但同时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道家、道教理论对朱熹的心性论方面也影响颇深。
《阴符经》有云:“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9]这就给北宋五子至朱熹所一直讨论的根本问题——心与道、理的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
朱熹认为,人性分为两个层面。一层是天命之性,在他看来,天命之性天生符合道、理,符合天地万物的本心,也是人性的根本所在。或者说就是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论”之“善”。而另一层是气质之性,那便是人之欲望,是小人私情,违背了道与理。这时候人欲作为人性当中的“恶”被重点提出来,成为天道、天理的反面。以此来解决道德原则和封建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因此,朱熹提出:“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则智故去而理得矣。”[6]可见其受道家、道教理论影响之深。
朱熹在构建心与道、理的关系时,最终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主张。由于对“天理”的释义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也就为朱熹哲学理论成为宋明清三朝显学打下重要基础。
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具体方法上,朱熹与前代儒学大家略有不同。由于儒家的入世特性,前人多靠道德践行来实现对道的追求,而朱熹却主张通过心性休养来实现这一目标。可见在程门传授与佛教影响之外,朱子的修养工夫还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朱熹提出如果要保证人性中至善的天命之性不受损害,就必须学习如何静心理意,通过以静制动来抑制人性中至恶的人欲,这样才能达到“存天理”的目的。而道家自老子初创时就提倡以静修身,“至虚极 ,守静笃”,要人以无欲无求的心态去对待万事万物,才能真正把握人生至理,朱熹很明显借鉴了老子的这番“守静”理论。朱熹甚至还作过一篇《调息箴》,教人如何打坐调息,这甚至已经近乎道士所为了。
三 、结语
朱熹的思想当中的理气论、人性理论、功夫理论浸润着道教及道家思想的影响,但其思想内容和与前者有显著的差异,揭示这种影响,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与宗教的联系,有利于对朱熹的思想作出一些新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