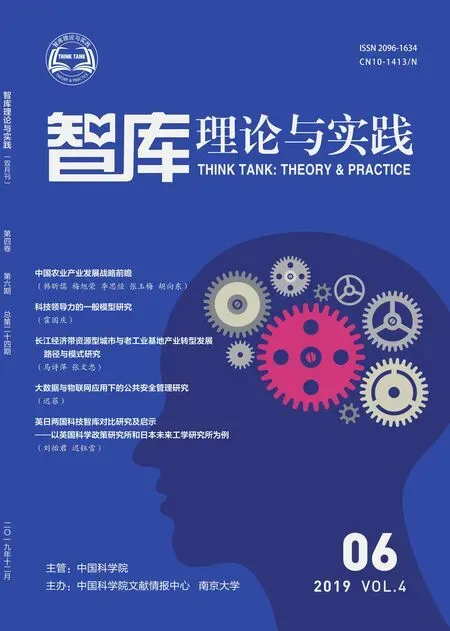功能疏解背景下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2019-12-26李佳洺
■ 李佳洺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101
2015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和2017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都将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北京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功能对人流、物流等有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大城市病”的重要成因,因此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产业功能的疏解将引起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尽管已有的相关理论明确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发展的重点将由制造业逐步转向服务业,但是并没有就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给出一个明确的量化关系。而产业结构作为政府进行宏观决策的重要指标,对未来产业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北京产业结构特征的剖析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将为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北京产业结构特征与面临的调整压力
1.1 北京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与特征
北京先后经历了消费型城市、生产型城市和服务型城市转变的过程,第三产业比重也随之呈现先降低再上升的变化趋势。建国初期,北京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城市经济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到1952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仍略低于第三产业[1]。1953年,北京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指出,北京不仅是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还是工业中心。到改革开放前,北京仍在积极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1978年,北京第二产业比重达到70.96%,是服务业的3倍以上。改革开放后,政府对北京的职能有了新的认识,并反思了工业优先的发展思路。1982年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将北京定位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并要求严格限制工业发展[2]。此后的1992年城市总体规划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使得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年间,服务业占比以平均每年近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3-4]。进入21世纪,服务业比重依然持续提高,2017年北京市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2,569.3亿元,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为80.6%(图1)。事实上,自1994年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后,服务业就开始主导北京的经济发展。

图1 北京产业结构变化趋势Figure 1 Changes in Beijing’s industrial structure
1.2 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外部压力
1.2.1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建设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为了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解决地区长期以来面临的产业体系难以衔接、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然要求北京对城市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做出调整,以适应地区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此外,雄安新区的建设也会对北京产业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雄安新区作为未来与广东深圳和上海浦东比肩的先行示范区,将成为北京一些高端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主要承载区,从而促进北京大量高端经济和产业功能外迁。除大型央企和国有企业纷纷宣布将总部迁移至雄安新区外,北京也大力促进中关村科技园等在雄安新区落地,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
1.2.2 “四个中心”的城市定位与非首都功能疏解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提出,北京要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并强调要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因此,自2014年起,北京就开始对区域性批发市场、一般性制造企业等进行疏解。到2015年底,北京疏解了220个区域性批发市场,79家工业企业。
同时,2017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进一步强调了北京“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并明确“坚决退出一般性产业,严禁再发展高端制造业的生产加工环节”。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必将促使北京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
1.3 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
1.3.1 城市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2012年北京人均GDP就超过了1.2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26万美元以上就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北京自2012年起就逐步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2017年,北京人均GDP超过2.05万美元,尽管距英国、德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人均GDP 3万~4万美元左右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毫无疑问北京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城市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前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吸引和集聚了大量的人才、资金等优质发展要素,人们更多注重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忽略了生活质量。当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后,城市居民也开始关注生活品质,城市社会、经济、产业等方面都面临转型。
1.3.2 北京“大城市病”十分突出 近年来,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北京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如2013年北京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为176 d,即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数不足全年的一半,但重污染累计达到58 d,即平均每周都会出现一天重污染的情况。交通拥堵也是北京发展的主要瓶颈,来自高德的数据显示,北京在2014和2015年连续两年成为全国最为拥堵的城市,2016和2017年也分别位于第3和第2位。尽管北京高峰拥堵延迟指数已经从2015年的2.06下降到2017年的2.03,但是相对于上海、广州等同为人口众多的一线城市来说,北京拥堵程度依然很高。除此之外,不断高企的房价、拥挤的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等都迫使北京需要对产业经济等进行疏解和调整[5]。
2 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困境
从北京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来看,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来看,随着制造业的外迁和疏解,未来服务业在北京城市经济中的比重很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但是与国内同级别城市相比,北京服务业比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北京服务业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超过广州后,就一直显著高于上海和广州。2008年北京服务业比重比上海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比广州也高出17个百分点。此后差距虽然收窄,但到2017年为止,北京服务业比重依然比上海和广州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图2)。然而,在北京市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GDP和人均GDP等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并没有明显高于上海和广州。同时,就北京自身而言,服务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低于制造业,因此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北京进一步大幅提高服务业比重的理由并不充分。

图2 北京、上海、广州第三产业比重变化趋势Figure 2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Beijing,Shanghai,and Guangzhou
总体上,北京产业结构调整似乎出现了两难的困境。从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和城市发展内外部环境来看,北京服务业比重仍将进一步提高,但是从横向比较以及自身发展特点来看,服务业比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提升的理由并不充分。而尽管“配第-克拉克”定律等经典理论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业人员不断向第三产业转移,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提升,但是这些理论和已有的实证研究都没有给出一个量化的对应关系。因此,未来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比重,直至成为城市唯一的经济活动,还是保持一定的制造业比例,将服务业维持着一个合理的区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此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要有利于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要考虑对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影响。即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否有利于京津冀地区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缓解北京的虹吸效应,扭转核心城市周边长期存在“集聚阴影”(agglomeration shadow)的局面,实现区域更加均衡的发展[6]。因此,对北京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剖析将不仅有助于北京产业功能的疏解和自身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且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
3 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总结和理论剖析
3.1 产业结构变化规律总结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有很强的相关性。由于人均GDP是经济发展水平很好的表征变量,因此选取人均GDP和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对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借鉴意义。
3.1.1 就国家尺度而言,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服务业比重大致维持在75%的水平 采用局部多项式回归(Loess函数)等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对“人均GDP”与“制造业比重”及“服务业比重”的相关关系进行拟合分析。从各国人均GDP与产业结构的对应关系来看,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制造业比重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而服务业比重则是不断增加。而且当人均GDP达到6万美元后,制造业比重会快速下降到接近于0,而服务业比重则接近100%(图3(a)所示)。
但是出现制造业趋近于0这一极端状况主要是由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澳门等规模很小的国家和地区造成的,从图3(a)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后趋势出现明显差异的拐点。去除这些规模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后,发现:当制造业比重降至25%左右后基本趋于稳定,而服务业比重上升至75%左右将趋于稳定,并不会随人均GDP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图3(b)所示)。

图3 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主要国家/地区产业结构与人均GDP关系Figur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DP per capita in major countries/ regions with GDP per capita exceeding USD 20,000
3.1.2 就省(州)尺度而言,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服务业比重大致维持在80%左右 用Loess局部加权回归的方法,对美国各州的“制造业比重”或“服务业比重”与“人均GDP”的相互关系进行拟合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的走高,制造业比重将无限趋向于0,服务业比重则趋于100%。但是这一状况同样是由于华盛顿特区规模较小①华盛顿特区2012年人口仅64.6万,位列各州中的第49位,面积也仅177 km2造成的。
去除华盛顿特区这一特例,重新进行回归拟合得到图4。由图可见,在美国各州,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制造业比重将不断下降,在下降至18%左右后,不同参数的拟合曲线走势出现一定分化,但总体来看,制造业比重将基本稳定在18%左右,不会随人均GDP增加而无限降低(图4(a))。对于服务业而言,随着人均GDP的上升,服务业的比重将不断上升,上升至80%左右时,不同参数的拟合曲线走势再次出现明显分化,当模型参数span值越小,即更多考虑高人均GDP的局部变化规律而非整体变化规律时,拟合曲线的走向趋向于稳定在80%左右。因此,随着人均GDP增加,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至80%左右时,各州基本趋势保持一致,当超过这一数值后,各州的发展趋势就出现明显的分化,总体上服务业比重更趋于保持在80%左右的水平上(图4(b))。

图4 美国各州产业结构与人均GDP的关系(除华盛顿特区)Figur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DP per capita in U.S.states (excluding Washington D.C.)
3.1.3 对于城市而言,不同职能类型城市产业结构有较大差异日本是全球重要的发达经济体之一,其首都东京不仅是其政治中心,而且是东京湾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按美金当年价格计算,东京都的人均GDP在1986年突破了2万美元。随着人均GDP的上涨,制造业比重不断降低,在下降到15%左右后,下降速度明显放缓,制造业比重趋于保持稳定(图5(a));服务业比重随人均GDP上涨而不断提高,上涨到85%左右时,上涨速度明显放缓,服务业比重开始趋于稳定(图5(b))。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均GDP从5万美金提高到7万美金时,东京都的制造业比重才由30%左右快速下降到15%左右,而相应的服务业比重则快速上升到85%左右。而在人均GDP达到5元美元之前,制造业比重是较为平稳地缓慢地由40%左右下降到30%,而服务业比重上升也较为平缓。

图5 日本东京都产业结构与人均GDP的关系Figure 5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DP per capita in Tokyo
与日本东京都不同,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服务业比重都在90%以上,尤其是美国华盛顿特区,服务业比重更是接近98%。华盛顿特区2016年人均GDP高达9.76万美元,位列全美第1。其作为美国的政治中心,是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各国大使馆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产业结构较为特殊,服务业比重高达98%(如图6)。尽管从这3个城市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服务业几乎成为城市唯一的经济活动,但是这类城市职能较为特殊,并非传统意义上职能较为综合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图6 华盛顿特区“服务业比重-人均GDP”Loess回归Figure 6 Loess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share of service and GDP per capita in Washington D.C.
3.1.4 区域尺度越大服务业比重越低,城市职能越综合服务业比重也越低 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各州以及东京都等城市发展过程来看,尽管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制造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将快速下降,而服务业则快速增加,但是在人均GDP达到一定数值后产业结构就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然,这一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随着空间单元等级的降低而有所变化。
通常来说,空间单元等级越高,制造业稳定状态的比重也越大,而稳定状态对应的人均GDP也越低。稳定状态下,随着从国家级、州(省)级到城市级空间单元不断缩小,制造业比重逐步降低。而就城市级空间单元而言,具有特殊职能的城市的制造业比重要明显低于综合性的区域中心城市,见表1。

表1 不同空间尺度下人均GDP与产业结构特征比较Table 1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per capita GDP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3.2 不同类型城市产业结构差异的理论剖析
综合职能城市与特殊职能城市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不同类型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综合职能城市一般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对于周边城市有很明显的带动作用,如东京作为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东京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其发展带动周边的埼玉、千叶、神奈川,形成东京首都圈,并与川崎、横滨等一起将东京湾发展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经济区;而特殊职能城市通常偏重于某一特定职能,通常区域经济并不是围绕此类城市展开,如香港作为亚太甚至全球的贸易中心,虽然与珠三角地区有很强的经济联系,但是珠三角地区依然是围绕着广州和深圳发展,华盛顿和澳门分别以政治文化和博彩业为主要职能,更与周边区域经济产业有明显差异。换句话说,仍保持一定比例制造业的综合型城市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有较好地带动作用,而服务业比重趋近于100%的特殊职能城市与周边区域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
这样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是由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空间中的集聚与扩散特征造成的。服务业在空间中呈现点状集聚的特征,产业发展以等级扩散为主,即核心城市服务业更倾向于向下一个等级的城市扩散,而不是核心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而制造业在空间中则呈现面状集聚的特征,产业以接触扩散为主,即核心城市制造业更倾向于向距离较近的周边城市转移和扩散。这与两类产业产品的传输和运输成本有关。服务业生产的产品以知识和信息为主,除在较小空间范围内进行面对面交流外,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传输标准化的知识产品,对于周边城市还是较远的城市成本几乎一样,同时由于服务业产品需要较大的市场空间,因此产业更倾向于向距离核心城市较远,但市场规模较大的较高等级城市扩散,而非距离较近但规模较小的城市;而制造业产品是实体货物,运输成本与空间距离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制造业的转移扩散和产业配套更倾向于在距离核心城市较近的中小城市,同时中小城市也有充足且廉价的土地,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保持一定比例制造业的核心城市更可能通过产业链的联系,与周边区域的生产网络进行对接,从而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而以服务业为单一经济活动的核心城市更倾向于与距离较远但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联系互动,由于与周边城市缺乏较强的产业联系,所以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较为有限。
事实上,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服务业的发展对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呈现负向影响[7-8]。而且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明显下降,如Loannides和Overman对美国城市发展的研究表明,距离大城市较近而拥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城市发展并没有显著快于距离较远的城市[9];Partridge的研究也表明,美国大城市对于小于25万人的城市有一定带动作用,而对中等规模城市的发展则是显著的负向影响[10];Tervo对1880—2004年芬兰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自1950年后随着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富裕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带动作用消失了[11]。
4 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考与建议
尽管国家已经明确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定位,但是,北京作为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显然不能简单“去经济化”,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放弃发展大而全的经济体系,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高精尖产业结构。而且,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需要权衡北京在京津冀地区以及全国层面的作用和职能。
北京长期以来既是我国的首都,承担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也作为我国三大增长极之一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核心,但是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一定程度上造成首都政治文化等职能与城市经济社会职能分离的局面。因此,从远期来看,北京继续承担全国政治中心和区域发展核心双重职能,或者逐步弱化城市社会经济职能,主要承担首都政治文化职能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但是就近中期来看,基于北京自身以及京津冀地区的现实情况,北京仍然应该保持国家首都和区域经济中心并重的双重职能,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空间较小。与东京类似,北京未来既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承担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从城市职能来看,北京应该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区域中心城市。一方面,从此类城市的规律特征来看,城市应该适度保持一定的制造业;另一方面,与东京等世界城市相比,北京超过80%的服务业已经与东京产业结构相差不大,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同时与上海和广州等国内发展水平相当的城市相比,北京服务业比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因此,从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来看,产业结构并不是其主要限制因素。从京津冀区域层面来看,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对周边区域更强的外溢性也有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推进。总体上,无论从北京自身发展还是京津冀区域协同来看,北京制造业比重并不高,不应简单地推动制造业向外疏解,而应该注重制造业内部的提升和调整,部分高端制造的发展和试制环节的保留有利于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事实上东京依然将“享誉世界的东京的制造产业”作为城市的一个重要名片。
远期,如果定位于国家首都,则北京产业结构有较大调整空间。与华盛顿类似,作为特殊职能城市,北京只是承担国家首都职能,主要为全国提供政治、文化、科技等服务,并作为国际交往的舞台,提升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则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的疏解力度。但是近中期并不适宜,因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虽然能够大幅提高北京自身的发展水平,但是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并不强,不能有效缩小北京与周边城市发展的差距,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与周边区域产业梯度。尤其是目前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生产网络并不发达的状况下,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有效促进河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此外,河北要加强与天津的对接,逐步形成完善的制造业生产网络,以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地区经济的协同显然不应只是北京单方面的调整,京津冀地区长期割裂问题也需要天津和河北的积极应对。除去体制机制问题外,京津冀三地产业体系难以有效衔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京与周边城市存在显著的产业梯度差,而且高端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特征又使其对周边区域带动作用有限。因此,河北不应仅仅盯住北京,举全省之力推进环首都经济圈等战略,而应利用现有的制造业基础,加强与天津先进装备制造业等的对接合作,逐步建立完善的制造业生产网络,从而与北京和天津的科技研发、金融服务等进行对接,推动京津冀产业体系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