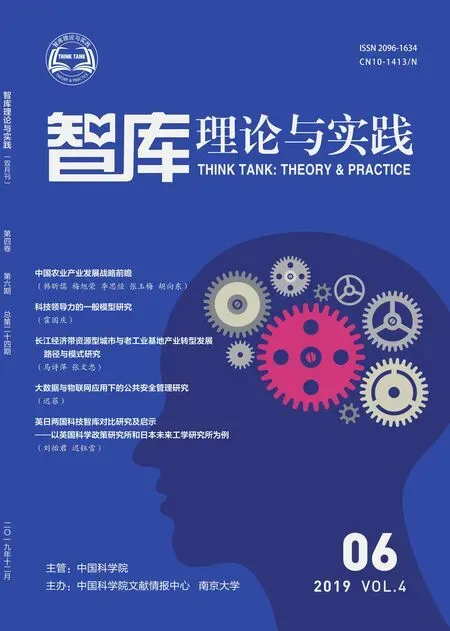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发展与就业挑战:基于失业风险恐惧的探索*
2019-12-26李佩张成岗
■ 李佩 张成岗,2
1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2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科技战略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084
历史上,科学技术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冲击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正在带来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新兴技术群不仅在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做事的方式,而且正在改变人类自身。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就业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就业活动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比如,平台经济孕生的新职业允诺了人们的弹性工作,引发了就业市场创新,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职业保障性的担心和恐惧。全面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带给就业的新挑战有助于系统认知新技术革命的全面性,有助于构建新技术革命中的思维框架,从而更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挑战。
网络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推进者曼纽尔·卡斯特曾经说道,在任何历史转变的过程中,系统变迁最直接的表现之一,乃是就业与职业结构的转型[1]。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对就业的冲击是经济和社会密切关注的议题,当下人工智能在生产和工作中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将加剧对就业的冲击。就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充分的就业可以促进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是一种“社会稳定元素”(卡尔-桑德斯,威尔逊,1933)和“社会控制机制”(帕森斯,1968)。涂尔干也曾强调,具有专业工作的群体可以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可以控制个人的利己主义,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纽带变得更强大[2]。对个人而言,就业是个人在经济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一种社会回报[3]。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的两个主要目标。然而,从“卢德运动”到今天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肇始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就业不安全感从未被消除。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已经对技术取代匠人表示担忧。技术性失业现象滥觞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已经历经了两百余年之论争。最初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技术不会造成失业,而詹姆斯·穆勒、西斯蒙第、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等认为技术会造成失业。20世纪30年代,在大萧条背景下,经济学家凯恩斯最先引出“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一词[4],并指出失业的原因在于节约使用劳动力的手段及其发展速度,超出了可以为这些劳动力找到新用途的速度[5]。凯恩斯在其著名的演讲“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1930年6月,马德里)中指出技术进步是造成普遍失业的原因,但这将为个人腾出时间来从事不以寻求报酬为目的,而是为了个人成长或娱乐为目的的其他活动[6]。凯恩斯的想法在当时被视为乌托邦。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美盛行这种关于就业、社会分配和美学式生活的乌托邦式构想,涌现出曾风靡一时的技术治理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7],认为技术是失业的根源,并主张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取代政治家和商人来治理社会。
迈克尔·B·舍勒(Michael B.Scheler)[8]和鲍德温(P.M.Baldwin)[9]的研究都直接表明,人被机器取代即为技术性失业。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自动化在生产领域的普及,罗马俱乐部、丹尼尔·贝尔、安东尼·吉登斯都表示技术对就业带来冲击。20世纪90年代,C.格伦蒂宁发表《新卢德宣言》(1990),杰里米·里夫金提出“工作终结论”(1995),加利诺(1999)从“技术-生产率-市场-劳动力需求”的关系来讨论技术性失业。国内学者国内关锦镗、曹志平、韩斌从科技革命与就业的角度分析了技术与就业的问题[10]。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迎来第三次浪潮,其应用的快速扩散对就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杰瑞·卡普兰(Jerry Kaplan)[11]认为人工智能将会导致持续性失业,卡尔曼·托斯(Kalman Toth)[12]提出“不劳社会”将会到来,理查德·萨斯坎德和丹尼尔·萨斯坎德(Richard Susskind,Daniel Susskind)[13]表明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性失业是大势所趋,小池淳义[14]指出人们的工作将被夺走。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替代效应,至少从长远来看,就业创造效应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15]。
可见,人工智能给社会系统带来巨大的变迁,并随其可能兴起新一轮技术性失业浪潮而强化了社会的失业感知,也增加了公众对失业风险的担忧和恐惧。基于失业风险恐惧的探索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挑战问题,可以反向窥探人工智能赋予社会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巨大冲击。从公众对失业的主观感知出发,对于精准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性失业大有裨益。
1 人工智能时代失业恐惧蔓延
人工智能内在地具备技术的特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问题可以被归为技术性失业范畴。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在速度、规模和深度上都远远超于一般性的技术性失业。仅从生产层面谈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已经过时,人工智能既可以取代可被编码为计算机语言的程式化工作,又可以取代难以被分解和编码的非程式化工作。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意味着人类可能“在本质意义上被取代”[16]。在人工智能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下,人们的就业不安全感和对再就业的担忧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弗拉基米尔·金普尔森和亚历山大·奥什切科夫(Vladimir Gimpelson,Aleksey Oshchepkov)将这一心理现象称为“失业恐惧”(Fear of Unemployment)。
“Fear of Unemployment”一词最早出现在1982年约瑟夫·纳尔(Joseph L Naar)[17]关于失业恐惧打击美国工会并对工作保障带来影响的短文中,也常使用“UnemploymentFear”一词。失业恐惧有两方面的体现[18]:一是对失去现有工作的恐惧,体现为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二是已失业人员对难以再就业的恐惧。“JobInsecurity”和“Risk of job loss”常被认为是工作不安全感的代名词。对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恐惧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学恐惧(Sociological Fear),Yuhua Liang和Seungcheol Austin Lee称之为“对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恐惧”(Fear of Autonomous Robo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FARAI),他们的研究指出,老年人、女性和文化程度较低且收入较低的人可能会更担心自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失业[19]。恐惧是面对潜在的危险在现实中发生时的一种重要的情绪,但恐惧缺乏责任感,并不是面对风险后果和不确定性时合适的情绪[20]。失业恐惧天然地体现了现时代人们对就业冲击的被动担忧但却缺乏改变就业现状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能力,因此超越个人层面的引导和规划对于缓解失业恐惧并寻求新的就业增长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失业恐惧伴随着一系列社会后果。首先,在个人层面,导致收入降低并降低消费[21],破坏自信心,压抑主观幸福感,消极地影响健康[22],甚至导致抑郁症[23]和引发自我伤害[24]。其次,在家庭层面,可能使家庭关系复杂化,负面地影响婚姻和家庭功能[25],直接降低配偶的心理幸福感,这一点在单一收入家庭中比在双收入家庭中更强[26]。父母的工作不安全感与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27],影响甚至蔓延到未出生的家庭成员[28]。最后,在企业层面,导致员工行为异化,体现出表面激进、内心消极的行为现象[29]。在职人员的健康投资下降,员工对失业的恐惧导致他们尽量避免病假或康复假以及其他医疗服务,因为雇主可能会将其误解为推卸工作[30]。此外,失业恐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步发展,使当地社会服务供求紧张。
失业恐惧问题伴随着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演进,泛在于东西方社会中。20世纪90年代我国曾出现“黑色失业浪潮”,随着失业制度普遍推行而逐步呈现,(可能)出现一种弥漫极广的失业恐惧症,但这一时期的失业恐惧并非因为新技术的冲击,而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把下海看作是走出失业恐惧和建立新职业的桥梁[31]。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失业恐惧普遍化。一项对全美公民进行的心理抽样调查,在回答“你这一生中最担心什么”时,59%的人选择了“失业”。弗拉基米尔·金普尔森和亚历山大·奥什切科夫利用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数据(Russian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RLMS),考察了俄罗斯工人在1997-2012的15年间对失业的恐惧,结果显示除了2007年,担心失去工作的人的比例一直高于50%。托比·沃尔什(Toby Walsh)[32]对300位AI和机器人专家以及500位非专家关于技术性失业的看法所做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尤其是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导致高失业率。《世界发展报告2019:工作性质的变革》揭示了机器人引发的失业问题给人们造成的恐慌已经成为未来工作讨论的中心议题,并预示未来的工作性质会发生变化。
2 公众失业风险感知分析
历史地看,技术创新和人类就业是共生发展的,然而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应用上的成就,意味着变革的步伐变得越来越快,对就业的冲击将引发空前的失业恐惧。算法和智能机器被用于各个领域,比如经济、商业、医疗、工业和法律领域。任何需要在没有足够先验知识的情况下使用数据进行预测的领域,都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技术发展的“三重逻辑悖逆”,即“以现代性为基础构架的技术社会中的主奴、不均衡性、目的与工具的三重逻辑悖逆”,同时又置身于“新全球化、新工业革命、社会转型三重叠加的挑战”的时代背景[33]。跟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预测,到2055年,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取代全球49%的有薪工作,而10-12%的失业率足以造成社会紧张局势并产生犯罪。
2.1 接近一半的公众有不同程度的失业恐惧
通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调查数据,可以基本了解公众的失业感知和失业恐惧程度。基于CGSS2015居民调查问卷中的“D28您是否担心有可能会失业”问题,从10968个样本规模中根据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最终选取对本研究有效的787个样本,对公众的失业感知进行初步研究。787个研究样本中,见表1,“非常担心”失业的样本有42个,占比5.34%;“有些担心”的样本有126个,占比16.01%;“有一点担心”的样本有196个,占比24.90%;完全不担心的样本有396个,占比50.32%;无法回答的样本有27个,占比3.43%。因此,在787个样本中,有不同程度失业恐惧(“非常担心”“有些担心”“有一点担心”)的样本比例为46.25%。“是否担心有可能会失业”的均值为2.86,样本中公众失业感知的平均程度为“有一点担心”失去工作。

表1 样本对不同程度失业恐惧的回答情况Table 1 Response to the fear of unemployment in sample
2.2 失业恐惧主要集中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
研究结果显示: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样本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4.86,样本的平均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整体上失业恐惧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就业安全感相对最高,但大学本科学历的失业恐惧在数值上较为突出而不容忽视。具体而言,见表2,“非常担心”失业的样本当中,初中学历的样本占比为50%,其次是小学学历19%,普通高中学历9.5%,中专学历7.1%,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学历2.4%,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样本构成主要特征群体。“有些担心”失业的样本当中,初中学历样本的占比最高为31%,其次是小学学历19%、普通高中学历18.3%、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学历8.7%,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样本构成主要特征群体。“有一点担心”失业的样本当中,初中学历25.5%、小学学历17.3%、普通高中学历13.8%、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学历10.2%、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学历8.2%,研究生及以上学历3.6%。“完全不担心”失业的样本占样本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初中学历占比最高26.5%。

表2 不同程度失业恐惧的学历分布情况Table 2 Education degree distribution of the fear of unemployment
2.3 失业恐惧群体主要为31-50岁人群
在失业感知的年龄分布上,见图1,失业恐惧群体主要为31-50岁人群。“非常担心”失业当中,41-50岁的群体占比最大,其次为31-40岁与51-60岁,少量19-30岁。“有些担心”失业当中,41-50岁最多,19-30岁以微弱的差别排在其次,再次分别是31-40岁,51-60岁,少量61岁以上。“有一点担心”失业的年龄结构分布排序为31-40岁,41-50岁与19-30岁数量非常接近,51-60岁,60岁以上。整体来看,31-50岁年龄群体的失业恐惧程度在失业恐惧当中占比最高,19-30岁年龄群体失业恐惧程度相对轻微。

图1 不同程度失业恐惧的年龄分布Figure 1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fear of unemployment
数据分析显示:首先,学历教育对公众的失业感知存在影响。表现在: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失业恐惧程度最高且人数占比最大,大学本科的失业恐惧问题也较为突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失业恐惧最轻微。其次,在年龄结构上,失业恐惧程度较高的年龄群体主要是31-50岁,属于正处于职业黄金期和稳定期的群体。再次,不同程度的失业恐惧人数占比总和为46.25%,说明失业问题已经引起近一半公众的关注,失业问题给公众心理带来的影响较广,不能排除这种失业感知有可能向更大范围和更严重程度转变。
2.4 人工智能可能加剧失业恐惧
根据《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19)》的预计,2019年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86.8亿美元,约占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的29.5%,其中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57.3亿美元,占全部机器人总量的66.0%。工业机器人安装量也可以体现出工业生产领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2018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为13.32万台,居全球首位。工业机器人的安装和使用提高了工业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对就业带来冲击。受人工智能的影响,公众的失业感知也会发生新的变化。人工智能所催生的就业岗位对人才要求非常高,不能否认高学历人群也将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和失业恐惧。引用社会变迁理论对技术和社会关系的解释,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物质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相差异步”是解释人工智能导致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所倡导的社会技术系统研究方法强调,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间缺乏协调是无效率和冲突的根源。早在奥格本的社会变迁理论中就对物质文化(技术发明)与非物质文化(社会)之间的失调问题进行详细说明,奥格本称之为两种文化之间的“相差异步”[34]。“相差异步”最直观地体现为社会系统相对于技术发明的滞后性。在奥格本看来,大多数技术发明并不是为了某一项社会制度而进行发明,在技术扩散阶段“社会的复杂性”对社会适应新技术带来阻碍,此外,技术与社会之间内在的差异性,以及道德、礼教和风俗等“团体的价值”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和社会的糅合。邱泽奇在其技术与组织理论中强调,技术行动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异步”,是技术化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源[35]。人工智能技术相比其他技术在发展速度和影响规模方面都具有超越性,借助大数据和5G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应用,并扩大其对就业的影响。
3 应对人工智能失业风险恐惧的政策建议
为防范和应对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失业增长”(jobless growth)和“无就业发展”(development without employment)[36]的可能性,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失业风险感知和失业恐惧,需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治理,提高社会应对失业风险的韧性,同时加强技术赋能和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并积极引导人类在技术社会中的觉醒。
3.1 加强人工智能的社会治理,充分促进“善智”发展
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历史沿革来看,技术完全有能力实现无工作的社会,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在技术的发展和扩散的整个过程当中,人类对技术进行了适应性“编排”,以尽可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就业需求。回顾技术和文明的发展演变历程,技术是可控的,但人工智能将技术失控的可能性放大到极致,因此亟需对人工智能进行可控的社会约束。技术和社会如何和谐共处一直是技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国家需求的技术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符号,影响着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的变革,对人工智能进行社会治理是大力推行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社会前提。具体可通过以下方面开展相关举措。首先,面对人工智能给就业带来的挑战,应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就业效应评估和预测,增强风险意识,以更好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导致的失业风险,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思考并精准计算人工智能创造的新的就业任务总量是多少,判断这些新任务是否属于人类更加具备优势的类别,进一步分析人和人工智能谁更具备执行这些任务的优势。长远来看,就业虽然并非人类的绝对需求(absolute needs),但目前整体的社会发育还未到达超越就业的阶段,因此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人层面共同致力于保持稳定而充分的就业。其次,合理分配人工智能衍生的“技术红利”。为应对在人工智能应用的初期,技术红利向少数资本方和技术方大幅度倾斜的现象,需要科学合理地分配人工智能技术红利,让公众享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再次,2019年全国两会正式提出“智能+”战略,因此需要从政策制定和实施层面积极推进“智能+”战略,实质性地推进人工智能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使之和谐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全面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善的人工智能。
3.2 增强社会系统的“反向适应”,提高应对失业风险的韧性
历史发展表明,社会相对技术的发展存在滞后性,因此需要增强社会系统相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反向适应,整体提高社会和个人应对失业风险的韧性。首先,合理归纳人工智能失业问题的原因。多项研究表明,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性失业问题完全归咎于人工智能是不合理的。人工智能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如国家的产业组成、制度脉络、在国际分工里的位置、竞争力、管理政策等,在就业方面都超过技术造成的特定影响。曼纽尔·卡斯特分析了欧洲和美国的信息技术影响就业的数据之后得出结论,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引进新技术,而是受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总的来说,在技术之外,市场需求和社会机制主导着失业的可能性。其次,市场和社会机制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应该做出适合社会发展的判断和决策,以应对技术系统快速变革但社会系统滞后而带来的就业问题。社会系统的及时调适对于应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可能带来的问题意义重大。需要有效协调就业市场的规范性和灵活性,保持政府就业保障职能的同时激发企业用工活力。再次,加强并完善不同层面的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社会系统反向适应的重要方式。人工智能导致就业结构变化,提高了以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比重,进一步拉大了就业差距和收入差距,因此应加强和完善相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再分配功能,提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将失业保险和就业支持政策覆盖城乡全体劳动人口,保障失业群体的基本生活,帮助其顺利度过失业期。最后,需要充分完善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就业相关的统计调查和研究,加强对智能时代技术性失业的专业化评估、预测和应对,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的专业性与有效性,积极有效对接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转岗就业。
3.3 有效推进技术赋能,精准提升就业能力
技术赋能、社会赋能和个人激励相结合是提升智能时代就业能力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表明就业能力影响员工的失业感知,提升就业能力是有效应对失业问题和失业恐惧的关键。首先,加强人工智能知识的普及是前提。人工智能是当下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越早认识、接受和接触人工智能有利于对可能的变化及早作出沉着应对,有助于减轻失业恐惧等人工智能导致的负面心理反应。其次,不同学历和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对于失业的感知是有差异的,面向所有潜在失业群体或失业恐惧的群体提供精准高效的提升就业能力的平台和途径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是培养人的职业自信和就业能力的基础,适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系统和职业培训系统的改革是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就业变革的必然途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教育变革的内生动力,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要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变化。人工智能人才需求逐年提升,但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才非常紧缺,在人工智能用人需求和人才供应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或空档。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创业规模和就业数量逐渐扩大,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以计算机视觉、服务机器人和语言处理为主,这些新的就业领域对就业人员的要求非常高,有数据表明人工智能企业需求的人才学历半数要求硕士及以上。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已专门进行人工智能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以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专门的人工智能人才。针对非大学生的职业教育和针对在岗群体的技能培训也应该向前迈进一大步,建立可持续、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体系。对个人而言,终身学习的理念将成为获取职业技能和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途径。再次,人工智能已经实现了给产业结构和生产领域赋能,同时也需要向个人赋能,以保持人类在生产回路中的位置。坚持“以人为本”,优先将公共资源投入到人的能力发展当中,并充分扩大人工智能新增就业的量和可行性,将就业创造效应充分辐射到不同层面的就业和职业结构当中。
3.4 引导技术社会中人的觉醒,催化人的自主性
从政策层面营造空间和现实路径,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致力于帮助公众在技术社会中形成客观认识,并自主地付诸反向适应和自我升级的行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技术可以自主迭代和发展,但不会自主编程或制定符合人类发展逻辑的规则,最终在人-技-社会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人类本身。“善人”是“善智”不可否认的前提,而人在技术世界中的觉醒是更为基础层面的前提。尽管心灵哲学、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领域从意识、存在、伦理、自主性、机器道德等角度展开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争鸣从来不绝于耳。然而,种种语境中过于形而上的讨论难免逐渐拉大人工智能与公众及其生活世界的距离。而当今的世界已经迈向一个技术和社会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公众参与在社会变革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在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因此,以下的努力显得尤为必要。打破疏离,让公众尽可能切实感知到自身的存在和生活世界正在何种程度上遭受来自人工智能的影响和冲击,让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和感知从陌生和恐惧向了解和自信转化,从思想和行动的单向对抗向契而不舍的学习和自我提升转化,最终有勇气和能力向一个人机共生的未来社会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