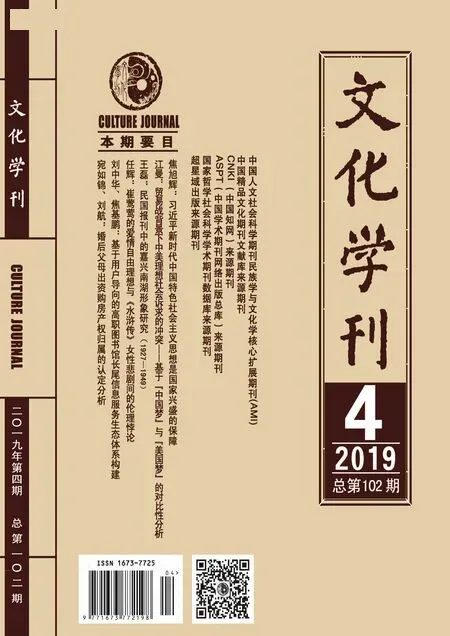民事恶意诉讼的程序法规制研究
2019-12-26宋莉莉
张 杰 宋莉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法治理念,更加愿意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不法分子受利益的驱使,企图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非法目的。这种不法行为是对法律严肃性的践踏,严重危害了国家的司法权威、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阻碍了司法的进步,我们必须对其引起重视,尽快找到规制民事恶意诉讼的良方。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民事恶意诉讼行为有了一定的研究,民事诉讼法也对其进行了一些规制。但是,在民事恶意诉讼的概念、成因、立法及司法防范等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本文重点从程序法规制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完善程序法的相关规定。
一、民事恶意诉讼的概念
当前理论界对民事恶意诉讼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汤维建教授认为,民事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无依据之诉,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1]。杨立新教授认为,民事恶意诉讼是指“对民事诉讼程序的恶意提起,意图使被告在诉讼中由于司法机关的判决而受侵害”[2]。王利明教授认为,民事恶意诉讼是指“故意以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致使对方在诉讼中遭受损失”[3]。综合各学者的意见,可以认为主观上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人都具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恶意,客观上都以表面合法掩盖实质违法,同时存在两点分歧。
第一,民事恶意诉讼的行为方式存在争议。上述学者基本上都将民事恶意诉讼的行为方式界定为滥用民事起诉权,这种界定方式很显然缩小了民事恶意诉讼的范围。民事恶意诉讼不仅仅包括行为人在起诉阶段恶意提起诉讼,还包括行为人在诉讼阶段滥用自己的合法程序权利。
第二,民事恶意诉讼的成立与否是否必须以造成被害人损害后果为前提。以杨立新教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民事恶意诉讼的成立必须要有受害人损害的发生,以汤维建教授为代表的认为只要求加害人主观上有加害的恶意,不要求损害结果的发生。笔者认为,民事恶意诉讼具有双重属性,其既是一种侵权法上的侵权行为,也是程序法上的非法诉讼行为,即使没有造成受害人损害,该非法行为也造成了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下降的不良后果,仍然应当受到惩罚。
民事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使他人遭受物质损失或精神损失,在明知无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采取非法手段,滥用民事起诉权、民事程序性权利的行为。
二、民事恶意诉讼的成因
民事恶意诉讼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有增无减,我们有必要探讨怎样对其进行规制。笔者认为,要从其成因入手,分析民事恶意诉讼为何在司法实践中频发,找出其产生的根源并对症下药。
(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导致司法权弱化
我国过去一直奉行职权主义模式,法官在诉讼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我国法院审判的改革,当事人被赋予更多的意思自治权。法官只能依据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主张、提出的证据进行审理与裁判,只有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一些程序性事项的特殊情况下法官才会主动进行调查取证。当事人诉讼主义模式强调最大化发挥当事人的作用,法官只需要严格根据法律程序审判案件,发现法律真实,无需还原案件的客观真实,因而在民事恶意诉讼案件中客观真实往往被法律真实所掩盖了,给了不法行为人可乘之机。
(二)法院考核评价机制不合理,过分追求调解率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加上调解具有结案快、化解冲突有效的特点,调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十分受欢迎,实践中法院也用调解率、结案率对法官进行考核评价。但是,调解制度在减轻法院审判压力、为诉讼分流的同时,也为民事恶意诉讼打开了闸门。《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自愿原则,很多恶意串通的当事人利用调解制度自愿的特点,通过调解结案,损害案外人利益。实践中法官迫于结案率的压力,很多时候因为急于调解而忽视了对案件真实性的审查。
(三)立案登记制度的不利影响
立案难曾经是困扰司法界和老百姓的一大难题,但从2015年5月1日起我国废除了立案审查制度,开始实施立案登记制度。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立案审查制下地方干预、案件敏感等导致的立案难问题,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了保障。然而,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实施,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开始恶意提起民事诉讼,企图通过立案登记制度的便利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背离了立案登记制的初衷。
三、民事恶意诉讼的立法现状
虽然目前我国立法没有明确民事恶意诉讼这一概念,但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对其进行了相关规定。
(一)实体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这两条规定,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是,由于分则没有对其加以细化,导致实践中这两个条款也很难适用。《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虚假诉讼罪,加大了对虚假诉讼即民事恶意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但司法实践中认定为该罪的情形并不多。
(二)程序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了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该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这是立法的重大突破,体现了立法对恶意起诉、滥用诉讼权利等非法行为的否定。《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新增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为遭到民事恶意诉讼侵害的案外人提供了一条事后救济的途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113条规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是程序法上第一次明确对民事恶意诉讼行为进行法律规制,虽然规定不够具体、细化,但体现了法律在规制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上的进步。
四、民事恶意诉讼的程序法的完善
民事恶意诉讼在我国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如何规制这一行为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完善程序立法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建立审前诉讼担保制度
诉讼担保制度是指为了保护被告的利益,防止原告败诉之后无法或者逃避对被告的赔偿责任或者承担诉讼费用,被告在法院立案前或庭审中,申请法院要求原告上交一定的费用作为担保。为了防止诉讼担保制度的滥用,其适用必须注意两点。(1)提出诉讼担保申请的人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进行了民事恶意诉讼,并且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2)诉讼担保费用不宜过高。担保费用设置过高,容易损害经济条件不好的当事人的诉权,造成顾此失彼。诉权保障是第一位的,不能因打击民事恶意诉讼的需要而损害了行为人的正当诉权。
(二)完善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
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借鉴的是美国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也称证据发现。该制度为了保障当事人庭前充分沟通,避免裁判突袭,强制性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情况下必须开示证据[4]。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当事人不懂得主动要求证据交换,法官判断证据的多少或案情复杂与否亦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组织证据交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法官应积极行使释明权,防止因当事人不懂得提起证据交换而让民事恶意诉讼进入审理程序。同时,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进一步扩大法官组织证据交换的范围,除涉及公共利益、没有关联性和保密特权以外的案件都可以组织庭前证据交换。
(三)完善撤诉制度
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3条、第145条对按撤诉处理和原告自行撤诉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原告撤诉的条件规定得十分宽松,原告的撤诉权十分强大,被告没有任何异议权,只需要法官审查符合撤诉的条件即可。实践中有很多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人在达成了自己利用诉讼损害他人名誉等目的后,通过不出庭诉讼、中途退庭来退出诉讼。法律应赋予被告撤诉异议权以平衡原被告双方的诉讼地位,法院对被告异议的理由进行审查,认为理由成立的可不准许原告撤诉。同时,为了保障原被告双方诉讼的实质平等,在被告应诉后,原告拒不出庭或中途退庭的,法官可以认为原告放弃了诉讼请求,对其进行缺席判决。
(四)加强对案外第三人的事前程序保障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无法有效对案外第三人进行保障。第三人对诉讼标的没有全部或者部分请求权,就无法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原本的诉讼[5];如果案外第三人与案件的审理结果也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那么也无法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加入诉讼程序,因此,当前法律规定的事前保障制度无法保障民事恶意诉讼中案外受害人的权益。日本法规定的“诈害防止参加”制度不仅使诉讼标的有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参加诉讼,并且可能因诉讼结果而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也可以参加诉讼,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诈害防止参加”制度,完善对案外人的事前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