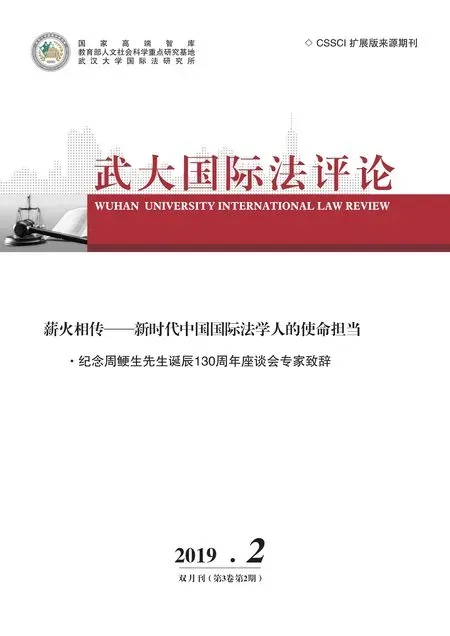联合国难民署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困境与出路
2019-12-26谢垚琪
谢垚琪
201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开始席卷欧洲大陆,并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热点之一。①参见鲍永玲:《欧洲难民潮冲击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危机》,《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65页。2018年6月20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Filippo Grandi)在国际难民日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由于冲突的爆发、再起、持续与恶化,全球共有6850 万人被迫流离失所。每10 位难民中,就有9位逃到邻国避难。这对难民群体与东道社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国际社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团结。为颠沛流离的难民们提供庇护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②《联合国难民署高专菲利普·格兰迪在世界难民日发表致辞》,http://www.unhcr.org/cn/11731-难民署高专菲利普·格兰迪在世界难民日发表致辞.html,2018年8月20日访问。正如格兰迪所言,难民大规模流动形成难民潮,进而在难民涌入国引发社会危机。联合国难民署与难民来源国、收容国和第三国积极开展多方合作,在既有的难民大规模流动应对机制下着力化解危机,实现大规模流动中难民的自愿遣返、重新安置和融入本土。然而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每年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数据显示,①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越来越多的难民处于岌岌可危境地,但仅仅依靠以上三种安置方案应对由难民大规模流动而引发的复杂情势却远远不够,难民大规模流动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联合国难民署主导下的国际合作与责任分担。②See Kevin Appleby,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fugee Protection System: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5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794 (2017).
一、难民大规模流动的界定及成因
(一)难民大规模流动的界定
为了引导难民有序流动,实现大规模流动难民以自愿、安全、有尊严和可持续的方式返回,联合国大会第71 届会议将《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③2016年9月19日,193 个联合国会员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一致通过《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以下简称《纽约宣言》)作为提交解决难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的决议草案,号召国际社会通过合作更好地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这一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问题。
《纽约宣言》第一次以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的宣言形式,界定了“难民大规模流动”这一概念,提出其中应该考虑的四点因素:第一,涌来的人数;第二,经济、社会和地理环境;第三,接收国的应对能力;第四,突如其来或旷日持久的流动的影响。《纽约宣言》指出“大规模流动”可能涉及难民或移民的混合流动,难民和移民流动的原因不同,但所走的路线可能相似,“大规模流动”的概念在于定义难民的非正常流动,而并不包括诸如移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正常流动。④See UN, A/RES/71/1, para.6.难民大规模流动的责任通常由难民接收国承担,然而因为涉及由于不同原因和采用非正常渠道流动的混合人口流,⑤See UN, A/70/L.34, para.4.大部分难民接收国自身经济不发达,应对能力有限,国际合作和责任分担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纽约宣言》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是由于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承受能力不同,所以“大规模”的认定一方面需要参考《纽约宣言》中的四点因素,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据个案,在具体情势中判断“难民大规模流动”的规模和影响。
(二)难民大规模流动的原因
难民大规模流动是一个涉及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人口学等诸多学科的复杂问题。笔者认为,难民大规模流动的原因,可以从人口学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中得到解释。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作用力的结果。在人口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居民推出居住地;而在人口涌入地则存在“拉力”因素把外地人口吸引进来。①参见吕晨:《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人口空间集疏的机理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推”和“拉”构成了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而难民的大规模流动在适用推拉理论的过程中也呈现其特殊性,即与普通的人口流动相比,难民流出地的推力比难民涌入地的拉力更加重要。
虽然作为经济因素的“拉力”,例如,稳定的生活环境、成熟的经济制度和健全的社会福利等是大多数国际移徙的驱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方向,但是就大规模流动的难民而言,战争、冲突、暴力、迫害、政治压迫等才是导致流动的主要原因。②See UN, A/70/L.34, para.7.因此从推拉理论“推力”的角度分析,产生难民大规模流动现象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战争和武装冲突
20世纪,战争的国际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旧帝国的解体、民族国家的扩大和增加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以及生态环境的每况愈下,导致难民大规模流动。③参见闫金红:《解读难民政策——意识形态视阀下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其中,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难民大规模流动和两次世界大战密不可分;而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难民潮的发动机和难民集散中心。④参见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20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根据联合国数据统计,大规模内战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数量逐步减少,然而从2007年开始则由4 个增加到了2014年的11 个。⑤See UN, A/70/709, para.6.虽然每次冲突的根源不同且原因复杂,但结果往往是产生大量的难民,他们被迫远离家园,在城市间辗转,甚至远渡重洋、跨越边界寻求庇护。与此同时,在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同时还会滋生跨国犯罪集团,对冲突后国家的稳定和建设造成威胁。
虽然国际社会针对战争和武装冲突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条约体系,但是少数国家对战争行为基本规则的不尊重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判断和遵守;武装冲突各方对国际人道法的无视,也直接导致了难民潮的卷土重来。难民是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直接产物,国际社会未能处理难民原籍国的武装冲突和暴力侵犯人权行为等问题是导致难民大规模流动的主要原因。①See Victoria Metcalf-Hough, A Migration Crisis: Facts, Challeng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odi-assets/publications-opinion-files/9913.pdf,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2.民族、种族、宗教冲突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不仅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民族、种族、宗教冲突也导致了难民的大规模流动。②See Kevin Appleby,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fugee Protection System: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5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791 (2017).如果在时间上把难民问题分为“冷战”“冷战后”“21世纪”三个时期,“冷战”时期的难民大规模流动问题往往带有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争夺的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国较量的产物。“冷战”结束以后,难民潮产生的原因出现了新的特点,难民潮的爆发与民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密不可分,几乎每一次难民的大规模流动,都有民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因素的影响,③参见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20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索马里南部的少数族裔在索马里内战爆发后为躲避屠杀,不得不外逃他国;伊拉克库尔德难民等都是例证。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下简称《难民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以下简称《难民议定书》)明确将“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④《难民公约》第1条第1款乙项。纳入到难民定义的客观方面中。国际法禁止基于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主张、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任何类型的歧视。这种禁止众所周知。⑤See UN, A/70/L.34, para.14.然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族裔、宗教或政治派别间存在不信任和紧张关系,一旦爆发冲突,难民大规模流动的现象便接踵而至。
3.环境因素
2012年,瑞士和挪威提出了“南森倡议”(Nansen Initiative),建议考虑因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跨界流动情形,并在国家政策和实践层面,对“环境难民”的大规模流动予以关注。《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也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减轻灾害风险和解决由此造成的难民大规模流动的问题。⑥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沙漠化、盐碱化和气候变暖等环境因素,导致“环境难民”的大规模流动。①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环境难民大规模流动情形虽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难民署的广泛关注,但是“环境难民”并不符合《难民公约》《难民议定书》以及《联合国难民署章程》对难民的定义,故本文对此不作进一步讨论。
二、难民大规模流动下联合国难民署的应对机制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简称联合国难民署(UNHCR / The UN Refugee Agency),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2月14日创立,总部设在日内瓦。联合国难民署受联合国委托负责指导和协调世界范围内保护难民的国际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是难民署的最高负责人,现任高级专员自2016年起由意大利外交官菲利普·格兰迪担任。
联合国难民署是1951年《难民公约》和1967年《难民议定书》的坚定守护者和践行者,它的首要目标是保护难民的基本权利,而最终目标是帮助他们找到长远的解决方案,让难民能够重获尊严并在和平环境中重建生活。目前联合国难民署主要通过自愿遣返、重新安置和融入本土三种机制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现象。②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一)自愿遣返
自愿遣返是指难民在自由和知情的前提下决定安全并有尊严地返回原籍国,重新得到自己国家的保护。在难民自愿选择回原籍国且原籍国的状况有利于他们返回的情况下,联合国难民署会与原籍国和收容国合作帮助难民返回。
自愿遣返仍然是现阶段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主要方式。原籍国和收容国应确保遣返出于自愿而非强迫,是根据客观分析得出的解决方案,并确保遣返在安全和有尊严的前提下进行。与此同时,为使难民重返家园,重新融入并持续发展,亦需要为难民提供足够的支持和援助。
根据2016年联合国难民署《全球趋势报告》数据统计,返回原籍国的难民人数在2016年大幅增加,达到自2008年以来的峰值,与2015年的20.14 万人相比,增加了一倍左右,达到55.22 万人,其中大约90%自愿遣返的难民得到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然而,由于难民潮的爆发和难民人口总数的大幅增加,同时缺乏有利于难民返回原籍国的条件,自2013年以来,自愿遣返的难民人数在难民总数中的比例不到5%,远低于每年新增难民的人数。①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难民已经返回的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从2015年的39个增加到2016年的40个。阿富汗的难民返回人数从2015年的6.14万人增加到2016年38.4万人,连续两年成为返回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些难民绝大多数由巴基斯坦返回原籍国,另一部分则从伊朗返回。苏丹报告的难民自愿遣返人数为3.72万人,几乎全部来自乍得。据报道,大约有3.61万名难民返回索马里,其中大部分来自肯尼亚,一小部分来自也门。②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由于难民返回本国的情况复杂,难民返回后的生活环境令人担忧。难民自愿遣返的最佳状态是难民的返回与新增难民的数量达到合理的平衡。而达到这一最佳状态,一方面需要各方协调一致作出努力以消除导致难民流离失所的根源,另一方面难民原籍国应支持选择返回者的重新融合。③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二)重新安置
重新安置又称异地安置,是让难民离开入境国,合法地在另一个国家定居并受到法律保护,享有《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赋予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重新安置可以让难民在一定时候成为入籍公民。但是,被安置到第三国并不是一项权利,联合国难民署不能保证所有被核实的难民都能得到安置。在全球范围内,接纳难民重新安置的国家数量很少。每一个安置国对安置申请的接受标准都有所不同。安置的过程通常十分漫长。由于每一个安置国的安置政策及每一个案的具体情况都不尽相同,重新安置平均需要花费的时间难以计算。
据各国政府数据统计,在2016年期间,重新安置难民总数为18.93 万人,比2015年的10.71万人增加了77%。在2016年接收重新安置难民的国家中,美国接收的难民人数所占比例高达51%,共计重新安置了9.69 万名难民。其他主要的接收国还包括加拿大(4.67万人)和澳大利亚(2.76万人)。④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联合国难民署在2016年帮助16.26万名难民实现了重新安置,比2015年增加21%,是20年来的最高水平。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申请重新安置人数最多,共计有7.72 万人。其次是来自刚果(金)、伊拉克、索马里和缅甸的难民。以上5 个国家的难民合计占到了重新安置难民人数的80%以上。①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共有来自69 个国家的难民从83个国家或地区重新安置到了37个国家。②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难民得到重新安置的平均时间长达18年。③参见史蒂芬·安格内特、安妮·科赫:《联合国难民峰会的意义和契机》,吴菲菲译,《环球财经》2016年第9期,第41页。尽管联合国难民署并不是负责难民重新安置的唯一主体,一些国家也接受独立于联合国难民署之外的重新安置申请以实现家庭团聚,但是国际社会重新安置难民的能力仍然十分有限。
(三)融入本土
融入本土又称就地融合,是让难民融入庇护国(地区),使他们得到庇护国(地区)政府的保护。这是一种持久解决难民大规模流动的办法。然而难民融入本土是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需要难民个人和接收难民国家的共同努力,难民在庇护国寻找永久性住所并融入当地社区的同时,也应在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享有独立但平等的权利。④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难民融入本土所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衡量和量化难民是否成功融入本土并不容易。在法律上,最大程度上的融入通常反映在获得持久的法律地位。归化(naturalization)通常是融入本土的重要手段,也就是难民获得庇护国的公民身份或国籍。然而,对归化的数据统计并不十分准确,它不得不受数据可用性和覆盖率以及政策和法律变化的限制,尤其是这些数据难以在难民和非难民入籍上加以区分。因此,这些数据只能作为参考,并且根据该数据所作的解读可能也低估了难民入籍的难度。
2016年,有23个国家报告其至少有1例难民入籍,而2015年则有28个国家。联合国难民署2016年安排了2.3万名难民入籍,而2015年则为3.2万名。其中,加拿大报告的接收难民入籍的人数最多,达1.63 万人,虽然这大大低于它2015年报告的2.59 万人。其他报告在2016年接收较多难民入籍的国家是法国(3200 人)、比利时(1400人)和奥地利(1200人)。⑤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综上所述,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情势表示关注,全力帮助难民寻求长远的解决方案。然而面对数百万大规模流动的难民,传统的自愿遣返、重新安置和融入本土安置机制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
三、难民大规模流动下联合国难民署面临的困境
在与难民有关的条约体系中,难民享有在大规模流动情势下自由迁徙自由和在除因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原因外不被驱逐的权利。在难民大规模流动情势出现后,联合国难民署作为联合国体系内处理难民事务的专门机构,通过自愿遣返、重新安置和融入本土等传统方式和紧急庇护、集群保护等非传统途径予以应对。然而难民大规模流动有着突发和无序等特点,联合国难民署在应对之际也面临难民公约和议定书对难民定义过窄、难民来源国与收容国责任分担不均以及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缺乏明确分工等诸多困境。
(一)《难民公约》将难民定义局限于政治难民
1951年《难民公约》和1967年《难民议定书》是国际难民法的重要渊源,也是国际社会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法律基础。然而《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书的订立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难民情势也由欧洲范围内小规模流动的政治难民逐渐转变为世界范围内政治难民、战争难民混合流动的难民潮。《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也面临着定义过窄、程序缺失等诸多困境。
1951年《难民公约》确定了国际法上难民的基本定义,①根据《难民公约》第1条第1款乙项,难民是指“由于1951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惧因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见的原因留在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而1967年《难民议定书》并未对《难民公约》的定义作出任何改变,只是废除了有关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所确定的难民定义,是因“畏惧迫害”而产生的传统政治难民。②参见罗超、高鹏:《国际难民问题的挑战、应对及中国的参与》,《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17年第2期,第140页。虽然该定义在公约制定时符合当时国际社会对“难民”的理解,但是难民定义本就处于发展过程中,政治难民能享受《难民公约》对难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而因战争或武装冲突而被迫大规模流入他国的“战争难民”则随时面临着被推回的险境。
在实践中,1969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以下简称《非洲难民公约》)将难民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包括由于外来侵略、统治、占领或危及公共秩序的事件等原因而被迫离开其常住地到其原住地国家或其国籍国以外的另一地去避难的人。①参见苏琳婧:《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的困境及出路探析》,外交学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1984年《关于中美洲难民国际保护的卡塔赫纳宣言》(以下简称《卡塔赫纳宣言》)除了与《非洲难民公约》保持一致之外,还将“国内冲突”和“大规模侵犯人权”也纳入到难民身份确定的客观原因中。新的有关难民的国际文件适应时代的发展,对难民的定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扩展。
国际社会在难民问题上的立法和实践,意味着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和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担上致力于加强团结与合作,以共同解决难民问题。②参见《国际公法学》编写组:《国际公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48页。《难民公约》中将难民定义局限于政治难民已不能满足联合国难民署在实践中甄别战争难民身份的需要。
(二)难民收容国承担过重难民安置责任
难民收容国与难民来源国相比,在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上承担了过多的不对称责任。难民来源国是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根源,理应承担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主要责任,然而该责任在实践中往往由难民收容国代为承担。联合国难民署2016年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指出,全球难民人数在2016年破纪录地达到2250万,其中包括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和救济工程处(UNRWA)所负责的530 万巴勒斯坦难民和联合国难民署负责的1720 万难民。③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责任分担不均直接导致联合国难民署在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过程中难以调和难民来源国与收容国之间的矛盾。《全球趋势报告》从来源国、收容国两个维度分析了难民大规模流动中两者责任分担不均的困境。
《全球趋势报告》指出:2016年难民的主要来源国是叙利亚,2015年叙利亚的难民人数是490 万,到了2016年底,难民人数增加到了550 万。④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尽管数量有所减少,但阿富汗仍然是难民第二大来源国。截至2016年底,阿富汗难民人数为250万,而2015年为270 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巴基斯坦持续最大限度收容了阿富汗的140万难民。
截至2016年底,来自缅甸的难民人数从2015年的45.18 万人上升到49.03 万人。根据数据统计,其他主要的难民来源国还包括:越南(32.94 万人)、伊拉克(31.6万人)、哥伦比亚(31.11万人)、卢旺达(28.61万人)、乌克兰(23.91万人)和尼日利亚(22.93万人)。①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总体上,大规模流动的难民来源国中前10个国家的难民总计多达1350万人,占由联合国难民署负责援助难民总数的79%,这一数据与2015年的76%相比有所增加。而这10 个国家除叙利亚外,都被认为是最不发达国家,无法承担管理难民大规模流出的工作;而这些难民往往文化程度不高、经济能力较弱,给收容国带来较大的管理压力。②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在2015年,土耳其是接纳难民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2016年底,土耳其接纳难民的人数达到290万,高于2015年12月的250万。土耳其所接纳的绝大多数难民来自叙利亚,280多万叙利亚难民占土耳其收容难民总数的98%以上,其中还包括约33 万新登记的叙利亚难民。此外,还有其他国家的难民也在土耳其寻求庇护,其中伊拉克有3.04 万名难民在土耳其登记,伊朗有7000 名,阿富汗有3400名,索马里有2200名。③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巴基斯坦接纳难民人数占全球第二,尽管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难民的返回。2015年底,巴基斯坦有160 万难民,而2016年底,巴基斯坦接纳的难民数量缩减到140万,主要原因是大约有38万左右的难民返回原籍国。而巴基斯坦的难民几乎完全来自它的邻国阿富汗。④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根据数据的统计汇总,由于难民身份的注销和难民离开以寻求重新安置,黎巴嫩接纳的难民人数也略有减少。但是,与2015年它所接纳的110 万难民人数和2014年的120 万难民人数相比,截至2016年底,黎巴嫩仍然接纳了超过100 万难民。黎巴嫩大部分难民来自叙利亚(100 万人),6500人来自伊拉克。⑤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在德国,由于2015年和2016年初通过了大量新的庇护申请,难民人口大幅度增加。到2015年底,德国的难民人数为31.61万人,而一年之后这个数字为66.95万。大部分难民来自叙利亚(37.51万人),同时,其他的难民来源国还包括伊拉克(8.6万人)、阿富汗(4.63万人)、厄立特里亚(3万人)、伊朗(2.29万人)和土耳其(1.91万人)。⑥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可见,发展中国家在收容难民方面承担着不成比例的安置责任。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统计,排在前10 位的难民收容国中有9 个是发展中国家,其中还有3个国家,即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①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
联合国难民署除了面临难民收容国承担过重难民安置责任的困境之外,还需要处理与国际移民组织之间的职能分工问题。
(三)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缺乏明确分工
联合国难民署虽然在设立之初是以解决难民问题为宗旨,但是经过近70年的发展,难民署所关注的人群早已不局限于《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中定义的难民,而是包含了战争、内乱和外来侵略等原因造成的难民,②参见苏琳婧:《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的困境及出路探析》,外交学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以及在数量上已经超过难民的流离失所者,同时还兼顾寻求庇护者、自愿遣返者和无国籍人。
国际移民组织的行政机构由行政署、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总干事四部分组成。国际移民组织在成立后作为关于移民问题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一直处于联合国体系之外。③参见郭秋梅:《国际移民组织与全球移民治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2016年第71届联大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召开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的应对难民和移民问题的高级别会议,国际移民组织也在该会议上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专门机构。
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在职能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而部分国家在应对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的同时,也并未就难民与移民作出适当、合理的区分。首先,理论上难民与移民的定义存在较大差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将移民定义为“不考虑移民的原因和移民的身份合法与否,单纯改变其经常居住国的行为”。④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Migrant, https://refugeesmigrants.un.org/definitions, visited on 10 August 2018.广义上的难民包括政治难民、战争难民和经济难民,是指因畏惧政治迫害、战争或自然灾害而被迫离开其本国或经常居住国而前往别国避难的人;狭义上的难民仅指政治难民。⑤参见梁西原著主编、曾令良修订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难民在身份上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往往是被迫离开原籍国前往他国避难的个人或群体;而移民则直接和经济发展挂钩,他们的目的更多的是前往他国寻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其次,难民与移民不仅在定义上存在明显区分,实践中难民与移民也易出现身份上的混同,著名的国际难民法专家詹姆斯·哈撒韦教授认为,难民和被迫迁徙的移民混同将导致对难民地位特殊性的忽视,而使难民难以在原有的框架下得到保护。①See James C.Hathaway, Forced Migration Studies: Could We Agree Just to“Date”, 20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349 (2007).在大规模流动的过程中,难民与移民最大的区别在于《难民公约》第33条赋予难民的不被推回的权利。②参见刘国福主编:《移民法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国际移民组织积极开展政府间合作以及和非政府伙伴的合作。从国际移民组织的名称来看,可能会产生它只关涉移民领域的误解,事实上国际移民组织的移民治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移民与发展、促进移民、规范移民、帮助被迫移民。③参见郭秋梅:《国际移民组织与全球移民治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而庇护者、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安置和遣返都属于帮助被迫移民领域。国际移民问题结构复杂,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只是国际移民组织的移民治理四个领域中帮助被迫移民的分支,而移民劳工、人口贩卖和偷渡、技术移民等隶属于其他三个领域的移民问题的解决都存在异质性,面临着不同的难度。国际移民组织的应对能力有极大的局限性。
尽管国际社会已逐步达成共识,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可凭一己之力有效地管理难民的大规模流动,但是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在难民大规模流动应对上的分工不明,会导致难民不推回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遭到背离,特别是在缅甸罗兴亚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情势中,安置工作就因为是两方分头负责而缺乏凝聚力。④See Arya Pradhana Anggakara, Legal Protection Aspect of Refugees in Indonesia(Case of Rohingya’ s Refugees), 64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Globalization 24 (2017).
四、联合国难民署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出路
如前所述,面对突发和无序的难民大规模流动,联合国难民署在应对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首先,《难民公约》将难民定义局限于政治难民,已无法适应当前形势;其次,难民来源国无力管控难民大规模流动情势,难民收容国承担过重的难民安置责任,也让难民来源国与收容国在难民安置和管控的责任分担上出现裂痕;最后,联合国难民署作为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核心机构,面临赋能缺失和与国际移民组织分工不明等多项挑战。由于新出现和尚未解决的各种冲突,世界正面临着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动难民人数。⑤See UN, A/70/L.34, para.15.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将战争难民纳入与难民有关的条约体系,实现难民安置责任的合理分担和明确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的职能分工。
(一)将战争难民纳入与难民有关的条约体系
现有的难民条约体系是所有国际法主体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法律基础。然而,无论是《难民公约》还是《难民议定书》,制定时间都在半个世纪之前,难民情势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将难民定义限制在政治难民的框架内,符合当时国际社会的社会形势。而难民大规模流动具有突发性和无序性,这是在上述公约制定之时国际社会未曾预料到的。《纽约宣言》不同于《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重点关注战争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情势,承诺从难民局势一出现就寻求解决办法,丰富了难民的定义。
在将战争难民纳入与难民有关的条约体系过程中可考虑借鉴《非洲难民公约》和《卡塔赫纳宣言》的规定,将“武装冲突”和“大规模侵犯人权”也纳入到难民身份认定的客观原因中。《非洲难民公约》规定该公约缔约国必须接受逃离社会动荡、普遍暴力和战争的难民身份申请,无论其是否有充足理由担心自己受到迫害。①参见刘国福:《国际难民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该公约扩大了难民定义的客观方面,将战争难民概念纳入到区域性国际公约中,联合国与难民有关的条约体系也可借鉴。
(二)实现难民安置责任的合理分担
联合国难民署应与包括难民来源国以及收容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密切协调,在其他有关联合国实体参与下,针对每个难民大规模流动局势制定和提出“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omprehensive Refugee Response Framework)(以下简称“全面响应框架”),以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中难民来源国与收容国责任分担不均的问题。
难民来源国与收容国在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上承担着不对称的安置责任。难民之所以大规模流入收容国,大多数是由于来源国爆发“国内冲突”或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形成强大的“推力”将难民推向它国。然而,难民来源国由于自身的能力有限和情势的突发,无法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方向进行引导,导致难民收容国承担了过重的责任。因此,《纽约宣言》的附件一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提出联合国难民署将和有关伙伴从以下三方面对收容国和收容社区予以支持:
第一,在难民大规模流动发生之前或之后,实施一项联合、公正和迅速的风险和(或)影响评估,以确定并优先处理难民、国家和地方当局及因难民存在而受影响社区的所需援助。
第二,酌情将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以加强为收容社区和难民提供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工作。
第三,考虑到需求的增加和对社会服务的压力,努力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当局和其他服务提供者提供充足的资源,但不影响官方发展援助。方案应有利于难民、收容国和收容社区。①See UN, A/RES/71/1, Annex I, para.8.
一方面,难民来源国应确保承认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自己的国家,并有权返回自己的国家,同时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在安全的前提下,在充分尊重人权的情况下,履行接受本国国民的义务,并考虑采取便利措施归还其财产,帮助回返者重新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②See Kevin Appleby,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fugee Protection System: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6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780 (2017).另一方面,《纽约宣言》确立难民来源国将为难民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原籍国创造条件,强调全面响应框架必须消除暴力和武装冲突等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根源,实现必要的政治与和平解决争端,并协助重建努力。难民收容国在与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及其他联合国实体、金融机构和其他有关伙伴合作应对大规模难民流动的同时,应适当考虑到它们的能力及其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
(三)明确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的职能分工
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出路不仅在于制定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达成全球难民契约,也在于明确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的责任分担。
1.确认联合国难民署的核心地位
《难民公约》在序言中明确提出,“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对于规定保护难民的国际公约负有监督的任务,并认识到为处理这一问题所采取措施的有效协调,将依赖于各国和高级专员的合作”。③《难民公约》序言第6段。不仅联合国大会确立联合国难民署在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时的核心地位,其他区域性条约也对难民署的国际地位予以了肯定。④See Will Jones & Alexander Teytelboym, Matching Systems for Refugees, 5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667 (2017).如非洲联盟的前身非洲统一组织在1969年《非洲难民公约》中强调了《难民公约》在难民保护领域的地位,明确了联合国难民署在非洲难民保护中的作用。⑤参见《非洲难民公约》序言第11段。同样,作为中美洲难民保护的行动纲领,1984年《卡塔赫纳宣言》的第一部分就提到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核心地位。⑥参见《卡塔赫纳宣言》第1章第4段。
确认联合国难民署在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中的核心地位,有利于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源在于难民来源国,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合作。联合国难民署以它践行多边主义的行动印证了它在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情势中的核心作用。
2.重视国际移民组织的辅助地位
国际移民组织自成立伊始就与联合国难民署一直保持着协作与互动,共同处理移民和难民的有关问题。《联合国宪章》第57条和第63条规定,联合国可与在某一特定业务领域负有广大国际责任的政府间专门性国际组织订立协定,使之成为其体系下的专门机构。①参见张丽君:《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IGOs)》,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移徙终于纳入到联合国人道主义机制和发展机制的工作之中,而在2016年国际移民组织也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专门机构。
国际移民组织作为负责应对移民问题的国际组织,在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相关组织后,与联合国结成一种更加密切的法律和工作关系。②See UN, A/RES/71/280, para.3.联合国难民署依靠自愿遣返、就地安置和融入本土实现大规模流动情势下难民的安置;国际移民组织通过帮助被迫移民而参与到难民治理中。重视国际移民组织的辅助地位,就是要在难民安置上,重视国际移民组织帮助被迫移民的经验,在甄别难民的过程中加强与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提高甄别效率。国际移民组织在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中的辅助地位不应因联合国难民署的核心作用而忽视。
五、结论
联合国难民署的《全球趋势报告》指出,大量的难民在流动过程中被迫以家庭为单位逃离家园,其中来自叙利亚、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及中美洲等地的难民以家庭为单位被迫逃亡的人数上升至历史新高。③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visited on 7 September 2017.难民大规模流动问题本质上是难民跨国无序流动的问题。保护难民是联合国难民署的基本职责,特别是面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特殊情形,联合国难民署着力避免未经评估分析就对难民强行遣返,从而保障难民潮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寻求庇护的权利。④See Marjoleine Zieck, Refugees and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Movement: From Flight to Return, 39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 (2018).联合国难民署通过自愿遣返、重新安置和融入本土等机制应对难民的大规模流动情势。然而,在实践中联合国难民署面临难民定义过窄、难民来源国与收容国责任分担不均、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缺乏明确分工等诸多困境。
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将战争难民纳入与难民有关的条约体系,实现难民安置责任的合理分担,同时明确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的职能分工。责任分担是联合国难民署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问题的核心。联合国大会在各项决议中反复强调应加强分担对难民的责任。联合国大会于2018年12月17日通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国际框架——《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旨在改变世界各国应对大规模流离失所民众和难民危机的方式,使难民和收容他们的社区都能够受益。《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以现有的难民国际法律制度为基础,以实现难民安置责任的合理分担为宗旨。①See UN Affirms“Historic”Global Compact to Support World’s Refugees,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8/12/1028791, visited on 18 October 2018.然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本质上只是一个用于加强国际合作而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难民大规模流动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有赖于难民来源国与收容国在联合国难民署主导下实现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