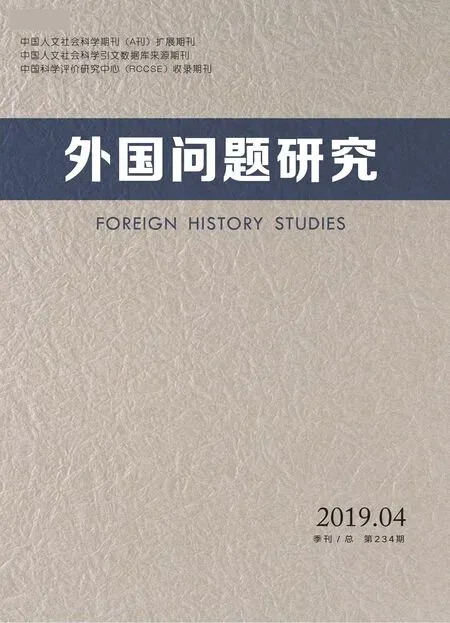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申采浩的东亚认识
2019-12-26金柄珉
金柄珉
(延边大学 朝汉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申采浩(1)申采浩(1880-1936),独立运动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号为丹斋,曾用锦侠山人、无涯生、丹心、韩君、燕市梦人、赤心等。先后任《皇城新闻》(1905)记者、《大韩每日新闻》(1906)主编、《家庭》(1908)主编、《劝业新闻》(1911)主编、《新大韩》(1919)主编、《天鼓》(1921)主编等。参与大同独立青年团、义烈团、无政府主义东方联盟、大韩临时政府议政院等活动。著有《朝鲜上古史》《朝鲜上古文化史》《朝鲜史研究抄》等历史研究著作及《乙支文德》(1908)、《李舜臣传》(1909)、《梦天》(1916)、《龙和龙的对激战》(1928)等小说作品以及《朝鲜革命宣言》《朝鲜之志士》等政论和随笔。是流亡中国的韩国近代著名的独立斗士,也是一位舍生取义的抗日斗士、独具一格的历史学家、夙夜不懈的爱国作家。近年来韩国近代史的研究全方位展开,其中申采浩及其文学的研究业已取得重要进展。随着申采浩在中国创作的文学遗稿(2)申采浩于1928年被捕并关押在旅顺监狱之后,其遗稿转交到友人朴龙泰手中。1949年左右,其遗稿经朝鲜驻北京大使馆转交到朝鲜。1962年,遗稿被发现于朝鲜国立图书馆。安含光、朱龙杰等研究者开始对遗稿进行整理与研究并出版了经过润色的申采浩文学遗稿集《龙与龙的大激战》。之后,《龙与龙的大激战》由日本学者传入韩国,于1977年收录到国汉文混用体的《改定版丹斋申采浩全集》中。拙著《申采浩文学遗稿选集》是笔者在平壤留学时搜集和整理的部分遗稿基础上出版的。及其所刊行的杂志《天鼓》(3)《天鼓》是申采浩于1921年刊行的汉文月刊,据传共出版了7期。崔光植在《丹斋申采浩的〈天鼓〉》一书中编译了其中的第一期和第二期,第三期只收录了目录。的部分卷号陆续被发现,对其流亡中国期间的思想轨迹的追踪以及对其文学价值的评价,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4)主要的成果有: 金柄珉:《申采浩文学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金三雄:《丹斋申采浩评传》,首尔:时代之窗,2005年;金宙铉:《申采浩文学研究抄》,首尔:小名出版,2012年;金宙铉:《申采浩的小说研究》,首尔:小名出版,2013年;崔洪奎:《申采浩的历史学与民族运动》,坡州:一志社,2005年;丹斋申采浩全集编纂委员会:《丹斋申采浩全集》,天安:独立纪念馆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所,2007—2008年等,另有多篇论文。
20世纪的东亚,由于传统秩序的裂变、新的国际关系的建立以及日帝的对外扩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上经历了一次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日帝对东亚表现出赤裸裸的殖民统治野心,导致中国、韩国面临着多重的历史课题:一方面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文化霸权,另一方面还要反对封建主义,实现近代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东亚认识和近代国家想象是在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展开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渐趋形成为主要的话语权力,由于历史现场的特殊性,彼此还交叉在一起。而韩国的东亚认识、近代国家想象又与世界格局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这一层面而言,进一步深入阐明申采浩的东亚认识,有助于深入探讨韩国东亚想象的历史与本质以及东亚的近代精神价值。
本文拟通过追踪申采浩的思想核心,即民族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差异,考察申采浩的东亚认识,即日本认识和中韩关系认识,进而阐明其在韩国乃至东亚现代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一、 申采浩的日本认识及其对东洋主义的批判
申采浩早在19世纪末加入“独立协会”。“乙巳条约”前夕,申采浩毕业于成均馆并有条件就任博士一职(成均馆设有馆长、教授、博士等职务),而他却拒绝安逸的生活,投身于爱国启蒙运动。在担任《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的记者、主编期间,申采浩发表了数十篇爱国政论、史论及传记小说等。他在当时“首尔的评论界”“始终凭借手中的一杆笔,将不可抑制的热情呈现于社会,从而打动民族的心脏”(5)安在鸿:《申采浩〈朝鲜上古史〉序文》,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编:《改订版丹斋申采浩全集》(上),坡州:萤雪出版社,1977年。,“以其犀利的笔锋和雄健华丽的文章震惊世界”(6)申荣雨:《丹斋狱中回见记》,《朝鲜日报》1931年12月19日。。申采浩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植根于以其主体哲学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了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之建构以及正面抗击日帝侵略等内容。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在哲学意识方面,申采浩强调人的二元论存在,主张“精神的、灵魂的存在是真正的‘大我’,躯壳的存在是‘小我’”“‘大我’是永生的,‘小我’是虚假的、死灭的”。申采浩还指出,“大我”是“我的精神、我的思想、我的目的和主义,是自由自在且没有成败的”,并主张,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的英雄们是精神和灵魂永生的“大我”。(7)申采浩:《大我与小我》,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编:《改订版丹斋申采浩全集》(下),坡州:萤雪出版社,1977年,第84—85页。申采浩从这一立场出发,强烈地主张“我”的自主性,进而主张“我”之存在及其历史的属性,以强调民族——“大我”的主体性。申采浩以主体哲学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样体现在他的历史认识当中,从而体现其民族史观。他认为,“历史是为‘我’与‘非我’的斗争之记录”,并指出了“我”的两种属性:“相续性与普遍性”(8)申采浩:《朝鲜上古史·总论》,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编:《改订版丹斋申采浩全集》(上),坡州:萤雪出版社,1977年,第31页。,综上,他是从历史——文化哲学的视角阐明主体的自主发展。
国之将亡之际,申采浩翻译和创作英雄传记小说,旨在“写过去之英雄,以召未来之英雄”(9)申采浩:《乙支文德传·序》,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编:《改订版丹斋申采浩全集》(中),坡州:萤雪出版社,1977年,第277页。。申采浩的英雄传记小说就本质而言是抗日话语,亦即以历史的、文学的方式对日帝侵略做出的回应。“韩日合邦”之后,申采浩的英雄传记小说被列为禁书,申采浩英雄话语之抗日性质可见一斑。此外,申采浩所著《读史新论》(1908年)以及《历史与爱国心之关系》(1908年)等史论和政论也充分地体现了以主体哲学为基础的民族史观。申采浩阐明自己的历史观称:“历史乃爱国心之源泉。故,史笔强,则民族强;史笔武,则民族武。”(10)申采浩:《历史与爱国心之关系》,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编:《改订版丹斋申采浩全集》(下),坡州:萤雪出版社,1977年,第75—76页。
启蒙时期申采浩的日本认识,正是基于上述主体哲学和民族史观而形成。他的一系列史论和政论,体现出他的日本认识及对巨变中的东亚秩序的真知灼见。其日本认识以1919年为界,之前与之后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如果说前期的日本认识更具源于民族史观的英雄话语、国民话语的性质,后期则更具源于民众史观的民众话语、阶级话语的性质。
在20世纪初爱国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像申采浩那样正面对抗日帝的侵略行径与文化霸权的文人并不多见。申采浩与朴殷植、张志渊等堪称韩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先锋。申采浩敏锐地把握世界的发展趋势,从崭新的文化视角和民族立场出发,对日帝的殖民主义本质、附庸于日帝的卖国贼以及被日帝当成侵略扩张之理论依据的殖民史观等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的《抗日声讨文》(11)申采浩:《抗日声讨文》,《皇城新闻》1905年。、《保种保国之元非二件》(12)申采浩:《保种保国之元非二件》,《大韩每日申报》1907年12月3日。、《对东洋主义的批判》(13)申采浩:《对东洋主义的批判》,《大韩每日申报》1909年8月8日—10日。、《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14)申采浩:《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大韩每日申报》1909年5月28日。等政论,对日帝的侵略野心及其本质做出了辛辣的批判。申采浩指出,日帝为了彻底地将韩国殖民地化,采取了种种欺瞒手段,并与韩国签署“乙巳保护条约”(1905年)、“丁未七条约”(1908年)等条约,又主张韩国必须接受日本的保护,两国需加强“亲善”和“协助”,进而主张为“韩国之安全”和“东洋之和平”而共同努力。对此,申采浩揭露日帝所谓“东洋主义”的本质,指出:当下“无韩人利用东洋主义救国者,却有外人利用东洋主义篡夺国魂者,对此应警惕之、慎重而对待之”“以一句‘我族之国,我族主张’作护身符,保全民族”(《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申采浩以此来大声疾呼:韩国人应尽早实现民族的觉醒,以应对亡国之危机。申采浩的上述民族立场与抗日救国思想,折射出其对东亚政治局势以及日帝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政治的敏感性。
当时,附庸于日帝殖民化的御用文人就“保种”与“保国”孰先孰后,亦即保存种族和保存国家孰重孰轻的问题出现过争论。申采浩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指出,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而绝非个别问题,决不可为“保种”而放弃“保国”,并痛斥那些企图以“保种”为借口出卖国家的卖国贼、御用文人们。
同时,申采浩通过批判那些甘当日帝之走狗的卖国社团、卖国贼,阐述了自己的时代认识与日本认识。例如,《日本的三大忠奴》(15)申采浩:《日本的三大忠奴》,《大韩每日申报》1910年4月2日。、《与友人绝交书》(16)申采浩:《与友人绝交书》,《大韩每日申报》1910年4月12日。、《呜呼!成为“国民”“大韩”两报之鹰犬禹龙泽氏的可怜相》(17)申采浩:《呜呼!成为“国民”“大韩”两报之鹰犬禹龙泽氏的可怜相》,《大韩每日申报》1909年6月27日。、《告韩日合邦论者》(18)申采浩:《告韩日合邦论者》,《大韩每日申报》1910年1月6日。、《致使国家灭亡的学部》(19)申采浩:《致使国家灭亡的学部》,《大韩每日申报》1908年3月16日。等文章,对宋秉畯、李完用等“乙巳五贼”“丁未七贼”等卖国贼,表达了极度的愤怒和强烈的谴责。“由于此国家有忠奴三人(指的是‘一进会’会长宋秉畯、‘东亚改进教育会’的赵忠雄、‘大东学会’的申箕善),我不得不哭泣,不得不痛哭,不得不失声痛哭,不得不捶胸痛哭,不得不惊天动地地痛哭。”(20)申采浩:《日本的三大忠奴》,《大韩每日申报》1910年4月2日。早在亡国前夕,申采浩就已经看破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主张自主的外交路线,其犀利的政治、外交眼光叫人刮目相看。他指出:“靠他国的力量实现独立如同掩耳盗铃。如果祈求于美国实现独立,难免会成为美国的奴隶,祈求于法国实现独立也难免会成为法国的奴隶,祈求于英国、德国,其结局是一样的。”(《与友人绝交书》),可见申采浩不仅具有坚定的民族立场,同时,也富有卓越的政治预见。
申采浩还立足于民族史观,对日本肆意歪曲和捏造历史的行径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在《读史新论》中,申采浩对日本学者们所主张的所谓《日本书纪》所载“新罗远征说”和“任那日本府说”给予了彻底的否定。申采浩还痛斥学部当局采用歪曲史实的历史教科书进行历史教育(21)日本的韩国史研究开始于德川时代,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更为活跃。其间出版了林泰辅所著《朝鲜史》。早在“韩日合邦”前,日本的御用学者们就已经开始散布“日鲜同祖论”,还肆意捏造所谓的朝鲜史“停滞论”“后进性论”等歪理。之后,朝鲜总督府下设“朝鲜史编修会”,动员御用学者们编写了一套37卷本的《朝鲜史》(1932—1938),对朝鲜历史加以严重的歪曲,这无疑是为殖民统治而开展的文化掠夺。请参阅姜万吉:《韩国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称这样的教育无法培养爱国心,而只会让韩国人成为“外人之螟蛉”(22)申采浩:《读史新论》,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编:《改定版丹斋申采浩全集》,第127页。。申采浩的上述观点提出于日本的殖民史观刚刚抬头之际,之后日帝便强制合并韩国,继而组织御用学者们大肆鼓吹殖民史观。申采浩对日帝的认识,尤其对殖民史观的认识,可谓极具超前性和洞察力。(23)申采浩还在《朝鲜上古文化史》(1929)、《朝鲜上古史》(1931)等论著中对日帝的殖民史观进行了批判。喜田贞吉、黑板胜美、内藤湖南等日本的御用学者们在20世纪初确立了殖民史观,提出“日本民族混淆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歪理。日帝则依据这些殖民史观捏造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中心说”等。申采浩当时是否已经了解喜田贞吉的“日本民族混淆说”以及通过内藤湖南的《支那论》(1914)、《新支那论》(1924)等论著了解“文化中心移动说”,尚不得而知。然而,他清晰地指出了日帝所谓“东洋主义”的本质——殖民主义的诡计和殖民史观的产物。
1919年前后,申采浩的思想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尤其是“三一运动”的失败、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决裂以及在北京期间的各种体验,使得申采浩对自己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英雄史观等产生了怀疑。他开始广泛地接受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最终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实现了从英雄史观到民众史观、从民族自强论到民众革命论的思想转变。他对日本的认识也随之变得更为透彻和明晰。他对日帝的殖民地扩张及大陆侵略之本质的准确把握,可以说在韩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申采浩指出,日本已经占领韩国,进而必将跨越图们江和鸭绿江抢占“满洲”和图谋蒙古,终将“向南图谋中国,向北侵犯西伯利亚,以实现一日开拓万里的成吉思汗之霸道”(24)申采浩:《朝鲜独立及东洋和平》,崔光植编译:《天鼓》第1卷,首尔:亚研出版部,2004年,第263页。,对人们不知晓日本的这一野心深表忧虑。他还指出,日本“设置抚顺煤矿及满铁以及其他商圈的扩张,已每日增加一千里”,劝告中国人不要被日帝所捏造的诸如镇压韩国的独立运动旨在保护“满洲”的安全之类的谣言所蛊惑。(25)申采浩:《韩汉两家宜加亲结》,崔光植编译:《天鼓》第2卷,首尔:亚研出版部,2004年,第323页。
申采浩进一步阐明,日本不仅是韩国的仇敌,而是整个东亚共同的敌人。因此,申采浩就抗日斗争提出了“民众直接革命论”和暴力革命。申采浩说,日帝一直是“吃我们世界无产民众……尤其是我们东方各殖民地民众之鲜血、肌肤、肉体”的野兽。(26)申采浩:《宣言》,金柄珉编:《申采浩文学遗稿集》,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申采浩的这一思想意识在其为“义烈团”所写的《宣言文》中集中地得以体现,并且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27)申采浩在“义烈团”的《宣言文》(1923)中指出,民众的觉悟并非源自某一神人或英雄豪杰,“先觉之民众为全体民众而成为革命的先驱是民众觉悟之第一道路”。这可谓是申采浩对自己之前的英雄史观的反思。如上所述,申采浩的日本认识体现出从民族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韩国的视角到东亚乃至世界视角的转变。
二、中韩关系认识与“东洋和平论”
毋庸置疑,申采浩对本国的认识是极为清晰和透彻的。他立足于民族主义分析历史和现实,断言道:韩国的亡国,原因在于未能看透日帝的侵略本质以及封建势力和亲日势力的腐败、无能与奴隶根性。申采浩的中国认识较为复杂。在历史问题上,他立足于民族史观强烈地谴责韩国的“事大主义”及“小中华主义”,同时也批判了中国的宗主国姿态,尤其是中华中心主义等。但是他对现实问题态度明朗,尤为明确地主张,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全球扩张下同样沦为日帝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韩两国,理应作为命运共同体,互为主体,共同解决时代所赋予的历史课题。
申采浩的中韩关系认识与其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认识有直接关联。早在爱国启蒙运动时期,申采浩就通过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潮,多维度地接受梁启超的近代启蒙思想,推进了韩国的近代性建构。对于申采浩的小说理论、英雄传记的译介和创作、哲学思想的确立以及近代意识的形成而言,梁启超的影响可谓深远且重大。(28)牛林杰:《韩国开化期文学与梁启超》,首尔:博而精出版社,2002年;金柄珉:《梁启超与朝鲜近代小说》,郑判龙主编:《朝鲜学——韩国学与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此外,申采浩在接受笛卡尔、康德、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的过程中,中国一直是主要文化信息源。申采浩1910年流亡中国之后,其思想发展与中国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若研究申采浩的中韩关系认识,必须对其流亡动机、中国体验、与中国文人的交流等予以详尽的探讨,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本文拟通过申采浩的文学遗稿和《天鼓》中的相关文章的分析,探讨以往研究中尚未论及的问题。
1913年,申采浩在申圭植的邀请下从俄罗斯远东地区来到上海。之后,申采浩开始与中国的进步人士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29)申采浩是在1913年受邀于申奎植,从海参崴(今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上海。当时申奎植是上海韩人社会的中心人物。申奎植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与孙中山、黄兴等中国的重要政治人物们有着直接交往。申奎植在上海设立“同济社”时,申采浩就是主要成员。后来,申奎植与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陈果夫等国民党政要联手,改办“同济社”为中韩联合团体——“新亚同济社”。申奎植在上海创办《震旦》杂志时,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等亲笔题词。可以推测,申采浩是在申奎植的影响下开始关注中国革命并与中国人交往的。1915年以后,除了在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短暂任职时期(1919—1920)之外,申采浩一直生活在北京。在开展独立运动和历史研究的同时,申采浩还撰文投稿给《中华报》等中国报刊(30)申锡雨:《丹斋与“矣”字》,《新东亚》1936年第6卷第4号。并创办《天鼓》(1921)杂志,不仅亲自撰文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还邀请不少中国人投稿。申采浩出入北京大学,开始接触到中国的新思潮,即无政府主义(31)申采浩与北京大学的李石曾、吴稚辉、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们有过交往。此外,据推测,申采浩与李大钊也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尤其是申采浩在北京期间与李会荣、柳子明等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可知,申采浩应该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李大钊、鲁迅等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参见金三雄:《李会荣评传》,首尔:读书出版社,2011年。和社会主义(32)申采浩在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一篇题为《金钱、铁炮、诅咒》的随笔中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指导亿朝民众”的“露骨的诅咒文字”。参见金柄珉:《申采浩文学遗稿选集》,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与中国文人有过多方面交流。(33)《天鼓》第1卷中刊登有两篇中国人的文章:种树的《争自由的雷音》和天涯恨人的《论中国有设中韩亲友会之必要》。可见《天鼓》对中国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申采浩本人与中国文人有所交流。从申采浩的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他当时已经接触过《新世纪》《新青年》《向导》等报纸杂志。申采浩的中国认识集中体现在他对“辛亥革命”“北伐革命”的肯定以及对新思潮的认知等方面。他在文章中称李大钊等为“学界领袖”,否定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肯定冯玉祥等爱国将领,表现出全新的中国认识。(34)请参阅申采浩的文学遗稿《致李守常请求图书阅览的信》《泰山行纪》等。从《致李守常请求图书阅览的信》可以看出,申采浩在1920年左右就兼容并包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当时中国的不少进步人士们也多如此。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北京代表组由李大钊组建。据悉,其9名发起人中有5名为无政府主义者。据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所记,李大钊、罗章龙、刘仁廷和张国焘本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而黄俊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为无政府主义者。参见金三雄:《李会荣评传》,首尔:读书出版社,2011年。从申采浩的《泰山行纪》可以看出,申采浩曾经在泰山与冯玉祥有过交流。申采浩在流亡期间,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格外关注中韩关系,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炮制的所谓“东洋主义”,从政治的和学术的角度深入思考东亚和平问题。申采浩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倡导民众直接革命或进行无产民众革命,这与他在中国获得的切身体验以及对中韩两国关系方面的新认识密不可分。通过申采浩发表在《天鼓》上的《韩汉两家宜加亲结》(第2卷)、《朝鲜独立及东洋和平》(第1卷)等文章,可以理解申采浩对中韩关系和东亚和平的新认识。
申采浩在《韩汉两家宜加亲结》一文中全面阐述对中韩关系的观点,申采浩始终将把中韩关系看作是解决东亚和平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表现出崭新的视角,即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敏锐判断和把握。申采浩在这篇文章中既谈到了中韩友谊的悠久历史,也论述了当下共生共存的迫切性、加强中韩友谊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并指出要改正以往的不足,加强相互了解和研究。申采浩指出,中韩两国江河向往,即朝鲜之江河西向于中华,而中华之江河也东向于朝鲜,“两国之山脉,亦然。有若相即而不欲相离者,此非两国亲爱之表征,而天所命也乎”,(35)申采浩:《韩汉两家宜加亲结》,第319页。并列举众多事例说道;“两国人亲爱互助之迹,其非己见于有史之初者乎”,进而断言中韩两国是“真实永远之友国”。(36)申采浩:《韩汉两家宜加亲结》,第319页。申采浩还强烈地呼吁道:“今试回首于朝鲜之域内,山河依旧,而主人已非,反观中国亦睡狮未醒,强邻四逼为两国人者,能不油然相爱勃然相助,以共臻于同存并茁之域也兮”。(37)申采浩:《韩汉两家宜加亲结》,第319页。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了大敌当前,中韩两国携手并肩、共生共存的历史必然性和迫切性。
申采浩认为,中韩两国要走上共生共存之路,就必须克服过去的不足和错误。如,韩国人“失于太谦”,中国人“失于自尊”;韩国人面对侵略者“婉转求生于其威严之下而不敢拔刃与抗者”,中国人自知“以我自大有妨于文化之增进”却难以改正,并强调:“我愿此后朝鲜人,勿以谦卑,图皮面之交际,中国人,勿以古史之妄笔据作正史而侮于相爱之地也”,(38)申采浩:《韩汉两家宜加亲结》,第320页。他主张,为了推进中韩两国友谊与交流,走上共生共存之路,必须解决历史上的相互误解和自身不足。
申采浩还认为,要实现中韩两国友谊,并实现共生共存,就必须了解对方,而想要了解对方,就要进行研究。申采浩指出,目前中韩虽然是相近的关系,却彼此不清楚对方的国情。他说:中国方面,“中古以还,冠盖往来,比前稍烦,然历史未出”,不晓得“李朝革王氏之命”“甲午乱之前,不知朝鲜有新党”。(39)申采浩:《韩汉两家宜加亲结》,第322页。申采浩列举了诸如黄遵宪、梁启超等曾从事学术或外交事务的人物竟然说朝鲜没有文字,说朝鲜的汉学落后于日本;朝鲜则只认识中国,而不认识自己;只懂得孔子、孟子,而不知道荀子、墨子;只晓得楚汉战,而不晓得洪秀全入京,也不晓得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等。申采浩说:“不能相知,安能相亲,不能相亲,安能相助”“望两国之人以两国之国情互相提供研究也”。(40)申采浩:《韩汉两家宜加亲结》,第322页。这无疑是作为学者的申采浩出于良知的真情呼吁。
申采浩强调,中韩两国国民必须同仇敌忾,“铲除强敌,奠定东洋,又不可离‘流血’两字”“尤当同心相矢,与敌做最后之血战,又刻不可忘者也”。(41)申采浩:《韩汉两家宜加亲结》,第323页。申采浩最后表示:“孙中山曾谓回复韩国之独立,为一缓冲国,然后中国可安,此故明知确论也。”综上,申采浩确实把朝鲜的独立和中韩友谊当作是实现东亚和平的关键之所在。
在此文中申采浩还写道,读到“天涯恨人”所著《论中国有设中韩亲友会之必要》(42)天涯恨人:《论中国有设中韩亲友会之必要》,崔光植编译:《天鼓》第1卷,首尔:亚研出版部,2004年,署名为“天涯恨人”的作者是何人不得而知。文章中高度评价韩国的抗日救国运动称,韩国的仁人志士“不惜牺牲其经血头颅,为东亚历史上放一线光彩”,对于韩国独立,中国不应该袖手旁观,“中韩亲友会,今日应时必要之机关也”。《天鼓》第1卷上还刊登有署名为“种树”的文章《争自由的雷音》,文章称:“朝鲜问题,不是朝鲜人己身的问题也,是关于世界和平最大的问题”,并呼吁中国应该帮助朝鲜的民族自决。申采浩作为刊行人,被这两篇文章所深深地打动。一文。如上所述,申采浩的中韩关系认识是以东亚的和平与人类的共同发展为宗旨,是植根于开放、包容的民族主义和清醒的世界认识基础之上的。
申采浩的东亚和平论在其《朝鲜独立及东洋和平》一文中得到了具体阐述和展开。申采浩在文章中称“西方学者往往以朝鲜为外交上东洋巴尔干”,(43)申采浩:《朝鲜独立及东洋和平》,第262页。并分析指出:巴尔干是克里米亚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朝鲜亦为近代东洋列强冲突的焦点,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均因朝鲜问题而起。但是巴尔干与朝鲜也有不同之处,巴尔干自古以来小国并立,朝鲜则一直是统一国家,巴尔干有拉丁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等诸多民族混居,朝鲜则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巴尔干由于众多民族相互反目而无法形成统一国家,朝鲜如今因为四分五裂而无法崛起,所以才被比作巴尔干。然而,巴尔干拥有自立和自决的民族,朝鲜却没有。申采浩表示,这一点让人悲愤。
申采浩还强调朝鲜的特殊性,并敦促文化的反省。他说:“朝鲜自古曾介居中倭之间,而为之藩瞥,使彼此不相害,此故数千年历史”“朝鲜人之在东洋,其保全平和之功亦大矣”。他还说,朝鲜自壬辰倭乱之后国力与人才匮乏,到了近世,日本因朝鲜问题与中俄开战,“而朝鲜人反闭口结舌不敢有一言云云其间。朝鲜盖已亡于此时也”。(44)申采浩:《朝鲜独立及东洋和平》,第262页。申采浩自嘲道,保全半岛以分割海洋与大陆的两民族实为朝鲜有史以来的天职,如今忘却历史,放弃天职,成为日本的奴隶,其罪甚巨。而列强对日本吞并朝鲜袖手旁观,亦非良策。申采浩认为:“欲言东洋之平和,其上策莫如朝鲜独立”“朝鲜独立,有视乎朝鲜独立运动强度如何及列强之悟解如何”。(45)申采浩:《朝鲜独立及东洋和平》,第263页。
综上,申采浩从政治地缘学、比较历史学、比较文化的视角阐明了东亚的历史及其特征,揭示了朝鲜在东亚和平建构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并阐明实现和平的过程中大国的作用。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连续与断裂的过程。即使是从当下的视角和观点来看,申采浩的上述分析依然具有前瞻性和真实性,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申采浩的东亚认识植根于民族主体意识,而其民族主体意识是与中国梁启超有一定的关联,韩国文人是通过梁启超的文本传播接受西方的主体思想和进化论思想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本土化的。20世纪初亡国前夕,申采浩能够敢于撰文揭露日本的侵略本质,而且洞察日本的大陆侵略阴谋,当然这是与其坚定的民族主体意识分不开的,同时也反映出其进步的时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申采浩的中韩关系认识和东亚和平思想也颇有历史价值,其对来华韩国流亡志士的中国认知和中韩合作的实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申采浩的中国关系认识来自中国的切身体验以及与中国文人的深度交流,尤其是其与接受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思想不无关系。申采浩的东亚认识在20世纪初东亚思想史上具有一定意义,他是在近代东亚思想史上最早正面反对日本的朝鲜侵略和中国侵略,并揭穿日本的东亚主义本质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申采浩的东亚认识不仅反映在其历史研究,而且也反映在文学创作,对此,也需要全面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