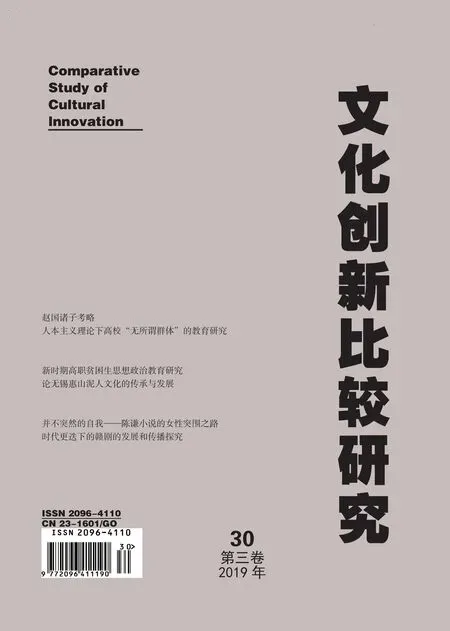从《文学行动》剖析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观
2019-12-26袁周
袁 周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1 何为“解构”
“解构”一词,其对应的英文字母是“deconstruction”,这一词汇用德里达自己的话来说,是来源于海德格尔的“摧毁”一词,即“destruktion”。他曾在一封“致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中明确说道:“当初我选择这个词,或者说它迫使我选择它,我想,那是在《论文字学》一书里。我当时希望把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或‘Abbau’翻译并吸纳过来,为我所用。”[1]虽然我们感觉在词形上“deconstruction”和“destruktion”没有多大差别,即德里达的“解构”和海德格尔的“摧毁”表面上有些相似,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有着显著的差别。
据考,胡塞尔首先在其《经验与判断》中使用“摧毁”一词,后来海德格尔使用“摧毁”对浸淫西方几千年的传统形而上学进行驳斥与批判,目的是让被遮蔽的意义得以彰显。然而,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虽然用“摧毁”一词来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但在其思想观念中,他仅仅是把“存在”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除此之外对其他名称和事物则不予讨论。他想要用“存在”一词指称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事物并认为“存在”是所有事物的基础。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依然没有能够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束缚。因此,德里达在其著作《论文字学》中,赋予“解构”更为积极肯定的意义。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这样说道:“理性支配着被大大推广和极端化的汉字,它不再源于‘逻各斯’——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应当被抛弃。它开始拆毁所有源于‘逻各斯’意义的意义,但不是毁坏,而是清淤和解构。对真理的意义也是如此。”[2]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个关键字眼“清淤”。何谓“清淤”,我认为清除的是思想观念内部的沉疴。何种思想观念?我认为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思想,如果要具体点来说的话,我认为是结构主义。因此,这句话就表明了德里达的“解构”与海德格尔的“摧毁”有着根本性上的不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仅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继承,还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超越。解构区别于其他理论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当我们在进行解构时我们的视角是不断转换着的,而非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解构的首要任务是先要将西方传统思想和理念中被人遗忘和被选择性掩盖的内容揭露出来,与此同时追求二者之间的和平共处。这样一种“和谐互补”的状态,最重要的就是排除所谓的“中心”和“权威”,要将传统形而上学思想中的“权威”打破,如此才能实现德里达所言的“清淤”的结果。
2 德里达解构主义文学观探析
德里达认为:“文学是一个具有某种欧洲历史的概念,可能很多非常伟大的思想文本或诗文本不属于文学范畴。应该是存在着不属于在欧洲16世纪以来的被称为‘文学那种东西’的伟大的书写著作。”[3]在我看来,德里达对文学产生如此深厚的兴趣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点,首先是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是一种书写形式,其次是常常有些具有独特性的文学作品吸引着他不断探寻。当我们了解到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实质之后,我们便能更加清楚地去探寻和掌握其解构主义文学观的内容。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观是其解构主义思想和解构策略的具体化、文学化,解构主义思想也是德里达探讨文学本质问题的强有力武器。
2.1 德里达解构了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抨击的是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言语和文字、真理和谬误、文学和哲学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构成的体系就是形而上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学与哲学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具有代表性一对概念。对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来说,哲学的统治地位和强大作用不言而喻,它不言自明地站在整个对立体系的顶端,相对于文学、宗教等事物来讲,哲学天然地与意义和真理更加靠近,众多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哲学本身就是真理的代表。[4]所以,在德里达看来,颠覆旧的哲学与文学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就是颠覆了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他为解构形而上学这座桎梏已久的大山找到了最关键的突破口。
按照浸淫多年的传统真理观来看,哲学是有关判断和陈述的科学,它描述着这个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客观现象和真实存在,因此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再现了现实世界的诸多方面,并且与真实现象之间具有相互对应和映证的关系,所以在许多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是更紧密的。与之不同的是,文学则常常描绘虚无的、不存在的事物,这些虚幻缥缈的东西或情感在很多情况下既无法被证实真实存在也无法被证伪,这在西方哲学家看来自然与真理背道而驰。从历史上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学家受到尊崇,而将诗的模仿解释为捕风捉影式的活动,无疑开了这一历史的先河。
然而,哲学和文学都要借助于语言(文字)符号进行表述,都是借助符号系统才得以存在,而语言符号本身所具有的隐喻特质,使哲学与文学一样都深深植根于隐喻之中。文学自然是需要依靠隐喻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它借助修辞等手法使自己成为这个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其实哲学也同样要考虑叙述和表达时语言的风格和效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依赖文学性的隐喻、修辞或象征帮助自己说明概念并进行判断,就像一些抽象的概念的说明都必须依赖于比拟和类推一样,哲学的表述是与文学性分离不了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哲学本身就是文学性隐喻的产物,本身是以隐喻性结构为基础的,假如将哲学中的隐喻全部清除,哲学本身将变得一无所有。从这一角度来看,德里达对文学与哲学的解构阐明了一种全新的被消解了的等级关系,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文学语言的地位,将它从以往对哲学的屈从和附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等级关系的颠覆,给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大厦以致命的一击。[5]当处于基础位置的哲学地位被打击和消解时,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
2.2 文学是一种建制
德里达说:“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借助于说明把所有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借助于形式化加以总括。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订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文学的法则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6]德里达用隐喻解构了文学与哲学的边界,可以这样说,德里达始终是站在文学和哲学的边缘处进行写作的。但是,他同样需要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他用符号来表达某种概念,则意味着他无法坚持自己的解构立场,所谓“解构”也将自行解构。如果承认语言符号可以传达确定的意义,则又意味着解构的自动放弃。与其他任何理论一样,这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面临的困境。我们都在尝试用一种理论解释这世间的万事万物,可到最后我们却只能发现其实这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异想天开,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单就从某一角度或某一方面就对文学本质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结果必然是会沦于以偏概全的片面性泥淖之中。我们无法超脱和凌驾于客观现实之上,以“上帝”视角来解释世间万象,不仅理论如此,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种绝对的正确的思维模式,我们都是从某个角度对世界的关注和思考。对此,德里达也早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特意创造了一系列类似“异延”、“印迹”、“补充”等术语,来实现他的解构策略的有效运行。
“文学占据了一个对颠覆的合法性永远开放的位置。这种颠覆性的合法性要求自我同一性永无保障,同时也不向人保证。它还假定一种权力,用以执行地制定法的条文,而这种法是文学可能充任的法。就这样,文学本身就制定法,它在制定法的地方脱颖而出。所以说,在某些确定的条件下,他可以行使语言的立法权力,规避现行的法律,不过它仍从这些法律中得到保护并取得自身发生的条件。这是因为某些语言结构的模棱两可所致。这些条件下,文学能够愚弄法,一方面重复它,一方面又改变它或者规避它。在愚弄法的一瞬之间,文学超越了文学。”[7]德里达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文学这种建制的独特性。它永远处于保持自身和超越自身的差异运动过程之中。也正是文学的这种特性,与德里达的异延的解构理论不谋而合。在德里达看来,文学本身的存在和运作就是解构主义最为有力的佐证。换言之,文学从根本意义上而言是最能代表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是他向“逻各斯中心主义”中二元对立关系发起挑战和抨击的最有力的解构力量。
3 结语
德里达一直是反理性、反权威、反中心论的干将,其解构主义理论思想也在极力探寻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正因如此,德里达的理论都尽量避免结论性的东西,甚至在写作风格上也大多艰深晦涩,让人难以捉摸,《文学行动》便是最好佐证。可实际上,德里达虽然批判理性思维,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抛弃理性的思维,正如他自己所说:“离开形而上学的概念去质疑形而上学的思考是不可能的”,或许这种矛盾是其思想理论上永远的印记与标签,难以消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