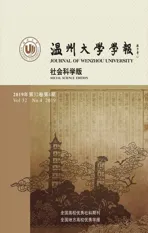传说中的刘伯温:民众生活愿望与社会理想的独特载体
2019-12-22黄涛,徐珍
黄 涛,徐 珍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刘伯温传说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刘基为基础,通过传奇性、神异化的故事情节,将刘伯温塑造成清官、能臣、才子、谋士、军师、风水师等形象。正义,智慧,神奇,是刘伯温形象的三个支点。传说中的刘伯温富于正义感,清廉勤政,惩恶扬善,主持公道,同情和扶助贫苦弱势的民众,为老百姓解难题、做好事,又是老百姓的知心朋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生活愿望和心理需求。同时,刘伯温又是智慧的,他足智多谋,常能出奇制胜,这使得刘伯温传说的故事情节曲折多变,精彩纷呈,富于趣味性,民众的聪明才智在创编和讲述刘伯温故事时得到发挥,听故事的人也在心智上发生感悟、得到启迪。而故事中的刘伯温形象又具备神奇性,他能算卦、会看风水,甚至在有的作品中具有超自然的神奇能力,能预知未来,这使刘伯温故事带有神异魔幻色彩,契合了民间尚存的神话思维和喜欢以幻想奇异故事来消愁解闷、脱离平庸情境的心理。所以民众乐于讲述刘伯温故事,也乐于按照既有的模式创编新的刘伯温故事。刘伯温形象是靠刘伯温传说塑造和传承下来的,又是新的刘伯温传说产生的基础和传播的动力。
现在搜集到的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刘伯温传说有400则左右,这已经是中国历史人物传说中篇数最多的。可见老百姓对刘伯温形象的喜爱程度,也可见出刘伯温形象的巨大魅力。
刘伯温形象的民间演绎,不仅是传统民间叙事文学口头传承的具体展现,更是广大民众结合自身生活处境而做的形象表达。因此,传说人物刘伯温形象的多重建构,其实是民众借助传说故事对自身的生活需求和社会理想所做的一种独特表述。民众讲述刘伯温,其实就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需求和社会理想。本文通过分析刘伯温形象得以形成的民众思想逻辑和刘伯温传说显示出的实用主义伦理观,探讨刘伯温传说所包含的民众思想。
一、精英伦理与民众实用主义生活逻辑的巧妙调和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把思想和实在与生活联系起来,就是实用主义的根本观念。”[1]在哲学领域,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引导人们建构起对真理的认知与思辨。在民间文学领域,人物形象因民俗语境内在的生活逻辑和实践行为而富有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自有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分野以来,这两种文化形态既相互影响和融合,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其中,精英文化由于借助统治者的强力推行、学校教育的有效灌输和文字记载的久远传扬,相对于民间文化占有压倒性优势,从而在中国文化格局中占据着领先性和主导性的地位。所以,可以说,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干是为精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统领的,精英文化并且渗透到民间文化的各个角落。但民间文化在接受精英文化的时候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经常有所保留和调整,有时按照自己的实用主义思路加以改造,有时把精英文化与其它文化按着民众惯有的思路和习惯杂糅在一起,有时按着生活常识和人之常情对精英文化加以反思和纠偏。有些民间传说故事情节设计的颠覆性、人物设定的复杂性及主题彰显的矛盾性,就反映了作为创作主体的民众对精英伦理接受与排斥、认同与反叛的矛盾心理历程。
民众的实用主义伦理观在河北耿村《状元杀和尚》的故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为:从前有一个年轻妇女,在丈夫不幸早逝后,一个人带着独子过日子。久之,她与河对岸庙里的和尚有了私情,常蹚水过河同和尚幽会。这事村里的人都知道,对此闲言碎语很多,她的儿子也知道,深感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儿子长大后进京赶考,中了状元。他回家探亲时,到父亲坟上烧了纸,就请娘进京享福。但他的娘恋着和尚,不愿跟他进京。他就为母亲修了桥,以方便娘过河与和尚相会。后来寡妇去世了。儿子回家为娘办了丧事,就把和尚杀了,并写了一副对联:“修小桥为母行孝,杀和尚替父雪耻。”[2]
这则故事饶有趣味又引人深思。其中隐含着多个悖论。它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是复杂的,其中有儒家的孝道节义思想,又有民众朴素实际的观念。故事讲述儿子为父母尽孝,寡妇应该守节,都体现了儒家礼教思想对民间文化的渗透;但是儿子行孝的方式却是别出心裁甚至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在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儿子的观念中,为母行孝与为父行孝及寡妇应该守节的教条发生了冲突,但他以民众认为圆满的方式解决了这种冲突,将修桥与杀和尚这两种目的冲突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既为母行了孝,也为父行了孝,也表达了对偷情行为的否定和惩罚。这种行孝方式与儒家严格的正统思想是不相容的,即按儒家苛刻的道德观,儿子不应该同情母亲的偷情行为,更不能为母亲修桥。这个故事既表现了儒家思想对民间的影响,也表现了民间思想的朴实性和独立性。故事中状元的行事逻辑体现了民众的实用主义思路,也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伦理观。当然,不通过政府审判处理而私自杀人,是不合法的犯罪行为,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刘伯温传说以刘伯温为主要叙述对象,围绕该箭垛式人物创作的许多故事反映出民众对精英伦理的普遍接受,但也常体现出按着实用主义逻辑对社会主流思想的调整、反思,或者将之与其它支流的文化调和融汇。
《半副銮驾》[3]434-435讲述朱元璋和刘伯温体察民情途中,遇到一位饱受家庭折磨的童养媳。听其遭遇,君臣二人决定帮助她脱离苦海。刘伯温请求皇上赐给她半副銮驾,由青田县官陪送,童养媳乘坐御赐的半副銮驾回了家,重拾尊严,从此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从人物角色的寓意性和象征性来看,朱元璋代表的是权势和地位,刘伯温代表的是贴有主流意识形态标签的精英伦理体系。也就是说真正调解了家庭内部矛盾的是隐藏在人物背后的权势地位和精英伦理体系。调解成功,喻示着民众对权力的诚服,对主流价值体系的信服,这从侧面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民间社会的渗透程度。而民众编创这样的故事,并非要宣扬皇家权势和精英伦理,而是出于对弱者童养媳的同情,借助权势和精英伦理,提高童养媳的家庭地位,压服仗势欺人的恶人。说到底,还是遵循着“好使就行”的实用主义逻辑。民众将自身观念与愿望投注到刘伯温身上,运用其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处世智慧和行为法则,营造出满足其生活愿望和情感诉求的传奇性故事,这其实是广大民众实用主义哲学的形象展现。
在民间社会,刘伯温既扮演着可以协助民众处理社会关系、调试矛盾冲突的益友形象,又充当着民众人生导师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说,他不仅以益友的身份出现,更多时候还会以代表伦理德范的导师身份活跃在民众的精神世界。
《太乙盆》讲述浙江南浔沈万山贫寒时偶然得到太乙盆(聚宝盆)而成为巨富,在刘伯温面前狂妄夸口自己富可敌国,刘伯温劝他低调,他不听劝,后来更加狂妄炫富。刘伯温认为是太乙盆害他变坏了,就用计使皇帝朱元璋借走了聚宝盘,沈万山在讨回太乙盆时惹怒了皇上,被治罪充军[3]224-228。在该传说中,太乙盆成为财富的象征,成为人性欲望的象征符号。对太乙盆的渴望程度寓意着人们对财富本身的追求程度,而民众对太乙盆的功能想象和对宝物拥有者沈万三结局的安排,一方面体现了对荣华富贵的追求,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另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在财富面前的节制自律态度以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观念。刘伯温用计惩治了因获聚宝盆而变得狂妄自大、贪得无厌的沈万山,这种寓意化的情节设置意在表明:民众是认可这种价值评判与行为范式的。他们也认同这种道德标准:做人要安分守己,不要贪念外来之财。这是民众为凸显自身所持有的自律意识和财富观念而做的实用性想象。故事中的刘伯温成为智者与德范的化身。民众试图通过这样的故事来表达关于财富的价值观和处事哲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众生活逻辑与精英伦理之间互动交流的结果。
二、作为庇护神的刘伯温:基于生存需要的民众诉求
刘伯温传说流传地区的广大民众将刘伯温视为逢凶化吉、保平安谋富贵的庇护神。民众对刘伯温庇护神形象的建构与塑造,可以视为其生活需求的意识凸显。陈华文认为刘伯温传说故事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共享式的智慧:“这种共享式的智慧,让刘伯温融入民间,成为民众的形象代表和民间智慧的代言人,人们喜欢刘伯温就相当于喜欢自己,传播这些故事,就相当于传播自己的理想。”[4]于是,民众在刘基真实历史事迹基础之上,根据自身的现实需求与社会理想,不断附会、黏附带有传奇性、神异化的情节。徐世征认为:“人民群众之所以将自己的智慧、爱憎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不断注入刘伯温传说之中,是因为其思想内容同人民群众的情感相通,显示出故事的人民性。”[5]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系统中,普通民众大都处于弱势的边缘地带。为了能更好地存活于世,尽可能消解封建官僚体系形成的精神压力,民众选择用刘伯温传说建构符合其自身生活需求和社会理想的精神符号,借以抵消命运无依感。
而传说中的朱元璋则被建构成一位性格复杂,让人捉摸不透的帝王形象。其中,他喜怒无常、视他人性命如草芥等形象特征被放大,与刘伯温几近完美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圆梦》[6]和《因梦行令》[3]365-366这两则传说充分展现了朱元璋人格的残暴无情和刘伯温的睿智机敏。这两则传说虽然在情节设定和角色定位方面略有差异,但故事母题和行为动机却基本保持一致。即因为一个梦,朱元璋便有了杀人的冲动与念想。这时,刘伯温出面好言劝说,将坏梦解释成好梦,终使结局发生反转:他的介入,让无辜者幸运地逃过一劫,也让朱元璋未失民心。故事显示,刘伯温在调解帝王与民众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至少在民众看来是这样的。对统治者的心思气性,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揣摩不透,而民众眼中的刘伯温却可以。面对统治者这种变化无常的气性,民众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因为稍不留意,自己就有可能奔赴黄泉了。那么,如何消解这种惴惴不安的焦虑感和命悬一线的危机感?答案就是选择刘伯温作为自我意识层面的庇护神,借以找寻超越现实层面的精神平衡。
关于刘伯温智救工匠的传说也凸显了民众试图假借刘伯温协调官民关系的心态。周文峰、郑文清主编的《刘伯温传说》共收录3篇该类传说异文,其故事类型基本一致:朱元璋在新建成的宫殿的不雅举动正巧被工匠撞见,工匠为此性命不保。危急时刻,刘伯温略施巧计,称该工匠是哑巴,最终将此事化险为夷。在该事件中,刘伯温在维护帝王颜面的同时,也保住了这位工匠的性命[3]431-433。民众似乎还不满意这样的结局,于是故事收尾处就有了没嘴王和哑巴殿的扩展性情节。刘伯温不仅让这位油漆工(也称雕花师傅,工匠)免于杀身之祸,还给他带来了人生转机:被朱元璋封为没嘴王,从此荣华富贵享受不尽。而这个大殿也在民间传称为哑巴殿[3]467-468。在民间话语系统中,刘伯温成为调和官民关系的关键人物。他游刃于官僚阶层与民间社会之间,有能力为民发声,为民谋富贵保平安。于是,刘伯温成为民众心中名副其实的庇护神。
刘伯温传说已沿承六百余年,在民间社会流传甚广。刘伯温,这位基于历史真实建构起来的文化人物,在历经数百年的传说演述中逐渐被神化,得到不同历史时期广大民众的持续关注与传颂。最新版本的《刘伯温传说》文集收录的刘伯温传说故事有376则,其可观的篇数及丰富的内容说明,刘伯温传说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在特定的传播区域,它影响着民众的生产生活;反过来,民众惯有的伦理体系和价值操守又会在其叙述过程中融入到该类传说中,经过长期沉淀,最终内化为一种伦理程式和价值范式,继续影响着后来的受众。于是,刘伯温传说的现实价值也在叙述者、接受者的传播互动中得到了夯实。这种内在的叙事逻辑成就了刘伯温的庇护神形象,民众通过文学想象和口头演述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基于生活需要的精神诉求。
三、作为平民形象的刘伯温:为民发声的益友角色
在民众的传说叙事中,刘伯温不仅是一位忠君爱民的贤臣,更是一位可以与他们亲密无间的益友。民众将刘伯温设定和建构为一位敢于为民发声、为民谋福祉、为民排忧解难的益友角色,并在精神层面与其建立了一种相对亲密的朋友关系,把他塑造成一种符合其群体价值观的文化符号。民众把刘伯温建构成平民形象,可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更容易将其融进自己的生活世界。于是,关于刘伯温降生(地)的传说及《天葬坟》传说的演绎,均塑造了一位具有平民特质的刘伯温。作为读书人,刘伯温少年成名,饱读诗书,聪慧机智,如《书凑礼》《千读伯温》《千里求师》①文中所举各篇文章,参见:周文峰,郑文清.刘伯温传说[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等有关刘伯温求学的传说,成为民众教化子女、教育后代的典型故事。作为贤臣,他熟悉百姓生活,了解民间疾苦,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为民发声。他虽居官位,但在立场、情感和趣味上与老百姓是贴近的、相通的,如同百姓的挚友。如《严惩衙役》《刘伯温勇改错案》《巧断黄豆案》及《高安县判案》①文中所举各篇文章,参见:周文峰,郑文清.刘伯温传说[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等有关刘伯温廉政类的传说,显现出他在处理官民关系、调试民众生活矛盾等方面的超常能力。对刘伯温益友形象的设定与建构,体现了民众试图通过这一形象疏导精神内压、超越现实、达成社会理想的努力。
主要流传于浙江青田、温州、丽水等地的《书凑礼》传说,讲的是少年刘伯温好读书的故事。这个传说可分为三个情节单元:一是少年刘伯温与私塾先生对对子,应答如流;二是刘伯温误把老汉玩笑话当真,听老汉说其15里外的天下村亲戚家有许多书,刘伯温马上向该村跑去;三是刘伯温春节去外婆家拜年,错把一叠书当做腊肉放进篮子里当礼品[3]22-23。这则传说中的刘伯温就是一个寻常农家痴爱读书的少年人形象。百姓编出这样的故事,就是把刘伯温当做好读书的楷模,用来教育自己的子孙勤奋好学。
在民众眼中,刘伯温不仅是一位满腹诗书的读书人,更是一位可以为他们排忧解难的可亲可敬的人物。流传于海南地区的《巧断黄豆案》是一则有关刘伯温处理邻里关系的传说。故事里的刘瘦子和王胖子是邻居,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先是王胖子偷吃了刘瘦子家的鸡,却用计将鸡毛和骨头埋在刘瘦子的猪粪堆里。刘瘦子把王胖子告到衙门,糊涂县令判刘瘦子诬告,重打三十大板。后来刘瘦子听说新来了一位知县叫刘伯温,就真的诬告王胖子偷吃了他家的黄豆。刘伯温用巧计识破了刘瘦子的诬告,但并不惩罚他,而是将他的错误与王胖子偷吃鸡的错误相抵消,并劝导说:“几个月以前王家偷刘家的鸡,今天刘家又诬告王家偷黄豆,如此下去,何时是个结局?两家本是邻居,应该和和睦睦,互相帮助才是,何必这样一直仇恨下去呢?偷鸡的事和今天的黄豆案,本县就不再追究了。以后若是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不论谁对谁错,本县均重重处罚。”两家从此和睦相处[3]507-508。这个故事里的刘伯温超出了一般的县官形象,不像县官,而像民间的和事佬、劝架者。作为县官,判案结果本该是对诬告者、偷鸡者做出相应的处罚,比如打板子。但这样处理的结果必然加重两家的矛盾,于事无补。刘伯温不仅用智谋破了案,而且采取了这样的和事佬的处理方式,不仅不做处罚,而且对犯错者也没做道德上的谴责,而是晓之以理,重在调解两家矛盾。如此行事、如此讲话的刘伯温,不仅是富于智谋的,而且是遵循民间处世原则的。他不是为判案而判案,而是为化解两家矛盾而判案。这种判案方式与此前的糊涂县令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刘伯温形象、这样的故事情节,完全出自老百姓的实用主义想象。在老百姓看来,两家的争执本来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偷鸡是小事,诬告的事也不是大事,不能因为这样的错误就把他们当成坏人来重罚,也不必进行严厉的道德谴责。这些行为固然不好,但社会上有这种人品瑕疵的人也不鲜见。只要采取适当措施让两家人不再闹矛盾和相互仇视就是最好的处理结果。这一传说充分反映了民间惯有的世俗观念和处事智慧,也塑造了熟悉民情、平易近人、善于调解百姓矛盾的“和事佬”式刘伯温形象。
在一些故事中,民众还将刘伯温与他们的生活习俗联系在一起,用以解释其习俗的形成原因。江苏等地有年前在门上挂芝麻秸和在院子里撒谷草的习俗,相传这跟刘伯温有关。传说《刘伯温救百姓》[3]461中说,朱元璋疑神疑鬼,大年三十晚上乔装打扮暗访民间,结果起了杀机。危急时刻,刘伯温用家家户户挂芝麻秸的做法,让其收回成命,最终保住了全城人的性命。这是用刘伯温故事对年前挂芝麻秸驱邪避秽保平安习俗的解释。这类故事将刘伯温形象与百姓日常生活建立起密切关系。
四、结 语
虽说传说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但是从文化史角度来看,传说内容蕴含的广大民众的思想情感与历史评价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性是可以作为民众文化史的一部分加以看待和研究的。传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某些人物事迹可以根据讲述者的表达需求进行虚构、嫁接、拼贴,然而这并不妨碍传说内容具备上述真实性,也不妨碍民众对传说故事发自内心的喜爱与“煞有介事”的相信。换句话说,这种传说真实主要来源于行为主体(创作、演述及享用传说故事的社会群体)对传说本身的行为体验和文化感知。民众可以借助传说表情达意,其思想情感和文化指向的真实流露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经过数代民众口耳相传、打磨附会的刘伯温传说,其实早已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且符合老百姓生活逻辑的思想体系与价值标准,它又可以反过来影响民众在生活世界中的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