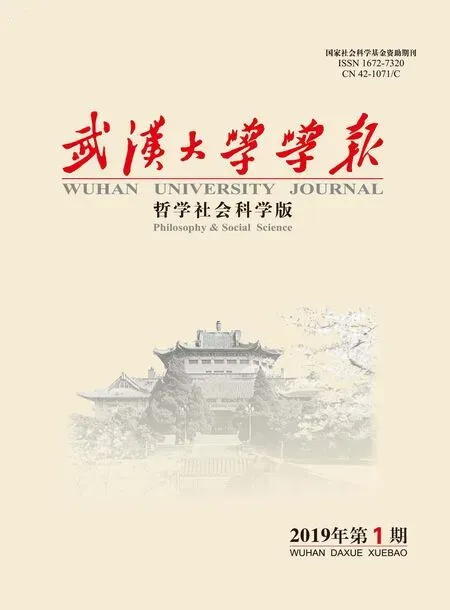“冯氏三藏”序集
2019-12-22冯天瑜
冯天瑜
黄安冯氏两代自 20世纪 20年代起,致力文物收藏与整理,已历 90余年而未辍。藏品略分三类--书画、信札、货币,合称“冯氏三藏”,近年笔者归类编为《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三书出版,并作三序分别绍介“三藏”。现蒙学报盛意,将三序汇为一篇,呈同好者阅览,笔者盼获指教。
一、《冯氏藏墨》序
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
--左宗棠 八言联
先父冯德清(1897-1979),字永轩,以字行,又字永宣,号无尘,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出身自耕农家庭,1923年入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师从文字学家黄侃(1886-1935)。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先父考取为一期生,受业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国学家王国维(1877-1927)、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第一期时尚未到清华),并开始搜集文物,这发端于对梁、王二先生惠赐墨宝及黄侃先生条幅的珍藏。梁启超赠冯永轩六言对联,书宋词集句。其原委略如:1924年春夏,梁夫人李蕙仙(1869-1924)病重住院,先生陪护数月间,从随携《宋词选》中择句,组成联语二三百副。此后数年,手撰集句赠送友朋、弟子。先父1926年(丙寅)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时,梁先生所赠,正是其中之一,上题“永轩仁弟”,落款“梁启超”,记时“丙寅四月”,白文名章“新会梁启超印”,白文闲章“任公四十五岁以后所作”,上联“遥山向晚更碧”(北宋词人周邦彦句);下联“秋云不雨常阴”(北宋词人孙洙句)。同时王国维所赠条幅,撰东晋陶渊明《饮酒诗》之一,上题“永轩仁弟属”,落款“观堂王国维”,白文名章“静安”,朱文名章“王国维”。先父在国学院的研究题目为“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毕业论文“匈奴史”由王先生指导。此外,先父集藏黄侃先生对联多种。梁、王、黄条幅常年悬挂武昌老家堂屋,先父常谈及三先生道德文章,偶议逸闻(留下印象颇深的是:因梁启超乃南海康有为学生,王国维乃逊帝宣统师傅,第二期开始任教清华研究院的陈寅恪戏称诸生为“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另还谈及黄侃先生与其师章太炎先生交谊的种种趣闻),故自幼我们兄弟对梁、王、黄三位有一种家中长老的亲切感。1927年,王国维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其时先父任教武汉,清华研究院在校学生(三期生)向校友发讣告。此讣告连同王先生为先父所开书目纸单,梁、王所赠诗幅,皆珍藏,历经战乱、政乱,不离左右。这大约是冯氏收藏之端绪。
父亲师承王学,致力古史考证及边疆史地探究,素有赴西域考察之志。大舅张馨(号敬丹)20世纪30年代任新疆教育厅厅长,诚邀父亲赴新。其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1897-1970)正以开明面目现世,招纳内地进步文化人士(如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先父也在其列,1935年与先母张秀宜(1901-1971,号稚丹)带我大哥、二哥赴新(二哥过继给大舅,故有张姓)。抵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盛世才委以迪化师范(当时新疆最高学府)校长、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礼遇甚隆。然父亲发现盛阴鸷可怖,遂决计离新。父亲在新疆一年,却集藏颇丰;(1)吐鲁番(古称高昌)文书,署名魏徴的手抄《妙法莲华经》长卷及贝叶经等。(2)清人墨迹,一如清两江总督牛鉴(1785-1858)对联,父亲边批两处;又如画坛“清六家”之首王翚的山水数幅(戊戌变法幕后功臣张荫桓素喜王翚画作,戊戌后张充军新疆,随带王画多幅,存留迪化,为先父收藏);三如左宗棠(1812-1885)率楚军平定阿古柏(1821-1877)、收复天山南北两路时留下的手书八言联,笔力遒劲,气象雄阔。字幅多油迹,估计是新疆人吃手抓羊肉时沾上的,另有左公篆字诗幅及部将给左公多封密札。父亲对盛世才的观察是准确的。父母离新后,大舅张馨被盛逮捕,继遭屠戮(中共驻新代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也被盛杀害,与政治关系不大的赵丹也下狱五年之久),随父亲赴新的四叔入狱,二哥及两位表姐颠沛流离数载。1944年盛世才在新疆的权力被国府削夺,1945年张治中主政新疆,与内地重新通邮,父母才联系上二哥,迎回武汉家中。
1938年秋日寇侵占武汉前夕,先父母举家乘木船东下鄂东山区避难。父母的方针是,生活用品尽量缩减,而藏书及字画、古器物全数带走。乡居数年,先父教过私塾,又在湖北省立第二高中执教,曾任该校校长。因日军反复“扫荡”,家里多次“跑反”(逃难),衣物多抛却,而藏书、文物则始终保存完好,乡间亲友为此肩挑背扛,出力甚勤。在鄂东山区期间,先父与避居罗田的国学大家王葆心(1867-1944)时常切磋鄂东史地及西北文献诸问题,王先生以七五高龄为先父收藏高昌出土文书题写横批。1942-1945年,先父应聘任安徽学院(安徽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筹划举办文物展览,以期激励师生及民众爱国热情。1945年抗战胜利,先父母率全家返回武汉,木船所运主要仍然是藏书和文物。年底先父应聘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所著《西北史地论丛》《商周史》《古文字学》《中国史学史》成稿于斯,此期也是藏品丰收之际。西安乃千年古都,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旧籍、古器物遍于坊间,品真而价廉。先父与相随西安就学的天琪大哥徜徉于街头古董摊前、城郊汉唐陵园,时有收获。大哥追忆诗云:“秦陵探胜,茂陵访古。偶得刀币五铢,幸获未央瓦当。喜不禁,父子且歌且舞。”先父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不满,课堂上下多作批评,被当局戴上“红帽子”,常有“职业学生”尾随、盯梢。先父遂于1949年初离开西北大学,转任湖南大学教授。其时内战正酣,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先父离湘回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父任湖北师专(旋改为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得以较系统地从事楚史研究,收藏古籍文物的情志有增无减。20世纪50年代,余念中小学时,常见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长衫客(大约姓高)造访武昌老宅,其人总是挟着一个灰布包袱,神秘兮兮地走进父亲书房,闭门良久,出来时多半只拿着叠成小方块的包袱布。显然,这位来自汉口的古董商又在父亲处推销了几本古籍,或几幅字画。家中的衣食照例是简朴的,且不说我做老五的历来穿补旧衣装,就是父母也没有一件完好的毛线衣,工资半数用在购置书籍、古董上。家人早已对此视作当然,节俭是生活常态。
父母于20世纪60年代初退休,归武昌矿局街老宅所在居委会管辖。1966年“文革”爆发,居委会“扫四旧”之狂热不让于学校,老宅被抄家数次,颇丰厚的藏书一再遭扫荡,其中一些善本、孤本或被撕毁,或充作街巷妇人糊鞋样的材料,父亲作为楚史研究先驱,其撰著多年的30万言楚史稿本(1960年前后余曾协助抄誊)也不知所终,呜呼哀哉!为减少损失,我们通知母亲任职多年的湖北图书馆,该馆派人以麻袋装、板车运方式从冯宅抢救部分藏书(省图书馆还派汽车到街道办事处拖走一部分抄家后堆放那里的冯家藏书)。父亲踉踉跄跄尾随板车走了好长一段路。今之湖北图书馆特藏部还有若干盖冯氏印章的古籍,它们是逃过抗日战火、“文革”浩劫的幸存者。1996年,笔者为萧放、孙秋云、钟年等君著《中国文化厄史》作序,追述中国历史上惨烈的“书之十厄”,而家中藏书的遭际,过电影似的在眼前一一闪现。比藏书幸运的,是字画、信札与古钱币,因其一向放在七八只旧箱子里,置于堂屋天花板之上的漆黑空间(无固定楼梯,须搭临时梯子上去),抄家者未能发现。这样,字画、信札、古钱币大部分得以保存。
先父收藏书画,时代较久远的是唐人佛经抄本及明代画作,主体乃清朝、民国文士手笔。
字幅(包括条幅、扇面)
最早当为签署“贞观六年魏徵”的唐代手写佛经长卷。其他挥毫者是:
1.文士书家。明清之际诗人查士标(1615-1698),礼部侍郎、诗人沈德潜(1673-1769),康熙五十三年状元、书法家汪应铨(1685-1745),刑部尚书、乾隆“五词臣”之一张照(1691-1745),“诗、书、画三绝”郑板桥(1693-1765),乾隆“五词臣”之首梁诗正(1697-1763),其子、书法与刘镛齐名的梁同书(1723-1815),与翁方纲、刘墉、梁同书并列的王文治(1730-1802),古文家、桐城派主将、擅草书的姚鼐(1731-1815),“清代四大书法家”中的两位:翁方纲(1733-1818)、铁保(1752-1824),思想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焦循(1763-1820),与袁枚齐名的诗人、诗论家、书画家张问陶(1764-1814),嘉道间内阁大学士、总成《十三经注疏》的一代文宗阮元(1764-1815),道咸间文学家、篆刻家吴熙载(1799-1870),朴学家、章太炎老师俞樾(1821-1906),创内圆外方“张字体”的张裕钊(1823-1894),文史学家、《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1830-1894),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等并称“清末海派四杰”的蒲华(1839-1911),戊戌变法参与者、上海强学会发起人、金石学家黄绍箕(1854-1908)等等。
2.重臣兼书法妙手。嘉庆间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那彦成(1763-1833),道光间两江总督牛鉴(1785-1858),咸丰同治光绪间执掌军政的曾国藩(1811-1872)、曾国荃(1824-1890)兄弟,左宗植(1804-1872)、左宗棠(1812-1885)兄弟,李瀚章(1821-1899)、李鸿章(1823-1901)兄弟,湖北巡抚胡林翼(1812-1861),兵部尚书彭玉麟(1816-1890),荆州将军巴扬阿(?-1876),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沈桂芬(1818-1880),兵部尚书毛昶熙(1817-1882),闽浙总督何璟(1817-1888),光绪间出使英法大臣、较早倡导宪政的郭嵩焘(1818-1891),军机大臣、藏书及金石收藏家潘祖荫(1830-1890),戊戌变法中坚人物、同光两代帝师翁同龢(1830-1904),湖南巡抚、金石学家吴大澂(1835-1902),光绪间出使美、西、秘大臣张荫桓(1837-1900),状元外交官、赛金花的丈夫洪钧(1839-1893),书法名家、宗室中少有支持维新变法的盛昱(1845-1899),管学大臣、中国近代学制奠基人张百熙(1847-1907)等等。
顶层设计作为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在时间、空间的展现形态和发展路线的整体设计,是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完成的重要方法论,对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应用需求、能力要求、技术体制、实施途径等提出整体构想。系统性地谋划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与城市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整合建设,统筹强化基础设施、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产业等要素的整合与协同建设,协调智慧城市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规划等规划的内容与项目布局建设。建立顶层设计引领发展的机制,将顶层设计作为智慧瓷都年度建设滚动规划的重要依据,不断围绕顶层设计和滚动规划完善各应用系统的建设。
3.清民之际学人、政要。历史地理学家、书法家杨守敬(1839-1915),诗人樊增祥(1846-1931),保路运动领袖、书法家刘心源(1848-1917),戊戌变法主将康有为(1858-1927),同光体诗派代表陈三立(1853-1937,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民初江苏都督、故宫博物院早期负责人庄蕴宽(1866-1932),清末军机大臣、民国总统徐世昌(1855-1939),史学家屠寄(1856-1921),主讲两湖书院、辛亥后以遗老终守的梁鼎芬(1859-1919),清末湖南布政使、后为伪满洲国总理、书法家郑孝胥(1860-1938),张大千的两位老师:晚号“梅道人”的海派画家曾熙(1861-1930)、晚号“清道人”的书画家李瑞清(1867-1920),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提调程颂万(1866-1932),甲骨学开创者罗振玉(1866-1940),国学大师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王国维,近代出版业先驱、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1867-1959),清末湖北宪政派代表之一、民初湖北省省长夏寿康(1871-1923),清末宪政派领袖、民初众议院议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汤化龙(1874-1918),辛亥革命后四川副都督、广东省省长朱庆澜(1874-1941),民国元老、书法家于右任(1879-1964),北洋时期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学者章士钊(1881-1973),理学大师马一浮(1883-1967),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邓家彦(1883-1966),文字音韵学家黄侃(1886-1935)等等。
绘画(立轴、横幅和扇面)
此为先父集藏重点之一,然一批精品(如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画作)于十几年前损失,令人痛惜。作品尚存的有:明代弘治-万历间画家陆治(1496-1576),清初画家笪重光(1623-1692)、黄云 [与石涛(1642-1707)为友],“清六家”之一王翚(1632-1717),清中叶画家钱载(1708-1793)、朱筠(1729-1781)、奚冈(1746-1803)、刘德六(1805-1876),有“画石第一”之称的周棠(1806-1876),军机大臣、擅山水画的张之万(张之洞族兄,1811-1897),与任伯年、吴昌硕齐名的海上画派吴公寿(1823-1886)、朱偁(1826-1900),清民之际画家贺良朴(1861-1937)、与齐白石并称“南黄北齐”的黄宾虹(1865-1955)、人物画家王震(1867-1938,号白龙山人)、艺术教育家陈衡恪(1876-1923,陈寅恪兄)、逸笔超迈的陈曾寿(1878-1949)、兼通中西的黄山派代表刘海粟(1896-1994)等。古文家、以翻译西洋文学名作著称的林纾(1852-1924,字琴南),山水画也十分了得。一些书画、篆刻获于先父友人,如国学家王葆心,沈肇年(1879-1973),篆刻大家唐醉石(1886-1969),文史学者关百益(1882-1965),文学史家、钱钟书之父钱基博(1887-1957)、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1966)、思想史家刘盼遂(1896-1966)、文化史家吴其昌(1904-1944),藏书家徐恕(1890-1959,字行可),“画坛三老”张肇铭(1897-1976)、王霞宙(1902-1976)、张振铎(1908-1989),画家侯中谷(1890-1955)、薛楚凤(1902-1976)、赵合俦(1902-1982)、徐松安(1911-1969)等。笔者少时多次在家中迎谒耄耋之龄的唐醉石,叹服其制印的古拙、清雅,成年后方知唐老是西泠印社健将、东湖印社创始人;接待湖北文史馆首任馆长沈肇年;王霞宙曾来宅茶坐,谈艺颇精;作品参加民国首届美展的侯中谷盛年辞世,常被先父念及,其风骨遒劲的画作常悬冯家厅堂;薛楚凤曾任冯玉祥秘书,乃先父至交,画作清峻古雅,题字常带机锋。
笔者自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研习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史志,与学者、美术家优游艺文,40年来除购置张大千(1899-1983)等作品外,所获书画乃多位师友所赐:画家虚谷(1823-1896)、陈作丁(1922-2010)、汤文选(1925-2009),书法家黄亮(1903-1987)、曹立庵(1921-1991),作家茅盾(1896-1981)、姚雪垠(1910-1999),文学史家程千帆(1913-2000),国学家饶宗颐(1917-2017),享寿最高的辛亥革命志士喻育之(1889-1993)等,健在如周韶华、欧阳中石、陈立言等所赠墨宝。
“书画鉴藏千古事,山川吟啸六朝人。”金石、书画之学,创于宋代,清代此学复兴,其收藏、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可谓精深博大,先父承其绪。少时我常听其谈及:一旦得宽余,将著文介评藏品,以方便后人利用。父亲的努力,散见于若干字画的眉批、边批,还可见于与先父切磋文物内涵的沈肇年、钱基博的遗墨。1957年后灾祸迭兴,先父母晚境艰难,上述工作中辍。半世纪后吾辈重理旧物,续接先人未竟之业,常发水深难测之叹。藏品作者生平材料,名士易得,知名度未彰者则颇费周折;考析赠受关系,辨读行文、题签(甲骨文、金文及篆、隶、行、草、楷)及印章(名章与闲章,朱文与白文,引首章、压角章、鉴藏章等),抉发书画信札意义内蕴,更须用心费力。经一番探幽致远,也确有收获,一些作品的美学价值、史料价值渐次昭显,若干文化史中不可忽略人物(如焦循、张问陶、王锡振、蒲华、程颂万、曾熙、李瑞清、马一浮、林纾等)的书画,原来在家藏中隐而未显,今次得以“昏镜重磨”,每有“发现新大陆”之快感。至于收藏故事,当年先父偶有谈及,今日追忆、揣摩,参照藏品及相关文献提供的线索,每能打开新的认知门径。编纂藏品的一项工作,是追溯书画所涉诗文出处。在此一过程中,发现书画所题诗文与传世刻本多有差异,而且书家、画家变通的文字,往往更为生动或更为准确(当然也有不太妥当的改动)。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为书家、画家当年见到并引述别的版本;二为书家、画家有意变更原文(这种可能性更大),这也是书家、画家的一种再创作。本书并非考据学专著,主要功能是赏析书画作品,为了不影响阅读节奏,各条释文很少列出书画题写诗文与传世刻本的差别,然这种比勘考据工作,从版本学、诠释学视之,自有其学术价值,将另作专文阐述。整理昔贤遗墨,须国学知识(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宗教学以及书法、绘画、文字、金石诸专学)的综合运用,并仰赖历史洞察力和艺术体悟力。老来事此,可以说是对少时身处文物丛中而未能系统研习的补课。名士文墨,历来有赝品、仿作渗入,故“辨伪”是书画之学不可或缺部分。我们在整理藏墨时,对一些历时久远而又署以大人物名号的作品特别用心反复研讨,不敢贸然定论。如题签“中书令臣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贞观六年二月十六日”的佛经手写字幅,经认真考辨,特别是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获得的唐人抄写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作比较,发现二者的材质(硬黄纸)、书写格式、字形都十分相近。敦煌、吐鲁番(古称高昌)文书除被斯坦因等西方人运走外,尚有散留民间者,先父1935-1936年间在新疆以“编译委员会委员长”身份获得一件,当在情理之中,自此他将其视为最重要的藏品,多次邀学者题跋:抗日战争期间在鄂东,国学大师王葆心撰“高昌出土唐人写经”横幅;在安徽,1945年文物学者孙百朋作跋;抗战胜利后任教西北大学,1947年请西北大学历史系关百益教授题词;回武汉后,1953年又有篆刻大家、西泠印社重镇唐醉石题词。这些精研文物的学者都仔细观摹该写经,认定其可靠性。综合以上,可判断高昌出土墨绘纸本为唐人写经,是冯氏藏墨中历史最久远的一件。笔者近年又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先生、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胡戟先生审阅,他们认定为“唐物无疑”。有些遗墨的真伪,经历“肯定-否定-肯定”的辨正,如题签“姚鼐”的草书诗幅,初以为是姚作;后据压角章,推断是“同里后学”手摹姚作;进而对印章“臣鼐私印”“姬传”反复考辨,又对以珍珠白在青笺上撰写草书与传世之姚鼐书法比照,基本认定此件系姚之手笔,压角章乃收藏者补盖之闲章。另如文尾“子瞻书”的字幅,曾以为是后人冒充子瞻(苏东坡)的赝品,经反复查览比对,确认此件乃清末顾印愚(字蔗荪)对苏子瞻“元祐二年二月八日”《跋画苑》一文的抄件,以往我们忽略的顾印愚所钤名章“蔗荪”可证此情节。这些推测是否确切,入选藏品中是否另有赝品未能识别,切望方家法眼明辨,并不吝赐教。
展示的藏品,由仅有公教薪水收入的学人在长达半个世纪间,孜孜不倦地访缉,节衣缩食地购置,终于集腋成裘,蔚为艺文大观。藏品又遭逢战乱、政乱一再袭扰,历尽坎坷方得以部分保存,它们遭遇的灾厄和今日得到的善待,以一粒水珠映照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曲折与悲壮。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实力的提升,时下进入文物及艺术品集藏兴盛期,“淘宝”“鉴宝”已成热门话题。这一轮次收藏热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文物及艺术品的市场售价被格外关注、并极度放大于台面,人们言及藏品,津津乐道于拍卖价几万、几百万或几千万(近年甚至出现某一画作数以亿计的售价),而对文物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的认知则退居次席。以上种种,似与笔者自幼的闻见大相异趣:先父每有收获,评议的多是文物何等美妙、包蕴的史料价值何等深邃,从未言及某件值钱若干,将来会增值多少倍。对于以下两种状态我们充分理解:(1)权力及资本拥有者往往青睐文物,中外帝王(如乾隆皇帝、法王路易十四、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等等)以及财团、金主,不乏文物收藏巨擘,构成文物的会聚中心;(2)在商品-货币发达时代,文物及艺术品判定含金量,是其价值的一种毋庸回避的衡量标尺;文物及艺术品论价授受,合理合法,无可非议;对文物及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培育,是集藏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然而,笔者又确信:(1)文物集藏并非只是寡头专属,而当有民众参与、欣赏、利用;(2)文物及艺术品首先是文化载体,不应降格成金钱等价物,如果集藏的主要目的衍为金钱贮备与增值手段,藏品被铜臭淹没,实在是集藏事业的异化。中国现代收藏大家张伯驹(1898-1982)、王世襄(1914-2009)们将文物文化价值置于金钱之上,不惜破己财以护文物,倾力于保存、弘扬民族文化瑰宝,彰显其存史、教化功能,指示了集藏事业的正道,我们对其表示最大的敬意,并愿追迹后尘。友人何祚欢称,收藏事业应多些文化,少些商业。余深以此议为然。有人询问:冯氏藏品值金多少?余无以回答,因为自己的文物市场知识几近空白,也于此难生兴趣,引动关注的只是文物的史料价值和艺术魅力。近40多年来,余不时于清夜翻检图籍、把玩藏品,沉醉于历史现场感,在与先贤对话、相与辩难之际,思逸神超,偶尔迸放出意象奇瑰的火花,这可能是自己研习中华文化史的一种知识补充与灵感源泉。古哲今贤的书画可供观摹把玩,然其作为形下之“器”,又包蕴形上之“道”。于学术有兴趣者既可以从中获取细节性史料,也可借以领悟天道自然与人生哲理。本书收入的历史人物的字幅,多未收入诸人文集,故这批藏品系罕见甚至仅见之文献,包藏难得的历史文化信息。美术爱好者可以从观摩书画真迹中得到构图、笔法及题旨启示,本书收入先贤墨迹,可谓丹青溢彩,不乏艺术上的范本法帖。而林纾、姚雪垠、程千帆、饶宗颐及先父母等前辈学人,并非专业书画家,然墨迹所展示的功力,实在令我辈汗颜。观其墨宝,也有敦促今之学者提升人文素养(书道、文采仅为其一)的意义在。而我们兄弟于藏品的认识价值、美学价值之外,还能透见先父那通常是蔼然仁者、偶尔也如怒目金刚的形象,记忆起他为余讲授中华元典时的滔滔议论,以及母亲在一旁倾听时的慈祥目光。惠赐墨宝的多位师友,联翩乘鹤西去。睹其遗墨,宛若再识音容笑貌,聆听清教,不胜追怀之至!
2015年5月24于武昌珞珈山寓所
二、《冯氏藏札》序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杜甫《春望》
“信”,含消息、函件之意,别称书、缄、鸿雁、华翰等。“札”,本指古代用来写字的小木片,引申为公文及书信。造纸术发明前,我国的书写材料,早期为甲骨、石料、金属(如青铜器),因其笨重,又采用纺织品(称“帛”)、木片(书写后称“札”)或竹片(书写后称“简”)。东汉以降,纸张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但信函仍习惯性地称“书札”“笔札”“手札”,又称“书简”“尺牍”(牍,一尺长书写文字的木版,引申为公文或书信),更通常的称呼是“信札”。信札是人类发明文字后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我国现存较早写在纸上的书札,是西晋陆机(261-303)的《平复帖》。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为了祈求友人病体康复而致信问候,此即《平复帖》(“平复”即康复),是存世较早的名人书法真迹,也是存世较早的纸本书信(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魏晋时期,书札应用普遍,不仅有传递信息的实用功能,而且透现文学及思想成就,书法艺术也得以展示。魏晋士大夫崇尚玄学清淡,讲求风度文采,其往还书信,文辞简洁渊雅、书法劲拔潇洒,钟繇(151-230)、王羲之(303-361)、谢安(320-385)等文豪都是信札高手,文义、书法并美。此后千余年间,这种信札传统流播于文士,并影响民间,成为中华文化典雅风范的一种表现,当为今人继承与发扬。至唐代,信札广用,并出现专门用以写信的纸张。明清以来,特别是民国年间,信纸愈益专门化,出现所谓“笺纸”(“笺”为制作精良、尺幅较小的纸张)。笺纸,也称诗笺、信笺,指以传统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为文人雅士传抄诗作或信札往来的纸张。民国时著名的“十竹斋笺”“芥子园笺”,上有梅兰竹菊等隐画,或印有吴昌硕(1844-1927)、齐白石(1864-1957)、陈半丁(1876-1970)等人作的笺画,十分清丽。本藏札多以笺纸书写。信札收藏,或重其人(历代名士书信入选),或重其书(笔法雄健的书信入选),或重其文(富于文采的书信入选)。本藏札有兼备三长者,有特具一长或二长者、其百余通,主要是先父冯永轩于20世纪20-60年代收藏的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文士、政要的书札手迹,另收有先父友朋函件以及笔者师友来信。其编目为:文士论艺、湘淮谈兵、左营密函、花溪札丛、新疆政书、冯氏飞鸿。
文士论艺
湘淮谈兵
清咸丰同治光绪间形成湘系、淮系两大军政系统,权倾一时。湘淮两系多儒将,往还书信切关大政,其文章、书法皆有可观处。本书收集诸函,以致信者齿序排列,先后有--楚军统帅左宗棠之兄左宗植,函中左宗植恭贺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由湖广总督转任浙江巡抚,并感谢对其子澂的训诲;湘军主帅曾国藩致函李鸿章之弟李幼泉(1834-1873),详论攻剿捻军诸务,是一篇有史料价值的军政文书,其正文当是曾国藩口述,由文案用工整楷书撰写,信尾长篇批文,系曾国藩亲笔,边款“一等侯曾”。湘军又一主将、咸丰间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1812-1861)致李续宾(1816-1858)书,论及在湖北与太平军苦战情形及湖北崇阳民心向背的状况,称崇阳“四次造反,遍地皆贼,贼胜则举国庆贺,贡献不绝;贼败则士子掩卷而泣,农夫辍耒而叹。人心至此,尚忍言哉”!民心向着太平军,故胡林翼力主“宜杀”。这是清方高级将领关于当年人心向着太平军的记述,也坦白了清军滥杀的事实和出发点。湘军重要将领彭玉麟(1816-1890)于战争之隙致函王闿运(1833-1916),请其为先慈撰文纪念;湘军将领何璟致弁嗣龙函中详介汉水沿线炮船数量及部署,此皆为湘系要员对太平军、捻军作战的记述。湘军主将曾国荃致祁寯藻(1793-1866)二函,议及与太平军的战事,第三函致其兄曾国藩,落款署“一等伯曾国荃”,显系湘军攻取天京、曾国荃封伯爵之后;第四函致李昭庆,议与捻军作战事,当在1867年主持湖北剿捻之际。本目还包括淮系主帅李鸿章、要员沈桂芬、丁日昌(1839-1893)、张荫桓等论军政事务的信函。状元出身的史学家、外交家洪钧(人们对他的另一身份更熟悉:赛金花的丈夫)青年时代给李瀚章写信,言及光绪年间汉水航道情形。可见光绪间淮系影响渐超湘系,士子投效淮系者多矣。本目另附朱庆澜(1874-1941)、汤化龙(1874-1918)等清末民国政要书信,可略观其与曾李时代的联系与变异。
左营密函
19世纪70年代,清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淮系主持人李鸿章主张放弃西北塞防,集中力量于东南海防。此时湘系主帅曾国藩已经辞世,湘系另一代表、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坚决反对放弃新疆,力主塞防、海防并重,并以高龄挂帅,率楚军远征新疆,平定沙俄支持的阿古柏叛乱和回民起事。有诗纪其卫疆业绩:“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先父冯永轩景仰左公,20世纪30年代在新疆工作时,集得左公条幅和诗笺手本,并汇集左公部将致左公军情密札多通,此为研究当年西北卫边战事的宝贵史料。刘祥汇1874年(左宗棠以钦差身纷出征新疆的前一年)密稟左宗棠,介绍西北地情民状,特别逐个汇报西北军政官员的政绩品行,这显然是左宗棠出征西北前夕了解当地民情官风的一种举措。曾任甘南各军提督的刘明灯(1838-1895)致函左宗棠,言及光绪元年甘肃发生的与“贼”之骑兵交战情形,这是关于西北回民起事的记述。湘军名将王德榜(1837-1893)时在广西,他致函左宗棠,言及广西军队北上之际,遭遇两粤边境战事牵制,一时难以挺进西北。满洲白旗人额尔庆额(?-1893)率吉林、黑龙江马队参与左军平定新疆,其致左帅信札,言及入疆之初的情形。以后额尔庆额部收复吐鲁番、迪化(今乌鲁木齐)。左军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史的大事,西北领土得以保存实赖此役,而左军将领致左宗棠密札是这场战事的片断记述,有史料价值。
花溪札丛
花溪札丛在先父藏札中数量最丰,此次选取42通,反映晚清湖北教育文化在内忧外患中逆势成长的情形,可见清末社会生活之侧面。赵章典(1826-?),字花溪,湖北江夏人,生而磊落,交游甚广。往来最密者,为“姻如弟”屠仁守(1832-1904)。屠系湖北孝感人。咸丰二年(1853),太平军攻破武昌,赵家被难九人,赵章典以身救父,得免遭杀戮。屠仁守信中也记述自己“两次为贼所得”侥幸逃脱的窘境,目睹了家乡孝感从繁华城郭化为灰烬的瞬息巨变,他描述的“英、法觑直沽,苗、回乱云贵,骷髅恣肆于蜀中。豫州捻匪号数十万,屋无不焚,人无不掳”,“田园寥落,骨肉流离”,正是咸丰乱局的写照。屠仁守自谓“遗落世事,厌弃词翰,懒于治经”,但又终能自振,以为“人不可不识忧愁,亦不可竟为忧愁缚。睁开眼孔,则天地大;竖起脊梁,则山岳凝”。凡此种种,皆是乱世文人千回百转的心态投射。屠仁守与赵章典也论及时事,如左宗棠收复新疆,称誉“左侯真天人,必令当轴处中,乃能运筹全局”,又指出“新疆虽有红旂之捷,善后尤为不易。外人窥伺已久,长蛇封豕,非伐狐搏兔之技可了”,指出新疆善后治理的艰难,实为睿智卓见。赵章典作为湖北文坛名宿,与友朋往来论艺。如广东南海人谢朝徵著《白香词谱笺释》《郢中酬唱集》,来信商讨校书误字、赐助刊印诸事,体现清人文集流通之状貌。又如湖北恩施人樊增祥(1846-1931),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在汉江行后,作诗八首,录奉赵章典教正。樊增祥的这八首诗,清光绪十九年渭南署刻本《樊山集》中仅收录一首,且与信札手书有数处异文,如信札手书“短袂西风里”句,刻本《樊山集》作“旅袂西风里”,显然优于刻本。至若其余七首,刻本均失收,弥见这件信札手书的珍贵。本目还收录不少地方要员和社会名流的通信,如浙江盐使、江西布政使黄祖络(1837-1903),江南道监察御史陈懋侯(1837-1892)、安陆等府知府陈建侯(1837-1887)孪生兄弟,曾国藩幕僚、湖北光化县知县胡启爵(1838-?),福建书法家蔡敦益(1853-1895)等。通信内容涉及广泛,从私人契据、饮食起居(如胡启爵屡言为痔患所苦),到子女教育、时事新闻,悉皆言意谆谆,深自肺腑。赵章典于咸丰六年(1856)“取二三交好所往来书札文词”,汇为一卷,名曰《同心言集》,取《周易·系辞》“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语,共计56篇,辑录与屠仁守、王嘉榖等人酬唱及研讨诗画之道的书信。本册札丛所选书信悉为《同心言集》所未收录,可作为《同心言集》稿本的姊妹篇,反映赵章典与晚清时贤的切磋往来。
新疆政书
新疆有“亚洲心脏”之称,晚清至民国,国家风雨飘摇,新疆成为中外各种势力的角逐之地。本目受信的中心人物张荫亭,民国创建初期安徽大通绅商代表,皖系早期核心成员,生卒不详,民国初年为新疆军事首脑之一,本册有多位新疆政要致函张氏,多称其“旅长”。致信者以齿序排列如次:潘震(1851-1926),安徽当涂人,辛亥革命后,任新疆省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后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汪步端(1858-?),安徽当涂人,民国建立后塔城首任道尹;朱瑞墀(1862-1934),安徽人,1913年在新疆古城营务处负责军需工作,后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陆洪涛(1866-1927),江苏铜山人,后任甘肃督军、甘肃省省长。陆洪涛虽然不是安徽人,但出身皖系,其他三人均为安徽人,因此他们在给张荫亭的信中均自称“乡(愚)弟”。潘震信函用“新疆国税厅筹备处”笺纸,汪步端称“俄乱方殷,边防吃紧”。辛亥革命后,朱瑞墀与张荫亭“同事北廷”(北洋政府),时有乡关之思,而又相互慰藉:“我先在省想蒙督军慰留,不许出省,而南疆之盼望者尤多,时局艰难,尚望免任其难,共维大局。关内人心不靖,旋里一节,暂可不必作此计议也。”朱瑞墀称“喀什文武、中外历前任,久不相睦,此中细节,一言难罄,若两方面有一方能识大体者,决不至于如前之决裂。弟到任后,比即以中外多事,推诚相布。嗣后均当确守范围,和衷共济。近月以来,所有一切,尚称相安”,此系辛亥革命前后新疆喀什政局的记述,可资民国史参考。
陆洪涛与段祺瑞(1865-1936)为同学,作为陕甘总督陶模(1835-1902)的随从到甘肃,任甘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辛亥革命后,陆洪涛部被编为振武军。1915年3月,陆洪涛为陇东镇守使,成为甘肃的实力派。同年12月,袁世凯(1859-1916)称帝,孙中山等兴师讨袁。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1892-1925)、曹世英(1885-1944)诸人积极响应。陆洪涛致信张荫亭:“团长胡景翼、曹世英诸人,皆以与陈督军(树藩)交恶,先后称兵占据渭北、泾原各县,屡攻省城。而卢匪亦以不得志于甘,由陕北鄜州、保安走耀县窜三原,与渭北各股联合,近日布满乾、醴、兴、武、盩、鄠、岐、郿等处,众已数万。”反映的正是当时的史实。陆洪涛同时提到“西安战事”进展:“京派援陕奉军,现已进驻咸阳,其兴平、武功已经陕军先后克复。又闻滇党退出陕境。”记述奉军、陕军与滇军交战的情形。当时,奉军因张作霖(1875-1928)投靠袁世凯而形成,陕军旅长陈树藩(1885-1949)效忠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的陆建章(1862-1918),滇军由蔡锷(1882-1916)领导,武力讨袁。陆洪涛、张荫亭作为甘肃、新疆的军事头目,密切关注“西安战事”。陆洪涛给张荫亭的信函中说:“现在陕局糜烂日甚,川警又复频来,陇上地阔兵单,三面受敌。”“陇东三面与陕接壤,防务必更吃紧,弟惟有督饬将士,扼要堵击,以尽我保境安民之责耳。”同时,他预估形势,并提醒张荫亭防御外敌:“近日长沙克复,合肥出山,南北问题可望有一定办法。惟德、俄单独媾和,迭见报纸,顷闻已成事实。果尔,则西北万里之边防宜早筹备御之方略。”陆、张等人均寄望合肥(段祺瑞)出山,收拾乱局。时任宁夏总兵(宁夏护军使)马福祥(1876-1932)也致信张荫亭:“自去秋南北纷争以来,乱者四起,吾甘狄道肃州之变可为寒心,幸能迅速扑灭,不致星火燎原”,“陕局糜烂”,“而各界遣代表求援宁军”,此为宁夏形势;“新省托鼎帅及台端维持,军民相安,干戈不动,视内地为乐国”,相比之下,张荫亭治军有方,新疆局势稳定。所有这些,均可资民国史研究。
张荫亭事迹,湮灭不彰。藉本信函可探吉光片羽。陆洪涛称誉张荫亭“据鞍矍铄,依然伏波精神也”,可推知张荫亭时或已年过六旬。伏波精神,用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前14-49)的典故。马援在62岁时,请缨南征,“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光武帝刘秀(前5-57)称赞:“矍铄哉是翁也。”陆氏又云:“回忆曩岁同舟,不禁晨星之感。知公一言,旧好必有同情。”足见关系匪浅。陆氏信函:“龙骧著绩,虎幄延釐,军中一范,关外同钦”“勋高豹略,令肃鸦军,引企戟门,莫名鼓舞”诸语,对张荫亭赞誉有加;马福祥恭维张荫亭“精神矍铄,威德炳扬,功在异域,诚倾远荒,知宿将风流不减,定远畴曩,博望昔日也”,将之比作定远侯班超(32-102)、博望侯张骞(前 164-前 114);朱瑞墀对张荫亭也有“勋高一代望重三边”赞语;可见这位荫亭旅长的人望。周务学(1886-1921)的信函更是十分恭敬:“久钦鸿范,沐惠露之均沾。远隔龙门,荷仁风之渐被。结蚁私于两地,徒鳌戴夫三山。敬维荫亭旅长大人鼎袚云蒸,泰祺日丽,仰见金汤巩固。”“弟忝摄道篆,时形愚拙,惊心岁序,虚掷驹光。”1918年任新疆阿尔泰道尹,1921年白俄窜犯阿山,城陷,周自戕殉国。由此可以推测这组荫亭旅长信函所反映的前后时间,大致是从1914年到1920年之间。乱世纷纭,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陶保廉(1862-1938),新疆巡抚、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随父赴新疆巡抚任,于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四月,作西北之行,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将随行经历著成《辛卯侍行记》。辛亥革命后,他在给裕堂的信函中说:“自军兴以来,商家多靠不住,拟暂存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有分行),一年为期,其息约四五厘,票据当代收存,惟日人呆板,非到期不得支取。到期时需原经手人领取,或改票再存,皆可。”可资经济、货币流通研究之参考史料。
本册还有杨彝庚(1864-1928)写给花溪(赵章典)的书信七通。杨彝庚1900年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疆,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督军、省长。1928年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易帜,不久被政敌刺杀,主政新疆16年。这七通书信,作于杨彝庚入疆后不久,信中有“弟到此月余,局事已就绪”诸语。信函多叙家常,如“偷闲课子作山居计,度日尚可敷衍”,但贫病交加,不免颓废,自谓“精神疲惫,竟成老耄之躯。自顾生平,劳薪久积,直不能再为子孙役耳”,“以寒士之生涯,进退每多顾虑,然以老惫思之,宜于冬间差满暂退为佳”,萌生隐退官场之意。所有这些,真实地记录了杨彝庚主政新疆之前的生活境况。杨彝庚遇刺后,金树仁(1879-1941)被推举为新疆省主席。1933年,金树仁去职后,手握重兵的盛世才(1895-1970),摄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成为“新疆王”。先父 1935年应邀抵新,任迪化师范(当时新疆最高学府)校长、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于1936年设法离开新疆。
本目书信为先父于1935-1936年间在新疆工作所集藏,其中涉及杨增新、朱瑞墀等新疆军政人物的往来信件。朱瑞墀致我大舅张馨(字敬丹,1898-1940,任新疆教育厅长)函,内容尤其丰富。该信写于1917年3月,称“中德已失感情,驻京德使已离北京。此件关系绝大,不无可虑。英、俄两领得此消息,固属得意,而我之对待更形棘手。刻间俄领来署密告,言该俄皇现已逊位,彼京亦颇有风潮。印度亦叠起叛乱,英领已照会前来”,述及新疆喀什动乱,英、俄借机干涉;北洋政府拟对德宣战,新疆与英、俄、德关系微妙;俄国发生革命(当指二月革命)、俄国沙皇逊位:新疆政界对局势忧心忡忡,我大舅希望离开新疆,而督军(当指杨增新)竭力挽留。这些情节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新疆的社会生态。我四叔冯德浩在1939年后被盛世才关押牢狱,1950年先父寻找其弟下落,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疆省府主席鲍尔汉(1894-1989,30年代与我父亲相熟),鲍立即复函,说明冯德浩及我大舅女儿的现状。鲍信纸有“新疆省人民政府用笺”字样,印章“鲍尔汉”,上汉文,下维吾尔文,此种印鉴少见。
以上信札于西北近代史、民国史研究提供难得一见的材料。
冯氏飞鸿
本目收有与清华国学院相关文书,如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后清华国学院在校生发出的讣告、清华国学院一期同学刘盼遂(1896-1966)致冯永轩函二通等,论学议事,皆具学术史价值。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父母迁居鄂东山区,家中什物多抛弃不顾,但文物书籍悉数保存。父亲在鄂东任省立第二高中校长,与避居罗田的国学大师、方志学家王葆心先生书信往还,切磋鄂东史地及文物考辨诸问题,又及子女教育事宜(本册收王葆心致冯永轩信函七通)。父亲在艰苦的抗战期间与多人通信,讨论文物收藏、保护、展览,于文化传承念念在兹。一代篆林宗师易忠箓(1886-1969)为先父挚友,1928年出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与先父四通信函中谈及收藏信札、鉴赏书画心得,指出“昔人有以作一佳书画如产一佳儿为喻者,然则获之者其乐又当云何”,论断清代著名学者张船山(1764-1814,名问陶)“于书画用力相若,当在其诗之上”,并于 1937年 7月 27日介绍先父加入中国国学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钱基博(1887-1957)、沈肇年(1879-1973)等文史专家通信,辨识文物,求得学术“精进贯通”。图书收藏大家徐恕(行可,1890-1959)、段永恩(1875-1947)等与先父书信述“旧藏清鉴”之乐。展读诸函,前辈学人风貌历历在目。先父20世纪40年代先后任教于安徽学院(今安徽大学)、西北大学,李则纲(1891-1977)、黄文弼(1893-1966)、刘盼遂、彭泽陶(1898-1989)、张西堂(1901-1960)等先生有多通书信往来,与先父讨论教学、教务等话题,也依稀可见先父当年所教科目有古文字学(金文)、考古学、史部目录学、声韵学。当时,李则纲为安徽学院教务长,时贤称李则纲先生与顾颉刚(1893-1980)、闻一多(1899-1946)齐名。黄文弼为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专家,从1927年至1966年前后39年间先后四次赴新疆考察,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研究多有贡献,乃新疆考古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西北考古第一人”。刘盼遂是著名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与先父同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为先父至交。张西堂先生亦海内名家,时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上述信札为先父在北京、武汉、乌鲁木齐和西安等地集藏,装订成册并注有眉批,涉及人物有文人学者、军政要员,所议可供研究近现代史、楚文化史、西北边疆史参考。信札呈现曾国藩、胡林翼、洪钧等人亲书笔墨,或雄健奔放,或优雅端庄,不让一流专业书家。李瑞清信札,笔力苍古,堪称极品。张裕钊信札之书道颇见功力,其名刺(名片)亦有意趣。这批信札兼具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可谓读书人收藏之读书人信札,体现了先父守护、传承中华文化的拳拳之心。
本册最后收入来信三通,其一为姚雪垠(1910-1999)函告拙稿发排以及他的《李自成》第五卷的创作与发表情况,其二、三为程千帆先生为其外孙女在《人文论丛》发论文事致信笔者夫妇。往事历历,仿佛如昨。
2018年5月26日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楚康楼803室
三、《冯氏藏币》序
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币帛为本。上智先觉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仰观,铸而为钱。使内方象地,外圆象天。大矣哉!
--(西晋)鲁褒《钱神论》
金钱是一个好仆人,却是一个坏主子。
--(法)小仲马
笔者少时,父亲在西北大学任教(1945-1949),寒暑假从西安回武昌,总是携带一口大木箱,我们兄弟好奇,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一观内里,父亲一旁笑道:“里面是好吃的‘点心’--大块有字的是唐长安城墙砖,雕花的是汉代瓦当,较小的长方形、圆形‘糕饼’是战国及汉唐青铜铸币。”在笑谈中,兄弟们初识夏商“贝币”,战国燕“明刀”、齐“大刀”、赵“铲币”、楚“鬼脸钱”,以及“秦半两”“汉五铢”和唐以下各种通宝钱。在实验中学读初中时(1954-1957),假期我还从事一项劳务--用粗针将古钱币以索线缝在马粪纸上。父母偶尔在一旁指点:某马粪纸缝的是魏国布币,某马粪纸缝的是楚国蚁鼻钱,某马粪纸缝的是新莽的货泉……至于清代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光绪通宝”则是我们少时熟悉的钱币,踢毽子往往以这些当年广存民间的“通宝”做底板。今日整理出版先父大半个世纪之前的古币收藏,不由得想起儿时经历,引动对先父母音容笑貌间跳跃着的“贝币-布币、刀币-半两钱-五铢钱-通宝钱”的生动记忆。
货币,本质上是商品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约定。货币包含以下意蕴:第一,人们普遍接受的用于支付商品劳务和清偿债务的物品。第二,充当交换媒介-价值、贮藏、价格标准和支付标准的物品。第三,购买力的暂栖处。
货币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术语,其含义为:甲、由政府法律规定强制使用,可充当交易媒介、价值标准、记账单位及延期支付的工具;乙、作为交易媒介的流通物,包括硬币、纸币、银行券。自古以来,货币形态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实物货币阶段:以实物(粮食、布匹、毛皮、工具、陶瓷、家畜、装饰品等)为等价物,供交换用。第二,形制货币与称量货币阶段:贝币、布币、制钱皆属形制货币,称量货币由金、银、铜、铁、铂金铸成,模拟实物金属币的镍币等也为称量货币。第三,纸币货币阶段:价值符号(包括可流通金融证券,如支票、股票、债券等)。第四,电子货币阶段: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本文呈现的是第二类,主要是铜铸币。其命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第一,以币面名字命名。如“齐刀”“明刀”“五铢”“元宝”“重宝”“通宝”等。第二,以币面图案命名。如清代银圆中央有盘龙纹,称“龙洋”。第三,以币体形状命名。如东周“针首刀”“圆首刀”“三孔布”,秦以下“方孔钱”。第四,以钱币重量命名。如秦“半两”,汉文帝“四铢”,汉代通用的“五铢”。第五,以流通地区命名,如“边币”。
中国古代铸币的计量单位有文、陌、贯(吊、串)。钱、两为称量货币的单位,而“文”是制钱系统的基本单位,一枚小平钱称一文。而在钱孔中穿木条或绳头,百文为一陌,千文为一贯(吊),南北朝始缩水,北宋一陌为 77文,一吊为 770文。钱币正面称“面”,或“文”,又称“月(röu)”。钱币正面的文字称“面文”,又称“月文”。钱币背面称“背”,又称“幕(màn)”,背面文字称“背文”,也称“好(hao)”。背面没有文字称“光背”,又称“素背”“素幕”。钱币内外郭之间无文字图案的地方称“肉”,厚者称“厚肉”,薄者称“薄肉”。钱币背面凸起的圆圈称“日”,又称“日文”。钱币凸起的圆弧称“月”,又称“月文”“甲文”“月痕”,圆弧向上称“仰月”,向下称“偃月”。从春秋战国开始,钱币始铸文字,如本书收录的齐国刀币有铭文“齐之法化”等,賹化钱有铭文“賹六化”等,楚国釿布币正面有铭文“铈钱当釿”、背面有铭文“楚”,魏国锐角布币有铭文“垂”,安邑二釿布帀有铭文“邑二釿”。秦代货币铭文“半两”,汉代货币铭文“五铢”,新莽货币铭文“布泉”。唐高祖货币称通宝,铭文标示年号,合成“开元通宝”。宋以后通宝钱书写年号成为通例。不同朝代,钱币形态不一,基本走势是从单面文字到双面文字,从“光背”到“日文”“月文”(标示币值)。钱币文字阅览有左读(由左向右读)、直读(按照钱币文字上下、左右排列而读,又称“顺读”“对读”)、旋读(按照钱币文字“上-右-下-左”排列而读,又称“环读”)等方式。由于读法不同,一些钱币文字的释读不免产生分歧。如本书收录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开元通宝”,一般顺读为“开元通宝”,但采用旋读方式则读为“开通元宝”,从而形成“××通宝”“××元宝”两种习称。人们还根据钱币的色泽情况分出生坑、老坑、熟坑。“生坑”指出土的钱,表面氧化严重;“老坑”指出土已久,铜锈被传世色泽新掩;“熟坑”指未经人土的传世古钱,一般呈黑色,光泽鲜亮。钱币还有一些雅号。例如汉代出于聚财的愿望称“泉”(一说王莽取帝位后,忌于“劉”字之“金”“刀”,将“钱”改称“泉”)。泉是四面八方汇集之意,又流向四面八方。泉字分解为白、水,因而又称“白水真人”。又如,“孔方兄”,铜钱内有方形孔,称孔方;“钱”字由“金戈戈”组成,戈-哥同音,故“钱”称“兄”,“孔方兄”称呼由此而来。
本书展示中国各历史阶段的古货币(未收纸币),皆属形制货币和称量货币。
三代贝币及龟币
我国最早的货币--天然海贝,产于南海,由装饰品演为货币,沿用于夏、商、西周三代。“贝”字甲古文“”,从“”(贝壳)原始形态演变而来,其甲骨文,字形像打开壳的贝,里面的短画代表贝的软体。贝币的计量单位是“朋”,“朋”字的甲骨文字形,如,均像两串玉(贝)串()系在同一根绳子(—)上,形成更大的一挂玉(贝)串。“朋”作为贝币的计算单位,过去有一朋二贝、五贝的说法,王国维、郭沫若等考证,“十贝为朋”。汉字中凡与财富有关的字,多以贝为偏旁,如買、货、贵、贮、赎、资、财、购等,此为贝币通行的历史遗迹。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墓葬中,发现成批铜贝(仿贝形的铜币),这种仿贝形的铜币曾流通,汉代有文献记载铸仿贝币的铜币流通。这是我国作为世界上较早使用金属铸币的一个显著标志。三代以后,还有金仿贝币、绿松石仿贝币,先秦时曾流通,汉代已为饰品,供赏玩。除海贝外,三代曾用龟甲做货币,梁启超《中国古代币材考·龟币》说:“古代用龟币,以全龟为之者固多,然割裂之者亦不少。”人们食龟肉,以龟壳作货币使用,后又将龟甲上的一片片盾甲作成龟币流通使用。春秋晚至战国末,楚国以青铜铸成形似龟甲、呈椭圆形的蚁鼻钱(鬼脸钱)。
春秋战国铸币
楚国将铜贝发展成为一种有固定形制和铭文的“蚁鼻钱”。蚁鼻,喻小,蚁鼻钱意为小钱;因其造型似鬼,又俗称鬼脸钱。从天然贝到铜仿贝或铜仿龟甲,再到有固定形制和铭文的铸贝,是中国古币的发展轨迹。中原腹地的赵、韩、魏三国和周王室流行布币,仿农具铲而来。而北部沿海的齐、燕地区流行刀币,则是仿渔猎工具刀而来。这昭示铸币是由实物货币演进而来的。本书呈现较多的布币(“布”“镈”通假,一种仿铲状农具的货币)主要是空首布,即有装柄的空心銎。由于其取相农铲,形似铲,故又称铲布。到战国时,布币主要是平首布,已无装柄的空心銎,形似铲状铜片。按形制之不同,可分为尖足布、方足布、锐角布、圆足布、三孔布等。齐、燕所用刀币,分“燕明刀”(刀身面文“明”字)、“齐大刀”两类,齐刀多有铭文“化”字而称“刀化”。
秦半两、汉五铢等称量钱
秦始皇扫平六国后,将秦国使用的“半两钱”推广全中国。此钱以半两为单位,钱文“半两”与实重相符。“秦半两”的出现,避免了以往钱文复杂难辨、轻重不一、币值不明等混乱状况。这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次变革。其外圆内方的形制,历代沿袭,直至清末。西汉初期,承袭秦制,推行“半两”钱。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改铸“四铢半两”。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废“半两”,行“五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五铢钱”从西汉、新莽、东汉、三国、晋、南北朝、隋,沿用 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行用地域最广、时间最久的长寿钱。汉武帝的五铢钱制,至西汉末王莽称帝时曾一度遭受破坏。王莽推行新政,发行三种新币:(1)“错刀”,值五千;(2)“契刀”,值五百;(3)大泉(重十二铢),值五十。后来又废止“错刀”“契刀”,新铸“货布”“货泉”,史称“新莽币”。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又恢复五铢钱制度。至东汉末,董卓坏五铢钱,铸小钱,开启此后三四百年货币混乱的端绪。三国时期,刘备在蜀汉铸行“直百钱”,孙权在东吴铸行“大泉五百”;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铸造“丰货”钱,钱文“丰货”,开始突破西汉以降的五铢钱制。
南北朝以降趋于规范化的年号钱
四川成汉李寿汉兴年间(338-343)铸“汉兴钱”,这是我国最早的年号钱。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铸“太和五铢”,其后孝庄帝铸“永安五铢”、齐文宣帝铸“常平五铢”、北周静帝铸“永通万国”,皆年号钱。唐朝统一后,废五铢钱,新铸“开元通宝”(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年号钱流行,是我国钱币史上的又一次变革。唐代除唐高宗、唐肃宗新铸“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年号钱外,通行货币多为“开元通宝”。故本书所收唐代铸币种类不多。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李環铸行“唐国通宝”、前蜀王衍铸行“乾德元宝”、周世宗铸行“周元通宝”。其中,“唐国通宝”钱面文为真书、篆书配对铸造,是中国最早的对钱。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铸行“太平通宝”钱,从此,中国货币历代所铸的基本都是年号钱。每逢皇帝改元,几乎都会新铸年号钱,并形成定制,历经宋、元、明、清,长达千年。年号钱有160多种,其中两宋16位皇帝改了55次年号,共铸造45种年号钱,近占古代年号钱的1/3。本书收录宋代年号钱共计43种。宋太宗“至道元宝”相传由宋太宗手书,从而开创“御书钱”先河,后继君王多相仿效。有名的“大观通宝”“崇宁通宝”,均为宋徽宗“瘦金体”手书。辽、西夏、金、元政权,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先后铸行钱币,本书收有辽道宗“大安元宝”、辽天祚帝“天庆元宝”、西夏仁宗“天盛元宝”、西夏神宗“光定元宝”、金海陵王“正隆元宝”、金世宗“大定通宝”、金章宗“泰和重宝”、元顺帝“至正通宝”等年号钱。朱元璋为吴王时,铸行“大中通宝”,流通较广,书中收有小平钱、济十、浙十、鄂十。明朝初年主要用纸币,中叶以后主要用银两,铜钱发行量少,存世更少,一些皇帝在位时甚至没有铸钱。明代年号钱有十种,本书有“洪武通宝”“万历通宝”“天启通宝”三种。
清代铸币的复杂状态
清代的货币体系沿袭明代中叶,以银为主,银、钱并用,商务大数用白银,民间习用铜钱。清代先后有12位皇帝,共使用13个年号(同治帝初用年号祺祥,旋改同治),年号钱13种。钱文有通宝、重宝、元宝之分。清代钱币制造的机械化,是我国钱币史上的一大变革。清末机制制钱的出现,使方孔圆形的传统钱币形式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地位急剧下落,并逐步完全退出流通领域。清末及民国各省自铸货币,如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在湖北铸币。先父在新疆工作时获多种地区流通的银币、铜币(币面有“迪化”“喀什”等字样)。在西安工作时获川陕边苏区铸帀,上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近代西方货币也逐渐进入中国市场,俗称“洋钱”,广东称“番银”。
地方性政权铸币
本书还收有统一朝廷之外的各种铸币。安史之乱叛将史思明所铸“顺天元宝”。明末清初各地政权纷纷铸行新币。公元 1644年,李自成推翻明朝,铸行“永昌通宝”。同年,张献忠在四川发行“大顺通宝”,张献忠战死后,其义子东平王孙可望称国主,铸行“兴朝通宝”。同时期,南明福王南京称帝铸造“弘光通宝”,南明鲁王监国铸行“大明通宝”,南明唐王福建称帝铸造“隆武通宝”,南明桂王称帝铸行“永历通宝”。这些钱币,本书悉有展现。清康熙发生“三藩之乱”,尚氏父子未铸币,吴氏政权铸新币“利用通宝”“洪化通宝”,耿氏政权铸“裕民通宝”。
本书呈现的中国古钱币,系先父在新疆、安徽、陕西、湖南、湖北任教时集腋成裘的珍品。其中以在十三朝古都西安所获较多。这批钱币历经抗日战争、“文革”等劫难而得以保存,实乃万幸!先父最后一个任教单位是武汉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湖北大学),其历史系在“文革”期间停办,1978年复建,本人协助退休多年的先父于 1979年初辞世前夕,将古钱币全数及百衲本二十四史捐赠给武汉师院历史系,以示对重建的支持。此批藏品成为后来兴建的湖北大学博物馆钱币馆基本馆藏(百衲本二十四史藏湖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业内专家评价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