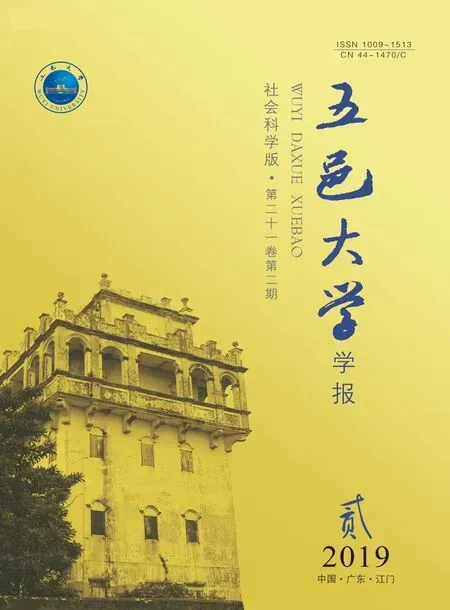雅各布森诗学在中国的旅行
2019-12-21杨建国
杨建国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一、引 言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是20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流变的核心人物。他一生学术兴趣极为广泛,横跨语言学(尤其是音位学)、诗学、诗歌和艺术批评、符号学、社会人类学众多领域,令人惊叹。雅各布森诗学在中国的旅行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事件,也是研究理论旅行过程中理论变异的典型案例。
二、雅各布森诗学在中国旅行的历史梳理
雅各布森诗学在中国的旅行大致可分为早期介绍期、影响扩大期、影响焦虑期、综合总结期四个时期。
20世纪80年代起,《读书》、《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内顶级外国语言文学刊物上陆续出现了介绍雅各布森诗学的文章。1982年,邓丽丹在《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中介绍了布勒、穆卡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人的语言功能观,重点介绍了雅各布森的语言六功能,即指称、情感、意动、寒暄、审美、元语言六种语言功能。[1]这篇文章是目前能追溯到的最早介绍雅各布森诗学的汉语论文。1983年,张隆溪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和《诗的解剖:结构主义诗论》,前文重点介绍俄国形式主义语言文学观,介绍了雅各布森所提出的“文学性”概念[2],后文则重点介绍结构主义语言文学观,特别介绍了雅各布森的“隐喻”和“换喻”理论。[3]王泰来在1983年发表文章《一种研究文学形式的方法:谈谈结构主义文艺批评》,介绍了结构主义语言文学观关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的讨论,也介绍了雅各布森在这方面所做的理论探索。雅各布森将“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称为“选择轴”和“组合轴”,并把这一理论广泛运用于西方诗歌,尤其是十四行诗的分析中。[4]钱佼汝在1985年发表《英语文体学的范围、性质及方法》,介绍了雅各布森诗学对于英语文体学的贡献,同时也关注英语文体学学术传统与雅各布森诗学的争论和分歧,例如保罗·沃思对雅各布森诗歌分析方法的批评。[5]这一时期对雅各布森诗学思想的介绍大都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等西方文论流派的介绍夹杂在一起,轮廓线条较粗,文字也比较简略。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雅各布森诗学在中国进入影响扩大期,有以下具体表现:
其一,出现了专论雅各布森诗学的文章,对雅各布森诗学的介绍集中于其中一点,并尝试将雅各布森诗学和中国传统诗歌分析结合起来。查培德在1988年发表《诗歌文体的等价现象:雅各布逊的“投射说”与文体分析方法的述评》,重点介绍雅各布森的“对等投射”说,并尝试把“对等投射”解释为普遍审美现象,由诗歌领域扩展到散文、叙事、音乐、美术等领域中。[6]任雍发表于1989年的文章《罗曼·雅各布森的音素结构理论及其在中西诗歌中的验证》则重点关注雅各布森的语音理论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作者广泛引用中外诗歌作品,例如《诗经》中的《将仲子》、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波德莱尔的《信天翁》、皮埃尔·徳·隆萨尔的《海伦》验证雅各布森的诗学,认为雅各布森诗学“对技术细节高度敏感,阐幽扶微,多有发现。但是同时,他们也容易对一般认为是小巧的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7]。
其二,对雅各布森诗学的介绍由国内顶尖外国语言文学刊物扩展到一些地方院校学报,如古建军的《简论诗歌语言的审美性:在语言学和美学的交叉地带思考》[8],魏家俊的《结构主义方法在中国文学中的应用》[9],张旭春的《从语言结构到诗性结构——索绪尔语言理论及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诗学》。[10]
20世纪90年代,随着雅各布森诗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影响的扩大,也引发种种焦虑情绪,对雅各布森诗学的研究进入影响焦虑期,出现了一批与雅各布森诗学思想相抗衡的文章。焦虑来源主要有三种: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涌入中国,引起了中国传统文论界的焦虑,担心中国传统文论在西方理论冲击下会陷入失音失语的困境,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曹顺庆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11]尽管曹先生的文章并非直接针对雅各布森诗学,标题中“失语症”一词无疑在这篇文章和雅各布森诗学之间建立起丰富的联想。
王元骧在《西方三种文学观念批评》中对“再现论”、“表现论”、“形式论”三种西方文学观念加以评析和批判,其中对“形式论”的批判以雅各布森诗学为主要目标之一。文章认为 “形式论”试图以“形式”、“手法”代替“内容”与“形式”,竭力论争文学语言没有“指称功能”,文学审美价值完全落于作家对于语言的编织和加工之上。最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包括“形式论”在内的西方文学观念加以研究批判,融合其中合理成分。[12]在《文艺内容与形式之我见》中王元骧继续对西方形式主义诗学的批判,批判了包括雅各布森在内的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法国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强调文学要遵守列宁所提出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原则”。[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界风向巨变,过去30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文本中心论让位于读者反应论、解构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话语。尽管这些理论话语各有自身的侧重点,出发点却大抵相似,即对文本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雅各布森诗学自然成为批判的首要目标。随着中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一批留学英美的学者回国任教,这些理论思想也传播入中国,代表性文章有王守仁的《作品、意义、读者——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述评》[14],姚基的《向文学本体论挑战:现代意图主义理论评述》[15],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写作》[16],苏鸿斌的《走向文化批评的解构主义》。[17]
21世纪以来,随着文献资料的积累,中国学界对西方各文论流派的理解渐趋融会贯通,雅各布森诗学思想的研究也进入综合总结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陈本益的《雅各布森对结构主义文论的两个贡献》不仅关注雅各布森对结构主义诗学的贡献,也关注他对于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贡献。[18]田星的《论雅各布森功能观对索绪尔对立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重点讨论了雅各布森对于索绪尔语言“任意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19]杨建国的《罗曼·雅各布森论文学文本》对雅各布森诗学中与文学文本相关的理论加以整理和呈现。[20]
周启超的《当代外国文论: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旅行”——以罗曼·雅各布森文论思想为中心》把雅各布森诗学放到整个斯拉夫学派的大学术传统和历史背景中加以考查,认为跨学科、跨文化构成了20世纪斯拉夫学术研究的两大特征,雅各布森诗学是最典型个案。[21]朱涛的《从诗性功能到审美功能:布拉格学派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学功能观之比较》深入讨论了雅各布森在布拉格学派的构建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讨论了雅各布森同马泰修斯、布勒、穆卡洛夫斯基、胡塞尔等人的学术互动。[22]
江飞的《雅各布森语言诗学和俄国先锋艺术》关注了一个为国内雅各布森诗学研究所忽视的领域,即雅各布森早年与俄国先锋艺术的接触。文章介绍了雅各布森早年列维奇、克鲁乔内赫、赫列勃尼科夫、马雅科夫斯基等先锋艺术家的交往,探讨了这段经历对他语言学和诗学的影响。[23]
三、雅各布森诗学在中国旅行的社会语境
雅各布森诗学在中国的旅行是中国本土文学理论在重构文学现代性的内力驱动下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一场“邂逅”,既有初遇后的欣喜,也有相处中的焦虑和躁动。
中国现代文学源起于晚清,初成于“五四”,其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中断,在20世纪最后20年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晚清时期,无论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其共同主旨都是要师法域外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正是这种与世界现代文学潮流相联系的新的文学视界和资源保证了晚清文学革新不同于传统文学变革的现代性, 开始了文学从思想主题到形式、文体、手法、语言等方面的现代性变革。相对于晚清文学革新来说,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更自觉更完全意义上的文学革新运动。它不再仅仅把文学作为政治变革的工具, 而是深入到文学本身的语体层次, 直接要求文学存在形式的变革,体现出文学本体的自觉,标志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立。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外历史合力的作用下,关于现实主义的种种僵硬教条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惟一声音,现代性在中国文学中处于停滞状态。王一川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分为现代1和现代2两个时期,认为“从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一个长时段,可称为现代1;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则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长时段,可称为现代2。”[24]上世纪最后20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国门的开放,现代性在中国文学中再度蓬勃起来,新诗歌、新小说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本土作家尝试着语言的先锋体验,中国的文学现代性进入建构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在文学理论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最后20年中,国内的学术期刊发表了大量有关西方文论的文章,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解构主义、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均有比较详细的研究和介绍, 几乎涵盖了当时流行于英美的所有流派。
雅各布森诗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旅行到中国,迅速传播,是中国文学理论在建构现代性的内力驱动下所引发的重要理论事件。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雅各布森诗学起到了以下几项作用:
1.突出了文本—作品在文学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帮助本土文学理论摆脱长期以来束缚于其上的道德压力和政治功利,从理论上促进了以自律为特征的现代文学观的再度萌发。
2.突出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向内转向,令文本细读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势方法,文本—作品的内部结构一度成为文学批评的首要目标,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在中国摆脱哲学、历史、政治的纠缠,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研究对象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自律学科。
3.突出了质料—过程一元意义观,打破了意义的形式—内容二元分裂,促进了语言意识的空前高涨。这种语言意识的高涨不仅体现于文学批评中,也体现于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先锋文学创作中。
4.凭借其在西方诸多文论流派中的枢纽地位,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对西方20世纪数个主流文论派别的融会贯通,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
5.凭借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多学科综合和多视角对话。
四、旅行与理论变异
理论旅行到新语境中,为新语境所过滤吸收,必然会带来“变异”,曹顺庆先生近年来致力于“变异学”研究,以研究这一理论现。[25]雅各布森诗学在中国的旅行为理论变异研究提供一则典型例证。
雅各布森一生颠沛流离,其学术活动大致可分为莫斯科、布拉格和美国三个时期。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雅各布森学术活动的叙述遵循莫斯科—布拉格—美国三阶段模式,形成一条自东向西连续无间断的发展线索,再加上雅各布森与列维-施特劳斯纽约邂逅,列维—施特劳斯从雅各布森音位学讲座中得到神奇灵感,日后在结构主义理论建构上取得杰出成就,形成20世纪学术史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部叙事。雅各布森是“结构主义”一词的实际创造者,随着他移居美国,布拉格也被视为结构主义发展中的一站,为日后结构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辉煌做好准备,奠定基础。这部叙事贯穿起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令雅各布森成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人物。
雅各布森对于20世纪文学理论的历史意义无须质疑,然而上述叙事所采用的连续无间断模式突出了叙事的两端,忽略了故事的中间,布拉格虽然未被完全忽视,却更多被视为莫斯科时期的延续和美国时期的准备,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身的特质。或许,应当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布拉格,投向这个欧洲十字路口,投向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思想背景和学术气质。捷克学者帕特里克·弗莱克撰文指出,相对于传统的法国—美国模式,近年来结构主义学术史更倾向于东欧—西欧模式,以“聚焦于中东欧结构主义传统的独立起源和不同的思想倾向,重视中东欧结构主义传统中不同于西欧传统而具有独创性的成分”。[26]19弗莱克本人则提出第三种模式——雅各布森模式,以“更好地认识到雅各布森游走于不同的学者、学术领域和学术传统之间所起到的交流、综合和传播的作用”。[26]16-17
雅各布森在布拉格时期的学术活动既非莫斯科时期的简单延续,亦非为美国时期所做的准备,而是一座独立的高峰。钱军的《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对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活动做了细致入微的再现,是了解雅各布森在布拉格学术活动的重要文献。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学术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跨国别、跨学科的特点。钱军先生根据雅各布森1985年编辑《特鲁别茨柯伊书信集注》时所做的说明,确定了37位布拉格学派成员,其中捷克17位,俄罗斯9位,乌克兰2位,法国3位,德国2位,丹麦2位,荷兰1位,塞尔维亚1位。[27]布拉格学派不仅在国别上分布广泛,在研究领域上同样“来者不拒”:布拉格学派的支柱之一马泰修斯是捷克著名的英国语言学者;另一位支柱人物特鲁别茨柯伊是现代音位学的奠基者;雅各布森自己更是兴趣广泛,在布拉格期间不仅致力于音位学的研究,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捷克诗歌和诗歌理论的研究中;布拉格学派的另一位著名人物穆卡洛夫斯基则致力于美学研究和艺术符号研究。
纳粹铁蹄踏响布拉格街巷,雅各布森仓皇逃亡,也把这一时期研究的独特气质留在了布拉格,再也没能重新拾起。阅读雅各布森与蒂尼亚诺夫在布拉格联署发表的纲领性文献《语言与文学研究诸问题》,很难不注意到这篇文献与雅各布森日后诗学思想的张力和冲突。《语言与文学研究诸问题》中核心词并非结构,而是演化。演化的概念,无论在文学研究中,还是在语言研究中,都要求突破共时和历时的简单对立,一方面要求引入历史,另一方面又要求按照系统自身的内在规律去处理历史材料:“共时与历时对立是系统概念和演化概念的对立,一方面任何系统必然存在于演化之中,另一方面任何演化也不可避免带有系统的性质。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共时和历时的对立也就失去了意义。”[28]4文献第八条尤其关注文学研究中历史的重要性,指出内在结构原则只能解释文学演化的大致原理,并不能决定文学发展的具体路径,解决文学发展具体路径问题,“必须分析文学系列与其他历史系列的交互关系,这一交互关系(系统之上的系统)有着自身的结构原则,必须对其加以研究”[28]5。“系统之上的系统”这一概念把静态结构研究和动态历史研究嵌合到一起,为文学研究指明了方向,遗憾的是这一方向在雅各布森日后的诗学研究中并未能坚持下去。
雅各布森这一时期完成的另一篇重要诗学文献是1935年在马萨瑞克大学所做的讲演《论主因》。这篇文章中雅各布森介绍并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中的“主因”概念,将其界定为“艺术作品的核心成分,它制约、决定、转化作品的其他成分,正是这一成分确保作品的结构一致性。”[28]75123年后,类似的表述出现在雅各布森又一次讲演中:“诗功能并非语言艺术的唯一功能,而是其主因,是决定功能,在其他语言活动中诗功能仅仅起到辅助作用,是附属成分。”[28]25从捷克到美国,尽管称谓未变,“主因”这个术语的概念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1935年的讲演中,“主因”不仅是作品内部的结构要素,同时也是作品外部的历史要素,是内外相交的汇合点。这篇讲演中雅各布森指出,一个时期的艺术有自己的“主因”,文艺复兴时期是绘画,浪漫主义时期则是音乐,[28]752“主因”处于历史变动之中,有升亦有降,“在总体的诗歌常规系统中,尤其在生效于特定诗歌体裁的诗歌常规系统中,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要素成为首要、必须要素;另一方面,原先的主因要素则降至次要从属地位,可有可无。”[28]754“主因”概念对于这一时期的雅各布森具有特别重要的方法意义,是打破静态共时研究和动态历时研究对立的重要契机,其所蕴含的力量可以“克服和弥合历时历史方法和共时方法”。[28]75623年后,“主因”成为界定诗歌结构的一个内在概念,其原先蕴含的历史倾向和动态能量已大部分耗尽,至少在雅各布森的诗学研究中是如此。
五、结 语
雅各布森诗学的中国之旅还在延续,他的学术传奇还在传播,或许叙述的方式可以有所改变。雅各布森的学术生涯并非由东方向西方连续发展的故事,而是一个被二战烽火打断,在新大陆上重新开始的故事。当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于布拉格,聚焦于雅各布森在二战前那段岁月,或许可以发现一个不同的雅各布森,一种不同的结构主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思考文学理论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