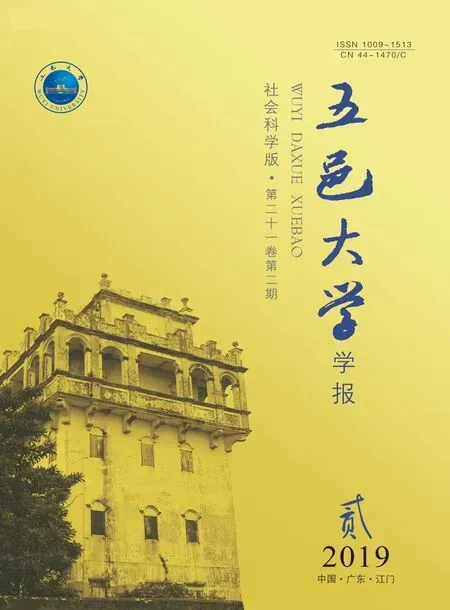陈澧今古文《五经》论
2019-12-21张纹华
张纹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中文系,广东 茂名 525000)
陈澧(1810—1882)被梁启超誉为“咸同年间岭南两大儒”之一,是广东少有的著述颇丰的学问家,著述见今人点校整理的《陈澧集》。陈澧如其自言没有完整著过一本甲部之书,但他的经学思想影响深远。陈澧丰富、系统的今古文《五经》论,不仅弥补了此前与同期广东经学家疏于阐述《五经》的不足,为广东经今古文学研究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而且其论呈现的去广东经今古文学门户、与汉宋学相调和的特点,成为咸、同年间广东儒学开始步入总结期的标志,反映了广东儒学家是试图集汉宋学、经今古文学之力应对儒学危机的。陈澧是近10多年来广东学术研究的重点人物,可惜其经学研究成果甚少。笔者不吝疏浅,总结其今古文《五经》论,以期对陈澧经学研究有所推动。
一、陈澧今古文《五经》总论
《五经》所宗之典籍、排序以及孔子与《五经》的态度,是晚清经学家判断今古文经学的重大问题,此即陈澧今古文《五经》总论的主要方面。
(一)《五经》典籍论
现存《十三经》中的《易》是西汉费直所传的古文经,费氏疏《易传》十篇。陈澧以费氏疏十篇为宗,兼取今文孟氏、虞氏《易》二家。“费氏以十篇解说上下经,乃义疏之祖,《易》者当以此为断。”[1]二册73页“此(按:指对乾之所以‘利贞”者的释义)虞氏之最精善处,亦惠氏最精善处。”[1]二册73页陈澧认为《书》伪古文经清人论难后已成铁案,故宗今文《尚书》。陈澧以古文毛《诗》为宗,兼取仅存的《韩诗外传》。“西汉经学,惟《诗》有毛氏、韩氏两家之书,传至今日。”[1]二册109页由于《周礼》仅有古文经,《仪礼》《礼记》则兼有今古文之义,故陈澧对三《礼》没有论及其高下,是为平视三《礼》。陈澧强调《左传》传《春秋》,兼论《公羊》《谷梁》之病。“《左传》依经而述其事,何不可谓之传?且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1]二册186页因此,陈澧于《易》《诗》《春秋》以古文为宗而兼取今文,于《书》宗今文,于三《礼》则平视之。
(二)《五经》排序论
由于认为“学者得以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1]二册12页,以《论语》者,《五经》之馆鎋,以及尤重孟子“性善”说,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不取现存《十三经注疏》之序,将《孝经》《论语》《孟子》置于其《五经》论之前,继而以《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为《五经》之序。因此,陈澧宗古文家《五经》之序。
(三)关于孔子与《五经》论
今文家认为孔子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更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故孔子殊非“述而不作”的圣人。陈澧认为《五经》皆经孔子修定。“‘天之未丧斯文’,夫子以为己任,盖谓删述《五经》,垂教万世,此即所谓夫子之文章也。”[1]二册27页陈澧指出,“圣人删定《尚书》,存盛治之文以为法,存衰敝之文以为鉴。”[1]二册95页“盖未修之《春秋》必书正月晦,孔子修之,改书二月也。”[1]一册48页古文家认为《五经》经秦火后仍存石壁,陈澧亦有此论:“幸而《周礼》出于山崖屋壁,即不尽周公所作,终是周代典制,岂可排弃之乎?”[1]二册126页因此,陈澧宗今文家的孔子与《五经》论,而论及《五经》存亡则取古文家之论。
综上,于《五经》的典籍,陈澧兼取今古文学;于《五经》的排序,陈澧独尊古文学;于孔子与《五经》的关系,陈澧宗今文。因此,陈澧是学有宗旨、有变化的,旨在调和经今古文学。
二、陈澧今古文《五经》分论
陈澧以为无学不经考据,好读《十三经》注疏。因此,陈澧《五经》分论延及历代研究的主要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五经》学“史”的性质,显得颇为翔实、丰富。
(一)《易》论
陈澧以《易》之道大,认为测《易》犹测天,亦是以《易》为史料,显然是古文家的观点。“夫《易》之道大矣,其犹天乎!易家之测《易》,犹天文家之测天也。”[1]一册351-352页《易》之六十四卦名“重卦”,陈澧反对其为伏羲、神农氏、大禹、周文王作。“自古无伏羲造书契之说,孔冲远独据伪孔说,且以《周礼》传会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无文字题识也。然《周礼》所谓三皇之书者,后世说三皇之事,非三皇时所作之书。”[1]二册68页“孔子言《易》之兴,但揣度其世与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1]二册70页陈澧认为孔子作《易传》,“夫子作《传》,所以解经之取象也。”[1]二册81页陈澧认为“十二消息卦之说,则必出于孔门”[1]二册72页。
费氏《易》、孟氏《易》、虞氏《易》、孔颖达《周易正义》、惠栋《易汉学》《周易述》、张惠言《易义别录》等是陈澧分析的研究《易》的主要著述。陈澧以费氏家法为宗,指斥虞氏《易》注经多不可通、孟氏《易》之灾异说乃唐时窜入。“此后诸儒之说,凡据十篇以解经者,皆得费氏家法者也。其自为说者,皆非费氏家法也。说《易》者当以此为断。”[1]二册70页“虞氏《易》注,多不可通。”[1]二册75页“章句止二篇(按:指《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而唐时所存十卷,以灾异窜入其中,必矣。虞翻自称传孟氏《易》。”[1]二册71页陈澧指出虞氏《易》、费氏《易》皆杂老子之说,《周易正义》有去老氏、释氏之功,“孔冲远等作《正义》,用王辅嗣注,近人诋王注,并诋《正义》,此未知《正义》之大有功也”[1](二册77页)。
陈澧指出惠栋《易汉学》有功于《易》学,“惠定宇《易》学倾动一世,平心而论,所撰《易汉学》有存古之功。”陈澧认为惠栋《周易述》存在释经改字而申其说之大谬,“所撰《周易述》渊博古雅,其改《明夷 六五》之‘箕子’为‘其子’而读为亥子,则大谬也。”[1]一册386页“惠氏谓‘五为天位’,箕子臣也,而当君位,乖于《易》例,逆孰大焉!此欲以大言杜人之口耳。如此说何以处虞氏乎!且《坤 六五》:‘黄裳元吉’。惠氏注云:‘降二承乾。’君位可降乎?惠氏好改经字,此则改经并改史而自伸其说,卒之乖舛叠见,岂能掩尽天下之目哉!”[1]一册387页
陈澧《易义别录跋》指出,张惠言《易义别录》独取虞氏《易》,而尊孟氏《易》,是为好古;且以十翼为商矍所受孔子之微言,是为大误。“两汉、三国说《易》之书,自王辅嗣注之外,皆散佚,赖有李鼎祚《集解》得见一斑。惠定宇《周易述》以《集解》为本而稍增损之。至张皋文乃独取虞注,因其义例而补完之,以存一家之学,此可谓好古矣。乃因虞氏自言世传孟氏《易》而推尊孟氏,且信孟氏所言‘田生枕膝独传’之语,又推而上之,遂以为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因虞氏而不歇灭,曾叠递高,至于圣人而后己,则太过矣。且夫子之微言,著在《十翼》,安有歇灭之理乎!”[1]一册388页
(二)《书》论
陈澧在宗今文《书》的同时,指出今之《舜典》亦为《尧典》,《洪范》术数之学不出于《春秋》,治经者当存而不论。“今《舜典》,汉时在《尧典》之内,而不足以证别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赵氏所驳也。”[1]二册88页“此汉儒术数之学,其源虽出于《洪范》,出于《洪范》不出于《春秋》,《春秋》无阴阳五行之语。然既为术数之学,则治经者存而不论可矣。”[1]二册93页《孔传古文尚书》的作者与其多出的二十八篇是否废,是经学家长期争论的问题。陈澧认为孔传殊非王肃作,二十八篇经文可废,而二十八篇伪传不可废。“此皆传与郑说同,而与王肃说不同,则似非王肃作也。或王肃故为不同,以揜其作为之迹与?”[1]二册97页“伪孔善于郑注者,焦氏所举之外,尚颇有之,今不必赘录,盖伪孔读郑注,于其义未安者则易之,此其所以不可废也。伪古文经传可废,二十八篇伪传不可废”[1]二册97页。
孔颖达《尚书正义》、蔡沈《书集传》、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惠栋《古文尚书考》、焦循《尚书正义》等是陈澧分析的研究《书》的主要著述。陈澧认为孔颖达《尚书正义》已知伪古文袭用诸经传之语,“如此之类,孔疏于伪古文勦袭古经传之迹,已指出之矣。”[1]二册98页陈澧重视蔡沈《书集传》,“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1]二册99页陈澧指斥江声、惠栋、焦循治《书》之失。“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矣;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也。”[1]二册100页“焦氏谓《正义》不引郑注者,‘即孔义与郑义同者’,此未必尽然。谓置孔传之似托,而但以为魏晋间人之传,则通人之论也。即以为王肃作,亦何不可存乎?”[1]二册96页在此基础上,陈澧认为理想的《书》的研究著述当如下:“江、王、段、孙四家之书善矣。既有四家之书,则可删合为一书。取《尚书大传》及马、郑、王注,伪孔传,与《史记》之采《尚书》者,《尔雅》《说文》《释名》《广雅》之释《尚书》文字名物者,汉人书之引《尚书》而说其义者,采择会聚而为集解。孔《疏》、蔡《传》以下至江、王、段、孙及诸家说《尚书》之语,采择融贯而为义疏。其为疏之体,先训释经意于前,而详说文字名物礼制于后,如是则书善矣”[1]二册101页。
陈澧没有完整注疏《书》,但他精于《禹贡》研究,如撰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黑水说》《禹贡道水次第说》等。《禹贡道水次第说》指出,“《禹贡》道水,先记不入东海之水,次记入东海之水,又次记入河之水。三者之中,又先西而后东,先北而后南。”[1]一册19页由于精治《禹贡》,陈澧为《禹贡图》《禹贡说》《禹贡新图说》撰写序言,分别指出其得失。“澧既读内府地图,又考得郑书之误,乃取胡氏图订正之。凡胡氏之说不误而其图位置不确者,移而置之。胡氏据邓书而图邓书实误,及胡氏自为说之误,皆改而正之。”[1]一册352页“盖君勤于考古,又健于游,考地理有疑,辄走数千里,目验而定之。读‘嶓冢导漾’,遂往甘肃而观所谓三洞者,以著于书。书中凡若此者,皆其卓然可传之说也。”[1]一册358页“自来说《禹贡》者,综覆群籍,无如胡朏明;专明郑注,无如焦里堂。君之书又出于二者之外,其所考者,自黄帝而下至本朝,自九州而遍及大地,上下五千年,浑圆九万里,罗于胸中,历历然可指而数也。君之书名曰《新图说》,而写寄方伯者有说无图。”[1]一册359页陈澧在《黑水说》中总结说:“凡考地理者,于边徼之地,必得得国朝康熙、乾隆内府地图而始明。国朝与地之广大,地图之精确,非汉、唐以后所及也”[1]一册18页。
(三)《诗》论
陈澧以《诗》兼孔门四科,“是《诗》兼四科也。《诗》者,乐章也,乐则其铿锵鼓舞也。”[1]二册27页陈澧引证《载驰》《有女同车》等《小序》,指出以上文字简略,故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故认为《诗小序》出自众人之手。齐、鲁、韩三家说《诗》,陈澧指出齐、韩皆非《诗》之本义,“齐、韩诗或取《春秋》,采杂说,非其本义”[1]二册109页。
毛亨《毛诗故训传》、郑玄《诗谱》《毛诗传笺》等是陈澧分析的的研究《诗》的主要著述。陈澧以毛《传》训诂为《诗》之大义,“毛《传》训诂之语,有足以警世者。”[1]二册107页在此基础上,陈澧指出毛《传》训诂的特点有三:一是用“也”字。“毛《传》连以一字训一字者,惟于最后一训用‘也’字。其上虽累至数十字,皆不用‘也’字,此《传》例也。然有不尽然者。”[1]二册105页二是与《尔雅》相同。“毛《传》训诂与《尔雅》同者。然则《尔雅》不尽在毛《传》之前,安知非《尔雅》取毛《传》之文乎?”[1]二册106页三是多载《礼》。陈澧指出郑玄注《诗》的特点有二:一是有感伤时事之语;二是多以《礼》说《诗》。综上,陈澧指出注疏《诗》必须兼取毛《传》、郑玄《诗谱》、朱熹《诗集传》,“不拘守毛、郑,亦不拘守朱《传》。戴氏之学,可谓无偏党矣”[1]二册120页。
(四)《礼》论
《周礼》《仪礼》《礼记》合为三《礼》。陈澧虽然没有注解三《礼》,但他撰有《丧服说》《孔子合葬于防说》《深衣说》《明堂图说一》《明堂图说二》等阐述三《礼》的文章,尤其是他对于《周礼》《礼记》中的《考工记》《月令》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周礼》之名始于西汉刘歆,本为六篇,原为《司空》的《冬官考工记》于汉初失存,汉人取《考工记》代之。陈澧认为,《考工记》有补经之用,正是由于其所记之工事不受重视,中国之物不如外国。“《考工记》实可补经,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记者,以一人而尽谙众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记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视之。惟其卑视工事,一任贱工为之,以致中国之物不如外国。此所关者甚大也。”[1]二册137页此外,陈澧指出,西洋诸器以轮为用是源于《考工记》,“《记》以轮为首,有旨哉。古人以轮行地,今外国竟以轮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图说》所载诸器,多以轮为用。”[1]二册137页《月令》是《礼记》中记述古代制度、礼俗且具有考证性质的文章之一。陈澧指出《月令》非周公作,以《月令》《左传》《周礼》正《公羊》,以《考工记》《月令》为据互相发明,阐述《明堂图》。“《周礼》《左传》咸有‘春蒐,夏苗,秋猎,冬狩’。谷梁家说自有据依。而《月令》孟夏‘毋大田猎’,公羊家说乃非孤证矣。”[1]二册70页“澧谓《考工》《月令》正相发明,盖室方二筵,五室乎列则广十筵,与堂广九筵参差不合”[1]二册40页。
《周礼》主要记述先秦的官制,因此,陈澧以其为古之政书。从刘歆开始,郑玄、孙怡让等经学家都认为《周礼》是周公作,陈澧也有此论:“郑君知《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以《周礼》之中,实有周公之制也。”[1]二册127页《礼记》既释《仪礼》,也有其他儒学家的学术思想。陈澧释《礼记》之“记曰”:“凡《礼记》所言‘记曰’,皆是古有此记也。记之所从来远矣。”[1]二册127页“如此之类,作记者时代在后,其述古事,述古制,述旧说,不敢自专而为疑辞。古人著书,谨慎如此。”[1]二册157页陈澧以为《礼记》有存夏、殷礼之功,“孔子言夏、殷礼文献不足征,而《礼记》尚存此数十条,记者之功大矣。”[1]二册158页《礼记》有大小戴之分,《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不取《夏小正》《曾子》十篇、《千乘》,陈澧认为这是作者的识见。
陈澧指出《周礼》《仪礼》都是有用之书。“此在《周礼》中乃小事耳,而后世行之,足以为民除害,安得云《周礼》不可行乎?”[1]二册136页“读《仪礼》以为不可行,而藉口于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说以破之矣。”[1]二册155页陈澧认为,“《仪礼》,礼之文也。《礼记》,礼之意也”[1]一册106页,故必须分类读之,如“《仪礼》难读,昔人读之之法,略有数端: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今人生古人后,得其法以读之,通此经不难矣”[1]二册138页。
郑玄三《礼》注、孔颖达《礼记正义》、敖君善《集说》、程易畴《仪礼丧服文足征记》是陈澧分析的三《礼》著述。陈澧指出,治三《礼》不能超出郑、贾的范围。因此,陈澧比较郑《注》、贾《疏》之异同有三:一是贾《疏》能用郑君推约之法;二是郑《注》、贾《疏》皆能补经;三是郑《注》、贾《疏》分别以汉制、唐制况周制。陈澧指出孔颖达《礼记正义》名疏《礼记》实释三《礼》,“孔冲远于三《礼》,惟疏《礼记》,而实贯串三《礼》及诸经。”[1]二册179页由于兼重郑《注》、贾《疏》,陈澧指斥敖君善、程易畴删郑注、批郑注之失。“此(按:指元时敖君善作《集说》)删郑《注》而窃其意以为己说,然则郑《注》合耶?不合耶?”[1]二册154页“此(按:指程易畴《仪礼丧服文足征记》)数语可了者,何必刺刺不休乎?”[1]二册154页陈澧总论郑玄三《礼》注的特点有四:一是有宗主,亦有不同;二是并存今古文;三是兼注《礼》、律;四是注经尊先儒、不繁、甚慎。
(五)《春秋》论
《春秋》是周代编年体史著,孟子率先以《春秋》为孔子作,孔子以此使乱臣贼子惧。陈澧激扬孟子《春秋》论,强调经、传结合。“其事、其文、其义三者,不独深明《春秋》。凡后世史学,亦后世史学,亦包括无遗矣。”[1]二册54-55页“且后儒去传解经者,彼其所著之书,亦传之类也,非经也。使古之三传可去,何不并去其自著之书乎?夫圣人之作经,所以必待传而著者,圣人虽异人者,神明而朽没之期亦等”[1]二册213-214页。
汉代古文家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今文学家则反之。陈澧指出,《左传》依据述事,传孔子之学。“《左传》依经而述其事,何不可谓之传?且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1]二册186页陈澧还指出是后人附益致《左传》解《春秋》不通,“《左传》解《春秋》,书法有不通者,必后人附益”[1]二册188页。 《公羊》《谷梁》也是专门解释《春秋》的典籍,但它们与《左传》之记述之传不同,而是属于训诂之传,陈澧也有此论:“盖《谷梁》以《公羊》之说为是,而录取之也。《谷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驳之,或与已说兼存之。”[1]二册194-195页“《公羊》有记事之语,但太少耳。”[1]二册195页“《谷梁》述事尤少。”[1]二册205页《公羊》多有灾异之说,陈澧予以反对:“此乃汉儒好言炎异风气耳,夫自古国家治乱,每意所指,则人将轻视之,复何益乎?其尤谬者,定元年‘霣霜杀菽’。穿凿如此,人岂信之乎?信乎!《公羊》之罪人矣。”[1]二册201-202页陈澧认为,《谷梁》重义例,但多不通。
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春为公羊注疏》是陈澧分析的研究《春秋》的主要著述。其内容有四:一是称许董仲舒以阴阳说《春秋》;二是斥何注以时月日为褒贬;三是斥何注穿凿文义;四是斥何注诋毁《左传》而用之。在此基础上,陈澧提出治《春秋三传》的心得有二:一是宗《左传》;二是平视之。
三、结 语
陈澧虽然对没有著甲部之书是有遗憾的,但一方面,门人桂文灿所著《易大义补》《毛诗释地》《周礼今释》等的内容、体例、命名等都承载陈澧的心血,这在《与桂皓庭书》中有充分体现。“闻欲以仆所说《周礼》八法为大著缘起,但仆所说实未的确,仍须足下审定之。仆以官属为今之属员,但《周礼》官属非尽属员,似今所谓该部、该衙官职。两否两说:官联即今所谓佥同,此无疑义;官常似今之所谓日行事件;官成似今之成案;官法似今之则例;官刑似今之参奏;官计似今之处分。皆不甚的确,祈审定之。有不安处,必须更易乃佳耳。”[1]一册425页另一方面,陈澧视著述为生命,故或屡修其著述,或其著述久未成书。“仆前为《礼图》初稿,从段说,今得足下说及星南之言,须再考索一番乃定。”[1]一册441页“澧为《谷梁笺》及《条例》,亦久而未成。”[1]一册117页因此,陈澧尚有《礼图》《谷梁条例》等未完著述。
郑玄注、王肃注、孔颖达疏以及清儒治《书》四大家等,都是陈澧旨在申明、修正的主要经典。无论是他的亦古亦今的《五经》总论,还是兼及经、传、后世研究著述的《五经》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陈澧以此肃清佛、老学说乱经贼道,以及诸儒释经有违圣学大义,强调《五经》之可行,以期巩固孔子学说地位。因此,宗孔、尊儒是陈澧《五经》论的一致导向,它们是在中国古代经学传统范围内论辨《五经》的。在陈澧之前,徐灏著的《通介堂经说》是广东经学史上留下纵论《五经》的著名经学著述,但徐氏的《五经》论殊非以“调和”为其主要特色,因此,陈澧的今古文《五经》论有其特色与学术史贡献。陈澧在最能反映其个人心态的《默记》中谈到:“澧老矣,所欲著甲部书,无一成者,欲以付后之学者:《周易费氏义》《毛诗郑朱合抄》《周礼今释》《仪礼三家合抄》《春秋谷梁传条例》《春秋三传异同评》《论语集说》。”[1]二册749页陈澧欲著之书,可视为其在学有宗旨基础上去今古文门户的《五经》论的最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