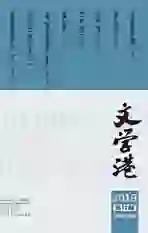何以归
2019-12-20王哲珠
王哲珠
开门后,李慎一头撞进客厅的灰暗里,他愣了一下,刚刚回来路上,街灯已经亮了好一会,家里的灯怎么还没开?家里人都……李慎的念头顿住,他看见客厅里那群人影,像有硬度的黑色物质雕成的,僵直而沉默。不知为什么,李慎伸去按电灯开关的手缩了回来,他试探着喊了妻子的名字,试探着喊了孩子的名字,试探着喊了父亲母亲,没有任何回应,那群影子就那么默默着。
是我。李慎清了清嗓子,尽量自然地招呼一声,像终于记起什么,把灯开了,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列坐在沙发上,望着他,没人应声,表情和目光难以形容,李慎感觉家人变得极陌生。
李慎走进客厅,故意扬高声音,我回来啦。他晃了晃手里提着的几个袋子,袋里装满肉菜。他刚从市场买回来的。
仍然没有人回应他。
李慎将肉菜放下,冲沙发上那列人摊开双手,说他得先去洗个澡,现在不敢沾家里任何东西。李慎的衣服又脏又皱,头发油腻,身上有一股怪怪的味道,他叫妻子帮他拿套家居服,他怕把房间弄脏了。妻子没动,像听不懂他的话,父亲母亲也没动,当他的目光落在孩子身上时,孩子进房给他拿了套衣服,看了看李慎发黑的手,直接把衣服放进洗手间。
李慎洗了很久,用洗发露和沐浴露洗了几遍,当他热气腾腾地换上家居服、把那套脏衣服扔进垃圾桶时,整个人有种重新开始的畅快,他想好好跟家里人分享这种感觉,但走出客厅时,那些分享的语言卡在喉咙出不来,家里人以原先的姿势默坐着,包括孩子,拿了衣服后又坐回去了,好像他们的姿势被什么神秘能量固定住了,要不是他们望着他,他会以为他们连目光也凝固了。
毕竟有些心虚,李慎努力活跃着气氛,问怎么不开电视,说着开了电视,接着抱来奶粉罐,说他饿了,先垫一下肚子,问还有谁想喝点牛奶。李慎就着牛奶吃了几片饼干,家里人依然如旧,电视的声音在他们的沉默面前显得滑稽,甚至有点怪异,李慎听不下去了,关了电视,讪讪地说既然没人想看,就关掉吧,有点吵。
电视关掉后突兀的沉默又吓了李慎一跳,他立在客厅中央,手足无措。看到自己买的那堆肉菜时,他拍了下脑袋,今晚我做一顿好的。
提着肉菜进厨房之前,李慎转过脸,说,我没事,就是在外面走一走,待一待,算是透口气。
说完李慎进了厨房,后背沾着一片硬邦邦的沉默。
李慎淘了米开好电饭锅,开始洗菜,父亲和母亲进来了,父亲厉声质问,你搞什么怪,被绑了还是被抢了?我以为死在外头了。
母亲猛扑过去,抱住李慎的胳膊,慎,到底什么事,你怎么了,怎么了……她呜呜地哭,不住地摸着李慎的头脑,像检查一架机器的零件是否齐全。
他们终于开口了,李慎松了口气。
爸,妈,真没什么事。李慎松说,我就去散个步,散的时间长了些,别操心了。
妻子郑俏俏也进来了,母亲朝父亲使了个眼色,父亲跟着退出去。
我回了。李慎抚住妻子的肩,我其实……
李慎想说一句“对不起”,但觉得这不是妻子想要的。
我只是待一待。李慎对妻子说,语调极温柔,他还想告诉妻子,这是最真实的原因了,但又觉得这话很多余。
李慎肩膀一阵剧痛,妻子咬了他,他忍着,妻子拍打着他的胸膛,拍着拍着,妻子的泪下来了,李慎伸手想为她擦泪,妻子用力扫开了他的手。父亲在外面喊李慎,妻子退了两步,吸着鼻子,擦干了泪。母亲进来让李慎出去,说父亲有事,晚饭她和妻子做。
父亲让李慎打电话,他列了一份亲戚朋友的名单,交代李慎,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好好说。
李慎愣着,跟家里人他能说出口,跟亲戚朋友怎么说?但父亲是对的,这是他该做的,这段时间以来,亲戚朋友帮着操心,帮着打听,帮着奔走,帮着安慰家里人……总之,他们尽了心尽了力,像某种力量帮忙撑着这个出了状况的家,李慎得给一个解释。
幸亏是隔着电话解释,李慎无法想象和亲戚朋友面对面谈论这事。几个电话后,李慎的解释和应答就变得有点程式化了。
听到李慎的声音,那边总是一阵惊喜,然后是一连串的询问,李慎含含糊糊地解释没什么意外,也没跟家里人吵架,更未跟外人发生矛盾,反正,生活的一切都在正轨上,他就是待一待,透口气。
为什么要待一待,家里不能待?单位不能待?亲戚朋友处不能待?有什么待不住的?为什么要透气?有什么让他透不过气?他有什么难处吗?他人感觉不舒服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正常人没事会这样么?
……
李慎在这些疑惑前沉默,他们的疑惑是有道理的,李慎不明白的是,独自待一待、透口气有那么奇怪么?他说的是真话,但像极了假话。他含含糊糊敷衍着,亲戚朋友们最后都表现得很大度,回来就好,别的都不算什么事,先休息。他们的宽容和关心包含了所有的不信任和不理解。
电话没打完,父亲不许李慎吃饭,让其他人先吃。没人吃,都盯着李慎打电话,当打完最后一个电话、走向饭桌时,李慎突然失去了食欲,他潦潦草草喝了点汤就说够了。李慎喝汤时,父亲母亲妻子孩子都看着他,一桌饭菜没人动。
回家之前,李慎逛进市场买菜,他脑子里安排着菜式,有父亲喜欢的,有母亲喜欢的,有妻子喜欢的,还有孩子喜欢的,他想象这顿晚饭的场景,充满了重逢的欣喜,生活重回安稳和日子归轨的通透。
都离开了饭桌,李慎将饭菜盘碗收拾进厨房,出来时,都各回各的房间了。孩子应该在学习,经过父母房间时,听到低而急的对话声,听不清内容,但李慎知道肯定跟自己的事相关,他急急走开,好像自己是个窃听者。他小心地打开自己的房间,扭门锁时有种奇异的陌生感。妻子缩在床的一角,他进去时,她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又飞快地垂下头,好像他是什么怪物。
李慎上床,慢慢挪到妻子身边,他知道自己不對,他得抱抱她,为这段时间以来她所有的担惊受怕、奔波劳累,他确实过分了,可他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李慎从后面抱住妻子,妻子肩膀猛地一抖,不知是愤怒还是恐惧。李慎紧了紧胳膊,妻子用力从他怀里挣出去,转过脸,直视他,为什么?
我想待一待,透口气。李慎看着妻子的眼睛,重复着说过的话,真的没什么事。
妻子哭起来,揪住李慎的衣领,好一个待一待、透口气,李慎,整整两个星期,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了,没有半个字,没有半句言语,手机手机打不通,借问借问不到,警察翻监控翻不到,城里找城外找回老家找,就差掘地三尺了……
妻子捂住脸嚎啕,李慎再次抱住她,她再次挣脱了。
李慎让妻子哭,他想,她的哭或许像自己的待一待透口气一样。
妻子却很快止住了声,擦干眼泪,重新抬头看李慎时,目光变得尖利,声音却压得很低,李慎,你告诉我实话。
李慎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说,我说的就是实话,就是想……
够了。妻子烦躁地挥了下手,别编了,你就是编谎也编得像样点,这么长时间的折磨,我要一个解释不过分。
李慎不停地解释自己已经解释过,不停地重复那个解释,不停地强调就是那样,那样简单也那样说不清楚,但他越强调越心虚,他发现这真实、简单又说不清道不明的解释在别人听来是如此不靠谱,甚至是荒唐滑稽的,李慎的声音渐渐变弱,终于完全沉默了。
无话可说了?妻子冷笑一声。
相信我。李慎说。语气里几乎带着恳求,我是过分了,但我说的是真的。
妻子开始为李慎的突然消失想象理由。
猜测李慎在外面有了别的人,这是最庸俗却是最普遍的理由,某个女人把李慎绊住了,这段时间李慎和那个女人或许去了某个遥远的地方,或许隐在某处过一种别样的日子。这种猜测让妻子有些歇斯底里,她双手揪住被子,浑身颤抖,若不是李慎及时把她拉回来,她将沉在自己编织的戏里无法自拔。猜测李慎工作或许遇到什么大麻烦,可李慎在那样的单位那样的岗位上会有什么麻烦,妻子想象不到,但这种猜测让她心酸,她看李慎的目光突然变得柔软。还有一个猜测是李慎厌倦了这样的生活,这生活里有自己,他对生活对自己不满,以致想逃,自从有了这个家,她用心用力地经营着,这家从未有过真正的风波,她以为是如此安宁稳当,这一切李慎看不到感觉不到也不珍惜。妻子再次被情绪带走了,又大哭起来。
为什么?郑俏俏摇着李慎的肩。
这次,李慎抱住了脑袋。
整个晚上,李慎似睡非睡,迷迷糊糊中一直听见妻子的抽泣声,他想安慰,但嘴巴像被什么粘住了,他想揽住她,以前她生气时,他只要把她揽在怀里,静静待一会,她大多会消气,但他双手无力,用尽力气终于碰触到她时,又被她甩开了。
熬到天亮,李慎整个人有种虚脱的疲累感,但他松了口气,窗外的亮色带来某种类似希望的感觉,也许是黑夜让人的情绪压抑了,稍缓缓会好点的。
李慎决定做早餐,以一顿正常的早餐重新开始正常的日子。
白米粥、蒸馒头、煎鸡蛋、瘦肉炒咸菜、花生米,很像样的一顿早餐,东西摆上桌时,李慎有种岁月静好的满足感,他立在客厅大声唤家里人吃早餐。陆陆续续地起来了,但没有李慎想象中的安稳,而是安静,过分的安静,甚至有种怪异的小心翼翼。看孩子吃完离桌,李慎忙跟着离桌,准备送孩子去学校。
跟到门口时,孩子告诉李慎他自己骑车去学校。
骑自行车?李慎很惊讶,虽说孩子已经上初一,但家里离学校挺远的,又都是热闹的大路,一向是他开车接送的。
孩子说买了辆自行车,他已经骑了一个多星期,习惯了,说以后上学他自己骑车就好,让李慎只管上班。孩子的口气又懂事又陌生,让李慎很不舒服,印象中孩子一向不算太懂事的。就是说,这段时间妻子没法接送孩子,孩子就这么独立起来了。
以后还是我送你上学,太远,路又热闹。李慎说。
孩子穿着鞋子摇头,说他没问题的,每天可以早点出发,不会误时间,骑车还能锻炼身体。孩子冲李慎摆摆手,出门了。
李慎突然有些空落落的,对于这段时间,孩子没有追问他,但他知道孩子有孩子的想法,更失落的是,孩子不会说出想法,只是客气。
有些事情变了。李慎不得不承认,等到回去上班后,这种感觉再无法回避,他再无法欺骗自己。
对那段空白时间,单位早就清楚了,并配合妻子帮忙寻找过他。离开前,李慎是向单位请了公休假的,两个星期,理由是大学同学聚会,在一个旅游景点很多的省,他顺便走走,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真正出门放松过。单位批了。两天后,李慎的妻子找到单位,请求帮忙寻找李慎,大学同学聚会是李慎编的,跟李慎的大学同学联系过,证实了。
进单位时,李慎高声打着哈哈,像平日一样招呼同事,半开着玩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他努力忽略那段时间,同事们欢快地回应,配合着李慎,也努力忽略那段时间,李慎的笑不自在了,想放放不下,想保持保持不住,就那么僵着,扯成怪异的表情。他看到同事眼里怪异的神情,但和他一样,脸上却带着若无其事的笑意,形成强烈对比。
像以前那样,李慎闲闲地沏了杯茶。边喝着茶,边有意无意地说,出去待了待,透口气,也没别的事,女人就是爱大惊小怪。
人是该透透气,要懂得享受。有人回应李慎,带着共鸣的语气。
有人点头,点得格外用力。
有人冲李慎微笑,努力笑得很真诚。
他们都表示相信,相信李慎没什么事,这段时间的空白没什么奇怪的,李慎的胸口沉下去,他知道最真实的理由被看成最荒唐的理由。
办公室安静了,每个人都忙着干活的样子,李慎一口一口地喝茶,茶很烫,但他喝得快极了。有人来捎话,说领导让李慎去一趟办公室,他如释重负地放下杯子,很高兴地想,或许有什么事要干了。
单位领导先是上下打量着李慎,關心地问他一切是否还好。李慎表示很好,一切都正常。领导很快变得严肃,提到李慎失踪的这段时间,虽然请了公休,但李慎的妻子将他的失踪报到了单位,报到了警察局,已经从个人事件变成集体事件,领导要求李慎对这次失踪做解释。
李慎解释了,说出那个真实的理由。
领导长久地沉默着,目光垂在茶杯里。
就是这样的,没别的事。李慎打破沉默,认真地说,他怀疑领导刚才是否听清楚了。
领导抬起头,狐疑地盯着李慎,盯得李慎莫名其妙地心虚起来。
确实没别的事,就是待一待,透口气。李慎重复着那个理由,重复完又后悔了,每重复一次,理由就变得更加可疑。
领导让李慎写一份报告,详详细细写清这段时间待在哪,做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怎么想的,也就是他的思想动向,要交代得明明白白。
念头是在一个深夜起的,那天晚上李慎的睡眠突然断了,翻了很久的身都没法重新睡着。他起床去了客厅,一个人在黑暗里坐着,竟感觉很好,那个念头随之而起。开始,他被自己吓了一跳,但很快激动起来,他还算理智,没有当即跑出去,而是开始做计划,天亮时,计划成熟了。
李慎请了公休,去了公园附近一家超市,进洗手间换了衣服鞋子,令他高兴的是,那天刚好下雨,他从地下车库出来时可以撑伞,换衣加上撑伞,监控里果然没查到他进超市之后的动向。出了超市停车场后,李慎就进了公园,找一个监控死角换了把伞,选择一条浓密的林荫道,他很肯定,那林荫道也没有监控。
李慎在公园后山脚下那片偏僻的小树林待了下来,那片小树林安置着不少石椅,但很少有人,偶尔有些流浪汉呆着,或有些寻找安静地带的情侣。要说李慎做了什么,他确实什么都没做,就是在小树林里走走,在长椅上呆坐,让脑子变得空空的。有风时让风吹,有太阳时让太阳晒着,有雨时让雨淋着,说不清的舒服自在。
才几天,胡子就把他的脸弄得苍老陌生了,他在某张长椅上捡了顶皱巴巴的鸭舌帽,扣得很低,走路时故意半弯着腰,熟人迎面而来也认不出他了。李慎开始在公园的垃圾桶里翻找,晚上还到公园外面路边的垃圾箱翻,找到的废品卖出去,买了面包、方便面和水之类的食物。有时,垃圾箱里还能翻到未拆封的点心饼干之类的食物,有的过期了,有的接近过期,李慎一一收起,吃了,他没想到竟会这样不在意,以前他还挺讲究的。这么吃着,也没出什么问题。
天气热,他在长椅上过夜感觉刚刚好。困了睡,睡到自然醒,饿了吃,随便吃,别人只当他是流浪汉,没人好奇,没人理睬。有时李慎会变得恍惚,原来这也是日子的一种,过着这种日子的真的是李慎?
就这样,过了两周。李慎觉得够了,想回家了,回归原先的生活轨道,那天早上,他在公园的湖边稍稍清洗了衣服,处理了胡子,傍晚,他离开公园,去了市场,用离家时带出来的几百块钱买了肉菜,然后回家,像平日下班那样。
这就是过程了,两个星期似乎很长,但这两个星期李慎过得极简单,处于没有故事的状态,没什么好描写的。
接下来该写思想动向了,领导将这部分列为重点,自己有什么思想动向?李慎疑惑了,那两个星期,他的脑子大多数时间处于放空状态,他没有思想可汇报。
李慎的报告没有过关,两个星期的行踪是交代清楚了,没有犯错,何况李慎又请了公休,目前看来李慎的身体也没受到影响,所以这部分没问题,成问题的是思想动向没交代清楚,不,是根本没有交代。李慎表示自己没想什么特别的,领导认为不可能没有思想动向,有这样超出常规的行为,肯定有超出常规的思想。这是单位需要了解的,是单位的责任。
李慎有种预感,他再无法完成这份关于思想动向的报告了。
晚上,李慎家坐满亲戚朋友,都是在李慎失踪期间为寻找李慎想过法子、奔波过的。李慎回家了,他们来关心他,看望他。没有明说,但他们的慰问里、拐弯抹角的询问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想知道李慎究竟是怎么了。若是别人这样还好理解一些,李慎不该啊,他们认识的李慎温文有礼,极懂得人情世事,对人很有心的,他运气一向也很不错的,在一个不算很知名的大学毕业后,顺利进了现在的单位,单位工资不算高,但毕竟是政府部门,他也干得不错,这两年小有升迁,工资也跟着升,李慎的父母都是有退休工资的,李慎的妻子也是有单位的人,只有一个小孩,生活滋润小康。按理说,李慎不该怎么样的,没什么想不开的。
李慎煮水沏茶,招呼着亲戚朋友,面带微笑,接受问候,接受安慰,脑子边飞快地转着,编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理由,好给这些热心人一个交代。
换第二泡茶时,李慎开口了,确实是有点事,一时糊涂。
客厅猛地静下,所有的目光敛成一束,直直射在李慎身上。
李慎开始谈论自己的工作,是如何琐碎无聊,没有年轻时想象的激情和意义,工作上的人事处理是怎样微妙困难,他工作得如何压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规矩小心。李慎说自己这么些年憋得太累了,就想松口气,那天脑子一糊涂就请了公休,想着先到公园散散步,觉得那地方不错,就待下了。
亲戚朋友们点頭、柔声附和,表示理解,万分理解,谁的工作那样称心如意呢,谁都有难处,可在职厌职也是正常的,意思是李慎说的那些问题其实算不上问题,他小题大做了。
亲戚朋友又说累了就休息,放松放松当然是该的,请个公休四处走走调节一下很好的,可得明明白白地调节,这有什么好瞒的。以这样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告诉李慎,像他那样的放松是不对头的。
亲戚朋友还比长比短地分析了李慎那份工作,说到底算是一个美差,工资还算可以,又不太忙,也不用担什么责任,安安稳稳,总之,一般人该知足的。李慎半垂着头,为自己的不知足羞愧。
亲戚朋友还是不信,但这个理由毕竟比之前那个靠谱得多,这就说明李慎正常了些,他们安慰李慎的同时,苦口婆心讲了很多道理。
李慎表示全盘接受。
母亲和妻子做了一桌好菜,招待了那群亲戚朋友。话说得差不多了,饭菜也吃足了,亲戚朋友陆续走了,走之前用目光或拍肩膀,对李慎表示鼓励,也表示宽容,对于他新的解释,对于他的“真诚”,他们终究是存有疑惑的。
碗筷收拾干净了,孩子在房里学习,妻子去洗澡了,父亲母亲在李慎面前坐下,看着他,李慎知道自己逃不开了。果然,父亲开口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慎装着专心沏茶,暗暗呼了口长气。
慎,你怎么就不能告诉我们。母亲声音哽咽。
李慎的头皮开始发麻,杂七杂八的念头在脑子里搅动。
就是日子过得腻了,出去透口气。李慎突然脱口而出,语调里含着赌气的味道,他自己也弄不清这话是真是假。
过腻了?母亲被李慎这话吓着了,猛地扬高声调,很快又意识到什么,抿紧了嘴,但眼睛里的惊恐却更浓重了。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李慎忍不住叹了口气。
那是哪样?父亲声音里含着怒意,过腻了!亏你说得出口。
父亲谈起从小到大未让李慎吃过什么苦,谈起两个姐姐对他的疼爱忍让,谈起工作的顺利,谈起妻子把家里安排得有条有理,谈起孩子成绩不错又懂事……
父亲谈了很多,总之,李慎嫌弃日子是毫无道理的,一切问题出在李慎身上。他要知道的是,李慎到底出了什么問题。
问题又绕回原点,父亲母亲不接他给的理由,李慎给父亲母亲各端了杯茶,逃似的进了自己房间。
妻子在房间里等着李慎。
我要求的不多,给我句实话。妻子看着李慎,语调冷冰冰,她失望的目光让李慎胸口发痛,他不知道自己的目光里是不是也充满失望,想到和妻子以这样的目光看着彼此,李慎有某种窒息之感。
李慎想告诉妻子,昨晚他说的就是实话,当然,有些情绪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只剩下那么一句话,但都在那句话里了,虽然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话到喉头却又吞下去,真实是经不起强调的。
十多年的夫妻,十多年的生活。妻子说,不值得一个解释?
俏俏,别这么说。李慎望着妻子,几乎有些恳求。
妻子看着他。
我一事无成,人已中年。长时间的沉默后,李慎开口了,一旦开口,李慎就陷入自己编造的理由里,语气和情绪都变得沉重。
李慎讲起自己的大学时代,虽然不是什么学霸尖子之类的,但也是意气风发,对未来有无数想象和设计,想象过自己会变成稍稍不那么平庸的一个人,至于怎么不平庸,他没有具体概念,可以肯定的是,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平庸者,他几乎可以一眼看到生命尽头。那天,他和几个朋友喝酒,谈起这个,越谈越激动,越谈越沉闷,他突然想找个地方,好好想一想。
我其实没想好要想什么,就是打算找个地方找个时间想。李慎说,你知道,这事很难说清楚,而且连我自己也觉得说出口怪怪的,所以我干脆没说,也是我糊涂。事后,我想说,可几天过去了,我越不知怎么开口了,因为我还没想清楚,就那么拖着,一拖拖了这么久,什么也没想出来,可又好像想明白了,人一辈子不就这样么,过日子不就这样么,怎么样就是平庸,怎么样就是不平庸,很多成呀败呀还不是人定的,所以我回家了。
李慎说完,看着妻子,妻子点点头,说,我明白。
李慎知道,妻子其实不明白,她毫不掩饰脸上带点冷意的疑惑。
睡吧。李慎说。他躺下去,扯扯妻子的胳膊,李慎想抱抱妻子,空调开得很低,他想和妻子一起感受被窝里的暖意,他相信在这样的拥抱和暖意里,很多心结会消融掉。
妻子躺下了,但轻轻抖掉了李慎搭在她肩膀上的手,并转过身去,背对李慎。
两人沉默着。
不知多久,妻子突然提起李慎以前的女友。李慎觉得莫名其妙,那是多久前的事了,是认识妻子以前的事了,他已经忘记了她的长相,忘记了两个人分开的原因。李慎觉得又好笑又好气,他拥拥妻子的腰,妻子很怕痒,平时只要胳肢她的腰,她会笑得身子发软,但这次她没笑,而是烦躁地缩了缩身子。
妻子接着谈起他们近几年的生活,两人间怎样渐渐地淡了,有些时候甚至是各人过各人的日子,很多事不跟彼此说了,不,根本没怎么沟通。妻子说,她有时看着李慎,莫名地有点害怕,觉得怎么跟一个陌生人在同一张桌吃饭,同一床睡觉……
李慎的手慢慢从妻子身上挪开,他觉得空调开得太低了,冷气渗入他的皮肉,把内脏和骨头都冻得发僵。
又不知多久,妻子睡着了,她半缩着身子,双手半抱着双肩,睡姿充满忧伤,李慎却再没有勇气抱住她。
天很快又亮了,李慎做了早餐。父亲母亲一大早出去晨练,只有孩子吃,而李慎也一起吃。
给孩子夹煎蛋时,李慎说,其实那件事是我跟朋友打赌。
李慎告诉孩子,他和几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聚会,讲起小时候的种种淘气,感叹转眼之间就成人了,突然想再淘气一次。不知是哪个人提起打个赌,赌敢不敢消失一段时间,就像小时候几个人在山上的小土屋过夜。李慎说主要因为是小时候的朋友,他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脑子一热就决定赌了。没别的什么,就是个玩笑,结果玩大了。
李慎看着孩子,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荒唐了。孩子看着李慎,轻轻地点头,李慎在孩子眼里看到某种宽容,那一瞬间他错觉自己和孩子换了位置,他成了孩子,而孩子成了父亲。
背着书包出门前,孩子对李慎说,爸,我自己上学真没问题的。他的口气温和得让李慎羞愧。
第三天,李慎重新给了解释,这次,给所有人的解释都是一样的。
一连几天,李慎感觉人不太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不好,就是很疲倦,浑身没力气,打不起精神,极想睡觉又睡不安稳。他看了医生,吃了几天的药,不见好。那天,办公室一个同事谈起一个朋友,正当壮年,突然一头倒下去,走了。于是,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感叹急病大病的可怕,感叹生命的脆弱,感叹人到中年的危险性。这些感叹变成灰色的烟雾,越来越浓重地笼罩住李慎,他的身子越来越不对头了。
第二天上午,李慎请了假,直奔医院。
检查结果,李慎得病了,治不好的病。
世界漆黑了,大脑空白了。
李慎在路上绕走了几个小时后,回单位请了公休假,然后换装去公园,找了张长椅静静躺着。他准备就这么躺下去,不惊动家人亲戚朋友,不让他们把他送进医院,去接受一堆奇奇怪怪的检查,不让医院把他困在病床上,穿着枯萎般的病服,浑身插满管子。他说想自己度过最后的狼狈日子,他走了,亲人朋友一开始会很突然,但这样也大大缩短了他们痛苦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适应没有他李慎的生活。
一个多星期后,李慎发现不单疲倦感没有了,胃口还越来越好,精神饱满。一开始,他认为是病情恶化前的平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又过了两天,精力反越来越充沛了,他决定去另一家医院复查。
复查结果出来,李慎除了血压稍高一点,别的什么问题也没有,也就是说,之前是误诊。
所以李慎回家了。
这个理由一出,李慎在很多眼睛里看到了信任和釋然,虽然都说他处理方式糊涂,却对他这次出走给予了理解。紧接着,安慰来了,关心来了,同情来了,这就对头了,李慎脑子没问题,性格没问题,行为也不怪异,一切正常,只是身体不好。这个社会,现在这种生活节奏生活习惯,谁的身体没有一点问题呢,一时间都起了深深的感同身受。身体不好是该受照顾的,所有的好意都给了李慎,好意像密实的网,把李慎裹缠得透不过气。他一次次强调,没事了,是误诊,
强调的次数多了,开始有人起了另一种怀疑,有可能李慎真的病了,故意说是误诊,其实他病得很严重,若不是这样,怎么可能像流浪汉一样在公园待了两个星期?他一向可是个正常人。
这种怀疑很快传染了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他们开始对李慎各种直接的询问,拐弯抹角的探听,各种察颜观色,要弄清楚李慎真实的身体状况。不知谁最先提出,要看李慎的身体检查报告,包括误诊的那份和后来重查的那份。
李慎没想到,事实被这样当真。
两份检查报告都丢掉了。李慎这话出口时已觉得荒唐。
家里人当真到底了,母亲先是一次次缠问是不是确实没事,接着让李慎再检查一次。这个提议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
李慎不肯。
再检查一次。妻子说,她声调不高,但每个字都结结实实的。李慎没法摇头,当李慎提到准备在公园里度过最后的日子时,妻子的目光充满失望和责怪,她说没想到李慎在那样的时候没想到家里人,没想到她,在李慎心里,家里的人算什么?妻子已经是有怨意的,愧疚让李慎点了头。
李慎决定再检查一次身体,所有人等着看他的报告。
妻子负责监督,前天晚上十点之后不吃东西不喝水,第二天一早陪李慎去医院,这个城市里最权威的医院。
和妻子走进医院时,李慎突然有些恍惚,四周有些晃,迎面而来的人有些面目模糊,他是真的病了吗?他有扭头跑掉的冲动。
拿到检查报告就能让所有人放心、结束这一切吗?李慎问自己,他很清晰地否定了这个顺利的想象。当检查报告到手之日,不管是什么结果,新的怀疑将冒出来。
李慎站住了,喃喃着,真的没别理由,就是待一待……
妻子几步赶上来,扯住李慎的胳膊,说,快点,可能得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