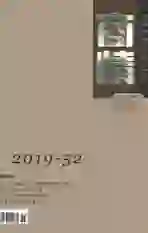论地震伤残儿童之长久性心理创伤
2019-12-17张旭明
张旭明
【摘要】汶川大地震后,残疾学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怀,在上海市的援建下,由张海迪题写校名、全国唯一一所专门接收地震残疾学生、设施无障碍、残健融合、全纳式九年义务学校——“都江堰友爱学校”拔地而起。学校有先进的残疾学生康复室,有香港“无国界社工”开设的心里咨询室,有专职的“生活老师”,有“残疾人绝技艺术班”、“五彩基金书画艺术班”等特色社团,十二部电梯分布全校,轮椅能到达每一个教室,有一百多位不是父母胜是父母的关爱残疾生的教职工,软硬件设施世界一流。但经过观察与思考发现:她们残疾肢体的康复、刀削斧砍般心灵创伤的抚平远比我们想象的难!所需的时间远比我们估计的长。
【关键词】关于无障碍 关于伤残治疗 心灵深处之痛
1、关于“无障碍”
都江堰友爱学校的各种设施都按照“无障碍”标准设计,但对于残疾生来说真的就无障碍了吗?为此,学校最近专门组织老师们坐轮椅、用拐杖,老师们得出的结论是:轮椅、拐杖本身就是一种障碍,再先进的轮椅遇到几粒石子、一个小坎、一滩水也是一个大麻烦,再先进的拐杖放在课桌旁、放在床边也会碍事。当我们坐在轮椅上尝试捡起掉在地上的一串钥匙轮椅险些倾覆时、当我们只使用了五分钟拐杖而手臂胀痛酸麻时、当我们学着残疾生用嘴去翻书、用牙去穿衣时,我们才最真切的感受到残疾学生在生活、学习上的艰辛,领悟到“无障碍”永远是相对的,只能是将残疾学生不能完成的事因有了“无障碍”而变成经努力而能够完成。我们正常人上二楼不觉得是一回事,很轻松,而残疾学生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推着轮椅上二楼可能要付出十倍的力气。所有从事残疾学生教育的人士都应该首先坐坐轮椅、用用拐杖,接收一次心灵的洗礼,才能从心里涌出关爱。在此我呼吁,大家一定要爱护好为残疾人修建的各种设施,不能随便破坏和占用,不能再有人为的障碍。
2、浅谈伤残治疗
许多人认为残疾学生们只要伤好了就完事了。但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一位专家曾问老师们:“有多少老师做过手术时的麻醉、做过全身麻醉?感觉如何?”只有个别老师回答生小孩时或拔牙时做过麻醉,感觉非常不舒服,可能会伤到神经,影响大脑记忆。而我校一些残疾学生做过多次全身麻醉,而一些做了截肢手术的残疾生,由于正处于身体生长发育期,过一段时间就得做一次手术以防止快速生长的骨头刺破皮肤长出来,也就意味着今后还会面临多次手术和麻醉,这对他们大脑、记忆有多大影响呢?我们正常的人有个伤风感冒都会影响工作、学习,我们正常的人有个脚崴腰伤都可能停下工作,何况残疾的小学生们?他们有的体内还带着钢钉,有的残疾同学每当天气变化,伤残的肢体就会疼痛,还要去克服假肢与残肢磨合带来的伤痛。可以想象他们将用很大的毅力和很多的精力去克服常人无法体会的困难,去坚持学习。
3、关于心灵深处之痛
汶川大地震后,都江堰友爱学校来过很多从事心理研究的人士,他们对于残疾生早期应急心理治疗、中长期心里康复功不可没。但残疾学生心理问题其实还很多,其严重程度往往因人而异,与肢体伤残程度也不一定成正比,要获得“康复”可能还需很长的时日,甚至可能是终生无法抹去的“痛”。例如我们一般的人不会感觉到“灰尘的味道”,但来自汶川映秀镇的周玉烨同学,因为在地震后倒塌的教室里埋了近三十小时而对“灰尘的味道”极其敏感,直到现在,甚至教室里打扫卫生扬起的“灰尘”也会让她联想到教室倒塌后呛人的恐怖的“灰尘味道”。一位来至北川的同学,地震时被埋在教室的废墟中,同学的血滴落在她的脸上,因此至今她对红色的液体、对温暖的、滴落在皮肤上的液体感觉十分惊恐。我们能够给残疾生修建好的学校,提供学习用具,保证较高的生活质量等等,但我们无法提供他们因肢体的伤残而失去的很多东西,例如当女孩们夏天都穿上漂亮的裙子时,来自汶川映秀镇,高位截肢失去双腿的张春梅同学曾因无法再穿上漂亮的裙子而伤心、落泪。当看见男生们穿着球衣在球场高兴的打篮球时,来自都江堰,过去喜欢篮球,在地震中左手、左脚严重受伤的王治荣同学眼中流露出羡慕和失落的眼光,因为他不可能再飞奔在心爱的篮球场上。我們能给孤残学生以老师的关爱,但无法代替家庭、父母的爱,例如每遇节假日学校放假,就会有众多的家长来校接自己的孩子,家人相聚,孩子在父母怀中撒娇,隆隆的亲情…这时是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们最孤单、苦闷、痛苦的时候,因为任何爱都无法取代和超越父母的爱,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心灵伤痛。
关爱因地震而残疾的学生,是我们心声,是全社会的共识。关爱的前提是对他们详细的了解、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关爱他们是一种系统工程,需要大家真心付出,需要时间。残健融合不只是一句口号,需要大家协力。根据研究观察发现也有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如有的老师不愿意自己的班级里有残疾孩子,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关照、责任和麻烦,也担心影响升学指标或成绩排名。有些家长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残疾孩子同班,觉得他们会拖累全班的进度和成绩,甚至荒唐地担心自己的孩子学到残疾孩子的不良习惯。有的学生也对“残疾”二字很排斥,如最近我们在搞一个问卷调查时,有的学生在上面写道:“这些问题很无聊,我不是残疾生”。以上现象虽然是少数,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看到残健融合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的看到它的任重道远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