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风物三题
2019-12-17刘志平
老茶馆
故乡蒲镇有一条老街,一条南北走向青石铺就的老街,因其长而窄,俗称扁担街。扁担的中心叫五世坊,也叫中心街。这里店铺云集,有做南北货生意的玉源昌老字号,有百货店,茶食店,布店,饭店,当然最具人气的就是我外公顾福康开的茶馆店了。
茶馆坐南朝北,门面宽敞,一个大厅可摆十张方桌,不似现在茶楼雅座包间私密,众人聚在一起,很热闹。大厅西头有一四角见方的土炉子,一如汪曾祺先生在《沙家浜》剧中写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那土炉上确实有七孔炉眼,像放大了的蜂窝,上面坐着七把锡铫子,不是铜的,我想外公小本生意,他置不起那铜铫子,但煮的水倒是正宗的长江水。每天大早,天还蒙蒙亮时,外公就卸了挞子门,点火生炉煮水。挑水的小陈,晃晃悠悠地挑着两桶清凉凉的水注进那两口大缸里,打上钒,水更清澈。水烧沸后,七把锡壶的嘴儿争先恐后地吹起欢快的哨音,欢呼着茶客早点到来。
天亮了,茶客不邀而至,有做生意的,有摸鱼打铁的,有跑腿帮闲的,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但同一个嗜好,喝茶,品茶,闲聊,会友。
外公茶具,颇有特色,有白底红花图案,明代的,有蓝底青花瓷画型,清朝的,全一色的盖碗,上面绘有才子佳人的图案,衬着碧绿的茶水,舒展开的茶尖,让人赏心悦目。
茶客上座,外公拎一茶铫,手向上一扬,一股清流倾注入盅,合上碗盖,待茶色开,茶客打开盖碗,用盖碗边沿,手腕一摆,把浮在碗面上的茶叶稍稍往边上一拢,轻轻吹一气,慢慢地抿一口,用舌尖尝一尝,于口腔内温柔一下,方才咽下,眯着眼细细品味:不错,是那正宗的雨前茶,好茶。
茶客边品茶边聊天,说的是古今逸事,家里长短。此时茶客很斯文,没有平日的粗鲁,持谦谦君子样,即使为一些邻里纠纷,借茶馆来评理诉讼,声音,言词也不激烈,用词也很斟酌,往往在几个老年人的劝说下,调和下,一杯茶的功夫,两家言归于好。
喝茶,品茶,修生,养性,说古论今,于人于世,好处多矣。
不知道我外公置办多年,多方收集的茶碗中,是不是有着正宗的明代清朝,如今已罕见的盖碗,我不知道。如有我并能将其收藏,多好!以此纪念我的外祖父。在我的记忆中,那些绘有才子佳人还有人物故事的盖碗实在是太好看了,儿时的美好印象让人难以忘记。
如今镇上已无一家茶馆,有的则是时尚的咖啡馆,那是年轻人聚会的场所。是另一种品味。不过在小巷深处,老宅院里还有三五个喜欢喝茶的老年人,常常驻在一起品茶聊天,当然这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茶室。在我的心里,它远远比不上我外公在解放前创业的顾家茶馆了,可惜顾家茶馆它终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小小的茶室或叫为茶座,可否算是一个小小的补充,聊补于无罢了。
我想念我外祖父的顾家茶馆,我在茶馆里度过了我幸福的童年,亲耳聆听了茶客讲的好多古今中外的人物和故事,知晓了许多历史的演变和兴衰。
剃头店
蒲镇有一条古街,一条逼直狭窄的青石板街,街两边挤满着高高矮矮,错落有致,参差不齐的民房和百年老字号店铺。薛家剃头店是其中的一家。薛家剃头是祖传,手上功夫了不得,修面,扒耳朵,堪称一绝。许多老顾客均是冲着这一手来的,图的个快活,惬意。躺在那清凉凉的木椅子上,任薛老爷子的剃头刀在头面上游走,那张剃胡刀闪着银光,亮闪闪的,却不像手术刀让人心寒,生畏,刀与脸亲密的接触,让人感到亲切。
薛老爷子的刀极少在人头上脸上划下口子,他从小就学会了用刀,刀峰捏得很好,在耳背,耳朵眼儿,鼻子,喉结,眼皮这些地方,都能极好的掌握好刀峰。刀峰直了很容易划进肉里,刀峰偏了,又剃不掉头发。刀峰得恰到好处,得顺着头皮抹过去。这就得讲究个度,这度偏偏又最难掌握,得凭心和手的感应。打小他父亲就给他一块狗皮,叫他蒙在木桩上练,狗毛丝子粗,和人的头发差不多,再后又教他用羊羔子皮练,羊羔子皮毛细,和刚满月的娃儿胎毛差不多,由此几十年下来,薛老爷子的手艺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了当地理发业的一块招牌。
前几年古镇新建了一条大街,许多店铺搬迁,老街自然冷落了许多,薛老爷子依然在这老宅子的一亩三分地上守候着那些老顾客。兒子却与他分怀二心,儿子不屑于这祖传的手艺,功夫再好,终究是一个剃头匠。中学一毕业,就进了国企,是一家几千人的大企业,气派,宏大,让儿子自豪了不少。可惜前几年不经意间破了产,儿子下了岗,工作不好找,只得跟了老爷子干上了祖业,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学了一点皮毛,就跑到外面学了一手的烫发,焗油,染发的新工艺,新技术,可惜无资金,买不起一间店面房,只得与老爷子同室操戈,分庭抗礼,所好歪打正着,有了祖传的名声又有了新潮的工艺,还吸引了不少新顾客。
当然老爷子也很固执,同样不屑于儿子所谓的新工艺,全是些化学的东西在骗人,自管自的,在那些老顾客的头顶上显示他的绝顶手艺。
今年初,老街全部拆迁,老宅子补贴了三十万。正中儿子下怀,儿子在新大街买了一间店面房。很潇洒地置了一套新式的理发设备,为那些时尚新潮的帅哥靓女们打理出一个又一个的时尚漂亮的发型。
不过在那间窗明几净的空调房里,儿子还给老爷子留下了那张老式的木头理发椅。老爷子没有退出他的历史舞台,照样在那些老客户的头顶上展示着他的手艺,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五元一位。
就这样传统与时尚冲撞,抵制着,交织地统一在同一屋檐下,似乎是那样平和地向前发展着,那间新店面房,还是挂着那《薛家百年剃头店》的老招牌。里面进出着各式各样,时尚的,守旧的,男女老少爷们儿。
桥候烧饼
烧饼可为早点可为晚茶,乃是人们用于果腹的一大众食品。然而桥候烧饼却是本镇那些讲究美食美味吃货们不二首选的佳肴。
早上和傍晚,桥候烧饼店人气最旺,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那些等着吃上一口刚出炉的热烧饼的买家。大早,老常客则早早地泡上一杯上好的龙井,稳笃笃地坐在那里,等着。烧饼一出炉,当然先让着这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常客,老人们则慢悠悠地嘬上一口,细细地品味,再抿一口茶,看着那些急吼吼的年轻人,抢先咬一口,烫得嘴直吹气,两手捧着烧饼像托着他刚出生的婴儿那般地小心,生怕摔了她娇嫩的身子。烧饼酥,托不好,则散成两半,丢了屑少了芝麻。可烧饼得趁热吃,才更香更酥更虚和。老人看着笑了,吃完后忘不了把那桌上的烧饼碎屑和芝麻拢进嘴里,心满意足地抹抹嘴,才算完成了这一天必修的功课。遇到老熟人打个招呼:去吃桥候烧饼了?
桥候烧饼出名久矣。
橋候是其小名,不知是因桥候烧饼店位于南大桥桥头,桥头桥候音似,还是小时候他老子给他取的小名,无需考证。总之不管是桥头烧饼还是烧饼桥候,两者已混为一体。乡亲们叫着顺口奔着好吃而已。桥候烧饼店面上的四个红漆堂堂的大字,头昂着高高的,成为白蒲镇美食一张响当当的招牌。在外工作的游子,求学的学子,乃至去外地走亲访友也要捎上这桥候烧饼。而桥候也很时尚,与时俱进,可以网购。
桥候烧饼生意红火,在于桥候精工细作,以质取胜。做烧饼不难,难的是做好,这要用心。怕吃苦,为讨巧,可用电炉烤,只要按按按钮,烧饼就出了烘箱。可那烧饼结实僵硬,好像就少了点桥候手心贴着把送它喂进炉子里的那一份亲切的手感味,少了点灵性,少了那份相融相知的口感。难怪人们说机器的终究没有人手做的好吃。
桥候依然用着那传统的泥巴糊得厚厚实实的炭炉子,这火炉不泄气,火头足,炉口不能大也不能小,大则火散,小则不拔火,不易全景式地看到烧饼在炉内的状态。
每天桥候起大早,先是拌面调酷,这酷得使劲地揣,要把它揣得发软发松,要让酷出汗,膨胀,伸展开腰身,此时桥候舍得出劲,好像在自已的婆娘身上用工。酷调好后生火烧热炉子,要把炉子烧热烧透,保持一定温度和火势。接着和馅,这馅有好几种,有萝卜丝的,有韭菜的,有脂油渣的,有甜有咸,食客任选。这些配料均要当日新鲜的,不得以次充好,尤其是擦酥料要足,要擦得均匀,再包馅,用那棒槌擀成圆圆的饼,边橄边敲出鼓点子,颇有音乐情趣,然后浇上糖稀,洒上芝麻。此时桥候大显身手,露着一条赤膀子,把烧饼贴上炉壁,双眼盯着在炉子挨火烤的饼,这火候要把握好,早一点晚一时都会影响到烧饼的口味。早一点则粘牙,晚一时则焦黑,一嘴烟火味。这火候全凭桥候的经验和眼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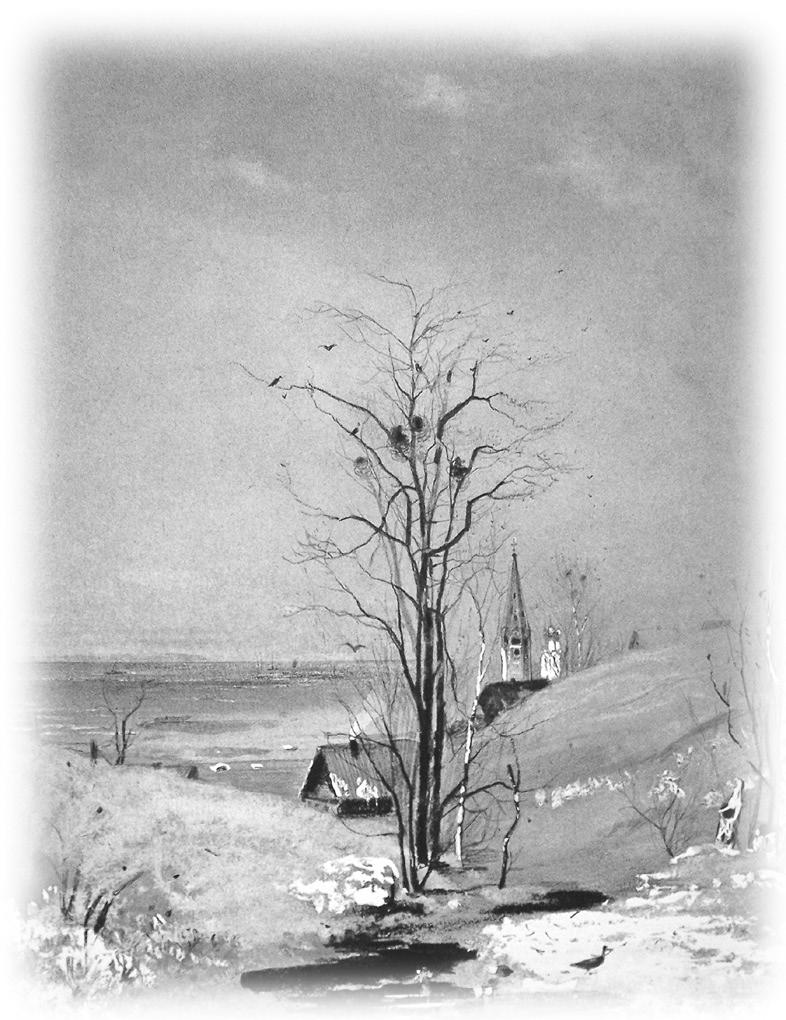
这出炉恰到好处的烧饼,香脆酥松糯口,色香味俱佳,是桥候烧饼的特色。
桥候从小做烧饼,如今已有二十个年头,他以此为生,不嫌苦,起早贪黑干得很开心,整天笑哈哈的。他很乐意做烧饼,好像他和这烧饼有着不解的情分。细看看他那圆柱型的身胚真像那圆桶样的炉子,他那胖乎乎的圆圆的脸不就是出自他手下的那烧饼样,只不过他小时候没患上天花,脸上少了些芝麻。
桥候人憨厚,实在,烧饼也实在。实在好吃。
【作者简介】刘志平,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雨花》《散文百家》《青春》《岁月》《牡丹》等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