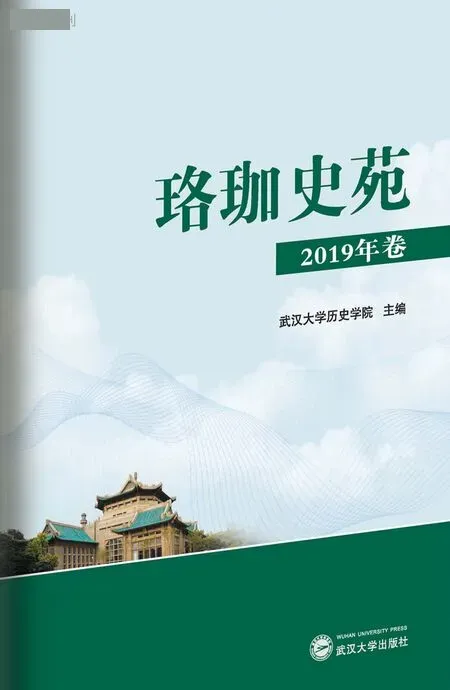跨学科视域下的西方身体史研究
2019-12-17张倩玉
张倩玉
“身体”,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观察人类自身的重要角度,也在建立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新文化史发展背景下,“身体”愈发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系统化和专业化的身体史研究应时而生。
顾名思义,身体史即研究身体的历史。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提到身体史研究需重点关注的对象应是:身体的符号意义和隐喻话语;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活跃角色;性别与性;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健康与疾病,医疗以及健康护理的发展;身体在体育领域的角色。①Mike Featherstone and Bryan S.Turner, Body& Society:An Introduction,Body & Society, 1995(1), pp.1-12.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则将目前身体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对身体器官、生理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二是身体与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关系研究;三是由身体延伸出的医疗史、疾病史、福利救济史、药物史等相关生命关怀研究。①王健:«理论前沿纵览⑤|“身体史”是研究什么的?»,上观新闻,2016年 9月 17日, 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30831, 2019年 6月29日。
可以看到,身体史不仅研究生物层面上的身体,也关注概念意义上的身体,并且以之为核心,探究身体与社会多层面的关系问题。也正是由于研究对象广泛而复杂,身体史需要与其他领域进行交互以寻找合适的发展角度。可以说,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探寻身体与社会的互动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思路,对人们更好的认识自我、丰富自我意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西方身体史跨学科发展研究的缘起
长期以来,“身体”处于“意识”的附属地位。基督教中对上帝的信仰隐晦地将意识置于身体之上,身体被认为是世俗和肉欲的象征。文艺复兴时期个人意识的觉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身体的解放,解剖的发展也为观察身体提供了条件。进入理性时代,一方面,身体被思想的绝对性地位所压制;另一方面,随着医学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身体的“自然性”有了向“技术性”发展的倾向。“身体”不单是人的生物身体,它的社会性开始被注意和讨论。工业化时代,马克思看到了工厂对身体的管理,劳动的身体为资本家的工厂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和财富。这里的身体是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于机器一般的存在,只能被动承受而无法主动去创造。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福柯笔下的“身体”,作为权力的施加对象,身体的主动性几乎消失殆尽,而只能作为驯服的对象被安置在需要的地方。尽管在这些理论中,“身体”都被看作一种被动的对象,其研究意义却逐步凸现出来。
20世纪70—80年代,后工业化时代带来了新的消费风潮,消费社会所带来的享受型生活凸显了身体同时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和作为消费对象的意义。同时,对女性的逐步重视也推动了身体史的发展。长期以来,女性被冠以诱惑肉体堕落的罪名,因此女性往往与身体的“罪恶”联系在一起。而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现代女性地位的提高,与女性相关的——诸如性与生产——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这也正是身体史的研究内容。可以说,一方面,性别史促进了身体史的发展,另一方面,身体史研究的成果又将为性别史提供新的研究材料。
随着身体逐步在社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领域中新文化史的方兴未艾也为身体史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计量史学相对,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食物和服装、语言与形象,它“表现出从围绕人的环境到环境中的人的这一变化的迹象;研究的问题则从经济的和人口统计的转变为文化的和情感的;影响的主要来源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转变为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①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 on a New Wor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1979(85),pp.3-24。 转引自陈新: «论20世纪西方历史叙述研究的两个阶段»,«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第93页。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身体史的研究基本沿袭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要路线,是社会环境变化促成史学研究对象转向的必然结果。杜丽红认为,全球化浪潮下消费资本主义盛行,社会文化越来越多元;诸如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等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伦理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促使历史学家们转向“身体”。②杜丽红:«西方身体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5页。
可以看到,身体史自产生伊始就浸润在多种文化相互交织与融合的社会环境中,这一方面给身体史带来了多样的研究选题,丰富了史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对身体史的跨学科交流和研究提出了要求。史学领域的“身体”已经不仅仅是医学领域中所提到的实验对象,也是作为一种表征意义而存在。这一象征广泛存在于政治、宗教、社会等各个领域,串联起思想与物质、文化与自然间的种种联系,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身体史的跨学科研究趋势一方面由身体史的成长环境所决定,另一方面又是观察身体必不可少的视角。通过多学科交叉与融合,身体能够在史学研究中更加回归本真,更多地关注人本身,更好地发挥其作为文化载体的意义。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身体史研究
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是身体史非常普遍的一种研究倾向。一方面,社会学涵盖内容广、领域宽,“身体”能够在社会学土壤中找到许多扎根之处;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对“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处理也为身体史提供了灵感。诸如在社会结构功能主义中,就强调社会的每一个部分对总体发挥的作用:“像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四肢、心脏、大脑)一样,社会的构成部分(比如家庭、商业机构、政府)以系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对整体发挥着好的作用。”①[美]戴维•波普诺:«我们身处的世界: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和身体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身体史为社会学提供有机模型,而身体史则吸取社会学的整体意识,考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各种社会因子是如何与“身体”相互作用与影响的。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社会中的“身体”了。英国人类学者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于1966年出版的«纯净与危险»就提出了“身体污染”,认为“两性的危险更应该被描述为与社会各部分进行互动关系的符号,能够反映出应用于更大社会系统中等级性或对称性的设计”。②Mary Douglas,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4, pp.3-4.法国社会学家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于1973年出版的«身体的技术»则认为身体是人类能够将自然转化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它同时承担着生物学中“物种”以及社会学中“个体语境”的角色。身体只有可能在刚刚出生的那一小段时间内能够表现出其自然性的特征,此后,通过走路、阅读和说话,身体将完全变成文化环境中的一份子;也正是通过这些技术的习得,人从一个自然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①Marcel Mauss, Techniques of the Body,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pp.364-386.
20世纪末,这种研究倾向进一步加强。诸如布莱恩•特纳的«身体与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的«五种身体:现代社会中的人体形塑»(Five Bodies:The Human Shape of Modem Society)和«沟通性身体»(The Communicative Body),等等,都是研究“身体”与社会的联系。②欧阳灿灿:«欧美身体研究述评»,«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24页。其中,特纳在1984年出版了«身体与社会»一书后,又于1995年与麦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合创了«身体与社会»(Body&Society)杂志,后者自此成为身体史研究重要的思想策源地。在杂志首卷中,他们提到,当身体开始成为一个在当代思想、医疗、时尚、妇女政治、技术以及私人生活、健康和旅游、想象与文学作品中受到明显关注的对象时,«身体与社会»的创办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作为教学和研究用身体的学术兴趣。③Mike Featherstone and Bryan S.Turner, Body & Society:An Introduction,Body & Society, 1995(1), p.1.
此外,«人类身体的历史碎片»一书也强调了身体与社会文化的交织。④Michel Feher,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New York,N.Y.:Zone, Cambridge, Mass.:distributed by MIT Press, 1989.这一系列有三个主要议题:神圣的、残忍的和作为模仿机器的身体;身体的“内在”与“外在”,即灵魂和疾病;身体的某些部分如何影响或者挑战人类社会功能,以及政治和社会功能如何反过来让人们在更大的社会“身体”(如学校或者组织)中承担着某种器官的角色。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选取了相对不那么常见的研究对象,诸如中世纪的妇女、非洲的游牧民族、日本的幽灵、提线木偶、16世纪的自动装置,等等。可以看到该书中“身体”的所有者不再局限于人类,还包括其他与人类外表或者功能相似的对象,在这里“身体”所代表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客观的物象,更强调的是人们对于“身体”这个概念的“认识”。
斯坦福大学史学博士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在她的研究中就非常强调这种身体史研究中的“再现(Representation)”与“感知(Perception)”。①费侠莉:«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蒋竹山译,«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4期,1999年12月,第129~143页。“再现”即将身体视为符号或象征。费侠莉以拜能(Caroline Walker Bynum)的«作为母亲形象的耶稣»为例,提到“当展现天主教的人道主义任务变得重要时,神学家将基督教男性化的君王形象转变为女性化的保姆形象”,这种性别运用方式强化了女性的形象。不同于“再现”是将身体作为联结意识与图像的载体,“感知”即强调“意识”与“真实”在身体上的关系与表现。费侠莉提到了杜登(Barbara Duden)的«皮肤下的女人»。这本书主要依据一名德国医生保存的女性病人的自我陈述,来研究女性是如何感知自己身体的,比如是否生病或者怀孕。杜登希望以此能够了解被生物性因素掩盖下的社会因素,“身体”不仅是我们与自然联系的一部分,也是表达自我意识的载体。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制造路易十四»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他认为,画家和雕塑家们塑造了一个表面光鲜的路易十四形象,“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接受了国王表面形象;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国王的光环基本上不过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用以欺骗人的把戏”②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46页。。人们如何去“感知”路易十四体现了他们对这具身体的态度和看法,而这背后自然有驱使他们做出这种表达的社会环境因素。
这种对于身体的观念或者感知也可以体现在对于某种身体器官的态度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上,比如«18世纪英国的剃须文化和男子气概»中就阐述了人们对于胡须看法的改变:胡须被认为是男子气概的显露,但18世纪英国的男人却流行剃须,这不仅表现了人们对于身体的控制欲,同时也是大生产和消费社会欣欣向荣的结果。③Alun Withey, Shaving and Masculin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013(2), pp.225-243.在这一角度,对于性器官与社会联系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诸如女性对于自己子宫的看法,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她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情感变化,也可以通过家庭或者社会对于生儿育女一事的态度来探究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环境。比如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cqueur)的«制造性»一书就认为历史上对于女性身体的压抑与“保罗书信”紧密联系在一起。①Thomas Lacqueur, 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Cambridge:Harvard U.P, 1990.例如保罗认为,婚姻能保护男人免于不受控的性渴望的威胁,因为与女人的性会挑战男人的理性。此外,拉科尔还著有«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讨论了从«圣经»到第三次妇女解放运动、概念艺术以及网络对于手淫文化的影响以及手淫与“现代自我”的关系。②[美]托马斯•拉科尔:«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杨俊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进入21世纪,关于身体与社会的研究更加注重长时段、全方位和多角度的探索。2005年法国学者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让-雅克•库尔第纳(Jean-Jacques Courtine)和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主编的«身体的历史»三卷本就对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身体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了“现代”的身体,但直到“一战”前夕,作为科学探索以及哲学思考的对象,身体仍然处于现代性与传统研究交叉的尴尬位置;而20世纪后半期以来,身体随着精神分析研究的发展而逐步变得重要起来,随后消费社会的出现以及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运动将身体抬到了供人们观察和讨论的台面上。随着现代生物以及基因技术科学的发展和媒体的曝光,身体更加频繁地进入人们视野,成为一种工具以及社会活动的执行者。③[法]阿兰•科尔班、让-雅克•库尔第纳、乔治•维加埃罗:«身体的历史»,孙圣英、赵济鸿、吴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此外,还有诸如«人类身体的文化史»六卷本,将研究时段扩展到公元前1300年到21世纪的今天,分别从生与死、健康与疾病、性别与性、医学知识与技术、公众信仰、对美的概念、被标记的身体、身体的文化表达以及自我与社会这十个角度对于身体史进行了权威和详尽的梳理。①Linda Kalof and William Bynum,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London:New York:Bloomsbury USA Academic, 2010, Reprint 2014.«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则是探究不同时段“历史环境如何创造特定的身体类型”以及“特定的身体类型如何产生特定的历史形态”②[英]约翰•罗布(John Robb), 奥利弗•J.T.哈里斯(Oliver J.T. Harris)主编:«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该书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从现代社会的实际议题之中,诸如器官移植、对身体的所有权(包括自杀和拥有死后躯体的拥有权)以及图像媒体对女孩苗条身材的推崇出发,来探讨“危机中的身体”:在技术与人类同步发展的时代,技术是否会失控?人的身体是否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被取代?这些问题点出了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和社会发展,人们对自我存在的意义所产生的怀疑和忧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政治学视角下的身体史研究
身体史与政治学的交叉在西方同样也是非常热门的研究角度,这一领域用的比较多的概念是“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即将一个国家、社会或者组织机构暗喻为一个生理上的人类身体。事实上,将政治与身体概念结合起来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无论是柏拉图认为国家的“疾病”源于各部门没能合理发挥效用,或是1世纪圣保罗将基督看作教堂这一“身体”的“头”,这些理论都为后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身体政治”这一概念愈发完善。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选取了20世纪以来有关领域的研究,并且根据研究内容将之区分为国家层面的身体政治与社会层面的身体政治。
就国家层面而言,“身体政治”受到“国王二体”概念的影响。恩斯特•康特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在«国王二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中提到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身体(Body natural),一个是政治身体(Body politic)。自然身体是人类的身体,会遭遇生老病死,而政治身体则是不能被触摸到或者被操纵的,这种政治性通过政策与政府表现出来,包括管理公共福利,但是必须受人民监管。这些自然要素和政治要素集合在一个人身上,形成了这一个不可分割的“身体”。政治身体不仅比自然身体更加丰满和庞大,它还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减少甚至消除脆弱的人类自然特质所固有的不完美情况。①Ernst Kantorowicz, The 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