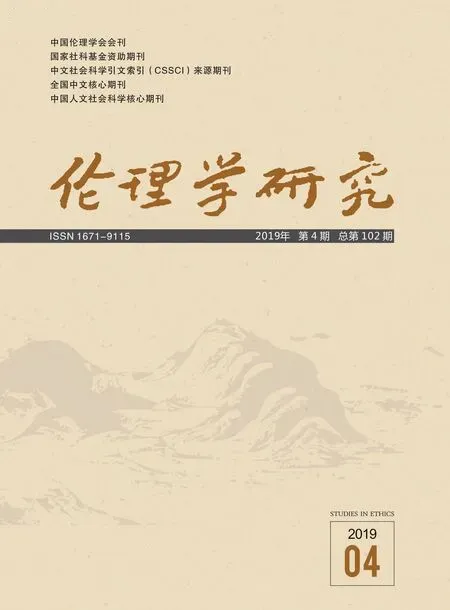论何殷震的女性伦理思想及其西学特色
2019-12-17常恒畅
常恒畅
何殷震(1886-?),原名何班,又名何震,字志剑,江苏仪征人,是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的夫人,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女权主义者。学界对于何殷震思想的研究多侧重挖掘其女权主义、女性意识、无政府主义思想等方面的内容①,本文拟就其女性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主体内容以及产生根源进行初步探讨。女性伦理是中国伦理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指的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女性,以其性别角色面临人生中各种情况而产生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它既包括女性自身的道德选择,也包括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②何殷震的女性伦理思想是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阶层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自主思考和探索的产物。研究这一女性伦理思想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在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女性的应对与突围,而且对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女性伦理思想的嬗变过程亦不无裨益。
一、背景与基础:何殷震女性伦理思想的资源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晚清的女性伦理观念与思想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并且出现了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系统相背离的诸多因素。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新思想逐渐影响了近代以来人们对于中国女性的固有认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性社会状况的改变,从而慢慢形成了对于女性道德要求的革新方向和崭新认知。
首先,西方传教士开启的“男女平等”命题讨论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男尊女卑”的旧观念,给国人带来认知上的强烈刺激。《自西徂东》《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等著述通过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传递男女平等的思想。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险语对》中阐述:“夫男,人也;女,亦人也。”直接表明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平等的人权。他提出应以“己所欲者,必施诸人”的“西教”之“恕道”取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者之恕道”[1],呼吁中国向西方学习。
其次,受到西学影响的维新派与革命派持续关注男女平等、女权思想等相关问题。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倡导“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中国传统的“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2](P36-40),不合公理,理当废除。谭嗣同也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理应“变不平等教为平等”,以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不平等之法”,这也是儒、佛、耶三教共通之义[3](P333-337)。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也援据其师康有为“孔教平等义”,痛斥男女不平等的起源,为女学张目[4]。革命派则以马君武为典型代表,他直接将西方的女权学说译介到中国,使国人直接阅读西方女权理论的文本成为可能。1903年4月,马君武译介了《弥勒约翰之学说》一文,其中第二节“女权说”,专门介绍弥勒的《女人压制论》与社会党人的《女权宣言书》[5]。可以说,马君武的译著乃晚清女权理论之源头[6](P78)。
第三,来自女性群体的自我觉醒。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钟》一书中,以“女权革命”为中心,考察和参照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与现状,认为中国的“女权革命”应区分为“人身自由权”和“参政权”“公民权”阶段,从而完成与男性共建“新政府”的历史使命。她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新式教育,把女性培育为“新国民”[7](P6-43)。1904年,吕碧城在《大公报》发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呼吁女性“以复自主之权利,完成天赋之原理而后已”[7](P51)。同年10月,秋瑾在《白话》杂志撰文,对中国传统女性普遍悲惨的人生际遇进行了描述,号召女性起而抗争。秋瑾呼吁妇女解放,并将女性的自我拯救与救国联系起来[8](P4-6)。
概而言之,这些来自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声音代表了由“男女平等”向“女权”逐步过渡的时代诉求,为何殷震提供了思想资源,对其女性伦理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
二、批判与重构:以“绝对平等”为核心的女性伦理思想
何殷震女性伦理思想既受到前代思想资源的启发,也构成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女性伦理嬗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一思想建立在对于传统伦理制度批判的基础之上,其理论核心是强调男女关系的“绝对平等”。
1.抨击封建家族伦理制度,呼吁“解放妇女”
首先,对儒家伦理话语进行批判,何殷震把历朝被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儒家学术称为“杀人之学术”,因其“以重男轻女标其宗”[9](P57)。在《女子复仇论》一文中,她对《礼记》《左传》《诗经》《白虎通义》等儒家经典中关于“男尊女卑”话语进行了整理清算:“盖以男为阳、以女为阴,又以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春秋繁露》)。由是,天下之最贱者,莫若女子;而天下最恶之名,亦毕集于女子之一身”[9](P66)。对于要求女子忠贞节烈的传统妇女观,何殷震抨击道:“以贞女之空名,迫女子以死亡之祸,然后知前儒所言之礼,不啻残死女子之具矣。”[9](P62)基于对于“男尊女卑”的深刻认识,何殷震提出要把女性从家庭、闺阁中解放出来,还给女子人身自由,让女子与男子一样担负家庭责任,以实现“妇人者人人同享解放之乐”[9](P142)。
其次,何殷震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关照妇女群体命运,激励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实现真正的独立。她曾对班昭所作《女诫》进行了极具针对性地批判:
及于东汉,班昭之学,冠绝古今,而所倡之说,尤为荒谬。观其所作《女诫》,首崇卑弱,谓女子主于下人,当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含诟忍辱,常若危惧。又谓:“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又谓:“阴以柔为用,女以弱为美。”以侮夫为大戒,以贞静为德容。呜呼!此说一昌,而为女子者,遂以受制于男为定分。名为礼教,实则羞辱而已;名为义理,实则无耻而已。此非所谓“妾妇之道”耶?[9](P67)
何殷震认为这一文本是首次提倡和崇尚女子卑弱的文化,将女子地位置于男人的权威之下,让女子经常处于一种惯性的弱势,并辅以义理、礼教等崇高名义,将儒家礼法粉饰一番,而实际则是促成了女性自我意识缺位的“妾妇之道”的产生。何殷震对于班昭抱有某种程度的痛恨,同时也有一份同情的理解。她并未认定“以夫为天”的传统话语里班昭的罪责,而是深刻地认识到班昭同样也是儒家知识系统中的受害人和牺牲品,“而班贼之为此言,又由于笃守儒书,以先入之言为主,则班贼之罪,又儒家有以启之也”[9](P68)。何殷震不仅关切同情妇女的命运,更看重女性自我意识的培养。
2.批判中西婚姻制度,革新婚姻制度
中国封建婚姻制度与家族制度是紧密相连的,前者是后者的产物,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因此,何殷震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也进行了批判,并倡导一种“绝对平等”意义上的婚姻制度。
一方面,何殷震认为男女在嫁娶上的不平等是导致女性婚姻不幸的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古代之时,位愈尊者妻愈众。如殷代之制,天子娶十二女,诸侯娶九女,大夫三女,士二女……而后世之嫔妃,则更无限制。显贵之家,蓄妾尤众”[9](P41)。何殷震要求女子自身须有明确的意识,时刻警醒女性在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中的悲剧性以及这种“男尊女卑”婚姻观的可耻。“纳采、纳徵之礼,一遵古制,而妇家对于夫家,或以衣物服御之微,竞相争执,则卖女之风至今尚在……名曰下嫁,实则以俘囚、仆隶自居。于此而不知自耻,是必女子非人类而后可矣。”[9](P55)另一方面,在考察男女婚姻的现实生活问题上,何殷震对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发难。“孔丘者,儒家之鼻祖也,而其人即以出妻闻。传之暨孙,均有出妻之行。盖以暴行施之于妻,莫孔门若。孟轲者,儒家之大师也,因入室而妻失迎,遂谋出妻,其专制室人为何如”[9](P57)。何殷震将儒家创始人塑造成了专制的“出妻”者形象,将在封建休妻制度下的女性婚姻的不幸展露无遗。
在批判了传统的婚姻观之后,何殷震表达了自己革新旧有婚姻制度的愿望。首先,她倡导的是“忠贞”至上的一夫一妻制,禁止男性纳妾,一旦有所违背,则将受到重罚,甚至有性命之虞。“如男子不仅一妻,或私蓄妾御,性好冶游者,则妻可制以至严之律,使之身死女子之中。”同时,也严禁女子婚内出轨,“其有既嫁之后,甘事多妻之夫者,则女界共起而诛之。若男子仅一妻而妻转有外遇,无论男界、女界,亦必共起而诛之。”[9](420)其次,她认为女子出嫁后不应该随夫姓,而应该父母姓并重,以保持女性在婚姻中的独立性。为了实践这一主张,她还掀起了关于“双姓”问题的讨论。她提倡女性应该承继父姓与母姓双姓,“自号其姓名曰何殷震”。随后又提出了改良的办法,“男子从其父姓,女子从其母姓”,以保障父族延续的同时母族的延续。再后来,何殷震提出“废姓论”以取代“双姓论”,在《天义》中作者的署名,例如“申叔”“震述”“震选”“志达”“公权”等,直接就没有姓氏。第三,主张如果婚姻不幸福,也是可以离婚的。“如夫妇既昏而不谐,则告分离。惟未告分离之前,男不得再娶,女不得再嫁。否则,犯第一条之禁。”这条规定是与“一夫一妻”制配合实施的。第四,讲求男女在婚姻中的绝对平等。“以初昏之男,配初昏之女。男子于妻死后,亦可再娶,惟必娶再昏之妇。女子于夫死之后,亦可再嫁,惟必嫁再昏之夫。如有以未昏之女嫁再昏之男者,女界共起而诛之。”[9](P43)这种希望男女在婚姻结合过程中认定婚姻身份的绝对等同体现了一种对于男女关系“绝对平等”追求的偏执。最后,反对欲望婚姻。何殷震不仅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鞭笞,而且在研究了外国的婚姻制度之后也表达了对其虚伪性的批评。“据甄氏之说,足证近世结昏之礼,仍沿古代劫掠之风”[9](P54),她认为资本主义婚礼制度“一缚于权力,再缚于道德,三缚于法律”,“均由肉欲及财欲结合而成者也”,“实与蛮族之财昏无异”[9](P135)。在她看来,古今中外婚姻的本质都充满了身体与物质的欲望,不同时期与不同国度的伦理制度、政府权力、道德法律则是维系这种欲望的强大机器,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破的。
3.解构中国传统伦理话语体系,主张男女“绝对平等”
无论是家族伦理制度,还是婚姻制度,都是生产“男女不平等”的中国传统伦理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何殷震深刻认识到了正是因为这样一整套知识生产体系与话语装置的持续运转,压迫女性的知识与学术被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导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平等可言的一丝可能性。她力图从根本上解构传统伦理话语体系,主张男女之间应该处于“绝对平等”的关系之中。
何殷震睿智地发现了关于“女性”的“天性”与“传统”皆由知识话语权力系统所建构,要实现“男女绝对之平等”则必须从最初的权力话语体系中找到突破口。首先,她考索历史,将“男为主而女为奴”和“男为人而女为物”作为男女不平等产生的根源,而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又可分为嫁娶不平等、名分不平等、职务不平等、礼制不平等四个方面[9](P41)。她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各种压迫机制,例如文字、礼制、学术等。她全面而细致地清理了儒教对妇女的各种限制和压迫,揭露了历代儒家“学术”知识生产机制的特点:“黠者援饰其说以自便,愚者迷信其说而不疑,而吾女子之死于其中者,遂不知凡几。”更是发出了“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9](P57)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喊。何殷震冷峻地发现并指出,这些系统都对男女性别序列阶层作了隐形地设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透过知识系统的不断更新迭代,持续不断生产着男女不平等。对何殷震来说,分别“男女”的机制是至关重要的逻辑起点,性别化的知识生产从男性主导世界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政治、文化与伦理等方面的权力设置,并进一步建构着知识系统中主体的普遍经验。
其次,何氏主张通过向男子“复仇”以建立男女平等的起点。在《女子复仇论》一文中,何殷震则提出“男子者,女子之大敌”的极端口号,号召女子对男子进行“复仇”。她指出:“今男子之于女子也,既无一而非虐,则女子之于男子也,亦无一而非仇。”坚决主张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同时“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9](P49)。何殷震从不相信现实中“天性”或“传统”的女性存在,她在《女子宣布书》中论述:“……男女同为人类,凡所谓男性、女性者,均习惯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之物亦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此诚所谓男女平等也。”[9](P43)她也承认“男”与“女”的内部也有宰制关系,也有男子提倡男女平等现实情况的存在。所以,她也告诫女子:“盖女子之所争,仅以至公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于女子下也。”[9](P50)
第三,她将复仇的目标指向了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以建立男女平等的经济基础。“惟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使男女无贫富之差,则男子不至饱暖而思淫,女子不至辱身而求食,此亦均平天下之道也。依此法而行,在众生固复其平等之权,在女子亦遂其复仇之愿。”[9](P50)。学者宋少鹏评述:“何殷震认为女子的解放和真正的男女平等只能存在于实行公产制的社会中。”[9](P77)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让何殷震感同身受,也成为她激进女权主义批判的出发②。何殷震把财产关系作为社会生活的关键,她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现今女子之陷于困阨者……则有同一之原因。原因惟何?即生计问题是也,即财产分配不平均是也。”[9](P115)何殷震通过对中国蓄婢制度的历史考察,认为该制度的产生,不是因为阶级制度,而是因为“生计问题”。在论及西方国家的现状时她说:“自十九世纪以来,富者挟其资本,以从事于生财,然财非一己所能生也,必役使他人以为己用。被以一言,即以平民之劳力,供富民之生财而已。”[9](P112)
在何殷震看来,劳动应该是人类的普遍活动,是劳动者生命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应该包含私人占有他人劳动所得的权力。她赋予了劳动一种纯粹的本体性,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经济学范畴的劳动概念。这样的劳动是一种女性自主的劳动,而不是被奴役的商品化形式的劳动。因此,劳动作为最后的思考落脚点,关系到女性的生计问题与财产分配问题,关系到男女平等的实现。可以说,由自主的劳动出发,只有当女性重塑她们从事劳动的身体乃是人类劳动的本体,整个人类社会才可能从财富和权力建构的工具化劳动状态中解放出来,男女之间的平等才能够真正实现。
第四,消灭政府,实行无政府主义,以建立对“男女绝对之平等”的制度保障。何殷震指出:“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与奴隶制度之起源同一时代。”[9](P198)她认为,国家是私有制度的保护者,而“生计”上的保障,是不能依靠国家的。真正的“解放”和“生计”在于消灭一切经济政治依附性的社会生活形式。何殷震抨击国家制度,认为只有在一个彻底重构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才能实现“男女绝对之平等”。她说:“如欲实行女界革命,必自经济革命始。何为经济革命?即颠覆财产私有制度,代以共产,而并废一切之钱币是也。”[9](P204)这种彻底地废除财产私有制度的立场,使何殷震与中国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区别开来,使她关于男女关系的理论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深刻的思辨性与彻底的革命性。
三、渊源与超越:何氏女性伦理思想的西学特色
何殷震以“绝对平等”为核心的女性伦理思想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的。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的滋养,使何氏女性伦理思想呈现出鲜明的西学特色。
首先,达尔文的进化论奠定了何殷震女性伦理思想的西学理论基础。西方的进化论,特别是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经过严复的翻译,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已经为当时国人所接纳。严复在译著《天演论》中将进化论的核心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何殷震在《天义》中则在比照的基础上重新阐释解读了生存竞争的含义:
物类互助之说,始于达尔文。达氏虽以生存竞存为物类进化之公例,然达氏所著《种源》,已言生存竞存之意,不宜偏小一方面观之,当从宽大处解释。生存竞存,即众生之互助关系。又,所著《物种由来》,亦谓:“动物进化,当代竞争以协合。及竞争易为结合,斯其种益迁于良。所谓良种,非必赖其强与巧也。其所尚,惟在扶持结合。故凡公共团体,凡彼此相遇愈殷挚者,其团体亦愈发达。”达氏之言如此。而赫胥黎误解其义,以为动物之中,惟强狡者乃生存。[9](P258)
在严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适者即为强者,其论述的本质上一种生存竞争关系。《天义》的理解则更接近达尔文的本意,认为无论多么强壮的生物都不能独活,竞争与协作相互依存,而协作是竞争的基础,也是推动生物进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生存竞争的含义其实是互助结合。
事实上,作为《天义》主编之一的何殷震能有如此卓识则是因为对于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接纳和吸收。在赴日本之前,何殷震与其夫刘师培等人已经通过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间接了解到克鲁泡特特金的学术思想。到日本后,则直接研习了克氏的《诉青年》《无政府主义哲学》《互助》《自由合意》等著作。因此,无政府主义构成了何氏女性伦理思想的又一个理论来源。何殷震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推崇一种平等、自由、互助的伦理原则,而落实到其女性伦理思想上,则确立了对于“男女平等”核心思想的绝对肯定。
除此之外,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也对何氏建构其女性伦理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传统伦理核心是“三纲五常”,何殷震在批判“三纲五常”方面深受其夫刘师培的影响。刘师培借用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对“三纲五常”这一传统伦理核心曾提出过激烈批评。刘氏认为:“自三纲之说兴而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只有权利无义务,为臣者,为子者,为妇者有义务而无权利,所谓论势不论理也。有权势者能论理,无权势者即不能论理。”[11](P48)正是由于“三纲五常”所规制的权利与义务的极端不对等,导致了上尊下卑的极端不平等现状。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歪理邪说“钳制民心,束缚才智”,也是中国国民精神萎靡不振,无意积极进取,而“厌世乐天”之心日生的原因。因此,刘师培主张以“平等”为核心重构中国伦理,“以振励国民之精神,使之奋发兴起”[12](P37)。刘师培参照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来观照伦理的起源,“盖伦理之生,由于人与人相接。其始也,由一族而合数族;其继也,由一群而合他群。其所以结合之方,皆由于人民之契约。”[12](P147)在卢梭的契约论思想中,契约之真谛在于平等,因此平等成为了伦理的精神内核。刘师培进一步阐释中国“恕道”与西方的“平等”最接近,提出要以“恕道”为主线构建中国伦理。他说:
与人相接,以我之所欲所恶推之于彼,彼亦以所欲所恶推之于我,各行其恕,自相让而不相争,相爱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 矩之道也。此言甚确。盖恕道于平等最近,故儒家之君臣父子也,祗言报施。报施者,即西人所谓权利义务之关系也。故恕道行,则三纲之说废。[12](P50)
何殷震基本接受和吸纳了刘师培的这一思想,通过以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为参照,在理论源头上建立了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思想与西方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不仅达到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批判的目的,而且为中国近代女性伦理思想发展指出了新方向。
事实上,一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影响了何殷震女性伦理思想的建构,从而奠定了何氏思想西学资源多元化的特色,而另一方面,何殷震女性伦理思想又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于西学理论的超越。
首先,这种超越性反映在对于“平等”和“自由”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何殷震十分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续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中刘师培极具代表性的发言就坦言了其所主张的与当时任何一派无政府主义均有不同:
无政府主义虽为吾等所确认,然与个人无政府主义不同,于共产、社会二主义,均有所采。惟彼等所言无政府,在于恢复人类完全之自由;而吾人之言无政府,则兼重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盖人人均平等,则人人均自由。[13]何殷震的持论与刘师培的主张几无二致,她亦认为“平等”比“自由”更为重要。在日本拜访无政府主义领袖幸德秋水、堺利焉,并与他们探讨是否应对初婚、再婚男女的婚配做严格限制时,何殷震这样理解与表述她和日本革命家的分歧:
盖幸德君及堺君之意,在于实行人类完全之自由,而震意则在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立说之点,稍有不同。[9](P347)
幸德秋水曾写信与何殷震讨论婚姻问题:“夫夫妇关系之第一要件,在于男女相恋相爱之情。纵令初婚之夫妇,心中无相恋相爱之情,则固有妨于夫妇之道。又令再婚之男,与初婚之女,真克爱恋和谐,何害其为夫妇乎?”[9](P347)在幸德秋水看来,爱情是婚姻的唯一基础,甚至爱情远在婚姻之上。何殷震却从扫荡“旧道德”的角度出发,要求一种近乎极致的“贞洁”至上的男女“绝对平等”婚配观。
其次,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何殷震在寻求女性解放之道上表现得异常彻底,这与同时代受到西学影响的其他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比照。如前所述,何殷震将废除政府作为寻求两性绝对平等的根本保障。何殷震在《女子复仇论》种宣示:
以女子受制于男,固属非公;以女子受制于女,亦属失平。故吾人之目的,必废除政府而后已。政府既废,则男与男平权,女与女均势,而男女之间,亦互相平等,岂非世界真公之理乎?[9](P50)
由此可知,何殷震已将“无政府”作为实现男女真正平等平权的绝对且唯一必要的前提。与何殷震同一时期的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也都以提倡“女权革命”为己任,但诸人所说均以女权革命与民权革命相联系。比如丁祖荫在阐释“女子家庭革命说”便直言:
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其目的同。政治之革命,由君主法律直接之压制而起;女子家庭之革命,由君主法律间接压制而起:其原因同。[14]
诸人之呼吁倡导“女界革命”,仍是出于政治革命或种族革命的考虑,他们将“女界革命”的进程设计为:“爱自由,尊平权,男女共和,以制造新国民为起点,以组织新政府为终局。”[7](P4-43)金一断言“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柳亚子之谓“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丁祖荫之称“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都表明了一种以西方妇女运动为楷模倡导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与政府的诉求。反观何殷震的女性伦理思想,她以“男女平等”为终局,誓言消灭一切政府。并且,出于对任何权力的警惕,何殷震甚至对于“女权”一词的使用也十分谨慎。在这种思路主导下,她又提出“发展女性”的新说,即实现女性身体与精神人格的双重自由与健全。何氏的这些观念和思想极大地超越了西学理论以及其影响的范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一种偏执的气息,但是在清末民初的具体语境中,其独立思辨的超越价值应该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余 论
何氏女性伦理思想内涵丰富,充满革命性,闪烁着思辨光芒,这使其与同时代其他女性伦理思想区别开来,成为中国近代女性伦理嬗变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何氏能够迅速吸纳西学观点并进行创发,根源还是在于其本身对中国文化传统在一定层面的认同与充分利用。尤其是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与中国社会早已形成的文化兴趣具有很大的契合度,这为何氏融合中西思想奠定了文化基础。比如反对财产私有制,主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归公用的单一共产制与儒家的财富“均平”的思想相契,而无政府主义的“平等互助”等伦理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至公”“仁政”与“德治”等理念相合。何殷震有时进行中西思想的互参与比附,“中国儒家谓之仁,欧人康德谓之博爱,若鲁巴金则谓之互助扶助之感情”[15](P117)。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刻意串联中西思想内在理路相通的典型手法不仅构筑了何氏女性伦理思想的肌理,而且也促进了中西伦理文化的交融与中国女性伦理思想的嬗变发展。
除此之外,何殷震在思想表达和论述过程中也不断在传统知识系统中寻找文化根源。例如通过把女娲绘制成身着和服的女性形象,并例数女娲功绩,盛赞女娲“与轩羲并隆”[9](P3),有意抬高女性地位,以宣传其妇女解放思想;又如在认知领域,接受历史传统中的异端思想的感召和启示,受到李贽“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观念的影响而形成自己“所谓是非者,强者所定之是非也”的论述[9](P273)。而她关于儒家学术乃“杀人之学术”的论断应该是受到了清代理学家戴震所指出的“以理杀人”的启发[9](P230)。
何殷震曾坦言:“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故创办《天义报》,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9](P307)基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双重滋养,何殷震所追求的“男女绝对之平等”具有强烈的理论思辨色彩。在金天翮、吕碧城的论说中大力提倡的女子新式教育,在她看来也是“奴隶之教育”,因为政府与权力仍然存在,而这将必然带来不平等。“盖人治一日不废,权力所在之地,即压制所生之地也”[9](P140)。她开辟了一个原创性的理论空间,从不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直接将女性解放的根本之道归结为“尽覆人治”,施行无政府主义。尽管这种理论有一定程度上的偏执,却也彰显了其在思辨层面上的深刻。
最终,在如何解决男女关系的“绝对平等”这一核心问题上,何殷震给出的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方案:即废除政府与家庭,施行“共产无政府主义”。然而,这已经完全背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这种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思路,在实践层面反而阻断了社会革命的可能路径,从而使她的女性伦理思想镀上了一层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成为清末民初多重思想世界中一种别样的景观。王汎森曾评价刘师培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具有“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的双重特质[16](P244),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刘师培的夫人何殷震。何氏的女性伦理思想反映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既批判传统,又依附传统;既痛恨西化,又自我西化。可以说,这一矛盾心态从后来的“五四”时期直至21世纪的今天,也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检视的。
[注 释]
①刘慧英.从女权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何震的隐现与《天义》的变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2);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J].中华文史论丛,2006(83);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须藤瑞代著,姚毅译.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彼得·扎罗.何殷震与中国无政府女权主义[J].黄淮学刊,1989(4);刘人鹏.《天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视野与何殷震的“女子解放”[J].妇女研究论丛,2017(2);另有刘禾、瑞贝卡·卡尔、高彦硕著,陈燕谷所译《一个现代思想的先声:论何殷震对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本文为英文版《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一书导言,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5期.该文章认为何殷震对于劳动妇女和农村经济困境等问题的批判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进行的,且极具开创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②李桂梅,黄爱英.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女性伦理的嬗变[J].伦理学研究,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