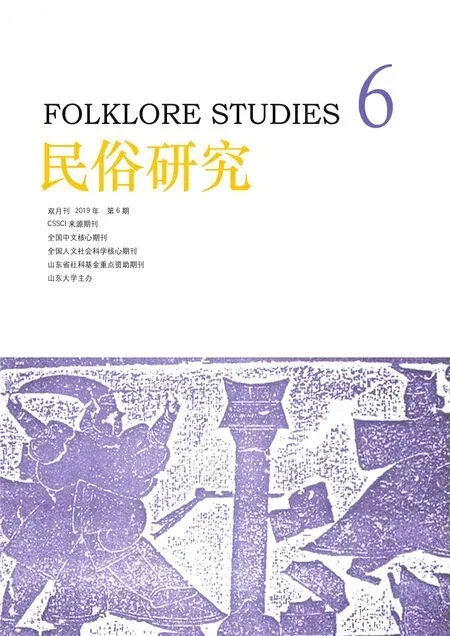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人民口头创作”课程的教学与“生产实习”
2019-12-16车振华
车振华
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影响,“人民口头创作”取代“民间文学”,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界的专用学术名词。它尤为强调“人民性”和“口头性”,对当时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54年,关德栋在山东大学开设“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并且围绕这门课程开展了两次“生产实习”,这在当时的民间文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试图发掘和梳理这段少为人知的学术史,希望对总结山东大学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和丰富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从“民间文学”到“人民口头创作”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从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和蔡元培的《校长启事》正式开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间文学研究大多是研究者的自发行为,由个人的学术兴趣所驱动,虽然也有社团,但组织性并不强,更不强调整齐划一。这一段时间,因为参照系和着眼点的不同,仅“民间文学”的名称就有“民间文学”“俗文学”“白话文学”等多种叫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调整和体制机制的变革,“本应属于国学研究或人文科学研究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却纳入了文艺工作体制,在文艺界成立了一个群团组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而进入了一个群团主导的时代”(1)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621页。。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0年3月29日在北京成立。其《章程》规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收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2)《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转引自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627-628页。。在成立大会上,周扬的讲话给新中国的民间文艺工作定了调。他说:“民间文艺是一个广阔的富藏,它需要我们有系统有计划地来发掘……但我们觉得最出色的民间艺术还没有发掘出来。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3)周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0页。郭沫若在成立大会上作了《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讲话,对民间文学“人民性”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了明确界定。郭沫若高度重视民间文学的田野采风,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民间文学研究的五点目的,其中第一点就是“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他提出,“我们现在就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着的风捕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4)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人民日报》1950年4月9日。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民间文学发展在指导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这一指导方针贯穿了整个1950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将苏联视为社会主义的样板而多有学习和模仿。“苏联民间文艺学理论的基本观点,被认为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取向。对它的吸收、借鉴,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新民间文艺学理论的基本风貌。”(5)黎敏:《中国社会主义新民间文艺学理论初创时期的苏联影响》,《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这种民间文艺学理论转变的一个关键词是“人民”。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民间文学理论家来说,“‘人民’的共和国,当然要确立‘人民’的文化,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其创造力需要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肯定。但对人民创造力的认识和肯定,需要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印证,而被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现的苏联民间文艺学理论就起到了指导和检验我们认识的重要作用”(6)黎敏:《中国社会主义新民间文艺学理论初创时期的苏联影响》,《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1950年9月,在新创刊的《民间文艺集刊》第1辑上,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钟敬文发表了《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人民口头文学”和“人民口头创作”的概念,以此替代了此前通用的“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等概念。“人民口头文学”和“人民口头创作”两个概念体现出浓重的苏联口头文学理论的色彩。钟敬文认为,按照苏联学者“所谓口头文学,一般是指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和传播的语言艺术”的定义,“我们就无需再象过去那样,把许多虽然流传在民间而本质上却不属于广大人民的东西算作口头文学或人民创作了。今后为着使大家对它的观念更清晰起见,干脆地废去那些界限广泛而意义模糊的‘民间文艺’一类的旧名称,采取‘人民口头创作’或‘人民创作’的新术语是有好处的”(7)钟敬文:《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序言,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人民口头创作”的名称很适合1949年后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又凸显出“人民性”“口头性”等特征,这正是当时对“民间文学”概念的认识。钟敬文将民间文学的作者“定位为‘人民’或‘劳动人民’,从而赞美民间文学在思想上、艺术上的优越之处”(8)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631页。,其所谓的“人民”,已经不再是指“民族全体”,而是“过于狭窄化、过于意识形态化了”。(9)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631页。虽然在1959年后,因为中苏两国关系发生了变化,“人民口头创作”的名称又恢复为“民间文学”,但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概念彻底取代了“民间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正宗。
二、山东大学“人民口头创作”课程设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高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赵景深、钟敬文、罗永麟最早在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震旦大学进行民间文学教学。在“人民口头创作”的概念取代“民间文学”之后,虽然有所争议(10)参见钟敬文《高等学校应该设置“人民口头创作”课》,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页。,但高校还是纷纷开设了“人民口头创作”课程,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补充。当时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开设了“人民口头创作”课程。据陈子艾《从“人民口头创作”课的课堂教学说开去——怀念钟老20世纪50年代的教学实践之一》一文回忆,当时北师大的“人民口头创作”课程是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上课一年,上学期每周二节,下学期每周三节。钟先生讲新课共十讲。”(11)陈子艾:《从“人民口头创作”课的课堂教学说开去——怀念钟老20世纪50年代的教学实践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的忠诚守望者——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48页。其课程大纲如下:
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人民口头创作的人民性及特征;第三章:人民口头创作在群众生活中的位置与作用;第四章:人民口头创作和作家书面文学关系;第五章:神话和传说;第六章:民间故事;第七章:民间诗歌;第八章:民间戏剧;第九章:谚语和谜语;第十章:新的人民创作。(12)陈子艾:《从“人民口头创作”课的课堂教学说开去——怀念钟老20世纪50年代的教学实践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的忠诚守望者——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48-49页。
由课程大纲可知,“人民性”和“口头性”在这门课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强调。
山东大学是继上述高校之后较早开展民间文学教学与科研的高校。1953年,受冯沅君邀请,关德栋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此时的身份是敦煌学家、俗文学专家和满学专家。上世纪40年代,关德栋通过敦煌俗文学研究而知名,其后他又成为以郑振铎和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学派”的重要成员,未及而立,就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小说、戏曲、说唱、小曲的研究论文,受到郭沫若、郑振铎、向达、王重民等著名学者的赞许。
到山东大学工作后,关德栋继续从事“俗文学”研究,并和冯沅君教授一起承担了“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因为专业相近,又有民间文学工作的经验,开设“人民口头创作”课程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通过查询当时山东大学教务处的课程表可知,从1953年关德栋到任,到1956年夏天他带领学生赴淄博进行民间文学采风,这期间山东大学中文系共四次开设“人民口头创作”课程,授课教师都是关德栋,授课时长为一学期。分别为:
1,1953-1954学年的第二学期,即1954年上半年,授课对象是大一年级,每周3课时,周三周六上课。
2,1954-1955学年第一学期,即1954年下半年,授课对象为大一大二两个年级,每周3课时,周三周六上课。
3,1955-1956学年第1学期,即1955年下半年,授课对象为大一年级,每周的课时安排为讲课2.2,讨论0.8,答疑0.55,周二周六上课。
4,1955-1956学年第2学期,即1956年上半年,授课对象为大一年级,每周3课时,周二周五上课。
《新山大》报1955年6月10日第二版刊登了山东大学各专业的介绍,其中,中国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旨在广博的系统的基础知识之上,特别是根据语言文学本身的系统性与基础课程的广阔性,进行专业训练,来培养比较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汉语言文学研究人才和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师资,而以汉语言文学研究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有15种,第13种为“人民口头创作”,其课程要求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讲授人民口头创作的基本问题兼及优秀作品”。与之并列的课程还有“文艺学引论”“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等。
1955级学生、后任山东大学教授的郭延礼在《关先生教学的回忆片段——悼念关德栋先生》一文中回忆,当时关德栋教授的“人民口头创作”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和讲义,所以授课的方式很灵活,他“不是一字一字地念讲稿,而是像平常谈话一样与学生进行交流,加之他渊博的知识,纯熟的北京话,讲起课来内容充实、新鲜,表达生动,语言动听悦耳”(13)郭延礼:《关先生教学的回忆片段——悼念关德栋先生》,中国俗文学学会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关德栋教授纪念文集》,2006年,第81页。。在讲课中,他还“插入民间文学中一些富有情趣的歌谣、传说,乃至奇闻、轶事,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求知欲很强的青年学子来说,听起来很有趣,像听故事一样。五十分钟很快过去了,下课钟声响了,往往是讲者觉得言犹未尽,听者感到兴趣无穷。所以当时同学们都喜欢‘人民口头创作’这门课”(14)郭延礼:《关先生教学的回忆片段——悼念关德栋先生》,中国俗文学学会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关德栋教授纪念文集》,2006年,第81页。。
据1955年关德栋与同样教授这门课程的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的通信可知,关德栋当时曾着手编写讲义。(15)1955年,关德栋与赵景深有过数封通信,讨论“人民口头创作”教学大纲和讲义的编写,可惜关信已不可见。参见车振华、王鲁娅《赵景深论“人民口头创作”信札考略》,《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1955年10月25日,赵景深将自己编写的“中国人民口头创作”教学大纲寄给关德栋,询问他“人民口头创作概论”的讲义是否着手编写。关德栋对大纲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并与赵景深交换了自己对这门课程的看法以及编写讲义的心得。可惜的是,关德栋所编民间文学讲义的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了。
三、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生产实习”
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除了课堂教学外,还要进行“生产实习”。作为教学法的“生产实习”借鉴自苏联,本来是培养工业、农业等熟练技术工人的一种方法,后来成为各个专业课堂教学的补充,各专业进行“生产实习”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山东大学“人民口头创作”课程“生产实习”的形式是田野采风,进行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这既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之初所提出的“发掘”民间文学遗产和“捕风”的要求。山东大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进行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高校之一。
在执教山东大学之前,关德栋已有丰富的民间文学调查经验。1950年,他搜集整理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蒙古族四个民族的民歌,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民间故事,结集为《新疆民歌民谭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50年春,他随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派往兰州大学的军代表到该校工作,任教于“少数民族语文系”。除讲授一些“民族史”和“民族政策”的知识外,在赵景深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他还从事当地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编成了《甘肃青海民歌集》。《甘肃青海民歌集》分为“甘肃民歌”“青海民歌”“西藏民歌”和“兰州鼓子”四部分,基本涵盖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民歌形式。其中“甘肃民歌”“青海民歌”除了歌词外,还附有曲调。《甘肃青海民歌集》请郑振铎先生题写了书名,赵景深先生为之作序,本拟由北新书局出版,后由于出版社调整和关先生工作的调动而搁置至今。(16)参见关家铮《赵景深遗稿〈甘肃青海民歌集·序〉》,《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
1955年暑假,关德栋带领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和1954两个年级的20多名同学,深入沂蒙山区的沂水县进行民间文学采风。沂水地处沂蒙山区腹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民间文学资料丰富,俚歌俗曲和抗战民谣众多。据参加此次采风活动的1953级学生、后任青岛大学教授的郭同文回忆,此次采风活动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历时二十多天,深入沂水县民间文学资源蕴藏丰富的四个点进行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7)资料来自于2011年笔者对郭同文教授的电话采访。郭同文在1956年2月9日《新山大》报上发表《我和农民建立了友情》一文,回忆了沂水当地的纯朴民风,以及他在沂水实习期间和当地农民建立起深厚感情的故事。
1956年7月暑假期间,关德栋又带领33名学生到淄川进行“人民口头创作”的生产实习,搜集当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实习时间为半个月。之所以选择淄川作为实习点,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淄川是煤矿区,有著名的洪山煤矿,可以搜集过去少为人注意的反映矿工生活的歌谣和故事;二、淄川为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故乡,可以去那里搜集有关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资料,以及蒲松龄的俚曲、民间传说等。
1953级学生孙庭华在《在蒲松龄故乡搞社会实习》一文中回忆:“全队由4个年级学生组成,共有队员33人,分成4个小组,分别在洪山镇、寨里乡和蒲家庄等6处,进行材料搜集。”(18)孙庭华:《在蒲松龄故乡搞社会实习》,《山东大学报》2009年3月25日。以下所引孙庭华的回忆皆出自此文。关德栋指导孙庭华所在的第6小组(共有7人,张杰为组长),进驻蒲松龄的故乡——蒲家庄。孙庭华回忆:“进村后,由于村干部鼎力相助,我们很快深入民间,和农民兄弟成为知心朋友。白天,头顶烈日,我们卷起裤脚,脱去衬衫,和他们并肩下地劳动,真正体验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劳动艰辛。田头休息,他们主动地给我们说笑话、猜谜语、讲故事。这时,我们也像当年聊斋先生搜集故事边听边记。晚上,在住处,点上蜡烛,埋头整理当天搜集到的资料,直到深夜才能上床睡觉。”当年30多岁的关德栋,“身着白短衫灰布裤,脚穿便鞋,头戴大草帽,手提黑布包。他这身装束,根本不像学者、教授,颇像县府机关干部”。关德栋平时与队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毫无学者和教授架子。
在蒲家庄,实习小组取得了一项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发现了几种蒲松龄的俚曲手抄本。孙庭华在文中生动地描述了蒲氏著作的发现过程:
一天,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那是早饭后,村长陪同一位慈眉善目、两鬓苍苍的老人来找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小心翼翼地解开一个黄布包,拿出数本深蓝书皮的线装书微笑问:“你们看这书中不中?”张杰连忙接过书来翻阅,原来竟是蒲松龄著作手抄本,全组如获至宝。顿时兴奋不已,异口同声说:“中!中!谢谢!谢谢!”。据村长介绍,老人名叫蒲英棠,年逾八旬,系聊斋先生八世孙。这些线装书,均出自他手。他于民国28年(1939年),用蝇头小楷抄写而成,为当时流传民间颇为珍贵的手抄本。征得老人同意暂借给我们用来手抄。关老师闻讯,从洪山镇小组赶来,对全组说:“材料异常珍贵。机会难得,全文照抄,一页也不能漏掉!”于是同学们开始了紧张地抄书工作。为了加快抄书进度,每晚不得不挑灯夜战到夜阑时分。由于全组齐心协力,昼夜奋战,我们终于如期抄完了聊斋外编。计有:《幸云曲正德嫖院》《禳妒咒曲》《磨难曲下部富贵神仙曲》《学究自嘲》《蓬莱宴》和《农经》。这些抄本为研究蒲松龄提供了殷实资料。
在蒲家庄,实习队在搜集民间文学作品之余,还在住处的大院里办了夜校,帮助农民提高觉悟和扫除文盲。他们克服诸多困难,自己编写、刻板,油印了《识字课本》,年轻人人手一册,在村里掀起了读书识字的热潮。
四、“生产实习”的成果——《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
这两次“生产实习”结束后,实习小组将采风所得编印为《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三册,分为“沂水卷”“淄博和洪山卷”。“沂水卷”所搜集的材料分为“歌谣类”“快板类”“谚语类”“谜语类”“歇后语类”“故事类”“曲艺类”,共七类,计11万余字,其中“歌谣类”所占篇幅最大。所收歌谣题材多样,其中有传统歌谣,如《五更调》《小白菜》《绣花灯》等。这些歌谣在坚持小调常见母题的基础上,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无论是方言土语的运用还是对地方特有景物、器具的描摹,都呈现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全面反映了当时沂蒙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其中一首《十二月》云:
正月里,正元宵,俺想妹妹谁知道,清晨拉着大车去,盼俺妹妹来看热闹。二月里,龙抬头,俺想妹妹泪交流,清晨拉着大车去,伴着妹妹来吃糖豆。三月里来,三月三,家家门口扎秋千,人家秋千一丈二,俺家秋千一丈三。四月里,四月八,快快地里按黄瓜,人家的黄瓜才开花,俺家的黄瓜一大扎,清晨拉着大车去,伴了妹妹来吃黄瓜。妹妹吃肚俺吃巴,妹妹不来俺不开家。(19)关德栋等编:《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1956年,第35页。
歌谣中多有赞美沂蒙人民积极支前、英勇抗日的,如《打下沂水城》《抗日人家真光荣》《赶走鬼子享太平》《送军粮》《抬担架》等,表现了沂蒙人民同仇敌忾,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如《抬担架》:“一条扁担嗨呀呼嗨啊,两头弯弯嗨呀呼嗨啊。扇扇如飞嗨呀呼嗨啊,俺去送给养嗨呀呼嗨啊。俺去送鞋袜嗨呀呼嗨啊,俺去送子弹嗨呀呼嗨啊。我要上前线嗨呀呼嗨啊,帮助同志们嗨呀呼嗨啊。打倒鬼子回家嗨呀呼嗨啊,打倒鬼子回家才光荣嗨呀呼嗨啊。”(20)关德栋等编:《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1956年,第9-10页。《开展大生产》:“开展大生产,就在今一年,毛主席号召咱组织起来干,互助变工多生产,开荒造林把井钻,保证每亩多打十斤粮,每人保证一分棉。合作社要普遍,互助变工多生产,开荒造林把井钻,和平永远实现,这样每人有吃穿。军队有吃穿,经济不困难。咱们要改造二流子,贪吃的那懒汉。大家齐生产,你帮我,我帮你,努力干,完成号召帮助抗战,和平永远实现。”(21)关德栋等编:《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1956年,第14页。
歌谣中描写了沂水作为解放区的种种新气象,赞扬了勤劳奋发的劳动者,对女性勇敢追求婚姻自由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进行了热烈的歌颂,“识字班”,这一沂蒙山区特有的名词被沂蒙人民在歌谣中反复传唱:
识字班来真模范,拿上书本儿去上班,一上上了下二点,快到家里快纺线。各人识字各人好,现在的妇女提高了,能看书来能看报,还能看看北海票。有的妇女不识字,瞪着二眼干着急,人家识字懂道理,大瞪二眼干生气。(22)关德栋等编:《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1956年,第42页。
歌谣中多有作于1950年代之后者,这些作品,大多是赞颂党的好政策和吟咏当时工农业生产的新气象。正如《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的“编辑说明”所说:“其中某些看来似乎属于文人或工作队的作品。”例如,《打倒侵略的强盗》:“打倒侵略的强盗,建立和平的阵营,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世界的和平,团结起来高举我们的拳头,英勇向前,消灭我们敌人,争取民族解放,争取世界和平。”(23)关德栋等编:《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1956年,第23页。这类似宣传队的标语口号。其他如《坚决镇压反革命》《自由结婚》《共产主义社会万万岁》《爱国增产解放台湾》等也是如此。如《共产主义社会万万岁》:“今年一九五五年,新的形势大转变,上级颁布了总路线,一切的工作要实现,咱就在抗美援朝条件下,大规模经济建设订计划,又建设,又生产,工业农业大开展。文化学习大翻身,速成学校搞重点……买上猪,买上羊,积肥工作做的强,上在田里才能打粮,三大统购卖余粮……老百姓说是政策强,高高兴兴卖余粮。很高兴,很自然,为了三大来支援,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各个工厂都发达。”(24)关德栋等编:《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1956年,第109页。
“快板类”以歌颂人民军队和描写乡村日常生活为主,例如《黑妮黑小》:
八月十五是中秋,小两口子打黑豆,一场黑豆没打完,生了一个黑丫头。一岁两岁娘怀里抱,三岁四岁会爬行,五岁六岁遥街走,黑了个头长到了十八九。爹又愁,娘又愁,黑妮那里说黑话:“一不用烦,二不用愁,早晚找到个黑对头。”左手挎着个黑提篮,右手拿着个黑镰头,迈动黑步朝前走。前次出了黑庄头,到了黑石头沟里,挖了一棵黑老婆菜。来了个黑小放牛,头上戴着个黑苇笠,身上穿着件黑蓑衣,乌木鞭杆黑穗头,猪毛绳牵着个黑舐牛。黑小那里溜溜眼,黑妮那头点点头,咱二人天生就是黑对头。定上了八个黑轿夫,定上了六个黑吹夫,半夜三更把门过,点灯就使黑豆油。(25)关德栋等编:《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1956年,第120页。
这类作品语言诙谐,朗朗上口,充满了浓浓的沂蒙山区的生活气息。
“谚语类”分为“关于事理的”“有关农作的”“关于自然现象的”和“其他”。“谜语类”分为“工具及日用品类”“农作物、植物与食物类”“动物(鸟、兽、鱼、虫)”“动物的附件(人身上的东西)”“自然现象”“字谜类”“其他类”和“附录”。“歇后语类”分为“借音的”“喻意的”。所收“谚语”“谜语”“歇后语”都体现出朴素的农家智慧。
“淄博和洪山卷”分为“故事类”“歌谣类”“谜语类”“谚语类”“歇后语类”“曲艺类”,共计18万余字。附录为“蒲松龄俗曲及杂著”,包括《幸云曲正德嫖院》《学究自嘲》《禳妒咒曲》《富贵神仙曲》《蓬莱宴》《农经》《蚕经》《蚕经补》八种,共计20余万字。其中,“故事类”包括“关于洪山的故事”“民间传说”“一般故事”“笑话”“动物的故事”“神灵与鬼怪”“关于蒲松龄的传说”七类。其中“关于洪山的故事”和“关于蒲松龄的传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在有关洪山的故事中,洪山被描述为一座聚宝的宝山,吸引着芸芸众生前往寻宝。“谁能打开洪山头,管保白银向外流”,每次获宝的幸运儿总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误打误撞者。这种对金钱和财富的向往,以及对摆脱现实困境的强烈渴望,正是传统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主题。
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隶属于洪山镇,距离洪山煤矿不远,庄内蒲姓占大多数,他们十分敬重蒲松龄,称之为“蒲老祖”。关于蒲松龄的故事和传说,也在当地代代相传。这些故事一部分带有神话色彩。因为《聊斋志异》有较大篇幅写鬼写妖的关系,在蒲松龄乡亲的眼中,蒲松龄本人也与花妖狐魅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如《打败狐仙》便描述蒲松龄因为在书中骂鬼神而得罪了狐仙,狐仙要谋害他,结果他机智地打败了狐仙,并经历了一次张鸿渐式的骑物飞行。另一类赞美了蒲松龄机智风趣的性格和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如《狗骨头》《鲤鱼大闹滚水滩》等。这些故事将蒲松龄刻画为一位身穿老蓝布褂子、骑着小毛驴的智者,他聪明机智、自立自尊、不惧权贵。如《狗骨头》:
蒲松龄的一个朋友在京里做很大的官。一天,朋友的生日到了,京里来了很多贵官大人、王子皇孙给他祝寿,穿的都是绫罗绸缎,摇摇摆摆,大有昂然自得之感。蒲松龄也去了,穿的是老蓝布褂子,坐在席上简直是黄豆锅里按上个黑豆,只好一句话不说,呆呆地坐在那里。
席间,一个年青的王子皇孙见他不说话便逗趣地说:“聊斋先生,你不是会讲故事吗?讲个故事俺听吧!”蒲松龄赶紧推辞说:“岂敢!岂敢!乡下佬还会讲故事?”“快讲吧!快讲吧!”接着乱嚷了起来。蒲松龄见推辞不过便讲了。他说:“那一年我去南方游玩,走进一家铺子,想买双象牙筷子,掌柜的拿出很多来,一封一封的都用绫罗绸缎包着,我打开一看,都是些狗骨头,我说:‘掌柜的你还有没有?’掌柜的就又拿了一双来,是用老蓝布包着的,我急忙打开一看,啊!这真是象牙筷子!”
蒲松龄曾在《述刘氏行实》中赞美妻子刘氏为人温婉贤德,刘氏“入门最温谨,朴讷寡言,不及诸宛若慧黠,亦不似他者与姑悖謑也。姑董谓其有赤子之心,颇加怜爱,到处逢人称道之”(26)(清)蒲松龄:《聊斋文集》卷七,盛伟:《蒲松龄全集》第二册,学林出版社,1998年,总第1308页。。但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关于刘氏的传说》却颠覆了蒲松龄的这一评价:“蒲松龄的妻子刘氏,很厉害,人们都很怕她,她的园子里种了许多桃李,谁若偷去她的桃李,她就咒骂,偷的人就会手疼。”同一位刘氏,在蒲松龄和他的乡人眼中却是如此不同的形象,让人读来不禁莞尔。
因为是蒲松龄故乡的缘故,“淄博和洪山卷”搜集到很多神灵鬼怪的故事,其中多篇与《聊斋志异》有着相同的故事情节。例如,在《李半仙》的故事中,凡人为仙女破解天灾、骑上马鞭御风而行的情节,明显可以看到《娇娜》《张鸿渐》的影子。
五、结语
山东大学“人民口头创作”课程的设置和两次“生产实习”虽然是特定学术生态中的产物,但是它开启了山东大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先声,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中文系进行民间文学田野调查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次“生产实习”虽然以缺乏田野工作经验的在校学生为主体,但因为有严格的专业培训和高效的组织指导,使得整个采风活动科学、有序又富有成果。据郭延礼回忆,关德栋反复提醒参加实习的同学要注意调查方法,其中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第一,搜集民间文学,首先要尊重被搜集者,要抱着一种虚心向他们学习的态度……要有一种尊敬老师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第二,要忠实记录,这是搜集民间文学一条重要的原则。在记录歌谣、民间故事时,一定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本来面目,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想法随便更改增删、加工润色,即使作品中的糟粕也要忠实记录,并作必要的说明。民间文学从搜集整理到进行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绝对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倘记录不忠实就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27)郭延礼:《关先生教学的回忆片段——悼念关德栋先生》,中国俗文学学会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关德栋教授纪念文集》,2006年,第83页。
因为早于1958年“新民歌运动”轰轰烈烈搜集民歌的热潮,所以这两次“生产实习”较少受到浮夸风的影响,所收民间文学作品较为鲜活和真实,其覆盖的民间文学形式和作者群体也较为广泛。这部油印的《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当时曾寄赠很多同行学者,得到了学界的好评。2005年关德栋去世后,很多与他熟识的朋友和学生所作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两次民间文学调查和《资料汇编》(28)刘锡诚先生在《贤者之风——悼念关德栋先生》中回忆,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曾得到过一部,“可惜‘文革’中把这本珍贵的资料丢失了”。参见中国俗文学学会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关德栋教授纪念文集》,2006年,第25页。,对以关德栋为代表的山东大学民间文学团队所取得的采风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山东大学恢复民间文学教学不久,该专业师生就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课堂教学和田野作业的紧密结合成为日后山东大学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的优良传统。1981年4月,借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临沂召开学术年会的机会,关德栋带领学生在沂蒙山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民间文学采风,他们“分头走访了近百个偏远的山村,接触了当地许多有名的‘故事篓子’和民间讲唱艺人”(29)张登文:《名师益友——深切怀念一代俗文学大师关德栋先生》,中国俗文学学会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关德栋教授纪念文集》,2006年,第124页。。所搜集到的资料汇编为《山东民间文学资料汇编》(临沂地区专集)。这可算作1950年代的两次“生产实习”在二十多年后的余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