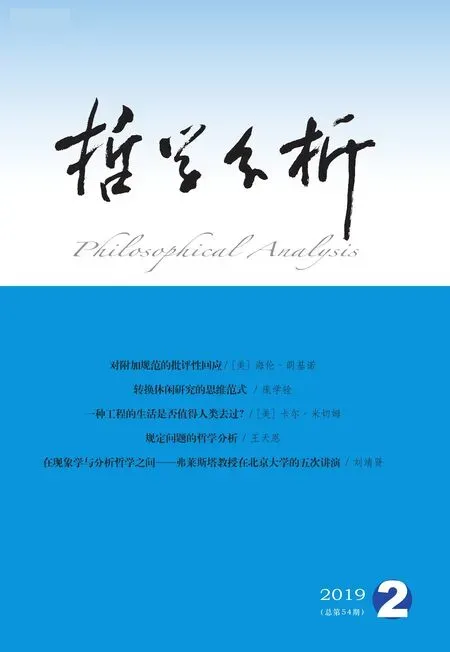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缺失了什么?
2019-12-16芬兰克里斯蒂娜罗琳
[芬兰]克里斯蒂娜·罗琳/文
董美珍/译
一、引 言
“潜存的异议声音不仅不能被忽视,相反,它们应该被鼓励扶持。”a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2.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就是这样一群哲学家的领军人物——他们为持不同观点科学家的认知利益进行辩护。bKirstin Borgerson, “Amending and Defending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 No. 3, 2011, pp. 435—449; Kristen Intemann, “Diversity and Dissent in Science: Does Democracy Always Serve Feminist Aims?”, in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ower in Knowledge, edited by Heidi Grasswick,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pp. 111—132; Philip Kitcher, Scienc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11; Miriam Solomon, Social Empiricism, Cambridge:MIT Press, 2001; Kitcher Philip, “Norms of Epistemic Diversity”, Episteme, Vol. 3, No. 1—2, 2006, pp. 23—36; Alison Wylie, “Introduction: When Difference Makes a Difference.” Episteme, Vol. 3, No. 1—2, 2006,pp. 1—7.所谓“科学异议”是指“与广泛接受的科学理论、方法或假设背道而驰的观点”aKristen Intemann and 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re There Limits to Scientists’ Obligations to Seek and Engage Dissenters?”, Synthese, Vol. 191, 2014, p. 2753.。然而,仅仅有异议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有足够的论据去挑战一种传统的共识观,即相关科学共同体的大多数科学家所共同接受的观点。bPhilip Kitcher, Scienc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p. 217.
科学异议被认为在认识论上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帮助科学家识别与纠正错误的假设。与此同时,科学异议也可以引导科学家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寻找新的证据、提出新的假设和理论,以及发展新的研究方法。c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80.即使异议不能给科学家提供一个充足的理由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它也可以促使他们在为自己的观点进行更有效的说明和辩护的过程中显示其观点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因此,异议通过改进科学理论而被广泛接受的理由,间接地促进了科学知识的进步。dMiriam Solomon, Social Empiricism, p. 97.然而矛盾的是,科学异议在显明科学共同体的批判性及对挑战的开放性中,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大众对科学的信任度。e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nd Kristen Intemann, The Fight Against Doubt: How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
我认为有必要为科学中合乎规范的异议制定标准,所以我讨论了海伦·朗基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CCE虽然强调了异议的认识论益处,它也引进了相应的约束来定义哪些是规范上适当的异议,即“应该有机会被倾听和认真对待的那种异议”bKristen Intemann and 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re There Limits to Scientists’ Obligations to Seek and Engage Dissenters?”.。朗基诺认为,异议者和共识科学家都应该遵循四个标准:公认的科学场所、接受批评、共同标准和知识权威的适度平等。c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p. 129—134.当异议者遵循CCE准则时,意见一致的科学家有义务参与异议;否则,他们可以理所应当地忽略它。
我认为CCE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应当以弱而非强的标准来解释共享标准;第二,要以社会的而非个人的方式来理解接受标准;第三,CCE应考虑到科学家的物质—认识资源,因为其形塑了科学家以适当方式提出或回应批评的能力。所谓物质—认识资源,我指的是履行知识职责所必需的资源,包括时间、智力——最重要的还有金钱。我对“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缺失了什么”这一标题的回答是:CCE缺失了对适用于科学的物质—认识条件公平性的描述。
关于公平的论述涉及一个原则,我称其为“认识责任的公平分配”dKristina Rolin, “Scientific Dissent and a Fair Distribution of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Vol. 31, No. 3, 2017, pp. 209—230.。认识责任的公平分配是认识责任的平等分配,这种分配使在交流中起关键作用的参与者之间因物质—认识资源的不对称而产生的敏感得到了缓和。当认知责任的分配是公平的,在物质—认知资源几乎相等的情况下,一个科学家不会被要求比另一科学家做更多的事情,也没有一个科学家被要求去做超过其所拥有的物质—认知资源之外的更多事情。这里认识论责任被理解为一种提供(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知识主张的义务,同时也考虑到其他科学家在任何特定时间的证据标准和背景假设。
二、提炼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
CCE关注科学家之间的互动,关心异议者的行为与“被打主意的”异议者e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nd Kristen Intemann, “Who’s Afraid of Dissent?: Addressing Concerns about Undermining Scientific Consensus in Public Policy Developments”,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Vol. 22, No. 4,2014. pp. 593—615.。例如,考虑到这样的担忧,即异议者通过营造一种其他科学家不敢公开表达观点的氛围而成功地在一场科学辩论中“获胜”。aJustin Biddle and Anna Leuschner, “Climate Skepticism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oubt: Can Dissent in Science Be Epistemically Detrimental?”调和的平等标准通过禁止恐吓科学家而道出了这种担忧。如果批评带来科学家观点的转变,那么此转变应该是被赋予平等的知识权威的参与者公开对话的结果,而不是政治或经济权力使然。b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 131.此外,对科学研究处于停滞的危险状态的担忧,源于科学家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异议者的观点作出回应。cJustin Biddle and Anna Leuschner, “Climate Skepticism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oubt: Can Dissent in Science Be Epistemically Detrimental?”接纳标准对这一担忧至少做了部分回答,因为它不仅仅关涉共识科学家们,持不同意见者也要对批评作出相应的回应。d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 130.当异议者不能对批评作出回应时,他们应该停止一遍又一遍地引用同样的反对意见。eKristen Intemann, “Diversity and Dissent in Science: Does Democracy Always Serve Feminist Aims?”; Philip Kitcher, Scienc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p. 221.然而,当持不同意见者遵循CCE标准时,他们理应得到关注,而不是被压制或质疑。f有关“针对”异议者的争议,参见Anna Leuschner, “Is it Appropriate to ‘Target’ Inappropriate Dissent? On the Normativ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Skepticism”; Erin Nash, “In Defense of ‘Targeting’ Some Dissent about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Vol. 26, No. 3, 2018, pp. 325—359。
CCE虽然具有优势,但它仍需要改进。在这一节中,我着重解释这两个标准:共同标准和接纳标准。这两个标准在区分适当和不适当异议的规范性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将论证应该选择对共同标准规则的弱解释,而不是强解释,这不仅是出于认知方面的原因,也是出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弱解释意味着科学家有义务寻求和参与广泛的科学异议。我还认为,接纳标准不应当被理解为每个共同体成员都有义务寻求并参与到广泛的科学异议探讨之中。正如朗基诺本人所指出的,接纳的义务属于科学共同体整体。g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 129.
我们首先讨论共同标准。该标准陈述了科学共同体公共认可的标准需要参考哪些理论、假设、方法与观察实践可能受到的批评而制定。hIbid., p. 130.批判性交流的双方都有义务解释他们的批评或对批评作出回应,以使其至少符合科学界公认的某些标准。此外,必要时双方都有义务明确自己的标准,并针对批评进行辩护——或者当他们没有成功地这么做时,解释为什么要修改标准。iIbid., p. 131.
共同标准规则可以被解释为强或弱。jKristen Intemann and 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re There Limits to Scientists’ Obligations to Seek and Engage Dissenters?”较强的解释是,该标准要求共识观点的提倡者和反对者拥有相同的理论美德,对这些美德的解释相同,背景假设足够相似。在强解释下,散漫的互动往往局限于专业团体领域。强解释标准会限制科学家参与异议的义务,也要冒排除异议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可能在认识论上富有成果的异议。aKristen Intemann and 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re There Limits to Scientists’ Obligations to Seek and Engage Dissenters?”; 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nd Kristen Intemann, The Fight Against Doubt: How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p. 52.共同标准规则的弱解释允许背景假设和一些理论优点存在分歧,且相关共同体可以容纳不同专业的科学家与受过教育的外行。共同标准规则只要求共识科学家的标准和异议者的标准之间有最小的重叠,例如,经验恰当性。bKirstin Borgerson, “Amending and Defending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一个较弱的解释涉及要面对那些在认识论上没有成果的异议的风险。cKristen Intemann and 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re There Limits to Scientists’ Obligations to Seek and Engage Dissenters?”参与认识论上毫无成果的异议需要花费本可以投入其他项目研究的时间和精力。dJustin Biddle and Anna Leuschner, “Climate Skepticism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oubt: Can Dissent in Science Be Epistemically Detrimental?”
2016年秋,福伊特将其工业服务事业部出售给欧洲私募股权公司Triton,新集团正式更名为“Leadec(中文名:利戴)”,自此,Leadec成为Triton的一员。新品牌包括了两层意思:从语音上来说,该名字源自英文单词“lead(领导、领先)”和“tec(技术)”;另一方面,新名字强调的是Leadec以成为市场领导者为目标,帮助其在汽车行业以及相关领域的客户赢得竞争优势。
我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对共同标准规则相对弱的而非强的解释(强调经验的充分性),因为广泛征求不同意见在认识上的好处可能超过投入毫无认识成果的异议所付的代价。支持弱解释的一种考虑是,人们很难提前判断批评何时会在认识论上取得成果。与其立即拒绝一些批评,不如认真对待那些只符合意见一致的倡导者的少数标准的批评。对共同标准规则的弱解释为批评背景假设、标准与解释标准留出了空间,从而使异议者的认知利益最大化,同时为理论美德的多元化提供了空间,它承认理论美德是多元的且能以不同的方式合理地解释和衡量。eHelen Longino,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Theoretical Virtues”, Synthese, Vol. 104, No. 3, 1995, pp. 383—397.
选择对共同标准规则的弱解释的另一个理由是,强标准所涉及的风险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而不是坚持苛刻的标准来减轻。当采用弱解释的主要风险为浪费科学资源时,它可以通过在科学共同体中分配认识责任来管理风险。并非所有科学家都需要回应所有的批评。有了认识责任的分配,一些科学家有义务进行批评,而另一些科学家没有义务这样做。知识劳动分工是将浪费科学资源的风险降到最低的有效方法,而这一争议在认识论上却收效甚微。
此外,还有一个以道德政治理由支持共同标准的弱解释。科学共同体通过参与异议为公众提供一个了解科学知识本质的机会。这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有价值的——即便与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批判性交流在认识论上收获甚微。
梅洛-马丁(Inmaculada de Melo-Martin)和因特蔓(Kristen Intemann)在他们最近出版的《与怀疑斗争》一书中指出,共同标准规则的弱解释尽管最初很有吸引力,但已不再能够完成我们所期望的规范性工作。一个弱解释很难以一种可靠的方式确定不合规范的异议。例如,如果我们对共同标准规范采用弱的解释,那么对进化论的否定或对人为气候变化的怀疑就不可能表现为规范上不适当的异议,我不认可这个论点。我认为,当一个弱的解释与接受标准同时出现时,它拥有充足的规范性,这是因为异议者经常诉诸的对证据标准的非传统解释可能会受到挑战,而这种挑战要求被接受。基于上述所有这些原因,我认为弱解释优于强解释。
接下来我们看接纳标准。接纳标准要求,当批评满足共同标准规则和公共场所标准时则接纳批评。a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 129.接纳可能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在回应批评中捍卫、修正或放弃他们的观点。朗基诺强调,接纳标准是双向的:不仅主张共识的人有义务作出回应,异议者也有义务作出回应。bIbid., p. 130.
贾斯廷·比德尔(Justin Biddle)认为,有关接纳标准的解释可以更加个人化或社会化。cJustin Biddle, “Advocates or Unencumbered Selves? On the Role of Mill’s Political Liberalism in Longino’s Contextual Empiric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9, p. 616.个人化的解释认为,当共同体的所有或大部分成员参与批评时,共同体就满足了接纳标准。根据社会化的解释,当“共同体设法对批评作出回应,或避免知识停滞时,就满足了接纳标准,而不一定是共同体内所有人,甚至大多数人都有如此反应”dIbid.。与比德尔不同的是,我认为朗基诺并不打算从个人的角度来解释接纳标准。在朗基诺看来,一种批评或对批评的回应被社会所接受,正如共同的标准被社会所接受那样,“是站在多个微观认知和微观批评的行动中”e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 131.。这意味着,即使共同体中的任何个体成员没有发现批评与对批评作出自身的回应,她依然允许批评或对批评的回应作为该共同体的立场。
对接纳标准的社会化解释要优于个人化的解释,因为个人化给共同体内个体成员分配了过重的负担。根据社会化解释,共同体个人成员可以让共同体其他成员作为代表从事与异议有关的工作。当科学共同体分配认知责任时,个体科学家的负担会明显减轻,使得一些科学家可以对某些批评作出回应,而另一些科学家对另一些批评作出回应。认识责任的分配不需要集体决策,它可以是一些共同体成员自愿回应批评,而其他共同体成员支持和赞同他们的工作。人们甚至可以争辩说,为了让科学共同体有效地运行,他们需要分配其认识责任,以便那些拥有最好方法解决特定问题的科学家能够代表整个共同体对批评作出回 应。
我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我论证了:共同标准规则的弱解释与接纳标准的社会解释相结合,能够使科学共同体同时实现两件有价值的事情。对共同标准规则的弱解释使科学共同体能够通过容纳广泛的批评性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意见的知识效益。对接纳标准的社会解释鼓励科学共同体发展认识劳动分工,使共同体成员无需全部承担参与所有批评的任务,从而将接纳认识上无成果异议的成本降至最低。虽然认识责任分配不能保证科学异议不会给科学界带来任何损失,但它可以帮助将此成本降至最低。与通过强化共同标准规则的更严格解释而将异议者排除在科学争论之外相比,这不失为一种更好的策略。
但有人可能会提出另一个担忧:CCE管理科学异议的能力,即尽管通过在科学共同体中分配对批评作出回应的义务,降低了参与认识上毫无成果异议的成本,但有权势而又足智多谋的异议者也可以利用其物质—认识资源,对共识科学家施加不成比例的沉重认识论责任。知识权威调和的平等标准并不会阻止这样的行动,因它关注的是知识权威而非物质—认识资源。虽然知识权威也是一种认识资源,但它不同于物质—认知资源(时间、金钱和精力),因为拥有知识权威的人可能缺乏其他资源,反之亦然。而且,即使在满足知识权威的平等性标准的科学共同体之中,物质—认识资源也可能分布不均匀。一个科学家可能比另一个拥有更好的物质—认知资源,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另一个科学家拥有更多的知识权威,而是因为他在满足资助机构的社会相关性要求方面更加成功。
因此,对CCE剩下的担忧是,当科学家们承受着不成比例的沉重的认知责任时,他们就不再能够对异议者作出回应。正如基希勒(Philip Kitcher)所解释的,异议者可能通过使对手筋疲力尽而获得其想要的结论。aPhilip Kitcher, Scienc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p. 221.下一节我将讨论这个问题。
三、认识责任的公平分配
之所以对强大而足智多谋的异议者产生担忧,是因为在没有对批评作出回应的情况下,如何应用接纳标准并不总是很清楚。试考虑以下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缺乏回应意味着科学家没有认识到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的认知责任,例如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异议,或者他们没有认真对待异议者。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因科学批评没有得到延续而没有满足接纳标准。在另一种情况下,缺乏回应意味着科学家未能履行对异议者的认识责任。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项责任,而是其缺乏有效履行的方法。对于后者,有人可能会说,一方面,接纳标准因科学家认识到他们的认识责任而得到满足;但另一方面,由于科学家没有切实履行其认识责任而并未得到满足。
鉴于接纳标准在应用方面的模糊性,最令人担忧的情况是,科学争论的结束不是因为达成了协议,而是因为争论耗尽了一些参与者的物质—认识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异议者可以辩称接纳标准得到满足,因为共识科学家虽有机会捍卫自己的立场但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异议者可以声称自己“赢得”了一场辩论,因为公共场所、接受、共同标准和知识权威调和的平等性这四项标准似乎都得到了满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CCE需要一个公平的认识责任分配机制。这一要求将使我们能够为自己持有的观点进行辩护,(修订的)CCE规范在第二种情况下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存在认识责任上的不公平分配。不合理地将沉重的认识义务强加给科学家是不公平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当被置于对其有不合理期望、具有更多认识义务的位置。
认识责任的公平分配是通过认识责任的调和平等原则来实现的。该原则指出,认识责任的公平分配是认识责任的平等分配,这种分配是基于人敏感于物质—认识资源差异的意义上而得到缓和的。认识资源的权衡是相对的,且在科学争论的背景下进行。一个拥有较少物质—认识资源的科学家,不能被期望像另一个拥有较多的科学家一样履行其认识责任。
鉴于调和的认识责任平等原则,科学家可能至少在两种情况下无法遵循认识责任公平分配的要求。一种情形是,一些科学家没有认识到与其他科学家拥有平等的认知责任。当持不同意见者用不断重复其反对意见而不是改变观点来回应他们受到的批评时,情况就是这样。另一种情形是,一个科学家比其他科学家拥有更少的知识资源,但是其他科学家继续坚持知识责任的平等分配。此时,异议者拒绝承认物质—认知资源的分配不均,并成功地让一位科学家承担了过多的认识责任。CCE对第一种情况已经了解,所以调和的认知责任平等原则对它的影响并不大。但第二种情况调和的认知责任平等原则增加了CCE的优势,因为它要求应当对物质—认知资源的差异敏感。
对于捍卫认识责任适度平等原则,还需要更多的论述。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认识责任的公平分配是认识责任的平等分配,因为认识责任不只限于自身,它也是一种道德责任,因为它通过尊重人,特别是尊重人的认知能力而增进他人的福乐。就我们参与求知实践而言,我们对他人的认识责任仅限于他们也是人。这种主张的道德理由在于对人的尊重,这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作为认知受众的他人。因此,在求知的社会实践中,知识责任的平等分配属于一种默认设置。这是因为对人的尊重产生普遍而公正的道德责任。普遍性在于我们所有人都拥有它们,公正性在于它们基本上以相同的方式对待我们所有人。
然而,认知责任的平等分配只是一种默认设置,因为并非所有人在认知实践中都同样具备了履行其认识责任的能力。这使我认识到在认知责任公平分配原则中调和平等的重要性。认识责任的公平分配需要对科学家的物质—认识资源的不对称敏感,因为不对称可能损害开放、包容讨论的社会空间,它导致的结果是认识责任的公平分配并不总是平等分配。
综上所述,CCE应该要求公平地分配认识责任,而公平地分配认识责任就等于缓和了认识责任的平等要求。这一要求如何帮助我们不去担心那些强大且足智多谋的反对者对其他科学家强加过高的认识义务呢?修正过的CCE版本使我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诊断出哪里出错了。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持不同意见和一致意见的科学家在认识责任方面是平等的,但当物质—认识资源在争议各方之间分配不均时,继续坚持平等的认识责任是不公平的。而且,当一个科学家缺乏必要的物质—认识资源时,责备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认识责任也是不公平的。
四、结 论
根据CCE的看法,当持异议者在公认的科学场所提出他们的反对意见,回应对他们观点的批评,至少遵循共同体中共有的一些准则,以及承认知识权威的平等性时,异议在规范上是适当的。CCE打消了对异议者行为的许多担忧,包括担心一些异议者可能会威胁或恐吓意见一致的科学家,以及一些会拒绝回应对其观点的批评的情况。CCE面临更严重的一个挑战是:通过对共识科学家施加过多的认识责任来压倒他们的政治策略。当科学家的认识责任远远超过其所拥有的认识资源时,责任就显得过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可能就无法履行对异议者的认识责任,而将未能遵守接纳标准的责任归咎于共识科学家是有违常理的。
我已论证了:为应对这一政治策略,需要公平分配认识责任。认识责任的公平分配就是平等分配,这种分配需要考虑到科学家拥有的物质—认识资源的差异而加以调和。当认知责任的分配是公平的,一个科学家不需要比另一个物质—认知资源大致相同的科学家做更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科学家会承受过度的认知责任。我们可以相信,批判性的交流会终于协议的达成,哪怕是暂时的,而不是因为交流使一方筋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意见者不太可能通过制造怀疑来阻止科学共同体支持有充分根据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