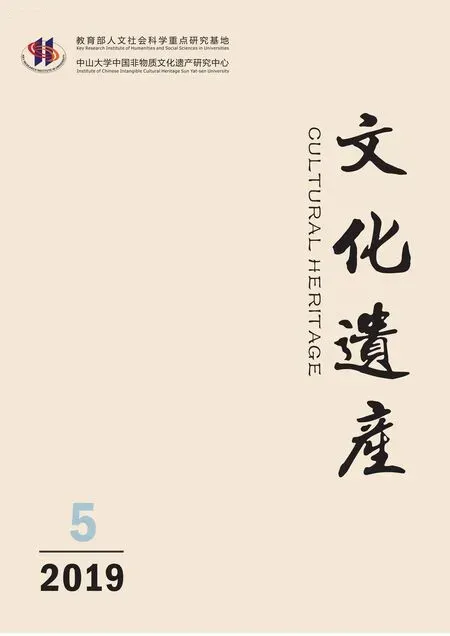“国家-地方-民众”视阈下的地方组织
——东莞明伦堂研究述评*
2019-12-16贾静波
贾静波
一、地方组织研究的理论视野
地方组织与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及发挥的功能与作用,是近年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迁,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演化与重构;进入21世纪后,伴随街居制的式微和单位体制的解体,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在社会参与、社会管理以及公共服务等范畴发挥有效作用,给当下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1)丁惠平:《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及其缺陷》,《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而近年对地方组织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当代社会组织的研究占据了更大的比例。笔者认为,古代、近代地方组织的研究亦应给予重视,作为曾经的社会结构要素,其研究对当代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并且有助于理清地方社会的历时性发展逻辑。
本文的研究述评对象——东莞明伦堂,即为一个历史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地方组织。它存在于1845年至1953年间,因拥有巨大的沙田产业而具备了雄厚实力,在地位和功能上早已超越了作为学宫内部建筑的明伦堂,足以干预东莞的地方事务,是一个类政府实力组织。在广东近代地方社会研究的多个范畴中,东莞明伦堂都是有代表性的突出个案,并可藉以参照分析中国近现代地方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过程,有利于理解相关的重要社会现象和问题。
地方组织处于国家、地方、民众互动网络中的联结点,要阐析其位置与作用,仍须回顾“国家、地方与民众互动”这一中国社会史研究要题的基本理论。国外学者业已在研究中形成一些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概念,其中对国内学界影响较大的如:克里福德·吉尔茨的“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2)[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域的结构性変化》,童世骏译,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21-172页。、以及黄宗智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实证研究提出的“第三领域”概念(3)[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32-433页;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场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程农译,《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核心-边缘”结构理论(4)[美]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叶光庭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63页。,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5)[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13-33页。,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关于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的开创性研究(6)[英]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1-178页。;此外,马克斯·韦伯提出儒教在中国发挥了调节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主要作用、从而维持社会秩序(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03-204页。的见解,玛丽·兰钦(Mary B.Rankin)(8)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p.126-167.;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70-201.、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孔飞力(Philip A. Kuhn)(9)[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1-229页。等学者对近代士绅群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作用和权力扩张状况所作的考察。国内学者对上述诸理论有所借鉴,在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实证的基础上进行思考与阐释,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士绅阶层、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民间信仰和传说、宗族社会、民间社团等具体领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10)参见 徐松如、潘同、徐宁:《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的理论与研究状况的概述》,唐力行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83-597页。。诚然,建立在西方历史和社会状况基础上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实情形的分析和阐释过程中,有时会表现得不适用甚至有论证断裂感。例如“国家-社会”理论范式在中国学界过于广泛的流行和应用,已有学者提出质疑并反思,认为这种理论范式更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质,并且会因过于关注结构分析而屏蔽行动分析(11)丁惠平:《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及其缺陷》,《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比较而言,“国家-地方-民众”的理论视野更为宽广,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尤其能够在结合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实证研究中,呈现出多重讨论维度。
那么,在“国家-地方-民众”的理论视野下,关于东莞明伦堂这一地方组织的研究做到了什么程度,有哪些得失?笔者综合目前所见文献,对这一问题试作解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东莞明伦堂并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经整理得著作1部(黄永豪,2005)和论文22篇,其中学位论文4篇(硕士论文3篇:韦锦新2002,黄素娟2008,谢景琴2012;博士论文1篇:王传武2015)。这些文献的研究主题主要分为三类:地方控制,沙田问题和地方社会事业,这三类主题都显示了对“国家-地方-民众”问题的观照。笔者将作分类述评,并从其中的学术焦点阐发开去,探讨东莞明伦堂乃至中国近代地方组织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二、研究焦点:地方控制、社会网络与社会事业
(一)在地方控制基础上展开的组织性质讨论
地方组织的性质涉及到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的权重比例问题,对分析地方社会的权力分配以及控制非常重要。不少学者关注了东莞明伦堂的性质特征及其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东莞明伦堂的专门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启,首篇以东莞明伦堂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是美国学者伍若贤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土地开垦、商人资本和政治权力:东莞明伦堂》(12)[美]伍若贤:《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土地开垦、商人资本和政治权力:东莞明伦堂》,刘志伟译,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10-544页。一文,由刘志伟教授据英文原作翻译了部分章节而成。此文考察了东莞明伦堂从清末到民国中期的组织运作及其对地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将明伦堂定位为“集团地主”性质,探究了民国时期明伦堂包佃人身份的转变,分析了明伦堂管理者与“二路地主”具体的获利方式。该文同时指出,20世纪20年代明伦堂在人事任命、财务整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从而有条件投入更多资金在地方教育和地方建设方面,为东莞和广东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作者辩证地看待了明伦堂在清末民初的经济社会中发挥的历史作用。
此前,伍若贤应邀来华所做的学术报告文章《清代民国珠江三角洲的乡族田与二路地主》(13)[美]伍若贤:《清代民国珠江三角洲的乡族田与二路地主》,《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中也谈到了东莞明伦堂。该文集中分析乡族田与二路地主的历史关系,讨论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性质和历史作用,认为造成民国时期农村危机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结构和人口压力的问题。明伦堂沙田田产扩张的例子用于论证官府和地方豪绅之间因税收问题发生的冲突。他认为,民国时期二路地主的背景发生了改变,明伦堂的二路地主身份性质是“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三位一体”。戴和将此文归入沙田之上生产关系的研究(14)戴和:《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概述》,《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明伦堂的研究在起点便具有了较为宏观的认识,将这个组织本身的性质以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置于重要地位。同时,“集团地主”“二路地主”等概念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探讨空间。
将东莞明伦堂进行专章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香港学者黄永豪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修订、于2005年出版的《土地开发与地方社会——晚清珠江三角洲沙田研究》(15)黄永豪:《土地开发与地方社会——晚清珠江三角洲沙田研究》,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5年。。该书着眼于沙田这种独特的土地资源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关系中的作用,具体讨论了沙田的田土性质如何影响地方乡绅的活动,兼及地方乡绅与国家政权的互动,从而展现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该书第三章以万顷沙为个案,阐述了东莞乡绅如何利用沙田的独特属性,将其拥有的政治、文化、人脉资源和主要地方势力结合,形成强大的地方组织,因而得以掌握万顷沙的控制权并影响地方事务。第四章以大良龙氏控制东海十六沙的过程,说明与万顷沙上游地区沙田控制方式的差异。结论中对比了万顷沙与东海十六沙的历史,表明在清代中后期乡绅是控制珠江三角洲沙田的主要角色:地方乡绅为取得官府的文化和政治体系的资源,推动了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而土地资源反过来也塑造着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基于翔实的史料,作者得出一个观点:作为影响地方社会的主体——乡绅,在地方控制角色上与宗族存在差异。从经营沙田、与官府的关系以及自身文化资源和社会地位各方面的考察来看,乡绅比宗族的力量更为重要,在地方社会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乡绅才是影响地方社会的主体,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华南地方社会结构与秩序的研究路径,提供了新的阐发方式,以往研究则是多将明伦堂的经营管理者确定为宗族。该著作对东莞明伦堂乡绅的身份和背景挖掘深入,运用了很多土地契约类的材料,对明伦堂与东莞地方社会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多有启发。
第一篇全文对东莞明伦堂进行专门研究的学位论文,是韦锦新的硕士论文(16)黄永豪写于1987年的硕士论文同样以东莞明伦堂的例子作为部分章节来论述,并非全文论述。《地方公产与地方控制——东莞明伦堂研究(1845-1953)》(17)韦锦新:《地方公产与地方控制——东莞明伦堂研究(1845-1953)》,中山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该文以明伦堂获得大片沙田的初期和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晚清至民国后期东莞地方社会的转变。他对明伦堂的性质表述是因不同时期的特点而定的:简要而言是一个地方公产的管理机构,后来又发展为半官方性质的地方财团,形成在地方割据分肥的官绅集团。该文从东莞明伦堂的运作和人事变更两方面探讨东莞地方社会领导权的转移,论述了明伦堂公产的确立与清末万顷沙的开发、民国时期的明伦堂与地方政治的关系、明伦堂经营方式的转变以及明伦堂对东莞地方建设的作用几个方面。该文的贡献在于:首次从完整的存在时间对明伦堂进行全面研究,陈述了明伦堂的资料情况,梳理了明伦堂的缘起及发展历程,尤其呈现了明伦堂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几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性,并讨论士绅和军人集团对明伦堂的控制和影响,点明了会计独立制度和田租征实方式对明伦堂经营管理产生的影响,在研究线索方面对后来者具有启发和指引的作用。但有关明伦堂与地方建设的领域尚未深入涉猎。关于东莞明伦堂的整体研究,还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
邱捷《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18)邱捷:《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一文,指出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问题:辛亥革命冲击了广东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包括警局、区乡办事所和团局),民初时这些机构便以各种方式来恢复或重建。政局动荡之下,省、县级政府不足以充分控制乡村,使基层权力机构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性,不少地区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格局甚至延续到40年代末,民国政府的新县政亦对其无可奈何。作者认为明伦堂也是这样的一个“公局”,当民国初年珠三角地方“护沙”自卫团与政府护沙军争斗之时,明伦堂这个旧有权力机构仍然被东莞士绅所掌握,一笔“开拔费”将政府护沙军请走,避免了政府护沙武装对万顷沙的控制。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伦堂在民国初年的权力格局及其对东莞社会结构所起的作用。(19)邱捷的另一篇文章《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的论述对象是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其后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也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明伦堂的管理情况在以往研究中并不明晰,一些回忆录中只提到当时存在“真”“伪”两个明伦堂,分别由原董事会和日伪政权管辖,佃户要向两边交租而生计艰难。王键在《抗战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对广东、海南的经济侵掠》一文中提到抗战期间日军对东莞明伦堂的掠夺和利用,即1939年侵粤日军指使台拓与伪政权合办兴粤公司,专为日军提供粮草,主要经营的便是东莞明伦堂公产及中山大学农场官产。(20)王键:《抗战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对广东、海南的经济侵掠》,《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文中梳理了关于台拓公司经济侵掠中国大陆方面的研究,指出大量档案史料典藏于日、台,如日本外交史料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及台湾中研院、台湾文献馆等处,包括大量原始档案。台湾学者朱德兰、钟淑敏等在台拓对华经济侵掠方面有较多探讨,但阐述主要集中在台拓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范围,视野仍须扩展。大陆学界近年来开始关注这一课题,但总体来说研究刚刚起步,原始史料也相对匮乏。王键此文令我们获得了有关明伦堂研究的更多线索,即藏于日本、台湾两地的台拓原始档案资料里,可能会找到东莞明伦堂“伪堂”在抗战期间的经营管理详请,进一步探究这种状况和对东莞乃至广东社会的影响。
以上,在地方控制这一领域,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通过考察东莞明伦堂的组织运作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得出其在地方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确定该组织的性质。那么,无论是集团地主(伍若贤所言,并且我们可以认定绝大多数地主就是当地的“绅”),还是乡绅(黄永豪所言)、士绅(韦锦新、邱捷所言)、官绅(韦锦新所言)作为组织掌控者,这些描述明伦堂组织性质的说法,都强调了明伦堂由“绅”所管理的本质。黄永豪提出,在影响地方社会的主体方面,乡绅的作用更为显著,并指出乡绅与宗族在地方控制角色上的差异。这是对华南社会结构根本问题的讨论,尤为可贵。已有许多研究阐述了宗族在华南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宗族成为理解华南地方社会的首要切入点,也是理解华南社会的基本方法和路径。在这方面,被称作“华南学派”的学者群体之研究取向影响颇大。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宗族在东南地区的地方社会、区域文化和它从宋明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充当了一个核心的角色,往往成为地方社会及其历史变迁的组织形态、意识模型、框架、途径、方式和表达等,宗族大体上成为中国社会“东南观”的一个范式。但是,进入中国东南地区必以谈宗族为核心的思路,是否也会对研究构成某种程度的消极影响?宗族对于相当多的“事实”并不具有整体的“普适性”,也不能上升到理论模型的高度。宗族对于地方社会及其历史变迁所具有的种种“内生性”意义,很可能是宗族的实践者刻意用话语构建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众多研究者不断累积、强调而带来的一种感觉或者印象。“华南学派”的学者自身已有这方面的反思:“宗族……是一个需要不断被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下去解释和讨论的‘问题’和‘现象’。……只是用它来说明关于中国的国家-社会体系的建构过程的一种(并不是唯一)重要表现形式。”(21)黄向春:《“学术共同体”抑或“范式”:我所理解的“华南研究”》,《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宗族形态自然也是社会基本形态之一。在东莞明伦堂这一地方组织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其组织管理层亦为地方上一部分有势力绅士的联合体,但是,强宗大族却并非这些绅士的必然背景,宗族势力只是一个影响要素而非全部。关于东莞明伦堂组织性质的研究,可以与宗族理论范式研究形成对话或补充。对此,黄永豪、韦锦新、王传武的研究可以说都在这方面有所强调和思考,但是在东莞明伦堂出现的历史条件方面探讨还不够深广,对明伦堂组织的超越性挖掘不够。而这种地方组织所凝聚的力量在其成员本身属性之上的超越性,正是在“国家-地方”这个研究维度上结合具体历史发展时期可作的突破。
(二)从沙田问题中解读的地方社会网络
沙田是东莞明伦堂的主要产业和经济基础,因而论及明伦堂必然涉及沙田问题。正是沙田的特殊性质导致了地权问题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复杂化,这种复杂化体现了国家制定的政策与地方实际施行的差异,并显示了地方社会网络的运作与影响。多位研究者对明伦堂的分析阐释基于沙田的层面展开。
日本学者西川喜久子曾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广东搜集资料和做田野调查,其论文《清代珠江下流域の沙田について》(22)[日]西川喜久子:《清代珠江下流域の沙田について》,《東洋学報》The Toyo Gakuho 63(1·2), 1981年第12期。以广东沙田的占有形式为研究对象,详细考证了沙田的具体形成过程及垦殖方式的变化,解释了“潮田”“围田”等概念及其差异,进而论述沙田经营方式的变化原因、土地所有权的种类及演变过程。该文以民国《东莞县志·沙田志》为主体,结合《顺德县志》《桑园围志》和张之洞奏折等文献材料,剖析当时沙田在圈筑、垦殖、经营、佃耕等方面的具体方式及惯例,明确了沙田上的所有权和生产关系。参考和援引的文献较为全面,尤有参考价值的是文后附注了一个学田、公产、义仓等名义下沙田的田产数量表,再加上35条详细的注释,有助于后来者了解和探究信息源。西川还提出一些拓展性的问题:沙田与乡绅之间的关系,沙田所有者应具备哪些实力,承包人的资本是如何积聚起来的等等,如今仍需深入探讨。(23)西川喜久子这篇日文论文有两个版本的译文,一是发表在《岭南文史》1985年第2期的《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考》,由曹磊石翻译,二是发表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1年第3期的《清代珠江下游地区的沙田》,由翟意安翻译。曹文比翟文更为详细,但翟文保留了更多的注释条目。这两个版本可相互参照阅读,以利于理解。作者以较大篇幅梳理了沙田开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围田”的出现阶段,详以东莞明伦堂为例,描述了东莞明伦堂获取万顷沙的过程,更难得的是她关注到与东莞明伦堂展开争夺的温植亭、郭进祥、郭亚宝等人,对他们的身份背景加以解析。
沙田地权问题离不开对国家宏观层面沙田政策的探讨。程明发表于1986年的文章《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述略》(24)程明:《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述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梳理了清代的沙田政策史,关注点在于清政府制定或改变沙田政策的目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政策上有一项重大变化:新涨沙田列为屯田,所有权收归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财政困难、军备匮乏,收管沙田可以扩展财源。国家对沙田租佃关系的管控较为松懈,导致大量的私下转租变卖等情形,如东莞明伦堂从承佃人潘敬义、潘德昌手中接佃沙田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文章还讨论了东莞明伦堂如何行使权力及如何成立武装来维护自身利益,并肯定了明伦堂管理的广袤沙田对当时东莞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吴建新《清代垦殖政策的两难选择——以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放垦与禁垦为例》(25)吴建新:《清代垦殖政策的两难选择——以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放垦与禁垦为例》,《古今农业》2010年第1期。也关注了清代政府沙田垦殖政策的变化及其实际应对。围垦沙田有时会阻碍水道,所以广东地方政府禁止这种围垦客观上是有益的,但各种利益集团与政府相博弈,造成禁令施行困难。为保护水环境和防止灾害,清代仍在有限的时期和范围内实行了禁垦令。文章援引了黄永豪对晚清士绅通过各种力量控制沙田的研究, 作为地方利益集团与政府博弈的具体例证。这个例证在明伦堂研究中屡有出现,即光绪十二年张之洞为清丈广东沙田而打击东莞士绅势力,遭到强烈对抗,东莞明伦堂乡绅甚至能够动员京官对张之洞施加影响,以致张之洞作出重大让步,充分证明了东莞士绅的政治实力。
叶显恩、周兆晴在《地权转移过程中的商业化精神》(26)叶显恩、周兆晴:《地权转移过程中的商业化精神》,《珠江经济》2007年第11期。一文中讲述了在晚清珠三角农业商品化加深、地权转移加速的条件下,出现炒买炒卖土地、或将土地买卖作为物业经营手段的现象。当时在拍围不久的边远沙区,耕作管理由“结墩而耕”变成围馆经营。所谓“围馆”,是该围田的管理机构,一般是建在围内平坦高地上的房屋、禾场、炮台等。围馆首领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雄厚的大耕家,他们委派代理人驻扎围内总管事宜。文中列举的代表性大耕家,就是民国年间东莞明伦堂最有势力的大耕家邹殿帮和何同益。对于二人财力和社会资源的描述,使我们了解到明伦堂管理万顷沙的手段和细节,有助于分析大耕家的身份背景及其资源,加深对万顷沙生产关系的理解。张晓辉的《略论民国时期广东经济的若干特征》(27)张晓辉:《略论民国时期广东农村经济的若干特征》,《广东史志》2005年第2期。一文则点明富商邹殿邦为东莞明伦堂的“二路地主”。
沙田地权这一研究角度,出现了首篇将东莞明伦堂作为专章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王传武的《土地产权与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演变》(28)王传武:《土地产权与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演变》,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该文对东莞明伦堂的定位是:以沙田为经济基础的一批地方绅士的联盟组织,考察焦点是:为何东莞能够产生明伦堂这样的组织,它如何控制和经营沙田,这种特殊的地权关系又怎样导致了地方绅士与官府的对立。该文在第二章第三节“东莞明伦堂的形成及其地权结构”中,论述了东莞一批科举新进之家如何制定有效策略,成功地建立起影响力巨大的公产机构;其“保佃接承”的控产方式,是后来与省级大员激烈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对争夺万顷沙过程的考察上,该文着重讨论东莞乡绅的谋略,前述黄永豪的著作则是聚焦于乡绅与官府的联结。该文亦细致考证了参与争夺万顷沙的东莞士绅的出身和生平,为我们了解这些当事人提供了详细的分析和更多线索。该文详细描述了光绪十四年(1888)明伦堂士绅与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冲突博弈,而冲突的主要分歧是双方对明伦堂管理之沙田的地权结构有不同理解。作者认为“管业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一角度对理解双方冲突的事实基础深有启发。沙田土地产权的演变也与沙田地区的社会流动样态及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大有关联,作者在这方面的考察中关注到地方自治问题和近代乡村的现代性问题,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可对后来者的相关研究提供启发。
地权是利益攸关所在,往往引起各种争夺。黄利平在《晚清珠江口的沙田争夺》(29)黄利平:《晚清珠江口的沙田争夺》,《寻根》2016年第6期。一文中以地方志和碑刻材料为基础,阐述了晚清珠江口地区社会沙田争夺的三种方式:区域之间的争夺、沙田业主之间的争夺和军队与承税业主之间的争夺。该文以东莞明伦堂获取万顷沙的例子阐述区域间的争夺。而这种地权引起的争夺还延续到当代。曹正汉《地权界定中的法律、习俗与政治力量——对珠江三角洲滩涂纠纷案例的研究》是有关明伦堂研究的一篇较为特殊的论文,其论述核心是当代的珠江三角洲地权问题,东莞明伦堂是一部分历史背景。该文表明即便在当代,政府制定的法律仍然不能成为界定滩涂地权的主要依据,实际中多以传统的沙骨权和围垦投资达成的既成事实为依据,并依靠当事人自身的政治力量来具体实施。该文以法治作为分析立场和观照角度,探索国家法律在地方社会的实际应用中遭遇困境的原因,即:中国法律的制定特别是实施并非全以法律规则为准绳,而多以社会规范为基础;政治领域与法律领域连接紧密,使政治力量有绕开法律直接争取地权的机会。作者在文中参考了黄永豪和伍若贤的研究,指出政治力量在珠江三角洲滩涂开发与产权界定的历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0)曹正汉:《地权界定中的法律、习俗与政治力量——对珠江三角洲滩涂纠纷案例的研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广东卷)第六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712-806页。。他在此文中重点分析的案例是1988一2000年中山市与番禺市的滩涂划界纠纷,详细描述了中山与番禺对万顷沙南端滩涂在划界和归属上存在争议、冲突升级的过程,后经省政府调解数次仍未解决,只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力量的消长暂时达成一致。文章表达了对日后沙田所有权争端仍会出现的预测和忧虑。该文的当代案例,让我们读到东莞明伦堂在终结之后、万顷沙衍生的新沙上发生的地权争夺故事。其中习俗、法律和政治力量对于地权的作用,以及各方博弈与力量的消长,均可与150多年前东莞与香山的万顷沙争夺过程比较和参照。
沙田的开发过程较为复杂艰难,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31)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凸显了宗族在沙田开发中的重要性。该文指出,沙田开发不仅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还需要与之适应的社会组织。有足够的且能协同一致的群体力量,才能进行堤围兴修、沙田开发和管理防卫等一系列事务。东莞明伦堂作为例证,一是说明大型沙田开发需要把商业资本与大宗族、政治势力结合起来,比如正因顺德龙山温氏家族拥有大族和巨商的地位,才得以先行承垦万顷沙。二是说明解放后在土改过程中有一条原则,就是将规模较大、不利于分散经营的水利工程收为国有,万顷沙因此成为国有的沙头乡华侨集体农场。这两点都说明沙田开发需要实力强大的组织接手才能实现,宗族是这样的组织,明伦堂是比单个宗族更强的组织,而解放后比这些组织强大得多的接管者,就是国家了。
关于国家与地方社会、宗族的关系,科大卫的著作《皇帝与祖宗》中结合华南社会的实例有详细阐释。该书的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二章提到了东莞明伦堂。在说明沙田业权的分配需要武装力量支撑,以及沙田业户与士绅、地方安保力量、官府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的关系网络问题上,作者运用了东莞与香山争夺万顷沙的诉讼过程和判决结果,以及虎门炮台的给养依靠万顷沙的部分沙田收入这些历史材料(32)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6-338页。。科氏还将明伦堂与顺德县团练总局并提,以说明东莞明伦堂的规模之大。在黄永豪对如见堂张氏家族在明伦堂沙田控制方面的研究基础上,科氏阐释了团练领袖在地方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位置,指出领导明伦堂的士绅都来自东莞的望族,亦参与团练运动,因而来自望族的士绅是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继而,他还点明了在同治三年(1864)左右,东莞明伦堂已成为东莞县的团练组织,由县里的高层士绅组成的机构——安良局管辖。明伦堂管理团练和管理沙田产业这两项事务是紧密相关的,而掌管明伦堂的士绅,自身也以股份制形式参与大型的沙田开发项目;明伦堂的佃户亦由明伦堂士绅担保,这样的保护网有利于这些佃户的家庭或宗族日后购置更多的田产。(33)科大卫:《皇帝与祖宗》,第352-354页。科氏的分析,从地方团练权力运作的角度,牵出地方的团练组织者与望族在沙田开发、威望营造方面的密切关系,阐述了士绅、宗族控制地方社会的力量。以张其淦等遗老身居上海仍遥控家乡的沙田事务等为例,科氏得出结论:20世纪的宗族形式虽变,实质未变,控制土地的宗族依旧稳健运作,保持着强大的实力,在清朝覆亡的时间节点,“新”与“旧”并非能够截然划分。(34)科大卫:《皇帝与祖宗》,第401-404页。
科大卫和叶显恩的研究,大体上仍是从宗族着眼来看待沙田的开发以及明伦堂。这与我们在上一部分关于明伦堂“属性之辨”的讨论有所关联,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宗族理论范式的反思,也可以从中辨析宗族、士绅在地方网络中发挥的作用。
此外,还有研究是从农业技术手段层面来探讨明伦堂的沙田管理。谢景琴的硕士论文《民国东莞县沙田农业研究》(35)谢景琴:《民国东莞县沙田农业研究》,华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讨论了沙田开发的潜力和阻碍,并对东莞沙田方面的农业调查和实验进行了分析,认为东莞明伦堂对沙田实行了新式的经营管理。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明伦堂当时对沙田的管理具备一定的先进性。
以上围绕沙田问题展开的明伦堂研究,既包含对地权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沙田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二者都与地方社会的网络运作密切相关。地方社会网络是“国家-地方-民众”视野下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可以产生很多精彩论述和思考。东莞明伦堂因拥有大片沙田成为实力强大的地方组织,而沙田作为人们“向海要地”扩张行为的产物,其形成、开发均受地方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影响,在利益分配方面涉及多重主体,生产关系上交织着复杂的社会网络。因而,在国家政策法规和地方执行之间,在明文法令和地方惯例之间,在阶层区分和对应所得之间,沙田的地权状态和经营管理方式产生了大量地方“发明”,其所有权和经营管理策略便会在争夺者的计谋和所有者的规划中产生种种特殊形态,反映了地方经验与国家管控碰撞后的表现。相关探讨有助于进一步阐发区域性、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呈现明伦堂在形成和管理过程中的更多细节。涉及东莞明伦堂的沙田研究,在上述问题的发现和处理方面剖析比较深刻,也产生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是广东沙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类论文采用的大多数案例时间段集中于万顷沙争夺时期和明伦堂成立的前期,明伦堂在民国中后期更多材料的阐发尚待加强。因而在地方社会网络的挖掘时段也偏于前期,民国时期的网络没有详细地勾勒。并且,研究者多强调士绅、宗族在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对“民”这一更大的网络主体探讨较少。所以,在地方网络这一层面,还有较大的开掘空间。
(三)地方社会事业方面的组织功能探讨
拥有广袤沙田的东莞明伦堂,不仅支持了东莞的教育事业,还在医疗卫生、公益慈善、路桥基建、农林水利等社会事业上进行了投入和倡导。这些话题在前述论著中出现了一些以概况为主的简要评介,尚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以下几篇论文专从地方社会事业角度予以讨论。
黄素娟的硕士论文《从捐资助考到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清中期至民国广东宾兴组织研究》(36)黄素娟:《从捐资助考到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清中期至民国广东宾兴组织研究》,华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将东莞明伦堂视为一个宾兴组织,描述了其作为地方教育的资助团体、转型为参与多种地方公共事务的机构之过程。宾兴组织这一概念,与一般所见对明伦堂的“地方财团”这个定性相比,更强调明伦堂专事资助教育的性质;该文也阐述了宾兴组织对地方事务管理的积极参与,主要从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绅权与官权的互动两方面展开讨论。
东莞本土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也对明伦堂与东莞社会的关联多有关注,并从教育和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进行了探究。王磊的《民国时期东莞明伦堂与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刍论》(37)王磊:《民国时期东莞明伦堂与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刍论》,《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年第30卷第9期。和《民国时期东莞明伦堂与地方职业教育发展探析》(38)王磊:《民国时期东莞明伦堂与地方职业教育发展探析》,《青春岁月》2017年第9期。,都是从教育方面讨论明伦堂对民国东莞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同时指出问题和不足。《浅析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以民国东莞明伦堂为例》(39)王磊:《浅析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以民国东莞明伦堂为例》,《长江丛刊》2017年第6期。一文将东莞明伦堂这一历史文化资源与当代高校德育主题相结合,阐发其育人价值。但是,这些研究在材料运用上还有待进一步全面、细化、深入,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尚未展开解析,比如:民国时期东莞的职业教育为何发展缓慢并走向衰落?东莞明伦堂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的功过如何评说?这些问题还需深入探究和阐释。
以上对东莞明伦堂在地方社会事业方面展开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研究方式以梳理和评议为主,开掘尚不深刻。教育当然是明伦堂最根本和最显著的事务,然而明伦堂在其他社会事业方面的作为,若与国内外的历史潮流对照结合,可能会产生更为多样的探讨路径。明伦堂的地方社会事业领域,是在“国家-地方-民众”视野中可以多加探讨的领域,相关史料挖掘不足是导致此前研究偏少的主要原因,随着研究者兴趣的拓展和明伦堂档案大型出版项目的出台,这一领域有望出现新的突破。
三、东莞明伦堂研究展望: 民众维度与宏观视角
上述有关东莞明伦堂的研究,研究者主体为中国内地学者以及香港和海外的历史学者,早期研究中海外和香港学者如西川喜久子(日)、伍若贤(美)、黄永豪(香港)等,在问题开掘和材料运用上较有深度。九十年代,东莞明伦堂主要作为个别案例出现于内地学者沙田研究的相关论文中。进入21世纪,东莞明伦堂研究的论著数量明显增多,尤其是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或重要章节,有1篇博士论文和3篇硕士论文,并出现第一部专章研究东莞明伦堂的专著(黄永豪2005);此外,学科视角也更加多样,除历史学之外还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法学、农学等;研究趋于细致和深入。将这些不同专业领域的思考和不同角度的解读联系起来,让我们看到东莞明伦堂研究的全貌以及更多的可能性。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清代,即万顷沙之争与明伦堂成立前期,而民国时期和解放前后、即明伦堂存在的中后期时段内成果较少。
第二,整体研究相对缺乏,目前仅有韦锦新的硕士论文是对东莞明伦堂存续期间的整体研究,黄永豪、王传武等几家专章专论有精到见解,但在更多研究中,明伦堂作为案例的剖析尚不够深入。
第三,东莞明伦堂的档案材料还未被大量研读使用,很多材料和信息仍被搁置,影响了研究者对东莞明伦堂整体情况的把握;此外,港台地区尤其是上文第二部分提到的“台拓”公司档案需要进一步地阅读和发现。而即将开展的东莞市档案局明伦堂档案出版项目(40)东莞市档案局馆:《东莞明伦堂档案学术研讨会7月5日在东莞召开》,《档案学研究》2018年第4期。,可以使明伦堂档案更好地发挥资料库和学术公器作用。
第四,研究方法上,田野调查尚不够全面和深入,笔者设想可对明伦堂组织管理者和参与者的后代、故里乡亲、地方文史专家和基层文化工作者进行访谈,获取更为丰富的口述材料,对文献材料进行补证。
第五,研究的理论探讨仍须拓展,如前述第二部分提到的与“华南学派”的宗族路径进行对话的空间;再如,“国家-地方-民众”的研究视野中,“国家-地方”维度在现有明伦堂研究中较为常用,但是在“民众”这一维度上的探讨还较为薄弱,国家、士绅、宗族都是显性的存在,而民众群体是隐性的,在研究中处于失语的状态。因此,无论在地方社会的结构和控制层面,还是沙田问题以及地方社会网络层面,或是地方社会事业开展层面,都需要更多地对“民众”在明伦堂的运作和影响中发挥的作用加以深入探讨。
东莞明伦堂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大变革和转型历史时期的类政府实力组织,在东莞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轨迹。这个轨迹的明晰化,可以回应地方社会历史上的一些普遍问题,并为当代东莞地方社会的结构与整合提供阐释。这种阐释的演绎化,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扩大讨论空间,思考更广范围内地方社会的未来走向,并为中国其他地域社会的整合研究提供一个案例和阐释逻辑。故而,东莞明伦堂的研究价值并非局限于这一组织或东莞地方社会内部,还有广阔空间需要深入探索。系统性、多学科方法的拓展以及团队规划的方式可望为该领域研究再添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