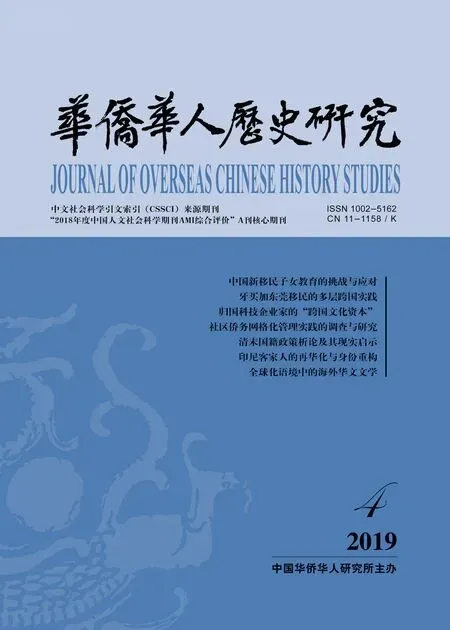从离散到跨国散居
——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
2019-12-15温明明
温明明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全球化’这个词汇,是晚近随着族群、影像、科技、财经、意识形态等实体、象征资本的流动,以及跨国的移动所形成的文化经济现象。”[1]21世纪初,“全球化”理论被引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术语“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应运而生。“全球化”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组合,绝不是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杂交之后重生的文学景观。在这里,“全球化”既是语境,也是方法。以往学界多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现代离散文学。随着全球化尤其是“地球村”的到来,华人跨国流动不再是单向式的“出走”,而是兼具“出走”与“回归”的双向复数式流动,离散已经难以描述当前海外华人复杂的后现代生存形态。本文引入族裔散居理论,解读华人离散遭遇全球化之后产生的各种拟态,从跨国散居的角度阐释海外华文文学越界生产的内涵及其身份归属,在此基础上试图厘清这样一个命题:何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
一、当华人离散遭遇全球化:归返、后离散与旅行跨国性
数字时代的世界因时空被压缩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人口的跨国流动变得日渐普遍、频繁和复杂,华人也被裹挟在这股跨国流动潮中。在“地球村”时代,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传统的华人离散遭遇流动更密集、更广阔的全球化之后,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异?很显然,离散不再是“离而不回”或“回而不走”,更多的是双向复数式的“来来去去”;而离散华人也“不再局限于简化的‘有去无回’或‘叶落归根’的选项”[2],反而陷入“处处无家,处处家”的复杂辩证。全球化改变了华人离散的传统形态,产生出归返、后离散、旅行跨国性等各种拟态。
(一)归返“母体”:留学与居留
20世纪60年代受东南亚种族政治及中国台湾当局对华侨学生的教育政策的影响,东南亚地区逐步形成了留学中国台湾的传统,其中以马来西亚最为突出。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批马来西亚华人成为一支在马来西亚华社颇有影响力的留台社群。在文学领域,李有成、李永平、张贵兴、潘雨桐、商晚筠、张锦忠、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等当代马华文坛的重要作家均可归入这一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马华作家均为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后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在台湾完成学业后,除潘雨桐、商晚筠等少数人返回马来西亚外,大多选择留在台湾定居。新世纪以来,部分海外华人开始回中国大陆留学,如少君、吕红、施雨、庄伟杰、许文荣、潘碧华等。许文荣与潘碧华属马来西亚在地华人之后裔。
从留学到定居,早期离散南洋的华人“回归神州”的愿望终被隔代落实,他们的“回归”可以说是对其先辈离散南洋命运的逆写。在这里,“‘回归’不只是离开原居留地而迁移到另一个重新选择的居留地,还包含回到主流或母体的意思。”[3]
此外,中国香港作家陶然也可纳入“归返”作家行列。陶然的祖父母辈就已经移民印尼,到他这一辈已是第三代印尼华人。20世纪60年代初,16岁的陶然被父母送回中国大陆求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因印尼排华定居香港。学界多注意陶然的“南来”身份,而忽视其作为印尼华人第三代的“归返”体验。“归返”与“南来”的双重身份与香港经验的相互纠缠对陶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作为“香港作家”的他具有复杂的面向。
与传统离散所描述的“源”、“流”关系不同,以上以留学渠道归返中国的华人广义上实现了向“源”的回归,“原乡”不再是只能仰望遥想的“家园”。这种“归返”可视为对传统离散的反动与逆写,确证了“源”、“流”关系是可逆的、非单向的。
(二)后离散
“后离散”中的“后”受益于王德威的“后遗民”概念,“不仅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而不了,甚至为了未来而‘先行后设’的过去/历史。”[4]所谓“后离散”,指的是第一代离散华人落地生根后,其后代再度离散的现象。无论传统的离散还是全球化时代的新离散,都暗含“移动”、“流动”之意,“过去的论述并未视这些离散华人为流动现象,似乎他们移居南洋或美加之后便落地生根,不再变易居所”[5]。“后离散”现象的出现是对这一论调的纠偏,使“离散”重新回到“流动”的论述轨道上。
“后离散”在华人离散历史悠久的东南亚地区屡见不鲜。“据保守统计,二战后东南亚地区华人海外移民总数可能近300万人。其中新加坡华人海外移民约26万人,马来西亚华人海外移民达105万,菲律宾华人海外移民约为7.8万人,印度尼西亚华人海外移民约13.6万人,泰国华人海外移民可能有70万,印支三国华人海外移民约70万。”[6]如此广泛而庞大的后离散群体确证了全球化时代离散的多元异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大量的离散华人第二代或第三代或主动或被动地再次离开居住地,携带在地文化基因开启“后离散”的生命之旅,说明在全球化时代,华人离散不可能因在地化而结束,所谓的“安顿”很可能只是暂时的。
欧美的不少华裔作家也属于华人后离散族群。如华裔美国作家林玉玲,1944年出生于马六甲华人家庭,母亲是土生华人。20世纪60年代末赴美留学,后移居美国。亚裔美国文学研究者多注意林玉玲的华人身份,而忽视其后离散经验和马来西亚背景,但她的文学作品多以马来西亚为观照对象,且在马来西亚出版。正如她自己所言:“身为作家,我的读者跟我的情感源头一样,仍然植根于马来西亚。”[7]再如近年在英国文坛逐渐引起注意的欧大旭,父母都是马来西亚在地华人,他在马来西亚完成中学教育后,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现留在英国从事写作。他们为东南亚地区后离散群体的叙事提供了样本。
(三)旅行跨国性
全球化时代,华人离散不再像我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单纯和透明,“海外离散社会虽有一定的地理根基,但不会固定于某一时空之中”[8]。即使是那些已经在地化的离散后代,也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版图上跨域游走。“旅行跨国性”是林玉玲提出用以描述这种现象的一个概念,本用于阐释香港英语诗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跨域旅居的现象。实际上,“旅行跨国性”广泛存在于华人中,他们跨国旅居、频繁奔波游走于中国及他国之间,成为“太空人”。
王润华可视为这方面的典型。他194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1962年赴中国台湾留学,1967年又赴美深造,1973年起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期间入籍新加坡,2003年又受聘中国台湾地区的元智大学,近年则重回马来西亚,担任南方大学资深副校长。其人生轨迹从马来西亚开始,中间经历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终又回到马来西亚。2017年,王润华即以“越界跨国”命名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学术选集,以概括自己一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向欧美的一批新移民,其中的大多数已落地生根。但他们与19世纪劳工的境遇已截然不同,“地球村”时代,“乡”不再遥不可及,大量的新移民每年不断穿梭往返于移居国与祖籍国之间。新移民作家严歌苓、虹影、刘荒田等近年长期居住在中国,张翎、吕红、施雨、少君、陈河等则往返两地之间,“居无定所”或者“跨国散居”已成为新移民作家的常态,他们都是旅行跨国性的践行者。
(四)重新阐释“diaspora”:从离散到散居
上文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华人离散出现的多种新拟态。如果仍然按照古典的“Diaspora”定义或早期犹太人的“Diaspora”传统来研究这些新拟态显然已不大适宜。20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大写的“Diaspora”向小写的“diaspora”转型,预示着这一词汇的内涵正在被重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卡其格·托洛利安(Khachig Tölölyan)等西方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论述,重新激活了“diaspora”,使其成为更富内涵的理论。对于中文学界而言,我们又该如何重新阐释“diaspora”,尤其是“Chinese diaspora”?这里的“阐释”既是重新寻找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汇来表达“diaspora”的后现代内涵,以彰显全球化时代跨域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也是重新解读“Chinese diaspora”,使其更符合华人的“离散”情境。
目前中文学界对“diaspora”的重新阐释大致有以下情形。首先,仍旧沿用对“Diaspora”的理解——离散,但将其内涵进行扩充泛化,区分出“广义”和“狭义”两种“离散”。这种阐释由于没有区分度,未能彰显其后现代内涵,在使用时仍需加以声明。其次,“飞散”,在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中,负责该词条的童明将“Diaspora”和“diaspora”均翻译为“飞散”,同时也区分出“新”、“旧”两种“飞散”。[9]这与阐释成“离散”没有太大区别,不仅没有反映出差异,反而在具体使用时还会陷入与传统翻译的相互纠缠中。
此外,一批从事文化研究、族裔研究、斯图亚特·霍尔研究的中国学者,则将“diaspora”翻译为“散居”,如张冲就明确提出“‘散居’(diaspora)一词源于希腊语diaspeir,意思是‘离散’或‘散落’(speir:scat tering)”[10],而邹威华也将斯图亚特·霍尔的相关文化研究理论翻译为“族裔散居文化”、“族裔散居美学”[11]。“散居”具有分散、扩散居住(留)等含义,既保留了“离散”中向外播散的涵义,又摒弃了传统“离散”的悲情意味,更能反映出全球化时代“diaspora”的多样性。同时,与“移居”相比,“散居”因暗示无针对性的方向,又带有可逆性。正如张锦忠所言,“移居是从一国移出,定居另一国,从一‘中原’到另一‘中原’。散居者则不然。他们固然也从一国移出,取得移入国的居留权、身份证、护照,但他们因工作关系而频频往返四大洲,往往还年年返回移出的故国与家人相聚,探望上了年纪的长辈,甚至到父祖辈的故国去寻根。”[12]“散居”已经成为代替传统“离散”的更佳翻译。
当传统的“华人离散”遭遇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华人成为散居族群,我们也可将“Chinese diaspora/diasporic Chinese”翻译为“华人散居族群”。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华人散居带有明显的跨国主义色彩,因而,当下的华人散居族群更恰当的称谓应该是“华人跨国散居族群”。他们在文化原乡(祖籍国)、生命故乡(出生国)与寓居之乡(移居国)之间跨国流动,心灵的家园不再被历史化而成为现实可回之所,现实的家园也不再被固定化而成为随时可离开之地,原乡、故乡与他乡相互交织缠绕,“离而不散”、“回而又走”逐渐成为华人跨国散居族群的生存常态。
回到本文一开始所提出的命题:何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全球化使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跨国散居华人取代传统的离散华人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生产者。他们跨越地理、文化、历史、语言、族群等的流动,改变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美学面貌,使其更具跨界张力。
二、写在家国内外:华人跨国散居与文学跨界生产
海外华文文学常常被看作是海外华人“写在家国以外”的文学创作,是一种远离原乡中国的文学景观,如19世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离散文学及20世纪中叶欧美地区的留学生文学,这是从传统离散的角度看待海外华文文学得出的一种“成见”。全球化时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海外华人由离散向跨国散居转化,既外于又内于家国的跨界书写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海外华文文学的常态。新移民文学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异军突起,新移民作家往往在家国内外同时写作,即使有些作品创作于移居国,但总是借助中国的文学刊物和出版机构传播,其主要的受众也是祖籍国的中文读者。在祖籍国创作、发表、阅读、获文学奖已经成为新移民文学的常态,近年被誉为新移民文学“三驾马车”的严歌苓、张翎和虹影,其创作无一不是横跨家国内外。
“移民社群经验不是由本性或纯洁度所定义的,而是由对必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可所定义的;由通过差异、利用差异而非不顾差异而存活的身份观念,并由杂交性来定义的。”[13]简言之,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散居美学是“一种混杂、错置、含混、差异的美学”[14]。建构在跨国散居美学基础上的海外华文文学无疑是一种跨界诗学,其所逾越的疆界既包括有形的地理、族群,亦深刻地指向无形的历史、文化、语言等,因为“跨越疆界者越过的,往往不是国家的疆界,而是他整个过去的历史,及过去与现在的身份和认同。跨越者在地理空间的活动变成意识与时间的流动”。[15]
詹柏思(Ian Chambers)曾将散居族群的生存形态形容为:“一脚踩在这边,另一脚却永远踩在别处,横跨在疆界的两边。”[16]这恐怕也是对跨国散居华人处境最生动的描述了。这个跨界之所我们不妨称之为一个在原乡与居留地既外又内的第三空间,一个经由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之后的跨界空间,在这个空间所生产的海外华文文学可称之为第三空间文学。李有成在与张锦忠对谈各自的离散经验时,曾敏锐地提出:“有些作家的经验比较cosmopolitan(世界性),他们可以到处走动,在不同国家居住。他们的作品很难归类,因此就被称为第三文化文学。”[17]无论是第三空间文学还是第三文化文学,其核心都意在指出:全球化时代,华人跨国散居,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一种写在家国内外的华人散居文学,一种建构在跨国散居美学基础上的跨界诗学。
海外华人跨国散居,无论是后离散还是旅行跨国性,每一次的“出走”都必然携带所在国的文化记忆,同时也必然遭遇另一种异质文化的碰撞,跨文化对话就成为一种必然。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因写作主体由离散转向跨国散居,家国内外的写作逐渐成为常态。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海外华文文学写作主体的跨域流动,更为主要的是将混杂美学全面植入到海外华文文学中,使其成为一种跨界诗学。此外,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后认同的时代,传统离散文学封闭固化的认同意识逐渐被跨国散居文学开放流动的认同所取代。
三、后认同中的身份属性:开放、差异与混杂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认为,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认知模式: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这种立场视文化身份为集体经验的反映,并隐藏在集体记忆中,是“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18];第二种立场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19]。第二种立场重视文化身份的集体属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文化身份的历史性以及差异的个体经验对建构文化身份的价值。斯图亚特·霍尔对“文化身份”的深入剖析,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启示。
全球化时代,二元对立的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已经难以描述跨国散居华人的家园意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现实一再表明:“家园不一定是自己离开的那个地方,也可以是在跨民族关联中为自己定位、为政治反抗、文化身份的需要而依属的地方。”[20]身份定位决定了何处是家,家园也从传统离散中的单一固定的生命诞生之所变成复数移动的身份依附之处,跨国散居华人流动的家园意识已成常态。正如陈志明所描述的:“在这跨国网络的时代我们不只有几个故乡,也可以同时有两个甚至超过两个家乡。21世纪的迁移和跨国寓居已经不像19世纪的离乡背井,而是全球化跨疆界的生活,个人在有适当的条件之下选择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建立家园。”[21]
跨国散居华人有多个家或家园流动的现实预示着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进入了一个后认同(post-identity)的时代。“后认同”既是对传统离散中“源”、“流”二元关系认同的拆解,同时它也是重新解读全球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的一种全新方法,正如霍米·巴巴所言:“我们正在告别(超越)单一性的身份和单一性的视角。”[22]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从差异的、多元混合的视角重新观察跨国散居华人的跨界文学产生。
“后认同”时代,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身份是开放的、未完成的,也是充满差异的、异质性的。“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本质,即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内在的、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根本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精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我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23]因而,“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24]全球化时代,我们再也不能轻易地对某个散居华人的身份进行鉴定,从他开始跨国散居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份就在发生变化,不断地流动也在不断地丰富其身份构成,异质文化元素的掺入使跨国散居华人的身份面貌变得日渐模糊。新世纪以来的大量新移民文学中,“即使是对移民现实生活的展示,也非常注重表现不同族群在文化伦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由冲突到融会的复杂过程,其审美目标直指全球化语境中多元生存之理想”[25]。这些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反映了新移民文学在寻找身份的过程中,已从文化混血理念中确立了一种身份杂交的后认同意识。论者常用“边缘人”来描述新移民的身份处境:“对于纯属东方血统的新移民作家来说,尽管他们人在西方,但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始终只能是一种远离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化心态。”[26]换个角度来看,在单一的西方民族主义视角主宰的身份认同中,以文化混血、身份杂糅为特征的新移民文学只能远离中心。
跨国散居华人身处第三空间,“在这个‘第三空间’中,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元素势均力敌,不会一个压倒一个,而且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27]在全球化时代,华人在跨国散居的旅程中获得跨界经验,这种经验使散居华人成为跨文化、跨族群的主体,多种文化声音的对话,建构了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身份的混杂特性。如在台马华文学是一批马来西亚华人“归返”原乡的产物,大部分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成为散居的主体。对他们而言,“三乡”混杂是必然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马来西亚是他们的出生地,是第一故乡,尽管有些已经放弃马来西亚国籍,但仍然无法“摆脱”马华作家的身份;很多在台马华作家在中国台湾居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时间,中国台湾已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第二故乡,“华”指向的是他们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原乡。“地缘故乡”、“流寓异乡”和“文化原乡”的三乡杂糅使在台马华作家成为多重身份的携带者。
跨国散居华人的认同是混杂多重的,旅行跨国性使他们在多个家园之间不断往返,从而打破了传统离散认同的封闭空间,趋向开放和未完成。正如伊·安(Ien Ang)所说:“杂糅标志着离散群体从‘中国’解放出来,因为‘中国’一直是‘华人性’看不见的主宰。解放出来的‘华人性’变成了一个开放性能指,为混合身份的构建提供了无限的资源可能,这也是离散华人能够四海为家、安之若素的基础。”[28]当然,并非所有的跨国散居华人都能在开放的认同空间中建构其混杂身份,理论上的身份混杂是一回事,现实中不同区域政治的认可又是一回事。在后认同时代,也有部分跨国散居华人处于“非此非彼”、“没有家园”的分裂境遇中。全球化语境中,华人跨国散居使传统家园变成一个更具阐释性的空间,“四海为家”的背后是认同的遽变。后认同时代,人们不再执念“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果“吾心安处即为家”是对散居的泰然若处,那么“处处无家,处处家”则是对心灵的重新定位。
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而言,全球化既是内容也是方法。“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有着深刻学术内涵的命名,一方面预示着一种全新的观念和方法被引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海外华文文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本文从族裔散居的角度,认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之新变,首先体现在创作主体的转型,跨国散居华人已经取代传统的离散华人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核心;其次表现为海外华文文学日渐成为跨界诗学,在美学等各方面都展现出跨界色彩;第三反映在海外华文文学正进入后认同时代,表现出开放、差异、混杂等特征。
[注释]
[1]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台北:麦田出版,2013年,第125页。
[2][4]王德威:《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中山人文学报》2015年总第38期。
[3][5]李有成、张锦忠主编:《离散与家国想像:文学与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541页。
[6]康晓丽:《二战后东南亚华人的海外移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7]张锦忠:《跨越半岛,远离群岛——论林玉玲及其英文书写的漂泊与回返》,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第204页。
[8]周敏、刘宏:《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9]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10]张冲:《散居族裔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1]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9~254页。
[12]张锦忠:《跨越半岛,远离群岛——论林玉玲及其英文书写的漂泊与回返》,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第195页。
[1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陈永国译:《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14]李有成:《〈密西西比的马萨拉〉与离散美学》,李有成、张锦忠主编:《离散与家国想像:文学与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145页。
[15]张锦忠:《跨越半岛,远离群岛——论林玉玲及其英文书写的漂泊与回返》,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第193~194页。
[16]李有成:《离散》,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09页。
[17]李有成、张锦忠:《离散经验——李有成与张锦忠对谈》,李有成:《离散》,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59页。
[18][19]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陈永国译:《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9、211页。
[20][22]童明:《飞散》,《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
[21]陈志明:《迁移、本土化与交流:从全球化的视角看海外华人》,廖建裕、梁秉赋主编:《华人移民与全球化:迁移、本土化与交流》,新加坡:华裔馆,2011年,第20页。
[23][24]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陈永国译:《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208页。
[25]洪治纲:《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26]吴奕锜:《寻找身份——论“新移民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27][28]黛博拉·迈德森:《双重否定的修辞格——加拿大华裔离散文学》,徐颖果主编,丁慧译:《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理论研究与文本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