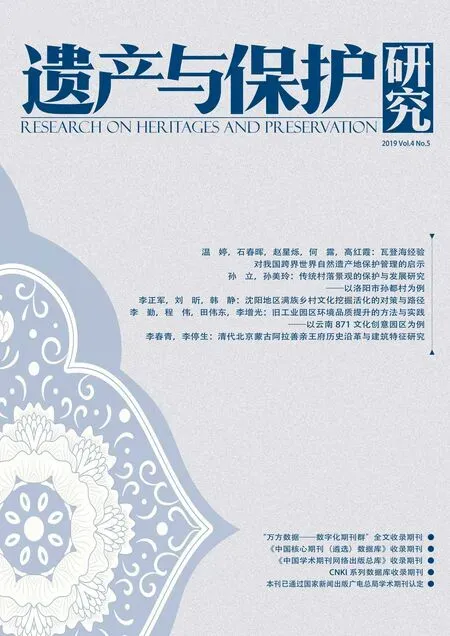藏区寺院藏书的成因及其特征
2019-12-14王黎
王 黎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藏区寺院藏书在佛经翻译的推动下,在佛教活动等因素的刺激下,在吸收印度、汉地佛经典籍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寺院藏书特色,即以藏文大藏经为核心的藏书体系。其藏书形成的原因、藏书的特征构成了藏区寺院独具特色的藏书体系,使藏区的寺院藏书在我国图书事业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本文将围绕藏区寺院藏书的成及其特征展开探讨。
1 藏区寺院藏书形成原因
1.1 历代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
佛教传入吐蕃后逐渐被藏区的统治阶级接受,并加以推行,佛经的翻译成为统治者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为弘扬佛法、巩固政权,藏区大量翻译佛典以教化民众。松赞干布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佛教,藏文被创制,这为藏文佛经的翻译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创制还造就了藏文佛经翻译的初盛,促成了寺院藏书的初萌与形成。赤松德赞时期,藏区的佛经翻译已成为吐蕃时期的高峰期。为了管理和收藏翻译的佛教典籍,藏区统治阶级开展了佛经典籍的分类、编目管理工作,编制了丹葛目录、旁塘目录、钦浦目录,使佛经的收藏有章可循。分裂割据朗达玛时期,佛教受到空前的打击,在封闭佛寺的同时焚毁了大量的佛经文献,使寺院藏书遭受了空前浩劫。
元朝统一中国后,历代中央政府为巩固对藏区的统治,利用佛教对藏区的影响,在政治上对寺院进行大力扶持,经济上给予优厚政策,译经成了政府行为,藏文佛典的翻译与传播得以确保。特别是明清时期,刻印、收藏大藏经成为藏区寺院藏书的标志和常态。一时间藏文大藏经的翻译和刊刻得到大规模发展。明朝中央政府将刻印的永乐版《大藏经》颁赐各寺珍藏,各寺院也为刻印大藏经纷纷建立印经院。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在藏区出现,其版本多达10余种。在大规模刻印大藏经的过程中,寺院藏书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元明清中央政府对藏区佛教的扶持,以及对藏区佛经翻译和佛经刊刻的重视,一定意义上对藏区寺院的藏书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
1.2 寺院佛教活动的影响
寺院翻译佛经的目的除了弘扬佛法、教化民众外,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培育诵经、辩经的僧侣人才。在翻译佛经过程中,为了校正所译佛典的杂乱无章和错误,寺院高僧大德们对已有佛经版本进行校勘、注解。同时,寺院组织辩经活动对各种资料进行整理、将其刊印成书,也使藏书内容更加丰富。
1.3 寺院教学、学术需要
藏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其寺院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教育文化机构。寺院不仅开展佛教活动,还要履行教育职能,开展文化学习、文化传播和文化研究活动。为寺院教学需要,寺院僧徒的学习教材均由本寺高僧刻印编写。因教学要求,藏区寺院还建有阅览室。甘肃拉卜楞寺历代嘉木样活佛特别重视教育,将所属教育机构逐渐发展为6大学院,为僧徒提供进行修辞、韵律、天文和历算学习的场地,类似藏区寺院的综合性大学。高僧大德们在教学的同时还开展学术研究,其研究成果有自传、专著、工具书。这些研究成果的收藏确保了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寺院的教学、研究活动也促进了藏书的发展。
1.4 雕版印刷术的运用壮大了寺院藏书
印刷术推动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书籍的生产方式,加速了文化的传播。藏区对佛教经典的需求客观上推动了印刷术在西藏地区的传播、应用和发展,进而扩大和加快了藏区佛教文化的传播。
11—12世纪藏传佛教先后产生噶当、萨迦、噶举、宁玛等诸教派,这些教派通过翻译传播佛法;通过著书立说,宣传各自的宗教思想。翻译促使佛教典籍需求的激增,手写佛典和著述已经不能满足大量的佛教活动需要。13世纪,藏区多次派人到汉地,将汉地的雕版印刷技术引进藏区。新型印刷技术改变了藏文书籍的生产方式,促使藏文佛经典籍的大量印刷。15世纪中叶,格鲁派建立,藏区各地寺院纷纷建立了印经院。印经院大量生产藏文佛经经籍,如纳塘寺刻印甘珠尔103函、丹珠尔225函、保存木刻经板5万余块。德格印经院刻印甘珠尔103函、丹珠尔208函,保存木刻经版20万余块。拉卜楞寺藏经数量高达12.88万余卷,保存藏文经板有6.2万余块。印经院刻印和生产书籍,促使藏区寺院藏书的发展和壮大。
2 藏区寺院藏书的特征
2.1 藏书具有教育文化功能
藏区寺院具有开展佛事活动、讲经说法(教学)、藏书3大功能。古代藏区无学校,在藏区传播知识和学习文化都要通过寺院来实现,因此古代藏区的主要教育形式为寺院教育。各寺院的活佛、高僧大德不仅通过在寺院的讲经说法、传授佛教及其文化知识,还在寺院建立自己的教派,宣传教派思想,培养教徒。藏区寺院的教学方法主要有:①僧徒背诵经文,并对所诵经文进行讲解。②辩经,通过答辩、辩论,僧徒间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在辩经过程中培养口才,启发思维。
随着寺院的扩张,藏传佛教教派不断发展壮大,各地建立了规模不等的藏传佛教寺院。格鲁派成立后,一些规模较大的寺院相继建立,如甘丹寺、札什伦布寺、拉卜楞寺、塔尔寺等。格鲁派还在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形成了藏区寺院特有的教育体系。寺院的教育功能使寺院藏书体系走向成熟,寺院也成为古代藏区藏书文化的发源地。
2.2 藏书内容、载体和版本形式多样化
藏区寺院藏书内容和版本形式多样化,内容上可分为佛教图书、非佛教图书。在藏区寺院藏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图书,但寺院所藏的佛教图书又可分为藏文大藏经、佛经单译本(大藏经之外的)、活佛和高僧大德撰著(对已译佛经的注疏、校注和疑伪经等)、宣教通俗文书、一般寺院文书、其他文字佛典。非佛教图书在佛教界通常称为外典,在寺院藏书中占比不大,但在我国藏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非佛教图书有医药、天文历算、僧侣自著作(包含文学、历史、文字、语言、韵律)等。
从藏书载体和版本来看,有手抄本佛经(主要产生在藏传佛教前弘期)、木刻本佛经(主要产生于藏传佛教后弘期),还有石刻佛经,其中石刻佛经是藏区寺院藏书的一大亮点。如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境内的和日石经墙、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境内的巴松石经墙等,都刊刻了石刻藏文大藏经[1]。
2.3 藏书编目受藏传佛教教派的影响
藏传佛教寺院对佛教文献进行分类、编目、著录时,是遵循了“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类原则。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在《藏文文献目录学》中提到“按教派编制全集目录的习俗以前就存在,是依照西藏佛教各教派产生的顺序编排”,也就是说,藏文佛教文献的编排是先按教派编目,后按教派产生时间进行分类,此编目和分类方法清晰地反映了各教派学术流变的历史过程[2]。
2.4 藏书来源独具特色
藏区寺院藏书来源主要由自刻、购置、政府颁赠、个人私藏等构成。
(1)自刻、自印是各大寺院藏书最主要的来源和补充途径。雕版印刷术传入,各寺印经院相继建立,寺院佛经和各类书籍的印刷逐步繁荣壮大。各大寺院主要刻印佛典、注疏、校注类书籍、高僧的著述和讲义,以及其他科学文献资料。大量书籍的自刻、自印使寺院藏书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2)购置书籍。如拉卜楞寺历代嘉木样活佛对寺院藏书的努力和贡献。拉卜楞寺建寺初期,一世嘉木样活佛就从西藏购置了经书,后又派人到准噶尔和康巴等地搜集了宁玛派的“伏藏”佛典,这些书籍奠定了拉卜楞寺藏书基础。二世嘉木样活佛为了满足寺院教学和寺院的拓展,历尽万苦,走遍藏区各地寻找佛经典籍,倾其家产购置佛经等书籍,共得珍品典籍3 000多种,提升了藏书的质量,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拉卜楞寺藏书[3]。
(3)政府颁赐。明朝永乐年间,明政府将南京版的藏文《大藏经》颁赐给各寺珍藏。色拉寺有永乐皇帝颁赐的甘珠尔1部,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用藏文印刷的佛经[4]。
(4)寺院个人收藏。青海塔尔寺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塔尔寺的藏书分集体收藏和个人收藏。其中,寺中活佛、喇嘛私人收藏的经典数量超过了寺院集体藏书的总量,且种类较多。阿嘉活佛院藏有佛经500多函,却西活佛院藏有佛经400多函,西纳活佛院藏经200函,嘉雅活佛院藏有佛经300余函,米纳活佛院收藏101函本《甘珠尔》1套。这些私人藏书是研究藏族历史、藏传佛教史的珍贵资料,是藏族优秀的文化遗产[4]。
2.5 藏书目的与服务对象具有独特性
藏区寺院藏书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本寺的活佛、高僧大德、佛教徒。其藏书的目的主要为供佛事活动和僧徒学习。藏区寺院藏书主要建有藏经殿或藏经楼,一般不对外开放,不提供对外借阅、使用。部分寺院还建有特藏经库,用于珍贵、罕见佛典的收藏,供政府层面的高僧等统治者进行阅读和鉴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藏区寺院藏书的形成与发展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寺院佛教活动的影响、寺院教学及学术研究活动的需要密切相关。藏书所具有的独特的教育文化功能和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使其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藏区寺院藏书成因和特征进行梳理,对于我们了解藏区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文化和宗教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