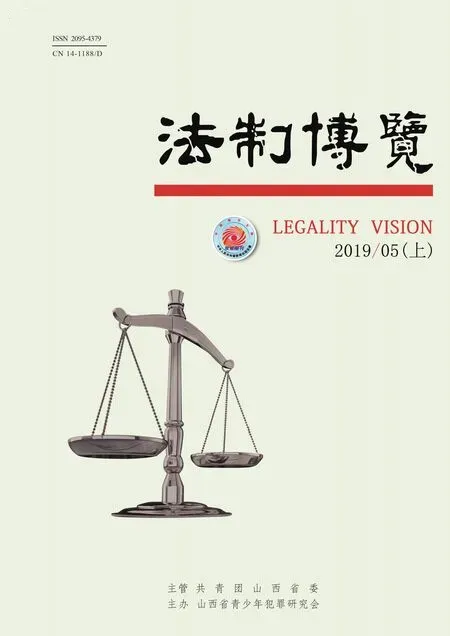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刍议
2019-12-14王培培
王培培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前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结合本民族经济、社会、文化,行使民族立法权,变通执行权,财政经济自主权等权利。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规定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由于各民族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人权保障,民族平等理论,这一制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被给予肯定,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刑事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少数民族刑事变通权的权利界域,适用效力等问题仍待解决。
二、少数民族刑事立法变通权之制度背景
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刑事立法变通权的本质需要整理其立法背景及其过程,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出自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条,这两条法律规定之间的内容大体相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中的刑事立法变通权主体为“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条的刑事立法变通权的主体为“省或者自治区的国家权利机关”,该两条规则的其他部分表述一致。由于在其他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仅规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变通权,因此这样的修改体现出我国刑事立法变通权在立法层面的规范性。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规定了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拥有刑事立法变通权,另外又对这项权利的运行设置了诸多的限制[1]。首先,少数民族刑事立法变通权的权利行使主体仅仅限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州和自治县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刑事立法变通权。其次,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使刑事立法变通权需要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综上可见,少数民族刑事立法变通权制度中的实体方面的权利主体与程序方面的权利主体存在一定的不一致,实体方面的权利主体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而程序方面的权利主体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是我国立法者在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少数民族刑事立法变通权理念之后得出的结论。之后立法者在各种观念的权衡度量之中选择了多方平衡的做法,侧重点在于立法统一方面,即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有立法变通权,但是该项刑事立法变通权的权利主体仅仅是省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且需要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从而对省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立法监督,使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立法变通权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之中。
三、少数民族刑事立法变通权的界域如何界定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应有一定的权利边界,需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基础,然后考虑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各自的民族实际情况,结合本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习惯法,做出具有本民族特色,与上位法不冲突,可操作的变通后刑法。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的权利界域可以根据犯罪侵害的法益位阶来进行划分。首先,犯罪侵害国家利益则不得变通。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往往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有关,这些行为往往不涉及刑事立法变通权中的少数民族地方性事务。故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分裂国家罪、间谍罪等等不得划入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的范围。其次,犯罪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除该犯罪行为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性事务之外的,其他犯罪一般不得变通[2]。该类型犯罪主要涉及到社会公共秩序的保障,容易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以及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比如投放危险物质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等等,这一系列的犯罪并不契合少数民族习惯法,并且也严重违反了我国现行刑法,故这些犯罪并不能归入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的范围。但是考虑到有一系列的犯罪,与少数民族自身的习惯法并不冲突。比如,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往往有打猎的生活习惯而随身携带枪支和刀具,由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本民族医药业代代相传的本民族医药无法由国家统一行政许可而无证行医,由于本民族与世隔绝地处偏远深山老林而砍伐树木破坏环境等等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相契合,可以纳入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的范围。最后,犯罪侵害个人法益的可以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的范围中,这类犯罪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案件中案件数量最多的一类犯罪,对于这一类犯罪的考察,需要考察涉罪嫌疑人在犯罪时的主观心态,以及主观心态之上的民族习惯,这一危害行为是否是特定社会环境因素下作用的结果,比如本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价值观的影响,这些涉及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当地的社会成员个人权利以及当地本民族地方性事务。
四、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之下是否排除民族习惯法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的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意指我国针对犯罪与刑罚必须由国家制定的基本法规定,也就是排除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习惯法成为我国刑法的渊源和司法实践中裁判的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要从封建社会末期开始说起,封建社会末期的刑事法律往往具有残酷性、任意性、干涉性,这样的特征造成封建国家权利过度肆意干涉公民生活,侵犯公民基本人权,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土壤中诞生出了刑事古典法学派,提出先进的思想与当时的封建社会司法专横和恣意定罪相抗衡,禁止类推,禁止不考虑溯及力的事后法,在这样的基础上罪刑法定原则的雏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之后出现了刑事实证学派,提出的防卫论等一系列先进刑事理念构成了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现代罪刑法定原则包括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其实质侧面包括了禁止不明确的刑罚和禁止残虐的刑罚,这是罪刑法定相对主义开始的标志[3]。在罪刑法定绝对主义和罪刑法定相对主义之间,其内涵价值并无改变,是为了限制公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上述的一系列观念均是为了保障人权免受恣意的刑事权侵害而为的奠基石,因此上述理念的内涵价值不会因为情势变化而变化,但是理念本身会因为情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会发生变化,出现了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等维护被告人的理念,这些理念的出现使得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内涵价值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增强了。在此同时,重视刑罚处罚依据的法律主义也变得灵活起来,把国家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危害行为可以在判例和习惯中找到对应的解释和处理,将判例和习惯默认为了国家刑事法律的法源,是刑事裁判的依据,也是判断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依据[4]。综上所述,国家刑事法律的渊源不仅仅是成文制定法,还应包括习惯法,因为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契合于保护人权的价值追求,同时和其实质侧面也吻合。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刑事立法变通权的做法时,同时满足和兼顾各个民族习惯权利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用做法,联合国曾在20世纪末通过了《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权利纳入到了应被国家立法保护的范围,在对少数民族地方制定相应的法律时,充分考虑其习惯和习惯法。这样意味着,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应将少数民族当地的民族习惯法作为其法源,尊重保护各民族习惯法,是现代社会人权保护基本理念的重要一环。
五、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后的适用效力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后的适用效力问题,是少数民族刑事立法变通权完善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笔者持采取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以及考虑少数民族特殊性原则相结合的标准。在适用问题的空间效力上,回顾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制度,其制度初衷是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自治,一方面符合了我国国情,另一方面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是我国《宪法》等法律在人权保障和民族政策方面的具体化,因此,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之后应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在适用问题的对人效力部分,刑事立法变通之后的主要适用对象应该是本民族成员,且要严格限定是长期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本民族成员,若是本民族成员在本民族聚居区外的涉罪行为,不应当适用变通之后的刑法,因为刑事立法变通是考虑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社会环境因素之后的适当变通,在失去了这些社会环境因素之后,涉罪嫌疑人的危害行为便失去了适用变通后刑法的制度土壤和前提。那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中长期生活的非本民族成员,因为具有相同的变通刑法的社会环境,是否也可以视为本民族的成员而适用变通后刑法呢?笔者持肯定态度,因为在长期的生活作业和交流沟通,非本民族成员和本民族成员对于当地的文化习惯风俗,社会规则价值等方面都是高度契合的,和长期居住在当地的本民族成员是雷同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涉罪嫌疑人是非本民族成员,其行为每时每刻都受到本民族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其深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契合当地社会规则以及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操作,认定非本民族的成员长期居住在本民族聚居区的标准如何衡量,比如对于本民族成员可以将户籍作为判断标准,对于非本民族的成员可以考虑其家庭成员几代人在本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活的时间长短等多因素考虑。但是对于在本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之外,没有了适用变通后刑法的社会因素时,也不应适用变通后的刑法。无论采取怎样的适用标准,都应该设置明晰的限制,来杜绝利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权来减轻甚至规避相应的刑事责任,逃避法律的制裁。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变通与现行的我国刑法之间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适用的关系问题,应该在现行刑法的空间效力的框架之下,形成一个具有本民族特征的适用界域,现行刑法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仍然具有效力,刑事立法变通后也不能与现行刑法的适用规范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