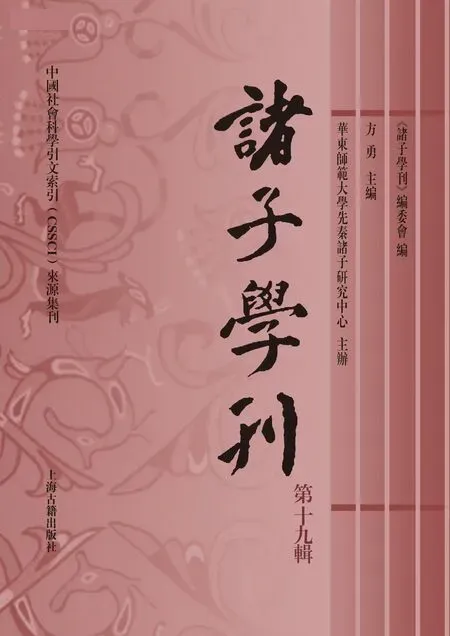《子藏》編纂與諸子學的當代發展
——201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講演
2019-12-14方勇
方 勇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很高興能有機會來作這次講演,今天要和大家一塊探討一下《子藏》與諸子學發展的問題。之所以選這個題目,某種程度上是因爲它在故地重遊時有種紀念意義。所謂“故地重遊”,是指我之前在北大中文系跟隨褚斌傑先生做過兩年博士後,這裏的一草一木我還是比較熟悉的,而這期間我的課題恰好是“莊子學史”,之後則以此爲基礎拓展至整個諸子學研究,構建出了我現在的學術格局。所以這裏很像一個起點,現在回到這裏和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研究狀況,頗有做“述職報告”的意思,也算是紀念那兩年的美好時光,來感謝褚先生的栽培之恩和諸位中文系前輩、同事的支持、幫助。
我們現在要説的諸子學,它是一個既傳統又新興的學科。説它傳統是因爲它的源頭可上溯至先秦諸子的時代,是我國傳統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説它新興,則是因爲它在近現代中國學術、文化轉型的過程中得到了全新的發展,被賦予了不同於古代的理論價值和研究範式。這種狀態下的諸子學有着歷史的厚重,又有着現實的活力,研究者對它應當充滿信心,但是如果要從更嚴格的眼光去審視,這兩方面又都存在着問題。它有着悠久的傳統,但它的源頭和高潮都在先秦,對於它之後的發展,國人的認知很模糊,在他們的意識中,子學的歷史似乎是一個虎頭蛇尾的歷史,甚至少數學者也基於此來質疑子學是否參與了中國文化主流的構建。另一方面,它借現代學術的東風,呈現出新的生命力,但很多研究方法都是一種探索,尚存争議,比如以西學知識隨意比附子學的研究方法,我們很難靠它們再開闢諸子學的新途。故而現代研究者對諸子學有自信心,也有緊迫感,自信來自沉寂了千年的子學在現代迎來了快速的復蘇,緊迫來自我們還要追求“諸子學的全面復興”,要消除復興道路上的各種問題。
“諸子學的全面復興”是我在2012年的學術研討會中提出的口號,這一提法之後得到許多學者的回應,因爲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它呼應着諸子學界先賢和今人的諸多實質性努力。早在民國時期,諸子學研究的先行者羅根澤先生便意識到當時正處勃興中的諸子學存在的問題,他曾提出“從西洋哲學的鐵蹄下救出中國哲學”,針對的就是時人拿諸子與西學妄爲比附的問題,同時他還大致設想了諸子學研究的五條新路徑,理念在當時也是頗爲超前。幾十年之後,在當時還是設想的課題現在已經被充分探究,諸子學的學術成果已經相當豐富,而且在理論研討外,以諸子學爲中心的各種學術活動正在被實踐,其中包括創建實體的研究機構、創辦長期的學術刊物、出版系列的學術叢書、召開大型的學術會議等等。這些努力對諸子學理論探討都有直接的推動作用,我們傾力爲之,是很有意義的。不過,還有兩種活動藴含的意義更爲長遠,這便是我們現在正進行的《子藏》工程和“新子學”探索,它們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推動諸子學研究的深入,更在於能應對前文提到的重大問題,助力於“諸子學的全面復興”。
《子藏》是一項專門針對子學著作的大型古籍整理工程,它收集了從先秦到南北朝的各類子書,以及新中國之前人們對它們的校覈、注釋、研究的專著。其收録文獻的形式也是豐富而全面,目前所知有關各子的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抄本、校注本、批校本以及專題論著等都在搜求範圍之内,並擇其善者而收録之。《子藏》工程的價值不僅在於整理文獻,它更大的意義在於彰顯子學的文化,這正如《佛藏》《道藏》之於佛教、道教的作用。正是有這種文化訴求,我們在《子藏》之後又進行理論升華,提出了“新子學”理念,和《子藏》一樣,“新子學”也不是單一的純學術工作,它着眼於對傳統中國文化的重審和當代中國文化的重構。《子藏》和“新子學”都有着高遠的立意,故而它們對諸子學的發展有着無可比擬的價值,下面,我以《子藏》工程爲主,對這方面的價值進行詳細的分析。
一、 《子藏》與子學傳統
首先分析一下《子藏》對於紹續子學傳統的意義,這正對應着開頭提到的第一個方面的問題。在我們一般人對於古代學術的認知中,每一時代都有其代表性的學術形態,比如先秦的子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清代的朴學。我們提到子學,首先會想到先秦,但先秦之後的時代,我們印象中便只有經學、玄學等其他學術,子學似乎再也没有回到學術的主流中,子學在這段時間發展如何,我們很難從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清晰明確的認識,故而在一般人對於國學的認知中,子學的傳統似乎有個巨大的斷裂,而且是一個將近兩千年的斷裂。我們現在常説文明的開新需要回顧這個文明的軸心時代,但我們回顧我們自己的軸心時代——先秦子學時代的時候,卻發現它有些模糊和隔閡,這跟軸心時代年代久遠有關(其他文明亦有類似情況),但子學傳統的“斷裂”在其中也産生着重要的作用。衆所周知,西方文藝復興時代回顧的是古希臘這個軸心時代,兩個時代雖然也相隔千年之久,但古希臘的文化被之後的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很好地保存,這爲文藝復興的巨匠回顧古希臘的輝煌提供了寬廣的橋梁,由此可見連綿不斷的傳統對於文化的復興和文明的開新有着多麽重要的意義。我們現在做的《子藏》也有這種價值,蕭漢明先生認爲《子藏》這個工作“如果説得大一點,相當於歐洲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所做的事情”(1)梁樞《〈子藏〉: 爲諸子繼絶學——華東師範大學〈子藏〉工程巡禮》,《光明日報》2010年7月19第12版“國學”版。。具體來看,《子藏》的一個重大意義在於它能讓看似斷裂的子學傳統從歷史的長河中再次浮現。在我們的印象中,子學在先秦後便不再是學術的主流,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就此停滯,如果我們深入歷史文獻中去耙梳就會發現,後世還有大量繼承先秦諸子著述形態的子書,亦有大量校勘注解諸子著作的成果,更有不計其數的零散評述解析分佈在各類書籍中,它們總量巨大,但卻又與其他類型的文獻混同在一起,深潛於歷史長河的底層,不爲人所注意。《子藏》把這些内容搜尋整合起來,向世人展示了其龐大的體量,比如,它的首批成果《子藏·道家部·莊子卷》便收録了相關著作302部,共162册,這是很出乎一般人意料的,之前大家以爲嚴靈峰先生所輯的《莊子集成》172部已經很全、很多了,没想到《子藏》又發掘了比它將近多一倍的材料。當然,《莊子卷》只是一個開始,《子藏》其他幾批成果正在陸續發佈,預計整個《子藏》完成之後,將能收録近4 000種著述,共出版約1 300册,整個體量大致和《四庫全書》相當。這讓我們看到子學在先秦後亦有着豐碩的成果,雖然它不是主流,但仍凝聚了後世學者巨大的心血與智慧。而且還應該看到,這些成果的分佈範圍又廣泛涵蓋了後世的各個朝代,其中,關於先秦諸子的注解闡發在歷代自然都屢有新作問世。此外,各代也都湧現了各具特色的成果,其典型者如: 漢魏六朝的子書,不僅承襲着先秦諸子著述的形態,也傳承着他們“立言”的精神;唐代相關的類書與抄本,雖然可能只是記録諸子著作中的某一文段,但對校勘意義極大;宋代相關的刻本,作爲某些子書的最早刻本,版本價值極高;明代關於諸子文本的文辭評賞,發掘了諸子文章的文學價值;清代關於諸子文本的考據,見解精闢,常有不刊之論;民國相關的專題研究,以現代學術路徑展開研究,對我們有極大的啓發,可見子學在先秦的高峰後,在歷代也有着新的發展,它作爲一種傳統,不僅體量龐大,也是延綿不絶、屢屢開新,它在歷史長河中雖然潛於底層,但卻是一股洶湧而綿延的波流。從這方面看,子學在先秦的高潮過後,它的傳統並未斷裂,仍以蓬勃之勢暗自發展,最終迎來了在近現代的復興。先秦和近現代兩處子學高峰之間並不是空白,只是人們被煙雲浩渺的歷史文獻遮蔽視野,未能看到下面所掩蓋的過渡主綫,那麽《子藏》就是追求把這條隱的綫給凸顯出來,接上這個在人們印象中已經“斷裂”的傳統。當然這意味着《子藏》要深入歷史文獻的煙雲中去耙梳摸索,藴含着極大的工作量與各種不可預測的因素,故而陳鼓應先生把《子藏》工程和“青藏鐵路”工程相類比(2)同上。,以説明其難度之大,但基於復興子學的使命感,無論路有多艱難,我們也要走下去。
當然,我們如此努力地凸顯這一傳統的連續性,不僅只是爲了發揮其象徵意義、給諸子學研究增加自信,更是爲了幫助現代的學者更好地去認識先秦諸子的思想世界,畢竟我們在回顧的是軸心時代,《子藏》所搜集的歷代子學研究材料是我們返本開新的重要憑藉。這些材料之所以重要,一則因爲它們的豐富性,二則因爲它們的時代語境與先秦諸子更接近,没有我們現代人那種强烈的隔閡感。這種接近又不僅體現在版本源流或語言訓詁上,更體現在某些問題意識深層的相通上。還是以《莊子》爲例,現代學者基本將《莊子》置於現代學術體系中來研究,將《莊子》文本和各自學科的專業知識結合,哲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學者都對它作出了不同的闡發,得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論斷,但它們能否反映莊子整體、本真的思想面貌,這也有待商榷,因爲學者們大多通過近人的注本來理解《莊子》原文,但莊子思想如同迷宫,僅憑這些簡單表面的注釋就能疏通它嗎?即使是現在比較通行、權威的《莊子集解》《莊子集釋》,也多是以解釋局部文句見長,對文章的整體脉絡和思想的整體結構論述較少,這跟清代朴學學風有關。可見,僅以這類材料爲憑藉,今人分學科的研究更易出現斷章取義的情況。這時,《子藏》中搜集的其他相關著作便能體現出它們的獨特價值,比如陸西星的《南華真經副墨》、釋德清的《莊子内篇注》、林雲銘的《莊子因》、宣穎的《南華經解》、劉鳳苞的《南華雪心編》等等,這些專著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除了解釋字義而外,更致力於莊子整體思想以及文章整體脉絡的研究,能幫助學者全面深入地把握《莊子》。《子藏》其他幾批成果所收録的類似著作還有很多,對於研究其他諸子的思想同樣有着巨大的幫助,可以説,這條子學傳統的重現爲今人把握先秦諸子的真脉提供了重要綫索。正是意識到這些著作如此巨大的學術價值,《子藏》項目組在編纂它們時一直秉持全且精的理念,“全”就是要把這類著作儘量全部搜尋出來呈現給學界,所謂“精”,就是要像《四部叢刊》一樣,盡可能選擇最好的版本,讓版本來體現其學術價值。此外,爲了方便學界更好地使用這套叢書,《子藏》項目組還會爲每種著述撰寫提要,考述著者生平事迹,揭示著作内容,探究版本流變情況。先按各個系列出版提要單行本,並在單行本出齊後匯總爲《子藏總目提要》。這些在文獻整理的基礎上精心撰寫而成的提要,可以很好地起到學術導航的功用。可以相信,通過我們這些努力,《子藏》將會成爲打通先秦諸子思想世界的新橋梁。
除了探究先秦諸子思想外,這條傳統本身也極具思想史價值。通過研究這些文獻,我們能發現,歷代人對諸子文本的闡釋都或多或少地滲透着各自時代的思想,而諸子思想經過這種闡釋也與各時代的思潮發生融合,共同參與了中國文化的構建。所以,我曾經説過,子學從來都是當下之學,它如同鮮活的生命體,不斷發展演變,這一過程貫穿了中國歷史,影響了中國文化。之前我們多强調諸子思想如何在先秦這個“源”上影響着中國文化,而通過《子藏》我們看到了子學傳統在先秦後歷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便能意識到它也在“流”上塑造着中國文化。
當然,這種塑造不僅反映在文本闡釋的層面上,也體現在歷代思想家對於諸子思想的借鑒與應用上,這些都處於更隱性的層面,僅靠《子藏》搜集文獻是無法將其完全展現的,所以配合《子藏》工程,我們研究中心還有諸子學術史、接受史的研究計劃,現在我的博士生和博士後都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每一人針對某一子在某一時代的傳播、研究、應用情況進行詳盡的梳理,側重諸子思想與各時代思潮的互動,力圖更全面地展示諸子思想對後世中國文化的定型所發揮的重要塑造作用。此外,我們提出的“新子學”理念,也是追求以這方面的歷史事實爲基礎,對此進行理論上的升華,從而完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審,進而實現對當代文化的重構。這些都是題外話,我們之後再進行詳細討論,還是回到《子藏》本身意義上來看,可以説,《子藏》爲我們重現的這一子學傳統是對諸子學自身的一種完善,也是對中華文明史的一種豐富。
二、 《子藏》與子學開新
以上分析的是《子藏》對於子學傳統的意義,屬於往回看,下面我們應該嘗試着往前看,分析《子藏》對於諸子學研究局面開新的作用。文獻的整理對於一門學科的發展有着重要的意義,這是被無數事實驗證的學術規律。傅璇琮先生在《子藏》研討會上曾列舉過很多學術史的例子説明這一點,認爲宋詩高峰的出現實際上與宋人對唐詩的編纂、刻印分不開,清代宋詩派、同光體詩的形成、發展同樣如此,都與當時宋集的大量編纂、刻印有關;再以《四庫全書》爲例,這部大型古籍叢書的編纂以及《總目提要》的撰寫也都大大促進了當時學術的發展和繁榮,影響遍及方方面面。傅先生的論述能給予我們很大啓發,我們有理由相信《子藏》作爲繼上述重大文化工程後的又一文獻寶庫,它對諸子學發展必然起到長久的推動作用。就像敦煌藏經洞的發現造就了敦煌學一樣,《子藏》的出現必然帶來諸子學新一輪的發展。
具體來説,這種新發展最直接地體現在諸子學新的學科增長點上。由《子藏》搜集整理的諸多文獻材料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研究對象,上文已經提到了它們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史價值,我們除了利用它們外,也要對此做一番詳細的研究,一則展現古典學術的特色與成就,二則爲當代諸子學研究範式的創新提供借鑒。還是以莊子學研究爲例,《子藏》的《莊子卷》將爲莊子研究打開新的世界,學者在此基礎上有很多課題可以發掘,比如可以專題的形式集中探尋莊子某一理論在後世的變遷,可以分學派、分宗派的形式集中探討各派的莊子學,可以地域或時代的形式集中描述某一空間或某一時間段的莊子學,還可以對某一部有創見、有影響的莊學著作進行個案研究等等,這種廣闊的開拓空間無疑會吸引更多學者投入更多精力加入到莊子的研究中來。當然,不惟莊子學,《子藏》其他幾批成果同樣會給其他諸子的研究注入全新的活力。之前,這些子學著作都淹没於浩瀚的歷史文獻中,極少被人所注意,《子藏》將它們全面系統地呈現給學界,學者在其中必然會發現更多新的課題,爲諸子學研究開啓新局面。
而從長遠來看,《子藏》對諸子學的開新還有更深層的影響,這主要反映在理論層面上。我們現在發展諸子學,不能僅追求“量”的增加,更要追求“質”的飛躍,這種“質”的飛躍便是一種諸子學研究理論或理念的革新,這就涉及了我們提出的“新子學”理念。“新子學”同樣是推動諸子學發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元素,它致力於擺脱哲學等現代分科體系的窠臼,建立以諸子傳統爲研究對象,具有相對獨立研究範式的現代學術體系。學科化是諸子學在現代發展的必然命運,章太炎《諸子學略論》、陳柱《諸子概論》等以“諸子”命名的著作很多都是承襲傳統子學的範疇和問題,未能以現代學科化的眼光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建構,諸子學没能在他們手中融入現代學術,之後胡適、馮友蘭等人關於中國哲學史的論著雖然將諸子學帶入了現代學術,但諸子學本身也付出了支離割裂的代價。“新子學”就是要吸取這兩方面的經驗,爲諸子學發展開一條新途,把諸子學打造成像敦煌學、海外中國學一樣的綜合性學術門類,在現代學術體系下謀求一個獨立的地位和完整形態。我們的《子藏》工作,恰是與這種努力相呼應,它把相關的文獻整合聚集起來,正反映着“新子學”對獨立形態的訴求,在這方面,它可以被視爲“新子學”理念的物質載體,經過這種整合而形成的龐大文獻集成,對於“新子學”的探索無疑會增加更多的理論自信。而《子藏》内部的結構劃分也契合了“新子學”對獨立研究範式的追求,《子藏》並没有依照現代學科體系把子學文獻分爲政治、哲學、軍事等門類展開搜集,在這方面我們主要還是承襲了傳統的十家劃分法,並參考《道藏》以“部”命名,形成“道家部”“法家部”“名家部”等門類,這能很自然地體現子學内在的紋理脉絡。並且我們將文獻搜集的標準定在思想性著作上,原來子部的醫卜數術等技藝性作品都不收録,這更能突顯諸子作爲思想家的本質。這些劃分原則和選擇標準並非率然爲之,這背後的考慮是跟“新子學”相呼應的。“新子學”理念是《子藏》項目啓動後提出的,但《子藏》早在籌劃時其整體的思路中便有了與“新子學”相通的意識。此外,“新子學”還追求發掘“子學精神”,以此作爲諸子學發展的核心理念,增强諸子學自身的標識性,而這種發掘的過程必然要經歷一個博采約取的階段,《子藏》所提供的龐大體量文獻正是爲這一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可見,《子藏》和“新子學”分别在文獻和理論兩方面齊頭並進,共同推動諸子學向獨立完整的形態發展。
“新子學”關注諸子學的自身建設,究其本源,其實也是爲了助力中國文化的建設。“中國性”是“新子學”理論探討的一個重要關懷,諸子時代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中有獨特地位,諸子所討論的問題影響着中華文明的進程,“新子學”就是要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中國文明的基本形態。這時的《子藏》便能配合着“新子學”發揮出其獨有的作用,因爲它是以子學爲綫索而對中國兩千年來的學術文獻進行的整理,它是中國古人在這方面智慧的結晶,也是一座藴藏着中國文化真精神的寶庫。上文所提到的“諸子問題”大都經由這類文獻得以保存並深化,《子藏》收録的子書白文自然忠實地呈現了這類問題在當時争鳴的原貌,而它所收録的相關注釋闡發則展現了後世對這些問題的深化。之所以有這種“深化”,這跟子學的學術形態有密切關係。子學本身就有一種不迷信權威的精神,故而子書的相關注析與經書注解不太相同,經注强調師法規矩,少有突破,而注子書則没有這麽多框框,作者秉持着自主思考與批判意識,能和諸子形成一種“對話”,將問題進一步向深層推進。而這種深化的過程,也是中華文化積澱發展的過程,《子藏》數以千計的相關著述整合起來更是展現了中國文明整體的演進。而“新子學”應該在此基礎上梳理這些問題,分析這些“對話”,進而將這類“對話”繼續下去,將子學打造成貫通中國傳統文化的橋梁與重構中國當代文化的基石。另外,我在《三論“新子學”》中又提出了“新子學”要“重構元典”“唤醒價值”(3)方勇《三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6年3月28日第16版“國學”版。,它們跟當代中國文化重構關係更爲切實緊密,“重構元典”的想法爲中國文化經典加入了更多諸子著作,《子藏》中相關的研究注解將會發揮無可比擬的參考價值,而“唤醒價值”則突出諸子思想對當代實踐的指導意義,但這仍要配合《子藏》的文獻才能使之發揮最大功效。綜上,爲了諸子學全面的復興,“新子學”要突出諸子學的獨立完整形態及標識性的“子學精神”,《子藏》便是承載這一理念的物質實體,同時,“新子學”又追求發現“中國性”以及重構典範、唤醒價值,《子藏》便是啓發這些創新的源泉。《子藏》與“新子學”配合,將爲子學開創新局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結 語
進行至此,我的演講也接近尾聲,在最後,我想借這次故地重遊的機會來梳理一下我治學經歷和學術源頭的問題,因爲我感覺我每一段經歷都在指引着我向現在的學術格局發展,不同的經歷賦予了我多樣的學術源頭,而這些源頭又都匯通於我莊子學及諸子學的研究。具體來看,我出生於浙江浦江,那裏是個人才輩出的地方,如明代有開國文臣之首宋濂,而宋濂著有《諸子辨》一書,它是古代重要的諸子學研究著作,而它兼顧文獻辨析與義理闡發,更是與我們現在諸子學努力的方向一致。至於我的祖先方鳳,他是宋末元初重要的遺民詩人,他堅持隱逸的志趣,作品中有很多《莊子》的印記,這種偏好也影響到了我的莊學研究。在碩士研究生階段,我追隨河北大學魏際昌先生,魏先生研究先秦兩漢文學,在他的指導下,我對這一時期的典籍有了較深入的把握,爲之後專治子學打下了基礎。而魏先生的導師則是胡適先生,胡先生爲諸子學的現代轉型作出了開創性貢獻,諸子學多元平等的精神與胡先生的思想傾向也很契合,我們現在調整、發展他的研究路徑,也是對胡先生、魏先生這脉學統的延續。在博士研究生階段,我跟隨吴熊和先生研習唐宋文學,這讓我對唐到清代的文獻情況有了較全面的瞭解,爲之後撰寫《莊子學史》和編纂《子藏》鋪平了道路,而且吴先生一直鼓勵我做大格局的學問,建議我在子學這塊領域上開疆拓土,對我的啓發和幫助特别大。之後來到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後,開始進行《莊子學史》這個課題,成爲我學術生涯的全新起點,褚斌傑先生在這個過程中從整體思路上給了我很多指導,讓我很快找准了研究思路。而北大中文系又恰是胡適先生曾工作的地方,至今在這還能感受到他留下的影響力,這也時刻鼓勵我要有大的志向,做些像胡適先生那樣能掀起時代思潮的事。而出站之後,我來到華東師大工作,除了繼續《莊子學史》的撰寫,我也在思考諸子學的發展與時代思潮的問題,因爲華東師大中文系一直有理論創新的傳統,20世紀系裏老前輩錢谷融先生提出“文學是人學”的理念也是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波瀾。正是在這種宏大目標的指引下,我把學術研究範疇由莊子學逐漸拓展至諸子學,既而有了《子藏》和“新子學”等一系列的探索,逐步構建了現在的學術格局。所以談到這,我感到我自身的學術向現在這個方向發展,有自己主觀的選擇,但更多的似乎是命運冥冥中的引導,有了這些緣,進而結出這些果。所以最後我還要借這次機會向過去幫助過我的各位導師和前輩以及同事表示感謝,爲了不辜負諸位的厚愛,我還會在諸子學這條路上繼續前行,爲實現“諸子學的全面復興”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