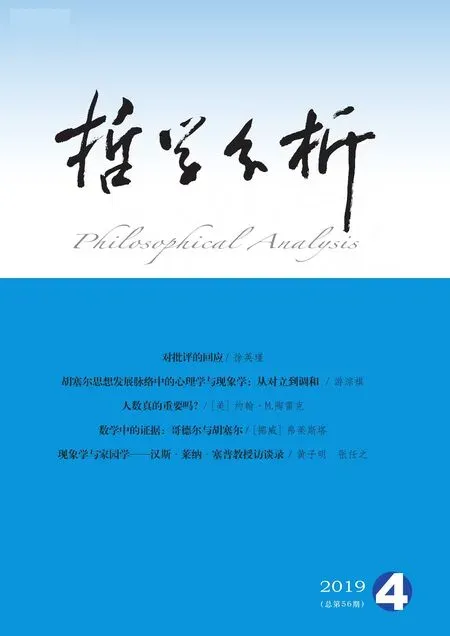从“兴于诗,立于礼”看诗性智慧
——试论《诗》礼合一的成德之学①
2019-12-14黄子洵
黄子洵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②《论语·泰伯》。在注释中,朱子把“诗”和“礼”分别与“学者之初”“学者之中”相对应,认为初学者首先应该学《诗》,在此基础上再来习礼。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③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8页。相比起刘宝楠的解释,朱子侧重于强调为学阶段的不同,并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区分出为学境界的高下。尽管如此,两位学者都把学诗、学礼视为求学的先后阶段,主张学《诗》之后,继而学礼,并引《礼记·内则》为证,“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④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3页。。
《诗》与礼被视作求学之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学习的不同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诗》与礼的关联:两者都从属于礼乐造士的传统,都是育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那么,这一解释是否道尽了孔子将《诗》与礼并称的用意?
虽谦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对六经精神的体究不可谓不深。夫子屡次将《诗》、礼并提,如“不能诗,于礼谬”①孔颖达:《礼记正义》,第1619页。,“诗之所至,礼亦至焉”②同上书,第1627页。,这只是对当时教育方式的客观陈述,还是另有深义?这一问题也可以表述为,《诗》与礼是否存在着内在关联?本文立足于孔子的诗学理论,以“兴于《诗》,立于礼”作为切入点来探究以上问题。“兴于《诗》,立于礼”③这句文本原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限于笔者有限的学养,同时也考虑到论文的篇幅要求,该论文只探讨了《诗》与“礼”的关系。至于《诗》、礼、乐三者的关系,则留待以后。虽寥寥数语,却内涵丰富,包含了多个层面的问题。孔子首先谈论了《诗》,而后由《诗》过渡到礼。针对“兴于《诗》”,我们不妨进行以下几方面的追问。其一,兴于《诗》何以可能?《诗》④在此,笔者有必要对“诗”的概念做一番梳理。自古至今,“诗”的概念一直处于历史演变之中。在比较诗学崛起之后,“诗”这一概念的基本蕴含大大丰富了。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诗”(poiētikē)是从动词“poiein”(制作)派生而来的,因此诗人是制作者,诗则是制成品。“诗学”一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指的是文艺理论,中世纪主要指的诗歌的创作技艺和技巧;21世纪以后,诗学用于泛指广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诗”除了用来指《诗经》之外,还可以指一般意义上的诗,即文人所创作的五七言诗体。本文所探讨的“诗”严格限定于《诗经》。文本中的“诗学”所指的是对《诗经》的研究。具备什么特质,使得《诗》可以兴?其二,这里的“兴”该如何理解?“兴”反映出《诗》的哪些独特之处?以上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诗》的本质及其哲学意涵。在探究“兴于《诗》”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诗》与礼相互贯通之处,并思考《诗》与礼的内在关系。
一、诗言志
子曰:“兴于《诗》。”⑤《论语·泰伯》。朱熹注曰:“兴,起也。诗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4—105页。。首先要追问的是,兴于《诗》何以可能?《诗》具备什么特质,使其能兴起好善恶恶之心?
《舜典》虽然提出“诗言志”⑦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这一观点,但尚未对“志”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荀子》指出《诗》与圣人之道存在着紧密关联。“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⑧《荀子·儒效》。杨倞将“《诗》言是,其志也”解释为“是儒之志”。
荀子论《诗》的落脚点在于圣人,杨倞论《诗》的落脚点在于儒。虽然圣人与儒的境界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圣人和儒来论说《诗》之志,意味着“志” 已具有了一定的价值规定性,而非某个有待规定的中立的意向或意愿(intention)。《诗》之所以具备“兴”的功效,与具有价值规定的志存在着紧密关联。
此后,学界关于“志”的解释逐渐抛去了圣人、儒者的光环。陈桐生指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者倾向于把“志”解释为“志意”①尽管我们可以在字义学上为“志意说”找到文本依据,《说文解字》以“志”训“诗”,以“意”来训“志”,但这不足以说明“诗言志”之“志”可以直接等同于“志意”。。晋人挚虞和唐代孔颖达牵合“志”与“情”两个概念,提出诗以情志为本。近人试图证明志中包含着情感因素,“诗言志”即“诗言情”。②陈桐生:《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以上关于“志”的种种解释?相比起西方文艺学区分出的作者导向、作品导向与读者导向理论,《诗》的情况更为复杂。倘若我们脱离《诗三百》的文本内容及历史语境,仅仅是在语义学的层面抽象地探讨“志”的内涵,“志”的含义难免失于空疏。
从《诗三百》文本的形成,再到整理汇编,再至最终的流传与讽诵,《诗》之志存在着多重性。正如清代学者龚橙指出的:“《诗》有作诗之谊,有读诗之谊,有大师采诗,瞽蒙讽诵之谊,有周公用为乐章之谊,有孔子定诗建始之谊,有赋诗,引诗节取章句之谊,有赋诗寄托之谊。”③龚橙:《诗本谊》,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诗类(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不少现当代学者同样看到“诗言志”这一命题内涵的丰富性。俞志慧先生曾指出:“这里的‘志’理解为作者之志亦可,理解为读者之意亦可,理解为修齐治平之抱负亦可。”④详见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8页。
这样一来,我们也许要问,在上述提及的“志”的多重维度中,哪一个维度最能代表《诗》之志?如果我们以维特根斯坦将概念比作家族的观念来作为追问的起点,也许我们能发现以上发问的不妥之处。“每一个家庭都是许多个家庭的集合(包括男系与女系),概念也是一样。在古老的时代,一个被任命为骑士的候选人,总免不了‘通报其家族的家族’的老套。当哲学家试图去界定一个用意广泛的概念之时,他似乎也该尽到相同的义务。”⑤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志”不应被简化为以上多重维度中的任何一种。因此,如果我们从这多重维度中单独拈出某一个维度,将其视作“志”这一概念的全部,我们将忽略掉其他维度对于“志”的重要意义。
尽管“志”不应被简化为某个单一的维度,我们仍能根据这众多维度的重要性的不同,区分出本末先后之序。
《诗三百》篇之所以能成形,位列六经之一,采诗、献诗、编诗的行动极为关键。洪湛侯先生曾强调汇编、整理过程对《诗三百》的最终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诗三百》篇的来源有民间采集、士大夫献诗、作诗配乐等形式和途径,这些采来或献来的诗歌,往往形式、字句、声韵都不一样。若不经过一番认真的整理,很难设想能够有今天的面貌。”①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17页。
作诗是个人层面的行为。而一经采编,再附乐歌奏,《诗三百》就不同于散落在民间、人们自发吟诵的诗作。“瞽矇和公卿列士献诗的目的是长君之善,正君之过,太师教诗的目的是培养行人,使之能专对、达政,二者多属家国之志而牵涉伦理、政治。”②陈桐生:《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第108页。从作诗到采诗、献诗再到编诗,《诗》完成了由个人领域到伦理政治的公共领域的转向。采诗、献诗、编诗之志作为重要纽带,使《诗》成为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生命体。众诗以自身为中心的独立性被削弱了,置身于一个整体之中,指向更崇高的目标——诗教。这样一来,《诗三百》的布局谋篇是我们探究《诗》之志的重要进路。③然而,以往学者多注意到《风》 《雅》 《颂》三者的差异,未能将其视为统一的生命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刘安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来区分《国风》与《小雅》,并试图用《离骚》这一他者来统摄《风》 《雅》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钟嵘将《国风》 《小雅》当作两种作诗风格的代表,并以此作为自汉至齐梁时代众诗艺术风格的源头。如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钟嵘:《诗品注》,陈延杰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又如,阮籍“其体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可以陶性情,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钟嵘:《诗品注》,第23页)诚然,《风》 《雅》的确存在区别,否则编诗者为何冠以异名,为何《风》先《雅》后?关键在于,明知《风》 《雅》不同,还要将二者编次于同一部著作中,其用意何在?《风》在先,《雅》在后,《颂》处于末尾。这一顺序究竟有何深义?在笔者看来,探究《风》 《雅》 《颂》的异中之同比放大三者的差别更有意义。欲观《诗》之志,我们不妨把风格各异的《风》 《雅》 《颂》视作一个整体。
《毛诗大序》将《风》 《小雅》 《大雅》 《颂》列为诗之四始,通过政教范围大小、政绩王化的程度来阐释四者的区分。四者形成了一个首尾浑然的意义系统,折射出圣贤的政治理想。平天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由身及家,由家及国,由国及天下,其立足点不离个人的成德。
一人之本,一国之事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前提。国中人人皆正,一国之风化才能兴起。一国之风化兴起,四方之风才能兴起,天下之化才能成就。在天下太平,王业成就之后,君王才能作乐,歌美先祖,因此,在《风》 《雅》之后,《诗》以三《颂》为终。《国风》以室家离合、宗族命运为出发点,诸诗的哀和乐多源于个人际遇和源于民生疾苦。《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视野亦由夫妇、室家等人伦切近处推及到君臣、朝野乃至夷夏。《国风》以《关雎》为首,由正夫妇至正室家,正室家及正邦国。二《雅》由室家推及朝政,意在正君臣,并进一步由正邦国至正天下。《颂》是四始之终,王化大成,泽及四海。功成作乐,通乎神明。
《诗三百》的布局谋篇启示我们,《诗》所言说之“志”是由正夫妇到正室家、由正室家到正邦国、由正邦国及正天下,最终德合天地,功告先祖的愿景。
那么,《诗》是如何言志的?《诗》之志是如何呈现与展开的?
单从字面义看,《诗三百》记录的无非是古人生活的各个面向,如个人的家庭生活、邦国的典礼场合以及宗庙祭祀活动等,展现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得以被塑造,如帝王、公卿诸侯、政府官吏、军事统帅、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妇女。①在《论〈诗三百〉形象类型及其审美意义》一文中,陈戍国先生对于《诗三百》中涉及的人物形象作了详尽的分类与说明。详见陈戍国:《诗经刍议》,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12—236页。初看上去,《诗三百》与志毫无关联。在上古史料缺乏的情况下,《诗经》更容易被视为研究上古风俗民情的材料。
这一困惑不仅存在于近现代学界,明代学者杨慎在《升庵诗话》也曾有过一番追问:“观《诗三百》,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周南》和《召南》所言多为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②杨慎:《升庵诗话新鉴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2页。
在杨慎看来,直接论及“道德”“性情”“修身”“齐家”的著作才有可能被视为言志、载道的经典。相比之下,《诗三百》是对个人遭遇的叙述以及对典礼场合的记录,更类似于记录古人生活的文献,充其量只能用作研究的史料。这样一来,我们更倾向于从《诗三百》中辨识各种各样的器物之学,而不是将其视为载道之言,从义理的角度去阐释《诗三百》之志。
实际上,《诗三百》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存世界。这是日常语言所无法提供给读者的重要维度。③王德峰老师曾对比过诗与日常语言的差别。“对同一件事的语言记录,因其方式不同,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是叙事,一种是由事入情。面对单纯的叙事,读者将无动于衷,他只是对某一个事件有了知识上的了解。面对‘诗的叙事’,读者却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他在了解到那个事件的同时,即被卷入了一个使事件之意义得以呈现出来的生存情感的世界。”详见王德峰:《艺术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5页。这一生存世界呈现的是在特定历史—文化维度中,人类生存的各个可能性维度以及人在现实中的可能性遭遇。通过观见前人纷繁复杂的生存面向与实践维度,读者有可能去探寻蕴藏在每一首诗中的幽深隐曲之志。
《诗》将一些角色和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角色与人物有着不同的遭遇,大多数时候,他们作为无辜者,承受了种种不幸。大多数人物面对着某些共同的困境,如长年在外服役、被谗言所害,同时也对这个世界怀有共同的盼望,如与亲人团聚、国泰民安。
每个人都试图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在某个独特的历史社会背景中,他们身陷何种困境,有什么难言之隐?在面对这些困境时,他们有怎样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最为关键的是,在这些复杂的伦理处境中,他们如何抉择?凡此诸种并不是通过一系列理论来直接阐明,而是通过古人的生命样态与生存实践得以呈 现。
《诗》展示了处于复杂的伦理关系与政治境况中的各类人的遭遇,启示我们思考人在世需要处理的多重关系,如自我与自我、家人、宗族、社会以及国家的关系等。在这众多的关系中,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是重中之重。伦理与政治是道落实于人文的必要途径。人能弘道并不是说人直接地与道相关,而是通过人文化成来体认道。
综上所述,《诗》的编次顺序由《风》及《雅》,再由《雅》及《颂》,这一布局谋篇意味着《诗》所言说之“志”是由正夫妇到正室家、由正室家到正邦国、由正邦国及正天下,最终德合天地,功告先祖的政治愿 景。
这一具有价值规定性的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诗》可以“兴”,但不意味着《诗》必然具备“兴”的功能。毕竟与《诗三百》处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或多或少也论及相似的愿景,晓谕读者善恶之理,但此类文献的兴发作用远不及《诗三百》。这样一来,为了进一步探究《诗》为何可以“兴”,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诗》言志的独特性何在?
二、释“情”: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
《毛诗大序》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①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除了“志”之外,《毛诗大序》还关注到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情。从心中有志到发言为诗,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形于言的前提是情动于 中。
诗之志不是以刻板生硬的形式得以呈现,而是与情相偕,活泼泼地从内心中流淌出来。《诗》贵在以情动人,而非直接说教,以理凌人,故感人而易入。
“情”贯穿于从未言到已言的整个过程。但对于“情”的确切含义,《毛诗大序》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黄宗羲曾区分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对我们厘清“情”的多重含义有所裨益。黄宗羲指出:“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如徒逐逐于怨女逐臣,逮其天机之自露,则一偏一曲,其为性情亦末矣,故言诗者不可以不知性。”①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序类》,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3—364页。
吴歈越唱、怨女逐臣源于“触景感物”,心中有所触动而形于言。但在黄宗羲看来,这种情只是“一时之性情”。“一时”说明了这种情感体验是暂时的,物现而生,物逝而散,变动不居,恒无定准。同时,“一时之性情”带有极强的个体性。这一情感体验往往囿于自身,缺乏普遍性,很可能只是当事人强烈的当下体验,未必能够持久,也未必能让他人有所感动。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因同一事物激发的体验也很可能存在不同。出于以上原因,黄宗羲认为“一时之性情”只是“一偏一曲”,位列性情之末。
“万古之性情”同样源于感物而动。“万古之性情”之所以可以称为“万古”,在于以下两方面特质。一方面,这一情感体验超越了个体性,为人类所共通。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另一方面,“万古之性情”稳定而持久。这一情感体验虽由具体的事物触发,但不会随物的逝去而消陨。即使时过境迁,“万古之性情”也不会减损半 分。
更重要之处在于,“一时之性情”本身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使其缺乏价值上的导向性,不足以成为涵养道德品质的基础。与此相比,“万古之性情”具有价值规定性和导向性,“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这一价值导向性将万古之性情与其他情感区分开来。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区分,本文将“万古之性情”称作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一旦萌生并细加护持,会以此为基点扩充开来,最终形成坚韧不移的道德品 质。
基于以上的区分,我们可以对“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情”做一番辨析。此处所指之“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感,并非“一时之性情”,而是“万古之性情”,是具有价值导向性的道德情感。
孟子曾指出道德情感与道德品质的重要关联。“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②《孟子·公孙丑》。朱子对“恻”和“隐”的解释分别是“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9页。。
旁观者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自然而然产生怵惕恻隐的心理体验。旁观者的怵惕恻隐并不来自他对自己处境的担忧,而在于他担心那个快要掉入到井中的孩子。这种恐惧和担忧并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①《孟子·公孙丑》。。从这一角度而言,旁观者的怵惕恻隐具备了一种道德意义。
孟子对“恻隐”予以了相当积极正面的评价,将“恻隐之心”视为“仁之端”。仁这一道德品质不是抽象的,必定存在于具体场景之中,反映于对具体人事的应对之中。仁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会有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恻隐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仁心仁德的一个重要标准。
与此相反,“不仁”的一个明显表征便是麻木与无感。程子认为,医书用“手足痿痹”来形容“不仁”,最为生动形象。不仁之人往往对周遭一切丧失了感受力。他人的一切处境无法激发任何的道德情感。 “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2页。倘若对他人的困境缺乏最基本的恻隐之心,仁德根本无从谈起。
同时,孟子也认识到,道德情感与道德品质毕竟还有差距。恻隐仅仅是人在具体场景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情感表现,并不足以称为道德品质。“恻隐”毕竟不能等同于“仁”。道德情感需要礼义来加以导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礼运》中的譬喻颇为可取,“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③孔颖达:《礼记正义》,第814页。。郑玄注曰:“人情得礼义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④同上书,第816页。以礼义导养人情,前提是因顺人情,而非革除人情,道德品质之于道德情感,正如稻禾扎根于沃土。因此,孟子对恻隐等道德情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四端经过扩充,能成长为道德品质。
那么,为什么《诗三百》将对道德情感的导养摆在如此首要的位置?
古人认识到,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实现自知的必要进路。正如纳斯鲍姆所指出的,“研究情感形式是我们寻找自我认识的重要部分。情感的作用不仅仅是实践知识的手段,而且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实际处境最好的认识或知识之重要组成部分”⑤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萌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同时,道德情感是维系人伦关系的纽带。小至室家中的父子之恩、夫妇之别,大至宗族中的长幼之序、朝廷中的君臣之义,情感是维系这些远近、亲疏关系的重要载体。可见,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道德情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题在于,道德情感的积极性与稳定性虽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但也难免失于一偏。“正直者失于太严,宽宏者失于缓,刚强之失于苛虐,简易之失于傲慢。”⑥孔颖达:《尚书正义》,第96页。道德情感的萌生固然是件好事,但倘若不对其进行积极地导养,道德情感的偏颇之处很可能会放大,以至于遮蔽本身的积极性。因此,对道德情感的导养不可斯须离身。
在古人看来,一个完善的人应能较全面、通透地理解自身的情感,洞察到道德情感的萌生与表现,并能对其收放自如。随着自己身处的情境不同,面对的对象不同,道德情感的表达方式也需要有差异。甚至在面对相同的对象时,情感的表达方式也须与时偕 行。
恰如其分、合乎时宜地表达道德情感须经历艰苦漫长的后天修为。若丧失对道德情感的调适,以致陷逆于某一极端状态难以自拔,那么“发乎情”将变为“役于情”。如何涵养道德情感,使道德情感的抒发中正平和,成为诗教关注的重要问题。
三、温柔敦厚,诗教也
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与此类似的说法也多见于其他文献中,如《礼解》曰:“温柔宽厚,《诗》教也。”(《白虎通德论·五经》)对于“温柔敦厚”的解释,以往学界存在诸多争论。
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②孔颖达:《礼记正义》,第1598页。孔颖达从仪态、性情两方面分别解释了“温”与“柔”,并将“温柔敦厚”归结为“依违讽谏”,即在下位者给上位者提建议时,往往采用委婉、迂回的方式。这一立场与《毛诗大序》“主文而谲谏”的观点一脉相承。
徐复观先生认为,孔颖达的解释源于“长期专制淫威下形成的苟全心理”③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他主张从《诗三百》中的感情特质来理解“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是就诗人流注于诗中的感情来说的。温是适当时间距离的感情,是不太热不太冷的温的感情,是创作诗的感情基础。‘温’直接导向的是‘柔’。温柔同时又导向了‘敦厚’。‘敦厚’与‘浅薄’相对,指的是富有深度与远意的感情,同时也是多层次,乃至是有无限层次的感情。”④同上书,第46页。徐复观将“温柔敦厚”解释作感情。这比较符合自“五四”以来以文学解《诗》的主流。这一派的学者多将“发乎情”的“情”解释为“感情”,从而主张《诗》生于人的情 感。
林业连先生同样认为孔疏值得商榷。“《孔疏》只有解释温、柔两字,并且只持‘依违讽谏’一个比较狭隘的观点来作为答案,不见得可以通解古人‘温柔敦厚,《诗》教也’泛指的大道理。”①林业连:《“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涵探析》,载《诗经研究丛刊》 (第二十九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接下来,林业连先生对“敦”的字义做了一番语义学的训诂,将“温柔敦厚”解释为“颜色温润、性情柔和、为人厚道”。“只有温柔敦厚,才能有健全的人格;也唯有人人温柔敦厚,而后有和谐安乐的社会和国家。”②同上书,第99页。林先生的解释质实平顺,从神色、性情、性格特征等方面揭示了“温柔敦厚”的意思。
孔颖达将“温柔”解释为“颜色温润,性情柔和”,并从言说方式上来解释“敦厚”,将其理解为“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林业连先生将“温柔敦厚”解释为“颜色温润、性情柔和、为人厚道”。焦循指出:“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③“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以比为争。”详见焦循:《毛诗补疏序》,转引自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17页。焦循侧重于从言说方式上来阐释“温柔敦厚”。综上,学者们多从颜色、性情、言说和处世方式来解释“温柔敦厚”。而这些方面都可归属于一个人呈现出来的、可以为外人观见的生命样态和气象。
那么,为什么“温柔敦厚”可以作为诗教的重要标 志?
如前所述,诗教的要义之一在于涵养道德情感,并使道德情感的抒发中正平和。“诗,持也。持人情性”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5页。。“持”字有“持存”“持守”等含义。“诗者,持人情性”强调的是诗对于道德情感的涵养和护持,使其以恰到好处的方式呈现出来。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⑤《论语·八佾》。朱子注曰:“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6页。《关雎》之情不失其中正之道。不独《关雎》如此,《变风》诸诗之情无不发而中节,故《毛诗大序》云“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⑦孔颖达:《毛诗正义》,第18页。。
道德情感存主于身心之中,实现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理想状态。这属于未发的层面。一个人的神色、仪态、语气、言辞等方面属于已发的层面。未发与已发并非毫无关联。道德情感上的涵养工夫和生命境界直接决定了此人所呈现出来的气象。反过来说,一个人的神色、仪态、言辞等外在表征同样能够反映出此人道德情感的涵养状态。道德情感有所涵养的人,自然会在神色、仪态、言语方面与常人有所不同,会呈现出“温柔敦厚”的生命气象。“温柔敦厚”是效验,其内在基础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道德情感。而诗的作用正在于涵养道德情感。基于这一原因,温柔敦厚可以作为诗教的重要表征。
《诗三百》的言辞“不以理胜,不以气矜,情深而气平”①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17页。,以中正平和、委婉迂回见长。诗人不以理凌人,而是以情动人、感人。我们可以通过欣赏《诗三百》的言辞观见诗人“温柔敦厚”的生命气象,进而体会其道德情感,领略《诗三百》的化育之 效。
从《变风》 《变雅》的诗篇可以发现,对于事理的过错,诗人固然不会姑息纵容,但诗人不会偏执于一事的是非,自鸣理直,逞口舌之快、血气之强,而是在体贴对方的立场和用心的前提下尽委婉隐谲之能事,唯恐触伤对方尊严及彼此情谊。
今观《变风》诸诗,不见丝毫谩骂、揭短之辞,唯务动之以情。《北门》刺君不恤臣,其诗不过哀叹己之颠沛窘迫;《兔罝》刺王室无威,诸侯不臣,其诗不过悼己生不逢时而已;《葛藟》刺平王不念宗族之恩,其诗不过伤己惸独,无人亲厚;《子衿》刺学校废坏,学人荒怠,其诗不过形容老师思念学生的情 怀。
即便是在直接陈述君王过失的《变雅》,诗人之情也并未偏于一端。“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明期望至重;“百川沸腾,山冢崒崩”,伤国运维艰,积重难返;“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恐天命之凶兆;“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念先王德泽,哀后嗣难续。《变雅》的目的不在于发泄自己的愤恨和怨怼,而在于使君王改过自新,因此《变雅》言语虽直切,却没有谩骂、侮辱之辞,自始至终都是以情理动人。
四、诗礼合一的成德之学
重视对道德情感的导养,使之中正平和,合乎礼义,不单是诗教所倡导的,礼教亦然。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②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28页。可见,圣人依人情而制礼。礼由内铄,而非由外力强加得来,正如男女之情是婚姻之礼的基础,长幼之序是乡饮之礼的基础。其中,礼与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者。礼并不是作为外在的力量生硬地附加到道德情感上,而是通过恰当的引导,道德情感能够以合乎礼义的方式表达出来。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③孔颖达:《礼记正义》,第1260页。“平好恶”并非是要根除人们的好恶情感,而是指情感的抒发应讲究时宜,止乎礼义。礼应是道德情感的存在方式。
人有视听食息,耳目口鼻难免成为外邪入侵的通道。“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入之矣。”①孔颖达:《礼记正义》,第1329页。因此,教化必定要落实于目之所视、口之所言、四体之动作周旋。诵雅言于口,躬行礼仪于日用践履之间,凡此诸种,皆在于营造涵养情性的雅正氛围,防微杜渐,扼恶于将萌之先,使民日渐迁善而不自知。
“温柔敦厚,《诗》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②同上书,第1597页。“温柔敦厚”“恭俭庄敬”都是为学之人变化气质、调和情性之后所达到的理想境界。古人未曾将《诗》与礼当作一门客观知识,吟诗与习礼的目的也不在于显示自己博闻强识或是谋求具体的技能,而是尊其为安身立命之本。
诗教之于口,礼教之于行。乍一看,二者针对的官能各异。其实,口与行莫不统于心,蕴之为道德情感。“先王以六经垂教,惟诗、礼、乐之用最切。《诗》、礼、乐虽分三者,其用则一。”③钱澄之:《田间诗学》,安徽: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1页。诗教与礼教是陶冶道德情感、涵养道德品质的成德之 学。
在先秦社会,礼无处不在。小至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大至宗族、国家、邦国之间的关系乃至天人关系等都需要礼来规范。冠礼、婚礼等贯穿了人的一生。意义深远的仪式营造出庄重肃穆的氛围,齐敬其身,宣导其情,去恶迁善。由此,人对自我的责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能够明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别、兄弟之情、朋友之 谊。
以礼制为纲纪的西周至春秋中期社会是孕育《诗》的温床。“礼乐文化的特殊背景使得中国政治、伦理、道德、宗教和艺术实践始终不能脱离礼的规范,并相互融为一体,统一于具体的礼典演习。”④王秀臣:《“三礼”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作为周代礼乐文明的累累果实,《诗》必然嵌入了礼乐文化的烙印。⑤在现当代诗经学界,《诗》多被视作一部表达主观感情的文学作品,应以西方文论作为范式来研究《诗》,将诗从礼制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钱钟书是以西方文艺学来治《诗》的集大成者。在《管锥编》中,他大量引用西方诗学理论来解读《毛诗》,认为《国风》言语切近,更近似后世的抒情诗,而《雅》 《颂》作为礼乐文明的集中反映,非但缺少个人情感的抒发,还有对典礼场景的大量描述。礼器、仪则之名不胜枚举,没有礼学基础之人根本摸不着头脑。顾颉刚幼时读《诗经》的经历可为其证。《国风》“句子清妙,态度温柔”,尚且能入心坎。至《小雅》便觉困难,“堆砌和严重的字句多了,文学的情感少了,便很有些怕念。读到《大雅》和《颂》时,句子更难念,意义愈不能懂得”。(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管锥编》论《毛诗正义》的条目共60则。撇开论郑玄《诗谱序》的一则,其余59则中,论及《国风》的多达47则,而论及《雅》的仅有12则,竟没有提到《颂》。数量悬殊的布局恰恰说明,如果西方文论能勉强凑合解读《国风》,那么它对于礼文繁复的《雅》、《乐》根本无措其手足。问题的关键在于,《风》 《雅》 《颂》是一个整体,对《雅》 《颂》束手无策的理论方法又能对《国风》的精神领略几分?可见,不通礼,无以治诗。《诗》是礼的精神在言说。《诗》与礼相结合,共同缔造了礼乐造士的传统。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兴于诗,立于礼”作一番新的诠释。“兴于诗,立于礼”不仅是孔子对当时教育方式的客观陈述,而是他对《诗》与礼内在关系的阐释。在礼崩乐坏的末世,礼文转繁。人们的关注点由礼之本转向礼之器。行礼徒有虚文而无实质,甚至借礼器的齐备来炫耀财力。同时,吟诗逐渐沦为无关己心的记诵之学。《诗》与礼的内在关联日益隐晦。
夫子与弟子讨论“素以为绚兮”一诗,用“绘事后素”启发学生思考礼之本,更进一步地借“兴于诗,立于礼”来汇通《诗》与礼的内在精神。《诗》与礼,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在探讨《诗》、礼关系时,我们不应执著于名称、形式等表象,将《诗》与礼视作全无关联的两者,而要援表入里,体悟《诗》与礼精神的统一①降及后世,诗与礼的内在关系隐晦不彰。后世对郑玄《毛诗笺》中“以礼笺诗”的做法贬多于褒。章如愚认为,“郑氏之学长于《礼》而深于经制,至于训《诗》,乃以经制言之。夫诗,性情也。礼,制迹也。彼以礼训《诗》,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欤。”陈善之认为:“诗人之语,要是妙思逸兴所寓,固非绳墨尺度所能束缚,盖自古如此。予观郑康成注《毛诗》,乃一要合《周礼》,束缚太过。不知诗人本一时之言,不可以一一牵合也。康成盖长于《礼》学,而以《礼》言《诗》,过矣。”转引自向熹:《〈诗经〉语文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页。两位学者之所以对郑玄“以礼笺诗”全无正面评价,是因为他们并未追溯到先秦诗礼合一的传统中去理解诗本身。而诗礼合一的传统正是郑玄心之所系。在郑玄看来,“三礼”并不是生硬地附加到《诗经》上的他者。《诗》中本来就包含着礼教传统及精神。礼是诗的内在规定。“以礼笺诗”的目的在于激活《诗》中日益隐晦的礼的精神。。
诗教与礼教都着眼于对道德情感的导养,目的在于为学之人的成德。这可以解释《诗》与礼的同,但不足以解释二者之异。《诗》与礼有内在关联并不意味着“兴于诗”与“立于礼”是一种横向的并列关系,而是先“兴于诗”,继而“立于礼”。这样一来,值得追问的是,《诗》与礼的差异何在?孔子为何用“兴”来言《诗》?
五、引类连譬的诗性言说
“诗言志,歌咏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②王夫之:《唐诗评选》,载《船山全书》 (第十四册),长沙:岳麓书社1981年版,第897页。可见,王夫之把《诗》的独特归结到了“兴”上。诗性言说的枢机在于“兴”。“兴”是中国诗学传统中的一个独特的范畴。这是很多学者的共识。
朱子把“兴于诗”的“兴”训作“起”。“兴,起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4页。什么是哲学意义上的“起”?“起”只是提供了一个端点,并未预设最终结果。“起”这一动作的结果会根据具体情境的不同、读者禀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种留白艺术开启了广阔的意义空间,不是限定,不是闭合,而是一种敞开,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可能。
众所周知,射线与线段的区别在于,线段两端都有端点,向内闭合,不可延长,而射线只有一个端点,具有向一方无限延伸的可能性。兴于诗的过程正如立足于一个端点无限延伸的过程,起点在于《诗》,落脚点却超越了《诗》,正如以手指物,目的在于所指之物,而非手指。
“起”的结果并未被限定,但这一动作并不是毫无原则、毫无方向的。《释名》:“起,启也。启一举体也。”①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这一训释包含着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起”这一动作是有所本的,目的在于“举体”,即由一隅兴起全体。只有着眼于“举体”,“起”这一活动才有意义 。
《诗》所言之物、诗人在某一历史情境中的经验正是这“举体”之“一”。“启一举体”之“体”指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技能、知识或道理,而是作为万物关系总和的整体,即道。道周流无滞,变动不拘,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在道之外,不复有另一个整体与其构成并列关系。道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据,虽超越于万物,却并非与万物相隔。万物作为“一”,与道之整体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唯有在与道的相互关系中,万物才能是其所是。吾国古哲未尝离物以观道,离事以求道。读《诗》“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识”不是把草木鸟兽当作客观知识来积累,而是从天地大化中来体认道。
可见,“兴,起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动作,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诗》对于道物关系的理解。道物不相隔,是“一”能“举体”的前提。更进一步的,“启一举体”是对“起”这一行为的基本规定。“起”并不是任意随性、毫无原则的,而是要以“举体”为目的。这样一来,“兴”就不仅仅意味着《诗》的艺术功能或是读《诗》后的审美体验②叶朗先生区分了“兴于诗”的“兴”与赋比兴的“兴”。前者是就诗的欣赏而言,后者是就诗的创作而言。陈桐生先生认为,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欣赏都是艺术活动的前后阶段,二者都离不开艺术感性。详见陈桐生:《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第155页。,而是在更高的意义上与“举体”相关联。
《诗》之兴,在于《诗》通乎道。与逻辑严密的论说文相比,《诗》言近旨远,由此及彼,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意义世界的敞开——由有限的言说引到无限的道。
兴于诗,并不是把一个具体的教义灌输给读者,而是为读者开启了一个更广阔的意义空间,供其优游涵泳,自得于身。“兴”实现的并不是对某个具体知识或义理的知,并不是从一个端点到另一个端点,从有限到另一个有限,而是使读者能够融入道之中,从一种潜在的无限的道的高度来反观自己。孔子与子夏谈诗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真正意义上的“兴于《诗》”。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①《论语·八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本用来形容庄姜的美貌。面对子夏的追问,孔子并未直接回答《诗》的字面义,而是通过思考“绘”与“素”的关系(绘事后素)上升到文质之辨的高度——文质相参,质为文本。基于文质关系,子夏进一步来反思礼这一概念,“礼后乎?”很显然,文质关系、礼与仁的关系等义理并不包含在“巧笑倩兮”的字面义中。但“巧笑倩兮”却开启了广阔的意义空间。
孔子称赞子夏“始可与言诗”。在孔子看来,“言诗”并不在于疏通《诗》的字面义,或是把诗背得滚瓜烂熟,在对答时能引经据典,而是能引类连譬,“闻一以知十”,由有限的言辞上达到无限之 道。
以诗为教,基于对人灵性中的自觉能力有着充分的信任。为学之人不是教义的灌输者,而是有待启发的灵动的生命。子曰:“起予者商也!”②同上。“起”是诗教的神髓。诗教重在对为学之人进行提点与启发,而非义理的灌 输。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③《论语·述而》。朱子注:“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5页。“开其意”与“达其辞”都充分调动了人的想象力与觉悟力。这一过程还需要恰当的时机,即“愤”与“悱”。“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子夏思考“巧笑倩兮”而未得其解,正是“心求通而未得”之时。孔子并不是把礼之本末的道理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借子夏思考“巧笑倩兮”的契机巧妙地让学生自己领悟出这一道理。
“素以为绚兮”引发了孔子对“绘事后素”的思考。但这远未穷尽诗句的启发义。个人的生存境况不同,文化积淀不同,同一句诗对他们开启的意义空间也各不相同。“绘事后素”并非诗之达诂,只是对“素以为绚兮”的一种诠释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人“《诗》无达诂”的提法并不是对一个经验现象的描述,即读者为了满足某个具体目的而断章取义,牵合诗意以就己意,而是对《诗》的本质规定。《诗》言说的是至高的道。《诗》的意象、场景虽有限,但《诗》相对自由的形式开启了无限丰富的阐释空间,能够最大程度地彰显道灵动周转的特性。这必然决定了《诗》之诠释不能限于一端。
结 语
《诗》所言之志包含着深刻的价值规定。采诗、献诗与编诗之志使《诗》完成了从个人领域到伦理政治领域的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的成书与流传从根本上不同于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诗》浸润在先秦礼乐文明的时代背景之中。诗教是导养性情、成德成人的生命之学,与礼教共同缔造了礼乐造士的传统。
《诗》与礼既有同一,又有差异。《诗》与礼都非外烁,而是源于人情,立足点在于导养道德情感,使其止乎礼义。但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作用方式也不同。《诗》的独特性在于“兴”,在于“起”,由有限的言辞与意象通达无限的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礼的独特性在于“立”,通过一系列节文度数使人心念纯正、行为周旋中礼,“卓然自立,不为外物所摇夺”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5页。。尽管如此,《诗》与礼莫不以成德、达道为终极归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