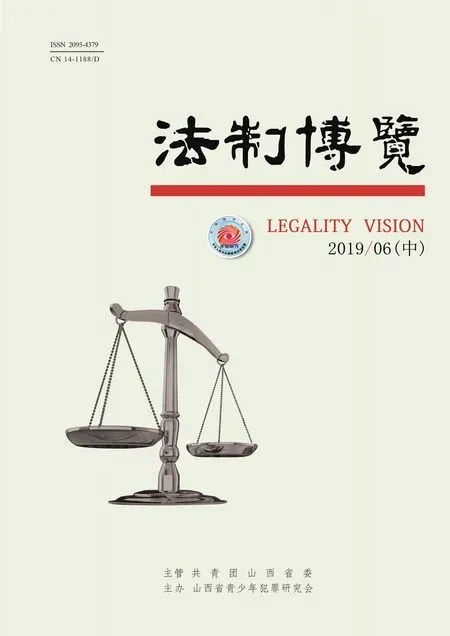民诉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浅析
2019-12-13马艺源
马艺源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207
一、先行调解的民诉法概念探析
我国2012年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第122条确立了先行调解制度,即针对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纠纷,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先进行调解,而后再确定是否继续进行诉讼活动。先行调解制度作为诉前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全面推行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要想实际运用于立案前的阶段,背后需要的是基于对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时间的综合考量。而民诉法中对于该制度仅仅用一条定义式的条文进行规定,没有相应配套的具体适用方法,还存在很大的立法空白点。这样的空白点给予了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对此有很大的弹性操作空间,从而未能发挥出先行调解本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二、关于先行调解制度适用阶段的观点争议
(一)司法实践层面的观点
对于这一制度的具体定性,从各自所处角度出发,理论与实务观点存在一些差异。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奚晓明法官为代表的实践论提出,“先行调解的适用时间并未有所限制,只要是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即可,至于是收到当事人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后、尚未立案之前,还是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后、移送业务庭审理之前,抑或是开庭审理前或者开庭审理后均在所不问。”以能实际化解矛盾为目的,持实践论的司法工作者往往倾向于将其存在与适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延伸至立案后、甚至审判阶段。司法工作者往往基于高效审判、迅速结案的角度进行衡量。一个成功的调解能高效且迅速地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首先,在立案之前就调解,能有效的分流一部分案件,拦截一些轻微纠纷。这一部分纠纷,在传统的“审查受理制”下,往往难以立案,从而引起当事人“缠诉”的行为,延长了整个诉讼活动周期。而改革后的“立案登记制”下,这一类纠纷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如果将其暂予登记,同时做出调解,则能将其拦截至诉讼程序之外,通过庭外的调解方式化解矛盾,减轻法官工作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不仅能达到法院解决纠纷的目的,还能节省司法资源。
但在进入到审判阶段以后,这一制度的合理运用却有待斟酌。一旦进入到正式的诉讼程序中,如何界定“先行调解”中“先行”二字,该时间阶段存疑。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如开庭前、开庭后、判决做出之前进行的调解是否还属于“先行调解”的范围?这几个阶段的调解能否将其归于正式的庭审阶段中,或者归于庭上调解中,或者归于为当事人为得到最终判决而作出的让步承诺,这些疑点难以回答。
从司法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最大的出发点和利益衡量因素是司法效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往往愿意采用纠纷化解模式来处理诉讼,降低工作量。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解释,却忽略了法律赋予其正当性与合理性来源。
(二)理论层面的观点
理论研究的角度还存在另一种声音。李浩教授认为,先行调解是指原告起诉后至法院立案前的调解。赵钢教授持有类似的观点:“在法律概念的使用上,《民诉法》第122条明确使用的是“民事纠纷”而非“民事案件”,这也意味着“先行调解”系指立案受理前的调解。因为只有在立案受理前,当事人之间的私权之争才表现为纯粹自然状态的“民事纠纷”而非“民事案件”。
学者更加倾向于从其字面含义解读这一制度的具体适用范围。要明确法律术语具体含义的适用,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情景下,而不是仅从理论层面下定义。先行调解中蕴含着时间阶段的层次区分,应该对它做出时间限制。“先行”的“先”体现在先实行、先进行,即先于某个特定时间或程序运行而进行。通过文义解释,将这一制度限于目前有效的法律规定中,严格界定了其法律来源正当性以及适用的合法性。
这一角度的解释虽保证了先行调解制度在运用过程中不被滥用,却忽视了其目的。比起传统的争讼模式,这一制度能更加有效地调和当事人的矛盾,用最高效的模式解决纠纷,建立起诉讼和调解之间的连接。通过调解,化解一部分案件,将司法资源留给其他案件,并不是一味地将所有案件只作简单的分流处理。
盲从性地将案件分流调解,存在一个弊端,容易出现“漏网之鱼”。对一些重大案件来说,其性质本身存疑,需要通过庭审,甚至提交审判委员会的方式审理,却在立案前的阶段就被轻易调解而结束诉讼程序,这样虽经过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却是对法律的轻视,对社会秩序,甚至是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损害。
三、小结
“先行调解”制度被《民事诉讼法》确认已有数年时间。这一制度的规定,为诉前程序分流以及诉调对接机制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衔接,但其还存在一些方面的立法空白有待完善,实践中对这一制度的具体运用差异性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