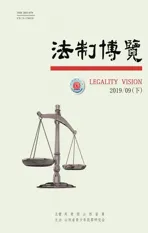居住权在我国的适用性*
2019-12-13杨晓凝
杨晓凝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居住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他人所有房屋的全部或部分及其附属设施,所享有的使用或占有的权利。居住权最初设立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弱势一方的居住问题,具有赡养、扶助、关怀的人文属性,对于有效利用房屋、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没有将居住权列入物权法规范当中,是立法上的失误。无论是从居住权在我国物权法草案被多次提及,还是从我国现有的社会状况考虑,都说明居住权在我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设立居住权制度时机已经到来,居住权应当尽早写入我国的物权法中。
一、居住权的现实作用
在民法典物权编中,居住权再次被学者们聚焦,是否存废引发各个学者热议。但是笔者认为,居住权的社会作用,其重点常常被放在保护离婚妇女,老人养老等这类社会弱势群体之上,而往往没有重视到其物权属性。
虽然我国自古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加上家庭抚养制度的法律保障,居住权防止老人老无所居的功能确实能够部分代替,但是,在社会急剧变迁,老龄化加剧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负荷越来越重的今天,新生时代在观念和抚养能力上都不足以再支撑起传统代际关系的正常运作,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1]再者,为了解决飞速增长的房价问题,青年一代负担高额房贷,年老父母花费毕生积蓄为子女购房的这种“逆抚养”现象也是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比起法定的抚养权利,长辈更愿意通过自己明确创设的权利来保护自己,这最终就表现为家长愿意将表征财富的房屋所有权交给子女,而自己保留必要的居住性权利。[2]在这里,居住权不仅仅是为长辈避免子女违背道德观念和逃避法律义务拒绝赡养而给予的预防措施,还是为老人提供另一种新的更加牢靠的物权保障。如果说2007年之前,否定居住权可以避免老无所居的现象的社会功能,但直到至今,其为解决老人“逆抚养”所带来后顾之忧的作用却不得不得到重视。
在我国现有的房屋交易中,只有“或租或买”的一刀切方式,这远远不能满足当代人对房屋的利用。如果增加一项可购买居住权的内容,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从购买者出发,购买居住权的方式既可以解决财产不足的窘境,又能供居住者长期稳定地居住;从供房者出发,对于房子的利用,可以选择完整的出卖,亦可以出租,还可以将居住与所有分离,分别出售,让房屋流通的渠道更加多样,财产所有人也能将房屋最大化利用。
二、居住权域外立法现状
居住权滥觞于罗马,在罗马法中归于役权。役权又分为地役权和人役权。居住权作为人役权当中的一项权利,在罗马设立的目的,起初,第一是为了保障是“夫权婚姻”或者生父家长权之下的婚姻中的女性在丧偶后的生存利益,第二是为了保障家主去世后,奴隶的正常生活。但是社会发展至今,即使“夫权婚姻”和奴隶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保留或再建立居住权,证明了其现实适用性。自近代法典化运动以来,欧陆国家的主要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均将之加以继受并有所发展。[3]所以笔者通过对比某些国家对居住权的立法现状,在其中窥探一二,并为我国居住权立法提供借鉴。
《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第1款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很显然,在这里的“居住权”具有最基本的人权属性,是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可剥夺的人天生具有的权利。在罗马法中,居住权最开始也并非表现为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事实,最后随着历史的推进,渐渐纳入役权的范围内。它是一种为特定人的利益而利用他人所有之物的权利,具有暂时性的特点。[4]《瑞士民法典》第776条第1款规定“居住权,是指居住于住宅内或住宅某部分的权利”。该法典对限制物权进行了规定,其中役权包括地役权、人役权,人役权又包括居住权和用益权等,这里的居住权仅仅是一种使用权。《法国民法典》几乎完整地移植了罗马法中人役权和地役权的二元结构体系。但是该法典中的居住权相比于使用权,其在内容上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比如不得处分和继承,例如该法典第634条规定:“居住权既不得转让,也不得出租”。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第二部重要民法典的《德国民法典》,在“役权”一章中对居住权做了如下定义,在排除了所有权人的情况下,将建筑物或建筑物的某一部分作为住宅加以使用的权利也能够作为限制的人役权而设定。和地役权相比,限制的人役权强调的是为某一特定的人设定的役权,而不是为了行使土地的利益,相比于用益物权,限制的人役权具有只能在不动产上设立,而且只能为某一特定的人设定的特点。[5]1951年德国的《住宅所有权及其长期居住权法》则设立了长期居住权,规定居住权可以转让和继承,并且居住权人可以从事出租等用益物活动。这使得居住权摆脱了人身专属的属性,发展成了一种收益手段。
三、对我国居住权之构建
对于居住权在我国是否应该构建,从2002年初次在物权法意见稿中被提及,不少学者就对此提出质疑和反对。为了确保居住权在我国民法典的稳定地位,排除反对的声音,笔者对主要被提出的质疑一一进行反驳。居住权中被否定的社会作用,可根据社会现实情况进行说明;居住权的一些瑕疵之处,笔者认为立法时应当在现有的法律中给予最准确的定位,其才能扎根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土壤中。
反对设立居住权的观点大抵如下:第一,起源于罗马法居住权的规定,一般存在于以人役权和地役权构成的二元体制当中,与国现有的物权体系难相融。[6]第二,在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及现有的法律保障下,居住权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子女有赡养父母之义务,一般不存在父亲去世后寡母无房可居的问题。[7]通过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法体系就可以代替居住权的社会作用。第三,居住权的设立,由于其具有很强的人生属性,限制了房屋的流通,使得房屋不能“物尽其用”。
对于上述否认观点,笔者认为,对反对观点提出的第一点,可以有两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1在人役权体系中的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由于其具有浓厚的人身属性而被归入一个体系当中,但是体系内的每一个权利都具有独立特性,单独发挥社会作用,彼此互相联系但又不互相干涉。即使在我国物权法里没有人役权体系,单独规定居住权的内容不会影响其性质,也不会涉及法典体系上的任何改动。居住权有其独立特性,适应我国传统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划分,把它置于用益物权一章作为物权法体系组织部分,符合形式逻辑。[8]在我国,具有明显人役色彩的权利也一直存在用益物权体系,比方农村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同样,在没有人役权体系下规定居住权也是合理的。2我国虽无二元结构理论,居住权虽具有人役性质但未必一定要将其纳入人役权当中,可以对居住权加以调整,再将其植入到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当中。将居住权的人役性和物权性分开规定。民法典只对其物权属性进行规范,而其人役部分则交由其他规范人身关系的法律解决。第二点,笔者在居住权的现实作用部分已经说明,即使我国有道德约束和法律规范保证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但是诸如当下“逆抚养”现象老人的后顾之忧,依然是现有法律无法覆盖的盲区。第三点,居住权使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实质是使房屋的流通能力更强,更有效实行“物尽其用”。房子的价值在于被居住而不是流通,居住权的授予,在于为居住权人提供稳定的住所而不是为其增加财产。受益人已经充分地使用了房屋的价值,为何一定要将房屋流入市场进行流通呢?再者,一旦居住权的消灭事由成就,比如居住权人死亡、主动放弃居住权等,房屋就恢复到完整所有权状态,此时也完全能够进入市场进行流通。
排除了设立居住权设立时可能出现的阻力后,针对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第159至162条,笔者对居住权设立的细节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物权编第159条第1款,并没有对居住权主体的范围进行限定,只要双方彼此达成合意,都可以设立居住权。但是居住权因最初具有人文关怀属性而被重视,但在这里却未体现。笔者认为除了约定成立居住权外,还应当有法定的居住权。法定居住权的权利人主要还是家庭成员。只要居住权人达到法律规定的条件,即使房屋所有权人未同意也不阻碍居住权的生效。第2款,居住权的设立,采用书面形式,是今后解决纠纷时的主要依据。第3款,居住权依登记设立,可以对抗第三人。尽管居住权虽与租赁权都是对房屋的使用,但是居住权登记对抗效力是与租赁权最主要的不同。
物权编第160条,限制了房屋的流转,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房屋不得出租。为了区分所有权和居住权,法律应当限制权利的转让和继承,否则所有权将被架空,所有权人对所有房屋行使所有权将受到长久限制,但是为了体现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尊重当事人双方约定对居住权的处分,笔者认为可在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后面加上但书: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法定居住权与意定居住权并不能混为一谈,非家庭成员居住权不具有人役色彩,居住权不再是生活保障手段,而是一种纯粹的财产性权利。[9]物权编第161条,法定居住权的消灭事由是居住权人死亡,但当事人另有规定的除外,但对于约定设立的居住权,应当增加一条对于约定性居住权的期限规定和灭失事由的规定。居住权的期限按双方当事人约定;居住权的灭失可以因其约定的期限届满或者房屋灭失或者其他当事人约定的灭失事由成就而产生。
第162条,以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虽然是单方法律行为,不同于约定的居住权,但同属于意定的居住权范围,其应当参照意定居住权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