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最后一年的元化先生
2019-12-10蓝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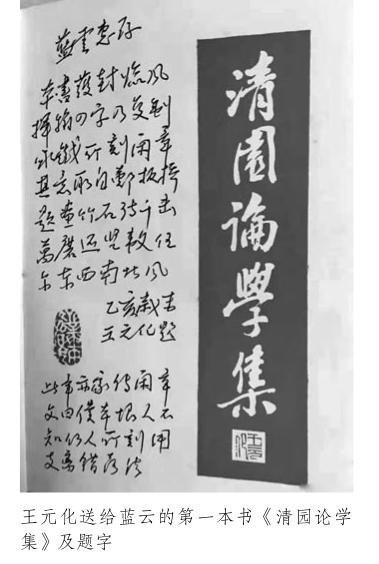

由于“文革”期间,我的中小学时代的日记曾引起了祸端,所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再也不愿去记什么日记了,避免再惹是生非。在先生身边工作,很多朋友说,你应该把和先生一起的生活记录下来,将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想,记它干吗呢?我只不过帮帮先生的忙,力所能及地干些先生要求我做的事情,先生也没有要求我记日记。所以14年间,几乎没有记录下什么文字。
后来,先生罹患癌症,我猛然意识到,和先生相处的时间不是没完没了的,而是进入了倒计时,每一天都何其珍贵!这时,我才感到应该记录下在先生身旁的所见所闻,说不定哪一天,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我开始破戒,记日记了,那是2007年的5月10日,距离先生去世的2008年5月9日,不多不少正好一年。以下是我关于王元化先生的最后的日记。
2007年5月10日
上午,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瑞贝卡及她的女助手一同来访,主要是请王先生谈谈他对毛泽东的看法……瑞贝卡问及先生是否见过毛泽东,先生说在1952年的全国文代会上,受到过一次接见。先生和许多代表一起等了很长时间,毛泽东来了,许多代表蜂拥而上,群情激动,而自己却突然失去了热情,呆立着,没有随人群拥上前去。
2007年6月29日
上午吴敬琏夫妇来瑞金医院探访,谈了一个多小时。
先生问及有什么可读的书,吴先生推荐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西班牙旅游笔记》《总统是靠不住的》。中午在复兴西路的小季风书店居然全部购得,果然十分吸引人,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的批判。
下午先生會诊,看来还是有些问题难以解决。
2007年6月30日
上午洪森来探视,先生又谈及对《论语》的看法。
先生不以为《论语》易懂(针对钱理群的观点),认为其实是很难读懂的。因为仅仅是学生们记录下来的孔子语录的片段,不知当时的语境等具体情况,理解其实十分困难,他曾写过几篇短文,谈过一些。
洪森作了录音。
2007年10月4日
上午《解放日报》司徒伟智来,带来了他早年购买的第一版《文心雕龙讲疏》和《思辨短简》,请先生签名,先生慨然应允,并送他《读黑格尔》《人物、书话、纪事》各一本。司徒告诉先生,他之所以知道先生是因为先生的姐姐王元霁是他的中学化学老师,王元霁老师曾对学生们说:“我的弟弟不是什么反革命,他是一个才子!”因为这句话在“文革”中挨了批斗,可是作为学生的司徒从此知道了王元化,并开始关注先生的著作,而且越读越有劲。先生问司徒,现在比较好看的报纸有没有?司徒说大概《南方周末》还可以。先生说,哦,《南方周末》我已经看不到了,他们现在不送我了。他们曾经向我索要题字,可是规定要我写:“从这里开始,我认识了真理。”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从这里开始才认识了真理,于是我就搁下了,没有题。也许因此,他们再也不赠报给我了。
司徒却有意外的收获,喜出望外地告辞。
午餐炒南瓜、烤麸、排骨莲藕汤。还有我做的百合汤,他还爱喝。
先生说想换一盆花,要草花,我答应去找找看。
2007年10月5日
先生要我读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的《五四运动与“东西古今”之争》。先生说,汤先生的其他看法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对他的文化三分法——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表示并不赞同。先生还说“文如看山不喜平”,感到汤先生的文章显得平了些。又读《报刊文摘》中洪森所撰《谈知识就是力量》,比较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教育,中国人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灌输,而缺少对知识背后的学问、智慧的认识。先生说洪森的观点是没错,问题是他还是没有说出所以然来。还说中国教育的弊端还不仅是“灌输式”的问题,还有应试教育和实用主义的问题。我学了就要考虑回报是什么,有什么好处,是“目光短浅”的问题。他说:“如果我小时候学习只是考虑回报,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司徒发来一则短信:“小蓝,谢谢你的安排,让我有一次聆听元化先生教诲的机会,而且,还得到这许多签名本的王著呢!……我建议你效仿艾克曼、胡颂平,编一本王元化先生谈话录,可好?前述二书,似容易就近从上海图书馆借得。倘有不便,则我可将手头此二书立时送来。就我视野所及,在胡适过去以后,王元化堪称中国思想学术界第一人。坊间流传有‘北李(李慎之)南王或‘北季(季羡林)南王,其实李有思想缺学术,季有学术缺思想,王则二者兼具。所以此事意义甚大,将嘉惠后学的。粗浅建议,仅供参考。”
我把司徒的短信读给先生听后,先生笑了笑纠正:“是流传‘北钱(钱锺书)南王吧!”
中午胃口仍差,为他做了他要的红烧素鸡,还有嫩荷兰豆,都只动了两筷子,说是没有饿的感觉,也没有精神。怎么办呢?无奈!
2007年10月12日
先生今天出医院,故一大早就赶往瑞金医院。
先生说睡得不错,就是老做梦。我问做什么梦?先生说梦见和张可阿姨在一起,张可阿姨走啊走啊,先生就跟随在她的后面,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后来好像是到了医院里。
我说先生一定是非常想念张可阿姨了,所以梦里就见面了。
回到庆余别墅,仿佛松了一口气,觉得轻松,至少生活方便许多。
先生谈及某某近来总是抱怨一切,抱怨别人。他说:勿道人之短,勿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之慎勿忘。我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要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可有人却反过来,专道人之短,专说己之长,这样不好嘛!
丹燕(陈丹燕)来电,要我和先生整理的谈话录文章及一些对先生的评论,并约定周一碰头。
2007年10月13日
早上陪先生走路,问爸爸的情况。我说爸爸情况不错,虽放弃去美国探亲的打算,但想在国内各地走走。先生说,怎么胃口这么好,我现在是任哪里也不想去了,毫无欲望了。又说,不过,如果有一场余叔岩的戏,就算情况再糟糕,我还是会撑了去的。

精神还算不错,为《上海社科报》段钢题写了大字“和园”,还替一位已经不记得姓名的索字者题了字。然后余兴未尽,还有兴趣写些什么。我想起前几天梦见张阿姨一事,就说不如就写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吧。先生依旧要我先用笔写下来,我便抄在纸上,再给先生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写到一半,先生说好像漏了些什么,我拿过原稿再读一遍,发现上阕漏了“纵然相见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先生说:“好一个马大哈,差一点让我和你一起‘马大哈了!”
饭后散步,和先生说起国庆节陪爸爸妈妈游丁香花园。先生说,1949年后他们住在丁香花园旁边,承义曾和柯庆施的儿子一同在丁香花园骑车玩,那时候张可阿姨不做事,先生不要张可阿姨恢复组织关系。那时候,他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已然存疑了。但是,那是1949年后先生家度过的一个短暂的幸福时光,后来便是一个接一个的厄运降临,他说自己是很命苦的,但他的儿子对他却说:“你还算命苦?”
2007年10月20日
与先生编写大百科约稿的书目,共计10多个专题,其中有一个谈毛泽东,拟标题时我建议为:读毛著记。先生说不好,不如用“读毛选记”,则可理解为“读—毛选—记”,也可读作“读毛—选记”,任凭想象,确实高明。
2007年10月25日
丹燕来谈,照先生的要求,恐怕有些难度。希望能常来探望陪伴先生,就所见所闻,联系其他材料来写。或是按照《九十年代日记》中有些比较含糊的记录来谈,可以谈得具體一些。丹燕说,比起萧红谈鲁迅,自己也许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因为萧红对鲁迅有过分的敬仰,难免有些神化了。谈到丹燕在大学读书时的一些旧事,先生很开心。我提起先生自己为自己的书设计封面,也很有意思。特别是《九十年代反思录》《思辨随笔》《九十年代日记》用的都是树叶子。《思辨随笔》用的是马蒂斯的装饰性很强的线描树,树丫伸展开来,挂着一片片树叶,枝叶相连;《九十年代反思录》是让娇娇找来的保罗·克利的冷抽象作品,是我先从书上看到了推荐给了先生,然后娇娇找来了画册,从中选了一片树叶由里向外层层蜕变着的形状和不同的绿色;《九十年代日记》更有意思 ,是先生家里有一只雪茄烟盒,上面用笔触流畅的寥寥数笔,在鲜蓝的底色上用橘色线条勾画的一片树叶,鲜活明亮,也许是体现了思辨过程中收获的快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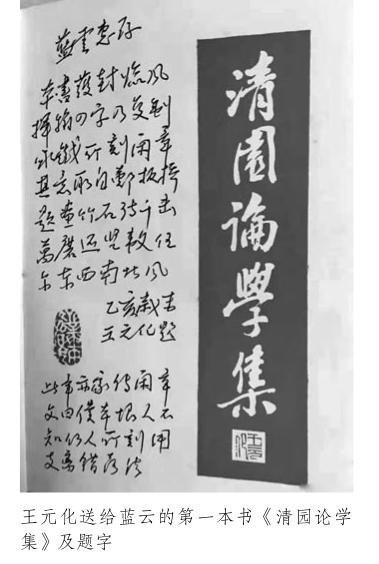
中午,我们三人高兴地吃了小周的手擀面,先生胃口依旧差!不知如何是好?
晚上,夏中义去看了先生。先生往往都是一对一约见夏中义,不想受到干扰。谈完后夏中义来我家,取走先生的题字。夏中义说,丹燕适合写印象记,但不适合写传记。
2007年11月30日
今天是先生的87周岁生日,瑞金医院的医生护士专门为住在医院里的先生庆生。她们在会议厅做了布置,买了蛋糕,为先生唱生日歌,一起吃蛋糕,先生很高兴,也有些意外。
先生对我说:在病中,我感到了人间的爱。
他说:蓝云啊,我原先总认为你是一个无原则的好人,你把一切都看得美好,把什么人都当作好人。而你总责备我对人过于严苛,近乎挑剔,把别人都看得很坏,这是对我的误解,是不对的。可是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你还是有道理的。你看,大家都对我这么好,医生护士都这么细心,打针一点也不疼,为我溃破的创口换药也不嫌避,还给我做生日。护工也是很呵护我,夜里但凡有一点点动静,小周总是很警觉,几次半夜起来照顾我。他还说,要不要请两个护工轮流值夜,否则怎么吃得消?甚至特为准备了一笔钱,嘱咐在自己走后留给护工小周,还托朋友在自己走后替小周安排一份工作。
他说:你看曼青、洪森、丹燕,还有那么多朋友们,给了我多么无微不至的爱,我感到你是对的。
2008年1月23日
告诉先生,在电视里看到文忠(钱文忠)谈季羡林先生的罗曼史。先生说,自己唯和张可阿姨,除此以外没有什么罗曼史。说当年谈恋爱时,荡马路路过复兴公园,先生提议去公园逛逛,张可赞成。先生就去买票。可是在卖票处,口袋里却掏不出一文钱来,在张阿姨面前实在感到很窘。可是,张阿姨一点也不在乎,大大方方买了票,拉着先生走进公园去。
2008年1月25日
先生不住地咳血,已有数月。大家告诉他患的是肺结核,慢慢会好起来。我们都在善意地欺骗着先生。今天他突然问我:“蓝云,你告诉我实情,我得的肯定不是什么结核,一定是肺癌!对吗,不要瞒我嘛。我不是傻子,你应该对我说实话。”他盯着我的眼睛询问实情,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却忍不住哽咽。先生说:“其实我早有预感,我的日子不多了。”我默默流着泪,先生用仍然那么淡定的口吻对我说:“你不要这样,你难过,我心里会更难过。我并不害怕死亡的临近。但我是一个缺少耐心的人,不能读写,成天睡在床上,从一个思想着的人,变成一个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生命对我已全无意义。就让我从容地有尊严地走。张可走时(一年半前)我很难过,最后的日子,我虽然也一直关心她,可是自己也是百病丛生,不能随侍在老伴身旁,我是遗憾的。而我生命的最后一程,我希望你陪伴着我,你能这样天天来我身旁,我心里很满足了。我总是说,我并不寂寞,但是我孤独。这十几年有了你,我就不那么孤独了。现在,我要离开你了,我最是放心不下你的今后,一个人会不会生活得快乐?你生活得好,我才放心啊。”忍不住伤心的泪,先生什么都明白了。
抱怨没有什么好书看,替先生读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是写读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们的生活纪事,先生说这部书写得好,每个人物都描写得很准确,我们一连读了好几天。
2008年1月26日
昨夜起,飘起上海难得一见的鹅毛大雪。和先生在病房赏雪景,先生指着窗外问:“描写雪景什么作品写得最好?”我想想说:“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先生说:“唉!不对。描写雪景最好的要数《水浒》了,在林冲夜奔那一场‘那雪下得紧……给我印象最深。”
2008年3月20日
连续几个周二为先生加班清点存放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室内铁皮柜中的文件资料并造册,上周六先生签字,统统交给华东师大王元化学馆。
赵丽宏为先生做了一批紫砂茶壶,集了先生所书“拔地苍松有远声”中的“苍松远声”四字,赵丽宏和宗福先等一同来探视先生,送来20把紫砂壶,说是请宜兴名家制作的,想让先生高兴。
2008年3月25日
一月前,过了春节,先生做了CT复查,因为出现了癌症的脑转移,医院决定进行照光放疗。照了一个多星期,反应很大,呕吐恶心,頭发脱落许多,听力下降,所以停止了放疗。每天依然进食很少,吃些我和小周做的汤汤水水。咳嗽得很厉害,依靠含有吗啡的阿桔片和止咳药水止咳。没有精神,挂营养液来补充营养。
上周二咳嗽大吐血,殷红的血喷溅在洁白的被子上,触目惊心。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说是随时可能有危险。
先生的妹妹王元美和他的儿子、女儿陆续从美国赶来探视先生;先生的表妹也从北京赶来和先生告别,她含泪和先生说:“哥哥,你受苦了,看见你这么受罪,我们心里很难过。”
先生说:“我已经从一个精神的人变成一个纯生物性的人,人其实是很可怜的。我的这位表妹其实一直是非常爱我的。”他们依依不舍地诀别,令我心酸!
2008年3月28日
娇娇根据先生的要求,做了一套清园学馆的装修设计方案的效果图给先生过目,也真是抛砖引玉。先生希望学馆门头上方的装饰要典雅大气,有“外滩”的建筑的味道,或者是带点欧式的乡间房舍的风格;布置要“有聚有散,有的地方繁复,有的地方简洁。还有学馆里要放一张先生母亲的照片,大一点,镜框采用‘清园笔札展的那一种”。真不愧是大家,总是有着自己的见解。先生的头脑一直清醒。
今天上午俞慰慈来,带来了日译本《思辨随笔》的样书。先生很高兴地翻看,对俞慰慈说学馆要展出日译、英译版著作,还要展示译者的照片及小传。先生要俞慰慈转告冈村繁先生,我在世界上好几个国家都有好朋友,美国有林毓生、林同奇;瑞典有马悦然,罗多弼;日本有冈村先生,请一定要转告冈村先生。
洪森也从香港回来了,一早也赶到了医院来。
由于听力越来越差,林同奇从美国打来电话,他已无法接听,于是林同奇先生把要说的话扫描后E-mail过来,和先生进行艰难的“笔谈”。星期天晚上收到林同奇先生来函,谈读先生书的感想(见林同奇来函)。
2008年3月27日
早上丁丁(汪丁丁)、小李从杭州赶来看先生。陆灏拿来了林毓生来探望先生时的对谈稿小样,《文汇报·笔会》要分两期发表。俞慰慈和赵坚也都来探望,赵坚带了日本最好的米来,说给先生煮粥。中午和丁丁夫妇,还有洪森一起在锦悦轩午餐。
晚上唐玲来电,说是从丁丁处得知了先生的情况,决定从杭州把李秀勤做的青铜雕塑胸像送呈先生过目,不知先生满意不满意。
2008年3月28日
一早和娇娇去医院,把娇娇赶出来的学馆外立面设计效果图拿给先生过目。共有10个样式,先生一一细看琢磨,提出了修改意见,让娇娇修改。还提出他希望用白色带红黑点的花岗石。
丁丁小李也在,由于一直在谈学馆的室内设计,主要是娇娇在谈。
王赞、舒展从杭州赶来,冒雨送来了先生的青铜像。先生说铜像似乎激昂了一些,希望更富于人文精神一些。他说自己性格中是有容易冲动的一面,但反思过后,先生总是在文章中斯斯文文地讲道理,先生说自己内在的本质、最至高的追求是——人文精神。
2008年4月8日
今天一早,先生就不开心,说学馆进展太慢,希望尽快把东西都集中到华东师大。但华师大有难处,主要是档案馆的态度不配合,需要先生自己发话,档案馆只能要什么再复制什么。又不便和先生明说。
2008年4月9日
张济顺来电,她已和殷一璀通了电话,表示要做工作尽快把学馆建起来。其实她们都很尽心尽力。殷一璀让华师大尽快拟一个文件,她会作批示,再召集华师大和档案局、上海图书馆三家一起开个协调会,明确要求把资料集中到华师大。
她说,其实学馆还未建,不利的传闻已经很多,说先生是个很超脱的学者,为什么人还在就要建纪念馆。还说某某有自己的目的,想当馆长。还说,现在建名人纪念馆要报中央批准等等。她们也是有不小的阻力。
张济顺真是除了对先生的敬仰,还有深深的爱戴之情!她们说一定加快进度。
先生口授了几个意见,希望把自己捐给档案馆的全部照片、信函、日记、笔记、光盘,都集中到华东师大王元化学馆,供展出研究之用。他在意见书上签了名。晚上收到林同奇来信。
2008年5月6日
昨天先生还清醒,说话也清楚。一早文忠到,后曼青也到了。
今天上午也还清醒,只是脸肿得可怕。医生说癌症的脑转移已经很严重了。
先生希望知道病情发展的真实情况,让他有所准备。他一再强调,他不希望抢救,不希望拖太久。
看着先生,很难过,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他还是关心学馆的事,特地叫来晓明(胡晓明),重申了要选晓明在他的《当代思想史的脚注》中的几句话,说是要刻在学馆的石碑上。
2008年5月7日
今天上午华东师大在医院召开了学馆建设的规划讨论。
讨论认为,学馆应当具备学术交流、学术研究功能、从长远发展,应当建立王元化学术研究基金、设立一个学术成果奖。
由对外联络发展处承担前期建设。
明天下午姜樑要召开上海图书馆、档案馆、华东师大三家的协调会。
会议认为,学馆不应该纯粹是展览馆,先生研究的领域较多,留下很多研究方向,可以供后人继续研究,也应该可以招收研究生。先生是个通人,不同的学科都有所涉及,因此教學科研可以整合。光是陈列就比较消极了。先生应当不仅是被瞻仰,师大领导要考虑,学馆不是陈列馆,不仅仅是供参观。先生对21世纪的贡献很少有人可以相比。
会议认为,第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王元化基金会,成立有力的筹款小组。建立王元化学术奖,打通文史哲的学术奖。要有筹款计划,有营销人才,根据财力来展开工作。
会议认为,体制可以虚实结合。
功能应当有基金会、教育功能、学术研究功能,培养人才功能,教授可以全球范围内聘请等等。
学馆的建立正在紧锣密鼓地和死神赛跑。
2008年5月8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居然还记得,一去就祝我“Happy birthday!”
丁丁、小李来,童世骏也来,但是先生已经不太能说话了。他示意要丁丁坐在他的床头,拉着丁丁的手说:“他是远道来看我的。”先生吃力地叮嘱我要带丁丁、小李上楼去吃饭,记在先生的账上。离开病房时,小李泣不成声。
我贴着先生的耳朵,告诉他学馆开会的情况。
洪森也来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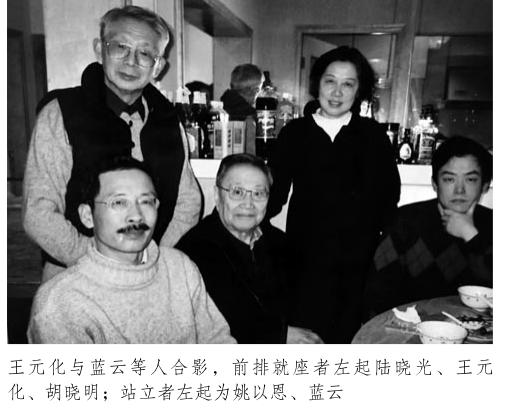
2008年5月9日
一早,先生的脸肿得更厉害了,吸氧气的管子在脸上勒出了深深的印子。手脚都肿了,但是仍然需要挂针。先生说话更加含糊不清,昏迷的时间也更加长久了。依稀能听明白的还是,学馆的外文译著,一定要放译者的相片,还有他们简单的小传。
晚上,晚饭后不久,小周从医院打来电话:“大姑(先生的护工都这么称呼我),爷爷走了,刚刚走的 。”我丢下手中的一切,直奔瑞金医院,同时,给先生的朋友和学生打电话,我赶到医院,先生安卧在病床上,睡着一般,但是,先生不再会醒来了,先生的苦难也结束了!很多朋友也匆匆赶来,赶不到的也纷纷来电话哀悼先生逝世。
大家抚着病床,把先生送到太平间,不能再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别了,生活里将再无我的先生,可是,对于我,先生在我的生命中永在。
责任编辑 周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