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杜维善先生成为忘年交
2019-12-10董存发
董存发
《杜维善口述历史》(以下简称“口述历史”)终于定稿,自2009年第一次见到杜维善夫妇(以下简称杜先生、杜太太),到现在已经八个多年头了。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很辛苦,但也乐在其中。定期当面拜访杜先生,就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把上一次的记录整理稿交上,求教不明白之处,聆听记录新的内容,还需查阅其他资料佐证、对照。如此反复,虽然单调,但扎扎实实,日积月累,集腋成裘。
以杜月笙、孟小冬为题材的传奇故事、逸闻趣事,历来都是电影电视经久不衰的主题,更不必说网络时代,各种新媒体批量粘贴复制、网络群发。虽然有些是历史事实、论述正确的,但是,很多是以讹传讹、博人眼球。而杜先生的口述历史则是杜家唯一健在的公子遵从“亲见、亲闻、亲为”的原则,忠实地讲述并记录了其父、其母、兄弟姐妹,在那个特殊时期、特定环境、特定区域的特别故事。杜先生对全部书稿逐字逐句修改审定,书中的照片95%以上都是杜先生的珍藏,而且是第一次对外发布。读者通过阅读杜先生口述的历史事件和传奇故事,穿越时空,亲临闻名遐迩的十里洋场不夜城,再现杜家在旧上海滩的风光,了解那一代人的平凡与杰出,寂寞与辉煌,功过与是非。
我與杜先生的缘分
我最早认识杜先生夫妇,是在2009年冬季。那一年,温哥华是暖冬,我们从冰天雪地的北京登机,在温暖如春的温哥华国际机场落地。机场里,小桥流水和原住民装饰,恍惚是走在了大自然的丛林里;机场外,灿烂的阳光照在脸上,暖融融、湿润润的;最惊奇的是,远处耸立着白皑皑的雪山,而近处满地的绿草格外抢眼,我试着用手抓了抓,是真的!真的草!我对我的幼稚行为,也感到好笑。
然而,见到杜先生夫妇,的确是让我如沐春风。之前,我的朋友沈辰博士曾有过提示,但第一次见面,我还是被杜先生他那酷似其父的外貌惊到了。在我的记忆深处,怎么也离不开海上闻人杜月笙的形象,那些传说的故事,深深地影响了我。而眼前的杜先生,身材修长,着中式夹袄,面带微笑,却有一丝丝威严,俨然是一位和蔼的学者。杜太太,出身名门,衣着典雅端庄,略施粉黛,一切都恰到好处,俨然就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大家闺秀的再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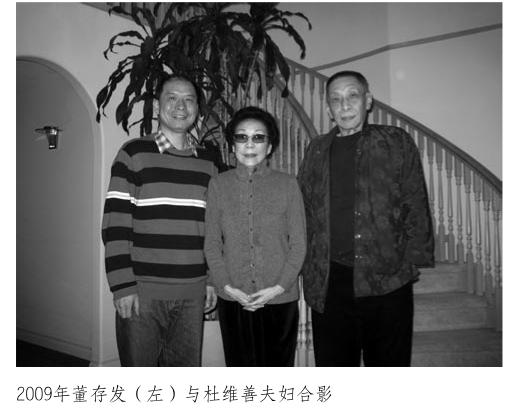
随着与杜先生往来增多,我深深地感受到,他没有丝毫帮会老大的公子哥儿气息,反而是一位温文尔雅、思维敏捷的学者。直觉告诉我,我与这位忘年的学者一定有缘。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本科学习历史,工作后进修金融,获得MBA硕士学位。后者是我职业时间最长、物质积累阶段,这能让我安心写作,粗茶淡饭,不必挂虑稻粱;而前者,却是我的志趣所在。所以,在异国他乡,我谢绝了金融界的美差,决然地坐冷板凳爬格子,执着于自己的乐趣。2010年夏季,我们全家移居温哥华。从此,我就有更多的机会拜访杜先生,慢慢形成了规律,每隔一两周就一定去一次杜先生家,听他讲老上海的故事和他的古钱币收藏。就这样,我们渐渐地成了忘年之交。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杜先生的生日公历是1933年12月16日,真是太巧了!我的生日也是12月16日,只是晚了30年,这就是缘分吧!
格物致知,禅意不尽
听杜先生讲古今中外的故事,很是惬意;然而,要严肃地记录整理杜先生的口述历史,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杜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知识十分渊博,谈话中,他不经意就引出古今中外的名人行家和诗词典故,我常常是一头雾水。杜先生就告诉我说,别着急!先把心定下来,才可以开始做事。就这样,我开始写毛笔字,把浮躁的心平静下来,系统地阅读了杜先生推荐的有关那个时代的各种书籍文献,了解背景知识和历史人物,以及坊间各种对他父母和家族的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说法,逐渐地可以理解并记录杜先生讲的杜家在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旧事。
杜先生从小就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经史子集的传统文化,根植在他的骨子里;而几十年西方科学的教育和职业历练,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事业和学术生涯。杜先生收藏和研究古今中外钱币,包括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在中国古钱币研究上,无论是半两钱,还是五铢钱、开元钱,他尽可能地收集到每一种版别,积累尽可能充分的实物资料,然后对每一枚钱币都认真地做测量、称重、断代、特征描述,书写好每一个标签;同时,借鉴最新考古发掘资料,运用西方地质学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的分类、排比、对照的扎实考证研究。所以,他研究撰写出来的文章书籍,资料丰富,说服力强。这种格物致知的治学态度,部分是来源于乾嘉学派,但又超越了传统的局限,借鉴了西学的优势。持续多年的访谈,使我切肤感受到,他不仅能够立足于丰富扎实的史料基础,同时,能够游刃有余地上升到很高的境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恰到好处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是穿越时空,意犹未尽。杜先生的这种方法,我以为是对于他父亲这样一个传奇历史人物描述的最好方法。其实,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我们这一代人似乎已经陌生了,我们太多地强调“以论带史”,甚至是为了证明某个既定的观点理论而剪裁历史事实,偏离了老一辈学者“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原则。杜先生的治学之道,让我对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有了更深的理解。
对佛教和佛学,杜先生有持久的修行和深入的研究。他接受了密宗上师施与的十几次灌顶,诵读了十万次金刚萨埵本咒。佛学的思想和境界,也体现在他的口述历史之中。本书起始于杜家祠堂,借用古人立德、立言、立行的“三不朽”,叙述了海上闻人、一代名伶和思古楼主的“德言行”。读者在这本口述历史中,不仅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亲历、亲见、亲闻的鲜活的故事,还有智慧和禅意,甚至略有神秘的传奇的深邃的意境。比如,他的老师与逝去亲人“扶乩”的心灵交流,“赶尸”“回煞”的逸闻趣事,对死亡和灵魂的独到见解。更有意思的是杜先生住院手术后,禅思冥想他的古“钱”而不知“痛”感,犹如现实版的关公“手捧《春秋》而刮骨疗伤”。
然而,在杜先生眼里,无论是当年风光一时的杜家祠堂落成,还是海上闻人、一代名伶的风采,甚至是古钱币学家的名誉,都是过眼浮云,灰飞烟灭,留下来的只有茶余饭后的谈资,评弹里的琴聲和说书人的余音,就像他最喜欢的那句偈语“禅声悟深远,微妙闻十方”余音袅袅,有味道而不绝如缕!到了几近鲐背之年的杜先生,在他的眼里,人生似梦,所谓的德言行的三不朽,似有似无,“到头一梦,万境皆空!”禅意绵绵。
三人行,我必师
这本口述历史能够最后杀青,得益于亲朋好友的众人添柴。在这个过度放大货币衡量的物质崇拜时代,从故纸堆里搜寻旧事、印刷成册,留下真实历史和传奇故事,不能不说是一种稀缺且高尚的行为,我不可忘怀心存感恩的人很多。
首先要感谢杜先生夫妇。十年一剑,付出心血最多、贡献最大的当然是杜维善先生夫妇!每次采访都会是两三个小时,持续多年。每次我来之前,杜先生就亲自准备好茶,提前泡好茶头,这样我来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斟水饮茶了。杜先生年过八旬,但是记忆力非常好,有的时候,他看我不明白,就反复解释,甚至找出多年前珍藏的资料给我参考。访谈结束,离开杜先生家,无论天气如何,他一定要站在家门口,目送我的车子离开他的视线,最后挥手道别,这么多年来,从未间断,他说,这是礼节,表示对别人的尊重。采访时,杜太太也时常会出现,往往为我们准备些茶点,偶尔也会参与进来聊上一会儿。杜太太年轻的时候,喜爱唱京戏,可以“一赶三”,也就是一个人先后客串三个角色,很不简单。杜太太喜欢读书,只看武打侠客的书,网络上流行的《鬼吹灯》《藏地密码》,还有其他鬼怪神秘的网络小说,统统喜欢。口述历史中的戏曲、武功与禅的境界部分,杜太太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有的时候,杜太太身体好,就做一大锅茶叶蛋犒劳我们,那是地道的老上海茶叶蛋的味道。我在上海读大学时,晚自习结束后,学校旁边弄堂里挑担子叫卖的茶叶蛋就是这个味道。
沈辰博士,现任加拿大皇家博物馆副馆长,他是我大学同学的研究生同学。我2010年去多伦多办公室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与杜先生有缘。他博士毕业第一次到博物馆工作时,就来温哥华杜先生家里登门拜访。二十多年后,沈博士已经在加国取得了学术和事业的大成。沈博士从书架上抽出杜先生的各种专著,让我到了温哥华一定要登门拜访杜先生,杜先生的老故事和丰富的收藏,都非常值得我访谈请教,由此,萌发了我做杜先生口述历史的想法。
书稿的最后一页终于翻过去了,脑内里挥之不去的是那些故事和传奇,犹如杜先生思古楼序中的“思古之幽情”。我特别喜欢杜先生的书房名曰“思古楼”,有心请杜先生为我的陋室书房也起个雅号。一次杜先生来到我家,看到窗外深秋的红叶落在绿绿的草地上,笼罩薄薄晨雾,随口说出“庭院静,树无鸟,满地落叶待人扫”,就叫出典于《龙文鞭影》“嘉宾赋雪,圣祖吟虹”的“赋雪楼”吧!杜先生特别喜欢雪天的空寂,落叶白雪埋浮尘,万物寂寥空茫然啊!这真是应了苏轼的境界:“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我在上海读书时种下的情结,在温哥华与杜先生夫妇成为忘年之交,捯出上海滩陈年往事,聊赋惆怅;冥冥之中,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历史还是传奇,其中的因缘,谁又能说得清呢!这正是:
思古楼里叙旧事,
赋雪楼畔记悠长。
雪泥片爪谁人识,
空谷幽兰风清扬。
2019年6月25日于温哥华赋雪楼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现任加拿大本那比市(大温哥华地区)图书馆管理委员会理事]
责任编辑 周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