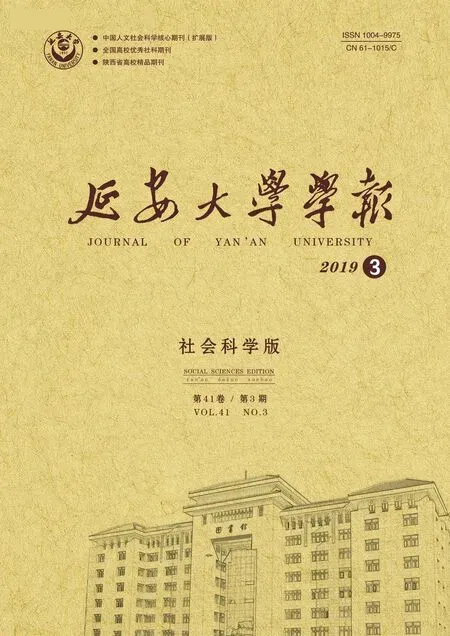李星沅主政陕西时期的社会治理举措及现实启迪
2019-12-09蒋勇军
蒋勇军
(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李星沅(1797—1851),湖南湘阴高坊(今汨罗市)人,道光进士,晚清重臣,经世致用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官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近年来,李星沅研究已引起学界较大关注,成为晚清人物史研究新的生长点。总体而言,相关学术成果不多,尤其对其社会治理涉猎较少。鉴于此,笔者运用大量一手史料,以1842—1844年为时间节点,以李星沅为考察对象,对其在陕西的社会治理举措及现实启迪进行勾稽梳理与全面剖析。
一、李星沅主政陕西时期的社会治理举措
1842—1844年,李星沅担任陕西巡抚。为了改变官场黑暗、吏治腐败、治安不靖、民风颓废的社会生态,李星沅强化社会治理,多措并举,旨在谋长远之策、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一)清查钱粮,消解财政危机:社会治理的着力点
道光以来,整个社会风气日益恶化,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国库亏空,钱粮拖欠现象十分严重。地处西北边陲的陕西也不例外。面临严峻的财政形势,清查钱粮便成为当务之急。
李星沅担任陕西巡抚期间,碰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仓库的钱粮极端混乱状况,官吏贪污成风,钱粮长期拖欠、账目不清、库存不多,亏欠现象十分严重。修补知县舒钧接任时,“查出陈椿冠任内库项,计短交道光二十三年(1843)已征未解民屯更地丁正耗及盐课等项银8240余两,又常平仓麦短少6800石,折银8160余两,共银16400两”。[1]100-101“手中有粮,办事不慌”,钱粮的多寡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是考量一个地方官有无政绩的重要标志。针对仓库钱粮亏损问题,李星沅决定亲自过问,清查钱粮。为此,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制定了详实具体的清查制度。其内容包括:遇新旧库存交代,必须按款核算,认真盘收;延期不清交者,立即据实揭报;防范含混过关,逃脱惩罚。“严饬各属,凡遇新旧交代,必须按款核算,认真盘收。如有延不清交,立即据实揭报,不准稍涉含混,以凭惩究。”[1]100-101二是严惩贪官污吏。据凤邠道崇纶、凤翔府知府汤宽秘密禀报,眉县知县陈椿冠经管仓库,发现有亏挪情弊,李星沅饬令彻底追查,冻结其资产,务令照例在规定限期内催缴。“应即饬提亲属丁胥人等来省,严切究追,照例勒限催缴。此外有无不实不尽,一并彻底根究,断不容敷衍了事,以清帑项而儆官邪。除将该故员寓所资财委员严密查封,其原籍家产,飞咨江西抚臣,饬令新城县迅速查抄估变,咨陕备抵处。”[1]100-101三是规定陕省每年库存钱粮清查的具体操作程序。“令将每年上下忙应征钱粮,除留支外,实应解司银数,分别正课,杂项依限造册详报。”对防范官员暗渡陈仓、腾借挪用起了一定的作用。四是派员明察暗防,查清库存钱粮实数。据布政使陶廷杰详称,“查得陕省各属,道光二十二年(1842)分额征民屯更起存并粮折银,除屯丁兑食及存留外,实应解司银1331439两,内除上忙已完银887878两,未完银443560两,今下忙续完银437118两,仍未完银6442两。又原额盐课银8980两,今下忙续完银4378两,仍未完银2310两。又带征道光二十一年(1841)原未完缓征起运银5978两,今下忙续征通完,又带征道光十六年(1836)原未完缓征起运银465两”。[2]40道光时期,陕西省钱粮亏欠如此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清代各级官员薪俸微薄,办公费用甚少,无法维系正常的开支;其次,每遇灾荒之年,官府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辗转挪垫,以致亏损;再次,清朝统治黑暗,阶级矛盾尖锐,灾荒频仍、兵连祸结,政府开支浩大,甚至寅吃卯粮,发生赤字;最后,清朝吏治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侵吞公款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弊政。
经过李星沅的大力整顿,陕西的赋税征收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带征(道光)二十一年(1841)未完缓征地丁银5978两,截止(道光)二十二年(1842)奏销止,已十分全完,造入(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拨册内报拨讫等情,具详前来。臣逐细覆核无异。除将未完缓征银两俟届期另行催解,并咨明户部外,所有应征新赋银两十分全完”。[2]65-66另外,勒令其子孙代赔之举措,也追回了部分侵吞及挪用的钱粮。“王承武将伊故父王松年罚赔银6800两先交3000两,馀银3800两现在设措续交;初庆彲将伊故祖初彭龄罚培银3000两,刘喜海将伊故父刘镮之罚赔银9000两代完银两全数解库。”[1]107
可见,李星沅在清查钱粮问题上不遗余力,他从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具体措施三个层面来完成对陕西钱粮的清查工作。李星沅竭尽全力清查钱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对腐败官员产生了一定的震慑力,对社会道德的滑坡亦也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对陕西财政收入的好转亦有促进作用。但清查钱粮作为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一项临渴掘井措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晚清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列强厚颜无耻的敲诈勒索、官吏敲骨吸髓般的无限盘剥、天灾人祸的无情袭击,使苦不堪言的老百姓无力承受越发沉重的苛捐杂税,致使拖欠赋税钱粮的数目与时俱增。加之,晚清吏治黑暗,为挪用库存钱粮,不少官员变本加厉、费尽心血、玩尽花样,致使库存钱粮亏损日趋严重。
(二)惩治盗匪,维系社会治安:社会治理的关键点
盗匪作为社会的一种异质力量,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的产物。它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威提出了严重挑战。道光年间,灾荒频仍、战乱连年,百姓生计艰难,致使弱者转为沟壑,强者沦为盗匪。“饥馑之年,天下必乱;丰收之岁,四海承平。”[3]盗匪肆虐,严重地威胁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这是社会失序、经济萧条、战乱频仍的结果。缉拿盗匪、除暴安良是巡抚的重要职责。“奸匪一日不靖,善良一日不安。”[1]112-113李星沅将剿灭盗匪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重要手段。他在陕西担任巡抚期间特别注意地方治安,在险要之地添兵设卡,尽力收缴民间兵器,缴拿盗匪。由于盗匪成分复杂,形态各异,对其一味加以镇压,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为此,李星沅为肃清陕西盗匪主要采取以下四项策略:
1.探访配合。顾名思义,就是侦探与暗访相互配合。所谓“侦探”,也叫侦察,指暗中观察和调查盗匪头目的数量、枪支情况、战马匹数、骚扰方式、占据村庄情况、四面通达大路或小路条数、山水阻隔情况、来往人数及姓名等。若知悉盗匪头目的姓名,还必须弄清其为匪时间、平日言行举止情况以及其家人和亲友情况,避免上当受骗,中盗匪圈套。为此,李星沅派得力人员四处侦探,以寻觅盗匪的踪迹、活动范围、人数等,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发现了其活动的踪迹。“至北山延、榆、绥一带,与四川、甘肃、山西诸省犬牙相错、岩径阻深,向多无业游民借佃种觅工接踵而来。如所称塘匠班子之类良莠莫辨、去留无常、昼伏宵行、此拿彼窜,每有劫杀重案。”[1]112-113可见,实施侦探、摸清匪情,是制定征剿方略、剿灭盗匪的前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必须慎重处理。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给征剿盗匪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进而加大征剿的难度。所谓“访”,指暗中访问调查,是与侦探相配合的一项措施,两者配合使用可相得益彰。李星沅在派得力人员进行侦探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派得力人员进行暗中访查、化妆潜伏取证,以便相互对照、调查匪情之真伪,以免误入圈套。如派吴应刚“奉委出省,自备资斧,设法踩访将及一年,较寻常获盗倍加劳贳”。[4]150-151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做到百战不殆。李星沅采取探访配合的方式,虚虚实实、假假真真,既能迷惑敌人,又能弄清匪情,为其科学决策、彻底歼灭盗匪奠定了基础。
2.搜察并施。“搜”指的是官府在征剿过程中对狼狈逃窜、去向不明的零散盗匪进行搜查。成群结队的大股盗匪被打得七零八散之后,流落至各个村落,以致踪迹难觅。对这些零散的盗匪,不能派遣大规模的军队加以征剿,且他们与村民混杂在一起颇具隐蔽性,实难对付。因此,李星沅认为,要充分发挥地方基层组织的作用,进行搜查摸底。其内容主要包括:搜查盗匪的联络之处;严格缉查来往人员;由乡村基层管理人员负责监督;偏远村墟,招募雇工监督;一旦发生劫案,立即予以核查。“臣复谆饬地方官,于城乡庄堡联络之处,仍令保正、甲长、牌头遇有前项人等,随时于十家牌书写姓名数目,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若户口畸零,村墟偏远,难以概立保甲者,则令地主招佃雇工时,先查明来历,引进担保,详载一簿。某处犯事,即就此簿核查。”[1]112-113“察”就是指对主动检举或被访问的平民百姓进行跟踪管理,对其恩威并施,并密切关注其动向,若发现与盗匪暗中勾结,隐瞒事实真相,或与盗匪狼狈为奸、寻衅闹事、劫掠讹索,可就地正法、从重法办、依法治罪。若发现他们并没有说慌,则是与探访情况相吻合,实事求是,则予以褒奖。“于工匠中择一二人,协同察访。果能侦缉得实,官为量给赏资。如敢徇隐窝盗,亦即随案提究。”[1]112-113可见,搜察并施是针对盗匪飘忽不定、踪迹难觅的情况对症下药,实行“靶向治疗”。一方面在关隘之处对过往行人进行核查,另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双管齐下,使盗匪无处躲藏,进而暴露于官府面前,达到一举歼灭、一网打尽的目的。
3.奖惩结合。奖惩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惯用的一种手段,是引领和强化社会成员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李星沅认为,要迅速彻底地剿灭盗匪,关键在于人才。“窃惟安民以弭盗为先,弭盗以得人为亟。”[4]150-151而要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形成良序竞争的社会氛围,必须通过奖惩制度来实现。他认为:只有赏功罚过、奖能罚庸、奖勤罚懒,才能使玩忽懈怠之官员产生畏惧感,使其循规蹈矩向优秀者看齐,进而奋起直追,促使其守法遵纪、恪尽职守、争取立功、为国效劳。同时,也要做到赏罚分明,该奖则奖、该罚则罚,大功大奖、小功小奖、大过大罚、小过小罚,使下级信服以增强内聚力。“钦遵叠檄文武,明定赏罚,申严保甲成式,认真妥实办理”“惟以赏功罚过,明示要约。其不甚得力者,必不肯稍为姑息;其较为出力者,必不忍没其微劳”。[4]150-151在征剿盗匪的过程中,李星沅对工作诚恳、办事认真、功勋卓越的官员实施奖励、予以表彰、请求给予提拔。如“略阳县县丞吴应刚,前经委赴豫省南阳府一带,踩缉蓝田县民赵合盛被劫案内逃盗,旋据拿获罪应斩决盗犯冯麻子、王举2名,罪应发遣盗犯屈发源、鲁洸明2名。又通判衔岐山县知县李文翰,首先拿获叠劫甘肃徽县事放张耀、宝鸡县事主冶忠孝家衣服,轮奸事主冶席氏案内罪应斩枭盗犯张发荣即萧老么,罪应斩决盗犯汪广子2名,并迭劫凤县事主赵尹氏等家、罪应斩决伙盗张添才,罪应发遣伙盗李转太2名;又前任泾阳县知县、升补陇州知州马国翰,拿获伙劫中部县事主焦士义家、轮奸焦赵氏案内罪应斩枭盗犯刘欣原即刘裁缝1名,均属缉捕勤能,认真出力。”[4]150-151由于李星沅赏罚分明,雷厉风行、言出必行,剿匪行动进展顺利。“地方官交相儆惕,自顾考成,缉捕渐收成效。”[4]150-151
4.剿抚并用。针对盗匪出没的规律及与周围的关系,李星沅制定了剿抚并用的正确策略。所谓“剿”就是剿灭,即在官府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准备工作就绪、面对悍匪恶盗的情势下主动出击,予以歼灭之。“内有穷凶渠盗、著名刀匪,或轮奸妇女,或拒捕伤差,均各就案确审照律究办。即罪止系杆枷杖,而所犯情事强横,亦必从重惩治,以消其桀骜之气,而生其畏惮之心。”[4]150-151可见,在李星沅看来,“剿灭”主要是针对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且不愿意投诚的匪徒实行剿灭政策。他认为要剿灭负隅顽抗的悍匪,一方面要调兵遣将,四面设卡拦截,防范盗匪逃窜;另一方面要集中优势兵力,长期埋伏,以逸待劳,出动奇兵,断其退位,挫其锐气,彻底歼灭之。所谓的“抚”指安抚、劝抚,即对经过规劝悔改的盗匪要给予妥善地安置,对他们多疑善变的性格特点,要有足够的耐心,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李星沅认为要剿灭北山盗匪,也要采取劝抚的对策,“尚知讲求捕务,黾勉小心,诚能以劝继惩,可期日有起色”。综上所述,李星沅的剿抚兼用策略,是以剿灭盗匪为宗旨,以安抚盗匪为路径,安抚是为剿灭服务的。李星沅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来剿灭盗匪是必要的、是切实可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从策略的层面来讲,在对盗匪征剿时,以抚为辅是颇为必要的。当盗匪力量强大时,不能将其一网打尽时,对其应施之以抚,既能达到分化盗匪,破坏其凝聚力,又能使匪患得以缓和。当盗匪内部发生内讧,力量削弱时,或集中优势兵力征剿负隅顽抗、不知忏悔者;或向其广施安抚烟幕,以高官、金钱为诱饵,诱使其投诚,然后杀之,可有效地分散其力量。二是盗匪主观上有接受招抚之动机,希冀投诚后能实现飞黄腾达的美好愿景,可减少兴师动众去征剿的成本,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以招编为幌子,可达到谫除之目的。四是以匪制匪。利用土匪内部各种矛盾,乘人之危,为己谋利,以便各个击破。五是派出心腹,进行现身说法,促使其臣服,使之为朝廷效劳。李星沅认为要彻底剿灭盗匪,必须整合民众力量,充分发动民众,与官府合作,做到官民一心,才能铲除民害。“禁暴安良,诚为地方之要务”“首严缉捕盗匪,以除民害”。[1]112-113鉴于盗匪往往选择州、县交界区域作为窝点,加之州、县之间相互推诿造成盗匪屡缉不获,无功而返。基于此,李星沅认为,要迅速谫除盗匪,必须与邻州县官吏沟通,争取各方力量紧密配合、协同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盗匪。“并咨会邻省不分畛域,一律兜拿,务期害去民安,勉循训示,不敢稍涉疏懈。”[1]112-113
由于征剿策略切实可行,加之又做到了“官民一心”“上下一致”“邻境一体”,因此,李星沅在剿灭盗匪的过程中所向披靡,势如破竹,颇有斩获。“拿获刀匪46名,窃劫等犯47名,逃军、逃流182名,统计275名。”[1]112-113“自4月至今,除命案凶犯不计外,复据先后报获强劫、轮奸、抢窃、拒捕、问拟斩绞遣军流徒各犯121名,军流逃犯及刀匪163名”。[1]112-113可见,要想取得剿匪的彻底胜利,既要讲究策略,又要注重心理攻势,双管齐下。
(三)赈济灾民,纾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的突破点
1843年6—7月,陕西滨临汉江及沿河各州县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雨连绵、房屋倒塌、河堤冲决、牲畜淹毙,嗷嗷待哺之声不绝于耳,真是惨不忍睹。“惟沔县、褒城、洋县3处被水较重,查沔县武候祠等32村庄,冲塌民房4170余间,淹毙男女大小94名口,城垣庙宇、武职衙署、兵房、驿路等项间亦被淹;褒城打钟坝等21村庄,冲塌民房1950馀间,淹毙男女大小14名口,栈道亦多冲坏;洋县胥水铺等63村庄,冲塌民房6090馀间,淹毙男女大小137名口。”[5]79足见被灾面积之广、财产损失之大、死亡人数之众。水灾阴影未弭,雹灾又趁机降临。1843年7月底,神木、府谷、北山等州县又连续三天罹遭冰雹,农业损失甚大,真可谓雪上加霜。“葭州前后圪葭州前后圪涝会等23村庄,田禾被雹较重,时交秋令,补种不及。”[5]81-82
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李星沅心急如焚。一方面亲自查赈勘灾,另一方面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筹措赈灾资金,实施赈济。
1.赈前准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施赈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方可有备无患,确保赈灾有条不紊。
(1)亲自勘灾查赈,了解灾情实况。为了弄清灾情实况,李星沅亲赴灾区勘灾查赈,核实灾民被灾程度、确定成灾分数,核实灾民户口,划分受灾等级,查清有无漏报、慌报情况,弄清被灾人口。1843年闰7月,李星沅亲赴沔县等被水较重的灾区,“臣查沔县、褒城、洋县均背倚南山,近逼汉水,又有山涧溪河参错,其间地势本极陡隘,兹以江河并涨,猝不及防,闾阎致遭水患荡析,情形殊堪悯恻”。[5]79此外,被水被雹的地方,“查得佛坪、留坝、宁羌、西乡、南郑、城固、陇州七厅州县被淹无几……所有勘明沔县等处被水较重”。[5]79总之,李星沅亲赴灾区勘灾查赈,掌握了灾区的第一手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官员弄虚作假、浮报冒领等情事的发生,为科学施赈提供了实际数据,为赈粮与赈款分配标准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标准,为确定成灾分数、蠲免钱粮提供了依据,确保了施赈有据可依。但赈灾贵在神速,勘灾查赈程序颇为复杂,级级上报、层层审批,拖延时日,影响救灾效果。
(2)动员官绅捐输,筹措赈灾资金。赈灾需要充足的资金作后盾,否则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了。为了消弭社会矛盾赈济灾民,巩固封建统治,李星沅鉴于藩库空虚、财政枯竭的实际情况,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捐输,为赈灾筹措资金。为了调动官绅捐赠的积极性,李星沅依朝廷规制,根据他们捐赠钱粮数量的多寡给予相应的爵位和功名。“士民捐银200两者给予九品顶戴,300~400两以上者给予八品顶戴;又现任官捐银500两以上者,纪录2次;1000两者加一级;1000两以上者以此核计”。[5]91在李星沅振臂一呼的感召下,一些怀着扶危济困、博济众施、祛灾祈福思想的官僚与士绅纷纷慷慨捐输,藉以救济灾民。如“地方偶被水灾,即各捐资助恤,共拯穷黎,实为义举,自应量予奖励。除捐银不及议叙者,由本省办理外,所有捐银1170两之南郑县知县朱清标,1120两之褒城县知县候国璋,820两之前署沔县知县陆华封,720两之城固县知县李炜,500两之洋县知县宫尔锡,同捐银520两之洋县民人吴成德,400两之捐职从九品衔张守业,300两之洋县文童李树勋、武童金鳞、金甲,城固县文童王正全、陈书山,民人龙自耀、陈振廷、赖容照,并200两之洋县文童姚文瑞,城固县文童陈师孔”。[1]125-126
地方官员与开明士绅量力捐输,一方面为赈灾筹集了一些资金,可缓解灾民的燃眉之急,消弭灾民的仇富心理;另一方面,官僚与士绅通过踊跃捐输可获得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大善人美名,为今后升迁或扶摇直上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筹码,同时也可排解民众对官府的不满情绪。
2.施赈举措
(1)发放银两。顾名思义,指官府以发放货币的方式来赈济灾民。这种施赈方式便于灾民直接购买灾后所需的各种物资,弥补交通不便所导致的赈粮不足的缺憾。因此,当地方遭遇水旱灾荒时,官府往往会根据灾情的轻重缓急、被灾地区的交通情况等客观因素合理分配赈款,以期节约赈源、扩大救济范围。救灾贵在及时,为了迅速赈济灾民,李星沅敕令“沔县需银3092两,褒城需银1982两,洋县需银5209两等情,禀请筹款给发,并据藩司请于该府库存备急项下就近先行借用”。[5]79为了确保银两发放及时到位,李星沅“严饬各员将现在酌发银两,认真散放,务令实惠及民,俾得及早修盖,无致一夫失所”。[5]79可见,发放银两这种措施在灾荒之际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可以根据灾荒的实际情况及当地灾民的实际需要采购必备的救灾物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交通不便所导致的赈粮不足的缺憾。
(2)蠲缓赋税。自然灾害的发生,总会给灾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损失。逢到水旱灾害,田亩减产以至绝收,土地所有者难以照常向政府缴纳赋税,在这种情况下,官府会考虑向灾民蠲缓赋税。为了抚恤被灾较重的灾民,稳定民心,李星沅请求朝廷基于灾情的严重情况,蠲缓被灾程度深的灾民的赋税。“所有应完下忙地丁银粮,恳请全缓。又该州寺子川等18村庄,及神木县北草湾沟等21村庄间被雹伤,收成未免歉薄,恳将下忙地丁银粮概行酌缓一半”[5]81-82;“所有榆林、怀远、神木、府谷4县,道光十三年(1843)起至二十二年(1842)止,民欠缓征地丁争粮草束,以及该4县并葭州道光十一年(1841)起至本年止,节年出易常社仓谷、出借折色籽种口粮银两,均请展缓。”[5]91李星沅请求朝廷蠲缓被灾严重的老百姓的赋税,暂时解决了百姓的负担,使其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为重建家园创造了条件。
(3)掩埋尸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为了防范瘟疫的滋生蔓延,李星沅下令将死亡灾黎的尸体予以掩埋,“当经各县饬即捞尸掩埋。”[5]79使被掩毙的245名灾民得以妥善安葬,防止暴尸荒野,以告死者在天之灵。
(4)施放赈粮。为了赈济嗷嗷待哺的灾民,李星沅饬令“捐廉散给贫民口食”。[5]79向灾民发放的粮食、谷物等救济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黎遇灾之时的困难处境,能够直接解决灾民的温饱问题,使灾民从灾荒的痛苦之中暂时解脱出来,摆脱生活的阴影,为灾后重建提供了保障。
(5)收容灾民。水灾造成数万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为防范灾民聚众闹事、劫掠财物、威胁地方治安。李星沅饬兵“搭盖席棚暂资栖止”[5]79,使灾民得以暂时安置,避免风餐露宿之苦。
综上所述,灾荒发生后,李星沅身体力行,亲赴灾区,及时勘灾查赈,广泛动员官僚、士绅捐输,确保赈前准备工作井然有序。实施赈济时,他根据灾情,统筹规划,实行了一些以发放银两、施放赈粮、收容灾民、蠲缓赋税为主要内容的急赈措施和采取了一些以掩埋尸体为主要手段的善后处置措施,使嗷嗷待哺的灾民能够得到及时赈济,使流离失所的灾民能够得到妥善安置,在解决民生疾苦方面发挥了扶危济困的作用,体现了人文关怀,具有人道主义的色彩,有利于凝聚民心。但这些措施只能救急,不能救穷,治标而不治本、“输血”而非“造血”。总体而言,由于时代局限,李星沅的赈灾措施属于传统救济范式,还不具备现代化因素,是权宜之计。加之,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财政短绌,赈济经费捉襟见肘,不可能使灾民从根本上摆脱进退维谷的处境。因此,仅仅靠施赈钱粮、安置灾民、蠲缓赋税是远远不够的。
(四)严禁邪说,纯化社会风气:社会治理的支撑点
宗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一种颠倒虚幻的反映,它是麻醉人们的精神鸦片。“宗教不但可以在变化无常的生活环境中给人以心理的支撑和精神的慰藉,使人归附到现行社会的目标上,为之提供认同因素,而且还可以通过维护社会控制,强化现行社会价值和目标提供克服罪恶感和异化的手段,来加强社会的团结与稳定。”[6]可见,宗教具有宣泄压抑、寄托安慰、规范控制的功能。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统治黑暗、灾荒频发,广大农民被迫辗转迁徙、颠沛流离,迫切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以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加之我国长期闭关锁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导致科技落后、迷信盛行,客观上为神道邪说的传布提供了温床,助其潜滋暗长。一些邪教组织趁机兴风作浪,四处活动,进行宗教迷信活动。1845年,龙华会传教士李一原、邓三谟、张利贞、苟喜云、谷善修、黄三、固上一、张清江、何春成、刘升、赵玉清等人在陕西汉中府、南郑县一带以传教为名,一方面广泛开展傩愿、算命卜卦、看相摸骨、做道场、打醮、看风水、招魂、迎神等迷信活动,散布谣言、蛊惑民众、骗取钱财;另一方面宣传和销售《推背图》《东明律》《九莲宝赞》《托天神图》《风轮经》《无上妙品》《普度条规》等书,“即事近妖邪,实属人中鬼蜮”“假称兵火,妄托鬼神,以劫难之危词,遂煽诱之私计,诚为人心所同嫉,即为国法所难容”。[7]不难看出,李一原、邓三谟等人散布神教邪说,实为妖言惑众、收徒敛财、伤风败俗。为了切断谣言的传播,防范社会危机事件的爆发,李星沅果断决策、主动出击,严厉打击神教邪说。经过周密的部署和缜密的安排,奉旨饬令“均应根穷明确,密咨速拿,以期除恶务尽”。[8]1821843年3月,在咸宁县事准升鄜州知州潘政举、长安县知县张钱、南郑县知县朱清标等人的协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之下,李星沅终于肃清了在陕西各地的神教组织。“张利贞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煸惑人心,拟斩立决;邓小谟、萧刚捏造灾难邪言,分途煸诱,拟斩监候;固上一、谢泳先、康汰生、顾品良、周导亨、王尚俭、苟喜云、谷善修依一切左道异端煽惑或人民,拟判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妈,各照例刺字。”[8]182
由此可见,必须将宗教管控纳入权力控制的必要补充手段来加以规范控制,若善加利用,加以规范引导,使其走上国家预先设计的轨道上来,屈从于天命、天理、国法和家规以及一切传统权威,则能发挥静心抑欲、谨小慎微、忍忿制怒的功能,达到稳定社会的目标;若被一些图谋不轨、不怀好意之人利用,则成为蛊惑人心、伤风败俗、散布谣言、迷惑群众、引发动荡的暴乱工具。李星沅从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大清统治的立场出发针对神教邪说,将其视为异端,通过采取焚烧其书籍、禁绝其言论、追捕其教徒、破坏其组织等手段来加以取缔,以图净其根株,使民众望而生畏、戒而远之,以达到纯洁社会风气、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李星沅在陕西的社会治理举措,构架了一个互联互促、同向发力的“四位一体”框架体系。具体言之,清查钱粮,消解财政危机,夯实社会治理之“基”;惩治盗匪,维系社会治安,筑牢社会治理之“网”;赈济灾民,化解社会矛盾,拓展社会治理之“路”;严禁邪说,纯化社会风气,熔铸社会治理之“魂”。
二、李星沅主政陕西时期社会治理的现实启迪
知古鉴今,以史资政。综观李星沅在陕西的社会治理,归纳起来,主要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四个层面的现实启迪:
(一)完善奖惩制度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策
奖惩制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的应有之策,历来被统治阶级视为治国驭人的重要权柄。晚清以来,奖惩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弊端丛生,尤其在当时政治黑暗、道德沦丧的社会语境下,更成为加速清王朝官僚统治集团贪污腐化的“助产婆”。在君临天下的人治社会环境里,统治阶级和官员的意志往往是奖惩制度推行的决定因素。加之,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使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奖惩制度失去了生存空间,反而成为社会治理不公平的渊薮。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要加强社会治理,必须不断完善奖惩制度,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赏罚不公、奖赏资格不明、奖惩过多过滥等问题,努力做到赏罚分明、赏罚适度、赏罚及时、奖罚合理。
(二)健全考核制度是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考核制度草创于秦朝,成熟于隋唐,发展于明清。长期以来,它是封建王朝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和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依据。晚清以来,考核制度逐渐趋于程式化,掺杂着颇多的人为因素,因此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运作程序繁杂、条款繁多,逐渐走向程式化,考核等级亦日益形式化,出现了名不符实的情况,甚至沦为官僚士大夫结交权贵、拉帮结派的一种工具,致使考核随意性加强。考核官员或出于封建权贵的咄咄逼人,或出于人际关系的通盘考虑,缺乏严格的评议标准与监督机制,漏洞百出,给投机取巧的封建官员留下了诸多空子,导致这一制度形同虚设。因此,只有健全考核制度,才能调动官员和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发挥其社会利器的功能,提高社会治理效果。
(三)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
利益表达机制是广大民众追求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社会成员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的正当行为。然而,受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地方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社会宣泄渠道缺失,利益表达机制不畅,致使隐瞒下情、掩盖矛盾、填塞言路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足为奇。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身试法者亦不乏其人。道光时期,陕西省盗匪活动猖狂、屡屡犯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表达。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导致不满情绪日积月累,产生负帕累托效应,引发土匪与民众的冲突。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确保民众表达渠道的畅通无阻,才能促进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进而增强社会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达到善治的目标。
(四)构架信息披露机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提
信息披露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提。然而在信息技术相当落后、交通极为不便的道光时期,神教邪说到处泛滥、迷信盛行、谣言四起,为害甚巨。正如徐绍孟所言,“迷信能剥削贫民的金钱,能毒害人们的身家,以杀一人,能害一家,能灭亡一个国家。”[9]正因为当时清王朝没有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政府与民众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致使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趁机兴风作浪、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混淆视听,进而使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终日惊魂不定,惶惶不知所措,感到极度焦虑、恐惧和无奈,影响社会稳定,引起社会动荡。可见,政府只有构架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始终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开诚布公、实事求是、毫无隐瞒地将掌握的信息及时对外发布,力求报道客观、准确、全面,努力做到冷热有度。唯如此,政府才能抢占话语主导权、占领舆论制高点、赢得舆论主动权,进而澄清事实真相、消除社会误解,借助舆论以正视听,为社会治理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