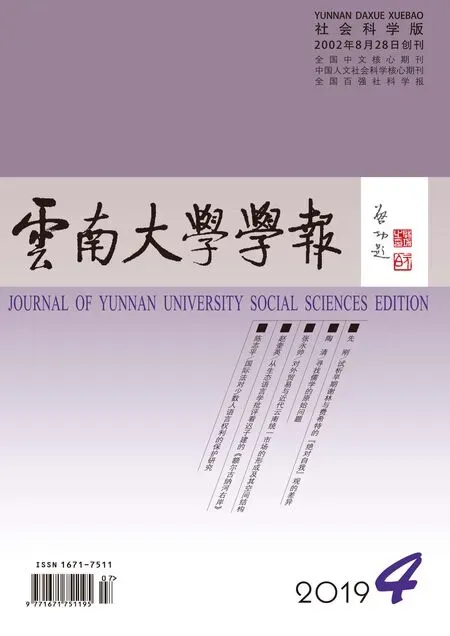谢林前期哲学的悲剧理论
2019-12-08姜学斌
姜学斌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神话以及悲剧艺术作品等是谢林悲剧理论的直接来源。在同一哲学的基本框架下,经过先验唯心论体系的积淀和艺术哲学的系统性阐发,前期谢林哲学中的悲剧理论得以完整呈现,这一理论既是对悲剧艺术形式做出的哲学表达,也是以艺术手段对同一性问题展开的独特论证。因此,谢林的悲剧理论兼有艺术与哲学双重本质。
一、“早期唯心论时期”的悲剧思想萌芽
谢林的早期唯心论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他改造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费希特的知识学,赋予哲学更多的客观性,谢林以自然哲学登上哲学舞台并初步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受斯宾诺莎实体论影响,谢林的自然哲学突破了费希特“自我设定非我”的限定,把客观之物作为第一位的东西,使主观的东西归附于它,从而客观的自然界获得了精神的意义。所以,在自然哲学体系中,自然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精神”,内在意识与外在自然的统一为客观的自然界能够实际地存在于观念之外提供了可能性。
自然哲学充分表现出客观事物的重要性以及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相互关系,但在谢林看来,自然哲学并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内容,主观之物作为第一位的东西并使客观的东西从其中产生的问题,必须要上升到先验的、绝对的层面才能得到解决,谢林由此转入先验哲学研究。在这一时期,谢林的悲剧思考来源于先验唯心论体系中对历史概念的探索,他把客观、无意识的自然力量对人类主观、有意识行为的干预作为悲剧产生的根源,将自由与必然、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的矛盾从历史性延伸到悲剧艺术的形而上学问题。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影响深远,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美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经典概念。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注]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3页。谢林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悲剧理论传统,试图将人类自由的创造性活动通过悲剧艺术表达出来。
按照谢林的观点,人的一切选择、抗争或努力等都是主观上有意识的活动,或者说是人进行的有目的性的行动,这种活动的本质就是自由,它是不能独立于主体之外而发生作用的内在精神。与之相反,必然性是一种客观的、无意识的活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非人力所能控制。但必然性并不是指一般性的自然规律或单纯的客观原则,它的最高根据同样源自观念世界,处于绝对中的必然性与自由是统一且不可区分的整体,确切地说,必然性是先验领域内绝对者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一种隐秘的、人类无法认知和把握的神力。
自由并非现成的东西,它产生于自我意识的活动,其生成过程受到一定条件的束缚,这种制约条件同时又是自由实现自身的必要保障,谢林将之称为历史中的“普遍的法制状态”。在普遍的法制状态下才会存在真正的自由,否则所谓的“自由”都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现象,因而自由本身和限制条件互为前提,是不可区分的统一体。由此来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自由产生出限制自身的东西。谢林指出,唯有自由内在包含着必然性,“自由应该是必然,必然应该是自由”,[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5页。才能把这个矛盾统一起来,使自由从本身产生出自我限制的普遍的法制状态,从而实现自身。普遍的法制状态的实质就是必然性,它不是偶然的、外在性质的产物,而是来自于自由本身,并成为与自由相对立的无意识的东西。
必然性作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干预人的自由活动,导致了自由与必然的直接斗争,这一斗争正是悲剧产生的先决条件,“全部悲剧艺术都是以隐蔽的必然性对人类自由的这种干预为基础的”。[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75页。所以,悲剧艺术呈现了人类处于客观神秘之力干预下的自由的创造活动,客观的、无意识的必然性强行参与到主观的、有意识的活动中,这种观点也就是谢林关于悲剧生成的“干预说”。干预说把悲剧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过程,显然带有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印记。
从表面上看,悲剧中出现的偶发事件或灾难、困境影响着悲剧主人公有意识的活动,但问题在于,外部环境的偶然性因素无法成为支配人类自由行动的决定力量,换言之,悲剧主人公不幸的根源与他所遇到的困难、坎坷没有根本联系,他的全部遭遇只是隐蔽的绝对必然性显现自身的形式,“这种必然性有时称为命运,有时称为天意,但不管是命运也罢,或天意也罢,都不会被设想为某种明显的东西”。[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75页。悲剧主人公的所有经历都是必然性预设的灾厄,它与任何主体意愿或主观性的东西无关,主人公的自由活动不得不面对这种客观的、无意识的“命运”,他的自由活动最终走向意识活动之外的结果。这就说明,必然性渗透到悲剧主人公的自由行动中,他的悲惨结局也因此成为命中注定的事。
这样一来,人的一切自由活动都处在命运的干预之下,尽管悲剧主人公本身所具有的自由本质始终指引他自主的做出判断或付诸行动,然而命运实际地操控着这些自由的活动;处在必然性干涉下的抉择或行为,又确实是因主人公内在的自由精神而发生。行动的结果并非取决于主人公的主观意愿,反之,这个结果与目的性、意识活动相悖,它是由必然性造成的。因此,主人公的悲剧性在于,所有遭受的厄难既是命运使然,同时又是其自由活动的结果。从自由和必然的绝对本质以及人的主体性来说,必然性是作用在人自身之内、隐蔽地藏匿于自由之中的先在,归根结底,悲剧性产生的根源应归咎于人本身,或者说是基于人的自由活动。
青年时代的谢林着力于构建以“绝对同一”为核心的同一哲学体系。自然哲学首先把客观自然与主观精神初步统一起来,先验哲学则充分地阐释了关于绝对、同一性的认识,但谢林指出,无论自然哲学还是先验哲学都不能替代同一哲学体系的全部,它们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谢林把绝对同一作为一切哲学的前提,“除了绝对的立场之外,不存在任何哲学”,[注]Schelling:Presentation of My System of Philosophy(1801),Trans. Michael G. Vater. The Philosphical Forum,2001(32),p.350.它是统一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最根本方式。“绝对同一是唯一的、不受自身之外条件限制的最高本原”,[注]Schelling:Presentation of My System of Philosophy(1801),p.351.一切事物最终都要在这里找到根据。悲剧的本质以及其中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等问题,在同一哲学时期的艺术哲学内得到进一步阐发。
二、艺术哲学的悲剧构拟
随着同一哲学体系的建立,谢林的艺术哲学也逐渐完备。在早期唯心论时期,艺术哲学作为先验唯心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综合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键环节;“绝对同一”理论成熟之后,谢林在同一哲学体系的架构中丰富了艺术哲学的内涵,使之全面、完整、系统化地展现出来。按照同一性问题的基本原则,谢林在艺术哲学中进一步完善了悲剧理论。
谢林将艺术世界分为现实序列和理念序列,前者是以雕塑为最高形态的造型艺术,后者则是以诗歌为最高形态的语言艺术。自古希腊以来,诗歌基本可以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其中抒情诗和叙事诗是诗歌最初的两种对立形式,抒情诗的自由属性注重表达主观上的“心灵萌动”,叙事诗则更倾向于表现一种纯粹的客观必然性。戏剧是诗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是抒情诗和叙事诗的综合。戏剧是诗歌最完满的艺术类型,能够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描述、自由与必然性的对立统一起来。自由与必然的矛盾状态,不是单方面突显主观上的自由或者客观上的必然,也不是要强调两者当中由谁来占主导地位,而是使它们作为互相联系、彼此均衡的力量存在。谢林据此对戏剧进行了定义:“只可能有一种描述;在这种描述中,所描述者是客观的,犹如在叙事之作中,而主体则处于情感萌动中,犹如在抒情诗中。这也正是这样一种描述:情节并非呈现于叙述,而是呈现于现实中(主观者被描述为客观的)。由此可见,我们所设定的体裁,应成为整个诗歌的最后的综合,——这便是戏剧。”[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369页。
戏剧包括悲剧、喜剧和近代戏剧三个类别,喜剧以悲剧为基础,并以构建与悲剧相反的要素而形成自身;近代戏剧是自由和必然混合、悲剧和喜剧穿插的状态,即所谓“混糅”的戏剧形式;与其他两种戏剧形式相比,悲剧是戏剧最基本的形式,完全展示出了戏剧的全部特征和内涵,甚至在谢林那里“索性将戏剧直截了当地解释为悲剧”。[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70页。这就要求悲剧的构拟应当符合戏剧的本质,明确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构拟悲剧的首要任务。
谢林早期唯心论时期的悲剧思想中已经表明,自由代表着一种有意识的、主观上要求达成某种目的的活动,必然则恰好相反,它是一种无意识的客观存在,悲剧就产生于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其中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必然呈现为客体,自由则呈现为主体”。[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89页。这种对立无法依靠经验性或偶然性的东西建立起来,需要到更高层面中去寻找根据。就此而言,一切偶然事件的背后都是绝对的必然在发生作用,“悲剧中绝不可能有偶然事件的地位”。[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76页。尽管悲剧的剧情发展线索和转折需要通过偶然事件表现出来,但这些事件背后表露出的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它引导悲剧主人公在非主观意愿的情况下犯错,由主人公做出看似自由的选择和行为实际都受到命运操控;随着情节不断推进,必然性才会逐渐展现出来,只要深入到与悲剧人物相关的事态发展本身,就能够发现偶然之中深藏的绝对必然。
总而言之,悲剧主人公的经历,即使因偶然因素产生了促进剧情发展、渲染悲情气氛的积极效果,但它并不是悲剧的真正成分,而是必然性用以隐藏自身的表象,其实质是超经验、非偶然的命运之力在情节中外化自身的一种方式。因此,悲剧所呈现出的自由与必然的真正对立只能发生在绝对中,“这一对立成为艺术的基础,必然在其中居于优胜地位者,因而成为艺术的最高表现,而自由并未处于从属地位;反之,自由居于优胜地位,而必然并未成为被战胜者”。[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67页。也就是说,自由与必然的斗争在绝对中又表现为最高的和谐,双方最高的对立同时也是最高的统一。
完整的悲剧正是立足于自由与必然的绝对同一本质而进行的内在构拟,其中涉及悲剧的对象、情节与合唱等基本要素。谢林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对象的论断,悲剧既不是要表现从善之人或作恶之人从顺境转入逆境,也不是要表现坏人从逆境转为顺境;作为承担悲剧命运的主体,悲剧的对象既非品质高尚的道德者,又非本性卑劣的罪恶者,而是鉴于其悲剧性而让人产生怜悯和恐惧之感的普通人。因此,真正悲剧对象的自身属性应当介于善与恶、道德与非道德之间:“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第97页。古希腊神话中塑造了诸多典型的悲剧英雄,比如著名的俄狄浦斯王,从其悲剧性可以看出,主人公在厄运来临之前可以享有幸福的生活和备受尊崇的身份地位,他所承受的厄运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善或恶所致,只是由于意外因素而过失犯错的结果。古希腊神话中的这种意外因素往往受制于“神谕”的安排,它在剧情中被描述为悲剧主人公无法违背的天意,而主人公自觉与之抗争的精神便来自于自由本质。尽管被命运驾驭,但主人公的自由精神与必然命运的斗争结果却并非是必然战胜了自由,而是二者同时成为胜利者,又同时成为失败者,“自由与必然的争衡,确实只是发生于必然战胜意志、而自由在其自身领域居于优胜地位之时”。[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73页。
悲剧对象身上所表现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使他在各方面均展示出了绝对的品质,情节的构拟必须以这样的悲剧对象为立脚点进行整体构思,“无论外在的质料如何,情节始终应来自主人公本身”。[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78页。悲剧情节的整体性构思和连续性特征把隐蔽的自由与必然揭示出来,并将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在人物和剧情中相结合。一方面,情节的整体构思使必然性和自由外化,必然性在一系列的客观事件中呈现出来,而悲剧主人公的绝对品质塑造了自由精神的外在形式。通过这种整体构思,一波三折的剧情始终处在稳定、完整的情节之中,悲剧主人公位于客观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他又摆脱了外在环境的支配。悲剧不是对人进行摹仿,而是摹仿人的活动和生活,因而情节的构拟不能局限于对单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或对人物行为的简单叙述,“情节不仅应外在地完成,而且应该内在地完成于心灵之中,因为内心的愤懑正是悲剧之所在。惟有在这一内在的调和中,始可产生结局所不可或缺的和谐”。[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81页。另一方面,不间断的情节在剧情中构建起内在的统一性,直接关系着外部事件和内心情感相结合的整体结构。情节的构拟展现了悲剧剧情的连贯性,而情节自身的完善则在于表现悲剧的最终结局,即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本质;情节的不间断不仅指时间上的连续,更重要的是情节本身的内在统一。在连贯的完整情节中,主人公的命运与事件的发展结果息息相关,其间一切外在偶然性最终被完全摈除,借助于对情节的直观,从观众的情绪上引发心灵的思考,使客观情节在主观意识中发生作用,观众与剧情之间实现更深层的交流,客观剧情和主观情感完满地融合于悲剧。
悲剧也包括一些看似无关紧要却又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古希腊悲剧的合唱就是这种要素的主要代表,它与主人公及剧情紧密相关,通过“摈除周围环境的偶然性”[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83页。的方式在悲剧中发挥作用。合唱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的思想从悲剧中脱离出来,渗透到观众的情感之中,引起观众与剧情的共鸣。合唱队从表现形式来看似乎外在于悲剧,但它与纯粹外在的观众不同,观众可以因剧情触发正义的情感或对主人公的怜悯之心等,而合唱队必须以中立的态度对待一切情节,它不能对剧情产生任何情感倾向,也不能干扰到人物的表现和悲剧性的发展,更不能参与到具体情节影响悲剧主人公的主要地位。谢林认为,合唱队是悲剧整体性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合唱的参与使悲剧摒弃了粗俗的情感取向,直接表达出人物真实的情感和情节完整的内涵,实现了艺术的象征意义。因此,谢林给予合唱极高的评价:悲剧的合唱“乃是至高无上的技巧之最佳的和最激动人心的创举”。[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82页。合唱对悲剧情节的发展具有多种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使伴随情节的反思客观化和人格化”,[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83页。它为人物和情节建立了紧密的关联性,把表面不相关的东西以及跌宕起伏的观众情绪、感受融入悲剧整体。合唱队由多人构成却从整体上表现如一人,以一个完整的象征性个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转变成一种外在的客观性并赋予人格特征,借此来缓解剧情中的恐惧、悲痛等震撼效果。合唱把观众的精力从单个情节转向悲剧总体,引起观众对悲剧的“沉静的直观”,使主观情感与悲剧的客观情节交融在一起。所以,合唱队不是剧情的辅助环节或者作为“置身于剧中的观众”,而是“在悲剧中赋之以真正的(即幻想的)必然性”。[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83页。
在同一哲学时期,谢林艺术哲学的悲剧构拟是从哲学范畴对艺术本质进行的阐释,悲剧由此成为艺术理念世界的最高形式之象征,这种诗歌的艺术作为表达绝对同一性本质必不可少的环节,参与到哲学体系的构建中。诗歌的艺术形式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本身所展现出的时代精神,从根本上说是哲学和艺术之间的同一性。就此而言,谢林通过悲剧理论表明了一种哲学与诗歌的关系:哲学并不是和诗歌完全分开的,它们最初结合在一起,具有共同的本原,甚至哲学本身就是诗歌;两者因自身的内容不断丰富,并逐步具体化、实在化而发生分裂,但随着诗歌的发展,它又开始与哲学联结起来,“从整个近代的趋势来看,哲学和诗正在走向相互交融”。[注]谢林:《论哲学视角下的但丁》,载于《学术研究方法论》,先刚译,第63页。在谢林那里,哲学始终是最根本性的东西,作为哲学构建的基本方式,悲剧艺术必然是哲学本质的映现。
三、悲剧理论的哲学本质
谢林前期哲学的悲剧理论以同一哲学体系为根本出发点,因而悲剧必须服务于同一性本质。进一步说,悲剧以艺术特有的方式呈现出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除此之外,在二者绝对同一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种历史哲学。
在谢林看来,艺术哲学所构拟的艺术,“始而并非作为艺术的艺术,作为既定特殊的对象的艺术,而是艺术形象的宇宙”。[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上),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21-22页。谢林追求的并不是感官刺激、肉眼可见的普遍艺术,而是一种作为思辨科学的“神性艺术”,“需要以艺术的哲学构建为前提”。[注]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5页。这种艺术从自身的绝对性出发成为“诸神的工具”,“它把神性的奥秘颁布出来,把理念、无遮蔽的美揭示出来”,[注]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第246页。只有经验之外的理智直观才能把握;一般而言的普通艺术是只具备实在性的东西,而“神性艺术”本身却是完全绝对的,当它处于与哲学的关系中时才会表现出实在性,并且“只有艺术才是哲学之真正的、完满的客观化”。[注]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第170页。悲剧必然要符合“神性艺术”的整体本质,把艺术与哲学两种属性综合起来,“悲剧的实质在于主体中的自由与客观者的必然之实际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局,并不是此方或彼方被战胜,而是两方既成为战胜者,又成为被战胜者——即完全的不可区分”。[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71页。简而言之,悲剧的本质是自由与必然绝对的同一,谢林的悲剧理论实际上是要表达二者同一性关系的悲剧哲学。
以此为前提,悲剧艺术的首要任务和最终使命是将自由与必然在绝对中的同一性呈现出来。绝对本身包含着无限者与有限者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关系不会使彼此彻底分离,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矛盾达到最高对立的同时,也实现了二者的最高统一,即在绝对中同一。有限者与无限者的对立内化为悲剧中客观的必然性与主观的自由之间的冲突,悲剧就从双方的对立中产生出来。必然性不是如病痛、财产损失、旅途挫折等依靠人的智慧或身体条件就能够克服的现实困难,“仅仅外在性质的灾厄,并不能引起真正的悲剧矛盾”,[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71页。而是作为一种“隐蔽”的先验力量强加于人的自由活动,在悲剧中表现为“命运”、“天意”或者“神谕”,使悲剧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陷入必然的厄运,这时主人公一切经验性的手段都无法摆脱困境,不论做出何种选择或努力抗争,结果都事与愿违,即使“诸神”也不能给予他任何帮助,一切行动唯有依赖于主人公的自由精神,毋宁说人的自由属性只有在必然性预设的灾厄中才完全显露出来,“真正的自由只能是一种基于绝对必然性的自由”,[注]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第95页。自由在与必然的斗争中获得了自身价值。
悲剧主人公因自由精神的指引与命运进行抗争以求摆脱束缚,而必然性驾驭下的自由活动又在非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失误、犯错,应验了“神谕”的预言,最终难逃罪愆,以不幸收场。然而,悲剧的意义并不在于主人公痛苦的遭遇或者悲惨的结局,“悲剧可以借助不仅同命运,乃至同生命完全和解的情感来结束”。[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75页。悲剧一般以主人公牺牲自由、自愿接受天意的罪罚告终,由此来看,必然性取得了最高的胜利;但同时,自由精神放弃自身,接受非主观所犯之错而受到的惩罚,甚至以舍弃生命为代价来赢得绝对的自由,置身于同必然性相同的地位,从而实现了自由的最高胜利,达成同命运的和解。可见,自由与必然的斗争不存在任何战胜的一方,而是同时作为胜利者和失败者存在,这样反而在本质上实现了自由与必然性的和谐。真正的和谐并不是指对立双方的绝对平等,而是说自由和必然性既是最高的对立,又是最高的统一,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绝对中是同一个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悲剧中自由与必然的同一实际上也是谢林对绝对同一的演绎过程。自由与必然从绝对同一出发,经过双方的主客观斗争使自由受制于必然,而自由凭借主人公的自愿牺牲来显现自身的最高存在,双方的斗争最终又回到绝对的同一中。这一过程不仅营造了一种悲剧特有的艺术效果,而且使绝对者通过艺术在现实中得以映现,哲学与艺术在其中得到统一。自由与必然在悲剧中的同一性需要依附于人展现出来,“人性是揭示这一关系的唯一手段”。[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68页。谢林所指的并不是经验性、现实中的人,而是人的理念,即灵魂和身体的绝对统一体。人之本性尽显自由本能又从属于必然性,两者于此综合,“同时既是被战胜者又是战胜者,呈现于其最高的不可区分性中”。[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68页。人性的特征从悲剧主人公身上显现出来,一切所能看到的不幸,或者说主人公遇到的各种困难、灾难等,都是必然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它作为客观的、无意识的神秘力量内化于人,而自由在必然性的强力之下却仍未受制于必然,反而取得了和必然性同等的地位,进入到双方斗争的平衡状态。客观的必然性与主体自由精神的先验关联,确立了艺术中的人性价值,“人性在艺术中的最高表现之成为可能,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果敢和气魄战胜灾厄,而自由作为绝对的自由,摆脱这一使主体有毁灭之虞的斗争,——对绝对的自由说来,斗争是不存在的”。[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68-369页。
自由和必然的斗争与统一不仅把艺术的哲学本质表达出来,而且在哲学中构建了艺术之美的特性。“美乃是现实中所直观的那种自由与必然之不可区分”,[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上),第38页。真正的美是追求一种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最高平衡,因而悲剧艺术的美就植根于自由与必然的绝对同一。悲剧作品的生成过程犹如一种美的创造活动,这一过程使美成为悲剧本身的艺术属性。“一切美感创造过程都开始于对无限的矛盾的感受,所以,随着艺术作品的完成而来的感受也必定是对于这种满足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必定又会转变为艺术作品本身。”[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303页。除此之外,主人公在悲剧结局时对一切厄运的释然,使他的自由意志摆脱了必然性的左右,当遭受最深的苦难时达到最高的解脱,并调和了必然与自由的矛盾,一种发自深层的崇高心境油然而生,悲剧借此完成了对人的心灵净化,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谓艺术的“净化”功能。因而谢林指出,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在悲剧中所显现出的和谐,带给人们的“并非备受摧残,而是被治愈”。[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74页。
通过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本质,悲剧艺术参与到历史哲学的构建过程中。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的实践哲学部分探讨了关于历史的概念及其发展理论,干预说初步建立了悲剧与历史之间的哲学联系。客观的必然性无意识地干预着主体的自由活动,“这种干预不仅是悲剧艺术的前提,而且也是人的创造和行动的前提”。[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75页。正因如此,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人类总体来说,全部创造活动都会受到必然性的制约,一切活动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目的性,历史的生成过程内在地包含着自由和必然两个对立的要素,人类在创造活动中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追求,从而推动历史持续向前发展。然而,“历史既不能与绝对的规律性相容,也不能与绝对的自由相容”,[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69页。历史本身包含着无限的进步,它以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为前提。历史的发展需要遵从一定规律,但却不是完全被限定在规律性之中,它需要一种“任性”的力量突破规律性的限定——“任性是历史的女神”,[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70页。而“任性”的活动又必须在规律原则之内进行。也就是说,任性与规律的统一性创造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历史,“历史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表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并且只有这种统一才使历史成为可能”,[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74页。这种统一性是历史生成、进步的根据。就此而言,历史与悲剧具有共同的本质,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冲突,不仅是悲剧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动力之源,即历史演进的关键所在。
以自由与必然的绝对同一为基础,谢林的艺术哲学通过艺术的构拟过程把悲剧与历史统一起来。在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三种诗歌艺术形态中,抒情诗是主观类型的艺术,富于主观性并产生于主体,叙事诗具有现实的客观性,在于对行为进行“绝对地或客观地观察”,[注]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第318页。这种被观察的行为就是历史。戏剧把抒情诗的主观性和叙事诗的客观性综合起来,因而戏剧本身也包含着历史性,其中悲剧就以史诗的形式体现出历史的特征。“历史学风格的最初原型是一种处于其原初形态的史诗,以及悲剧。”[注]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第206页。
历史的根本任务是记录事实,艺术可以使历史更接近真实,从而实现历史追求真相的最终目标。历史的阐述方式可以通过戏剧的特征表现出来:“这种阐述和戏剧中对于行为的解释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一部戏剧中,虽然个别行为必须发源于先前的行为,到最后一切东西都必须发源于必然性的最初综合,但行为的顺序本身却不能以经验的方式,而是只能借助事物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秩序而得到理解把握。”[注]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第203页。换言之,必然性在悲剧中借助于经验的、偶然的东西显现出来;以此相同,历史中的经验性成为必然性展示自身的工具。历史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叙事,而艺术作用于历史后,使它脱离了纯粹客观的现实世界达到观念世界,艺术作为一种参与机制,从现实性原则之外为历史寻找先验可能性。“在这样一种阐述中,历史必定会具有一部最伟大和最令人震撼的戏剧的效果,而这部戏剧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精神创作出来。”[注]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第203页。
从某种角度说,历史学和艺术可以在本质上等同起来,“艺术呈现出来的东西,始终是必然性和自由的一种同一性,而这个现象,尤其是悲剧中的这个现象,是我们真正为之感到惊叹的对象。这种同一性同时也是哲学看待历史的立场。”[注]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第204页。悲剧艺术中表现出的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也就是哲学中的历史观念,历史学家需要从悲剧出发寻找历史研究的灵感。在历史学家那里,“悲剧乃是伟大理念和崇高思维方式的真正源泉,他必须接受其陶冶。”[注]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第206页。
四、结 语
谢林前期哲学的悲剧理论是对同一哲学的艺术表达,自由和必然的同一性本质使悲剧在艺术与哲学、艺术与历史之间搭建起桥梁,艺术哲学则以悲剧理论为切入点对同一哲学体系进行论证。可以说,谢林前期哲学中的悲剧理论是带有鲜明艺术气息的哲学。另外,谢林的悲剧理论也启示了其他哲学家的美学思想。黑格尔哲学的美学体系中有很多成分直接来源于谢林,他同样把“史诗原则和抒情诗原则的统一”规定为戏剧的基本原则,[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 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3页。并进一步深化了悲剧的哲学内涵,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美学思想中都可以寻得谢林悲剧哲学的踪迹。与此同时,谢林悲剧理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哲学领域,而且深刻影响了许多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他们通过悲剧将艺术的哲学本质引入到戏剧艺术的创造过程中,使戏剧艺术作品呈现出一种哲学意味,从哲学反思的层面增强戏剧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