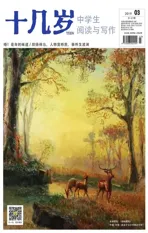同一个年,不同的味
2019-11-26李卓麦田格创始人
文/李卓(麦田格创始人)
梁实秋是不喜欢过年的,不过是“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拜年的时候“要叩头如捣蒜”,我反而觉得正新鲜;鲁迅这么新派的人物应该不喜欢过旧历年,他写的《过年》也显得有些冷淡,不过倒符合他一向高冷的气质;张爱玲笔下的年不是发生在上海,亦不是讲究繁复的大户人家,带着一双新鲜的眼睛瞧着农村的年味,倒比她平素写的文章来得可爱有趣;丰子恺这么有趣贪吃的老头,记忆中的年味盈满了各类饭食的香气。老舍的年是纯正地道的老北京味,钟寺、庙会、盏灯……那么远,那么近。相比之下,我们的年味儿或许平淡了,我们的文笔更是追赶不上,但也愿意趁着这个机会,来说一说四个不同年代人心中的年。
70后:年味是打扬尘和玩鞭炮 讲述人:夏丽鸿(1975年生)
又快过年了。少时说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平静得如一泓湖水,微风不起,波澜不惊。而今再来看这句话,总免不了心底掀起万丈狂澜,汹涌澎湃,心绪难平。匆匆而过的那些关于年的记忆,此刻如循环播放的幻灯片,一一浮现在眼前。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闹一宿。”小时候,临近年关,大人会反复叮嘱一系列注意事项,哪一天做什么,是要按顺序来的。我们把扫房子叫做“打扬尘”,到了那一天,全家出动,把扫把绑在竹竿上,将屋顶的蜘蛛网扫掉。有因此迷了眼睛的,也有蜘蛛掉在手上吓得大叫的,可不管怎样,所有的小孩子都会兴致勃勃地参加,因为如果表现得好,过年可以拥有更多的鞭炮。
鞭炮之所以获得小孩子的青睐,是因为它在守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守岁便要熬通宵,小孩们会把一百响的鞭炮拆成一个一个的,放在口袋里,鼓鼓的,心里就踏实了。年三十的晚上,小孩子们喜欢这样度过守岁的夜晚。后来小孩子才知道,其实大人早已睡去,并没有守岁。小孩子守岁,也许是大人们给予他们一年一次的放纵吧。
80后:年味是堆雪人和新衣新鞋讲述人:李卓(1985年生)
盼望着,盼望着,寒假来了,过年也快来了。
那时我们的寒假,还没有课外培训,没有大彩电,没有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喜欢看的电视剧也只在固定的时间放两集,耽误不了我们“放野”的时间。所以,很快一个村子差不多大的孩子就聚齐了。
堆一个大大的雪人是必须做的事情了,贴两块磨圆的煤炭,就是水汪汪的眼睛,找不到红萝卜,就用一个细长的红薯做鼻子,模样也算惟妙惟肖。打雪仗也是必须要的。风一样的孩子,就用深深浅浅的脚印和银铃般动听的笑声在雪白的世界里诠释童年的意义。从村口到山里,从田野到河边,那么放肆,那么自由,想必连飞过的小鸟也是羡慕的。倘若河面有冰,胆子大的孩子敢“蹭蹭蹭”跑到对岸,狠狠摔一跤也不会哭,只是哈哈大笑,爬起来继续踉踉跄跄地跑。等到了晚上,会有大孩子一家一家把小伙伴叫出来,大家带着自己的烟花聚在一个大坪里,什么冲天炮、彩珠筒,什么小陀螺、火树银花,你才放完,他又点燃一个。那样的夜晚真是迷人。烟花易逝,可孩子们还有无需成本的玩意儿,如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便携式的“小火炉”——一个空的小油漆桶,用钉子将底部钉许多小孔,像一个小筛子。放上几块烧红的木炭,再加一些木炭,就成一个小火炉了。将它在空中抡将起来,风灌进去,木炭熊熊燃烧起来,就能看到一个个红色的火圈。暖极了,快乐极了。
除了有一群小伙伴在一起野,更重要的是有新衣服穿,有新鞋子穿,有一定压岁钱可以买一些自己钟爱的小玩具。三毛在一篇散文中写过,那种偶然才得的喜悦,是不同凡响的。因为不能常穿新衣服,也盼了好久有一双白色的波鞋,所以除夕夜洗澡换新衣新鞋时,才觉得如此满足。
准90后:年味是归途讲述人:黄其(1989年生)
在那交通不方便的年代,年味是那浓浓的汽油味,是车厢里散不开的闷热和化不开的人味,更是过年回家这种急切、期盼的心情。
我自小便在湘潭读书。那是距离老家醴陵90公里的一座小城。这个距离,从那时的交通运力来看,往返是不方便的。即使如此,每逢节假日,妈妈仍会带着我和妹妹大包小包地去追赶中巴车,摇摇晃晃三个小时,回家过节。即使像元旦这样的三天假期,我们也不嫌麻烦地折腾。过年自不必说,义无反顾地加入春运返乡大军。
中巴车已算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即使如此,取暖基本靠抖。车身极轻,路况不佳,坐在车里摇摇晃晃,一刻不停。那时的我是晕车的,妈妈总是会提前给我备好话梅、老姜,上车后找好靠近车窗的位置,但下车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吐,排山倒海地吐。吐完,立刻生龙活虎,欢欣鼓舞。那时的我,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对回家这件事情心生恐惧和厌恶。是啊,小孩子哪里会计较这些事情。
坐中巴车也是一件极其“惊险”的事。我们需要先坐中巴车在株洲市区转乘,车子一到站,一群揽客的壮汉们便会将车团团围住,高声叫喊着。妈妈背着行李,牵着我和妹妹下车,立刻就被人群冲散,妈妈手中的行李也被人夺了过去,妈妈紧紧跟上,并回头确认我们也跟了上来。那人跑到另一辆中巴车前停了下来,把行李交给妈妈,叮嘱我们坐上去,又离开转身用同样的“伎俩”再去招徕别的乘客。而我们三个仍是惊魂未定,气喘不停。周身的鸣笛声,叫喊声,追赶声不绝于耳,至今仍然回响。我一直没想明白,从来没人问过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总是能准确无误地把我们带到正确的那辆车上?
年复一年地锻炼,我不再晕车,还喜欢上了汽油的独特香味。不过,后来中巴车渐渐淡出,家里也有了车,不再需要大包小包地挤车,回家变得方便许多。只是,我没享受太久这种方便。
90后:年味是清欢讲述人:喻涛(1994年生)
我的年是在新疆过的,记忆中新疆的年,一直是十分冷清的。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条小巷里,巷子不深,十几户人家,一多半是少数民族,还有汉族,大家已彼此熟悉,平时都很热闹。但一到过年,大部分玩伴就会在大人的带领下坐火车回老家去过年,他们有陕西的、河南的、湖南的,还有四川的……所以整条巷子只有几家门前会贴对联,贴“福”字,而更多的门前,则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因为习俗不同,还有的一些少数民族人家是不过春节的,所以记忆中小巷的年味,就是仅剩的几户人家撑起来的。
留下来过年的几户人家在这一天似乎会更加亲密,常常在大年三十晚上,互相送一份自家最拿手的菜,记得父亲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卤牛肉,切成一片一片的,十分有嚼劲。而邻居家最拿手的就是包子,有一年过年送了我家十五个羊肉白菜馅的包子,一直吃到了元宵节。对面的锡伯族奶奶家最拿手的是熏马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饭就是大人们聊天看电视,小孩子放烟花的时间。我总是要在放烟花之前,把小巷里其他的少数民族玩伴全部喊出来,我们一起看着我放出的烟花,划破宁静的夜空,他们总会觉得十分有趣,因为他们过年是不放这些的。我会带着他们走街串巷,一起用手中的擦炮去炸雪,一起在马路上滑冰,一直快到十二点才回家。十二点刚过,父亲就会在小巷里放一长串鞭炮,宣告着新年来了。城市的上空也会被烟花点亮,密密麻麻,十分好看。
我还记得那年的夜空,但如今,我已搬离了小巷,过年能吃到的东西也更加丰富多彩。仿佛一切都在改变,但不变的,依然是在那冷清中飘扬的年味,虽然细小,却十分浓稠。
00后:年味是在约翰内斯堡抢红包讲述人:黄熙茹(2007年)
2009 至2014 这六年,我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过的年。
那几年的年,在我小小的年纪里,过得热烈,珍贵而又年味十足。
爸爸的公司举办一个集体年。来自不同城市的家庭就因“年”的呼应行走到一块,有湖北人、四川人、山东人,当然北上广深一个也没落下,想想那画面,就好比一锅红红火火的“大杂烩”,也好比一幅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大拼图”。
在那一天,大家会早早包下一个中国老板经营的火锅大厅,大厅里必定会挂着红红的灯笼,循环播放着那几首吉祥喜庆的歌,水汽蒸腾的热浪里,大家一桌桌围绕开来。涮肉片,煮丸子,烫青菜,喝红酒,谈收获,分喜悦,展未来,送祝福……年味在热浪里弥漫开来,大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不知谁吆喝一嗓子,“群里有人发大红包了”,属于我们娃娃们的“武林大会”大爆发。人手一台手机,眼睛死死地盯住屏幕,手不断地触点屏幕,要知道这可是娃娃们的私房钱,不用上缴啊,来年在同学面前炫富的资本全指望这一茬丰收与否。当然我们的口号:“一分也是爱,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其实我还蛮羡慕以前的孩子拿压岁钱是拿现金,那沉甸甸的红包压在枕头底下,梦也是香甜的吧。
年代不同,经历不同,岁月留给我们的年味也自然不同。而在这些不同中,我们看见了时代飞速前进的步伐,也许70 年代出生的他,不曾想到,也不可能想到,40 年后的今天的我们的年味里已没有了对于新衣新鞋的期待,那刺鼻而又难忘的汽油味,已不曾多闻。我们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有了平板,甚至最惊喜的红包已不是压在枕头底下,而是在那虚虚实实的屏幕上。
我们也看到,年味并未淡去。从70 年代他们一直传递到00 年代的他们。这里的每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回忆那些年我们一起堆雪人,一起玩鞭炮,一起抢红包的背后,是回忆当初那个感情细腻而又容易满足的笨小孩,淡去的不是年味,而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
鲁迅在回忆当初儿时尝到的蔬果时,也曾发出类似的感叹:“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