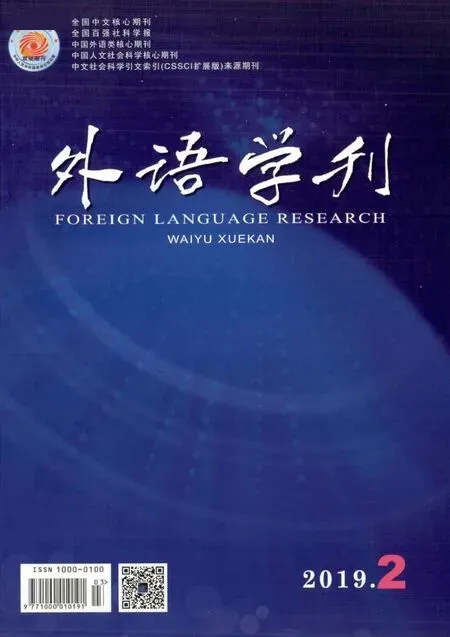溯源翻译研究:翻译过程研究的新范式*
2019-11-26陶源
陶 源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710062)
提 要:本文对溯源翻译研究进行综述,指出溯源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溯源批评主义;剖析溯源与翻译的天然联系,认为溯源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译文初稿形成之前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译者翻译策略的历时研究”和“译者手稿的顺序”。原文、译者和文本外诸因素的结合使溯源翻译研究进一步深入。在理论层面上,溯源翻译研究的发展面临着溯源与翻译的融合问题;在技术层面上,面临着手稿收集的困境,但翻译研究重要性的凸显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溯源研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引言
翻译过程作为翻译研究对象之一,一直受到关注。关联理论、顺应理论对翻译过程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陶源 2014),而认知翻译学以实证的优势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主流方法(王一方 2018)。溯源翻译研究源起于文学翻译,是一种以溯源批评主义(critique génétique/genetic cri-tics/critique)为基础、以“手稿追源”(manuscript genetics)的方法对译文进行分析的翻译过程研究(Deppman et al. 2004)。它不仅探究翻译文本自身的发展轨迹,而且追溯其美学和文学价值。近年来,溯源翻译研究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悄然产生,并呈旺盛发展趋势。它旨在通过研究译者的手稿、草稿、信件、札记等探究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并以此管窥翻译文本的来源、进化和发展。本文在介绍溯源翻译研究理论背景的基础上,论述该范式的研究内容,并探究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指明其研究前景,希望能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2 溯源翻译研究的理论背景
溯源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来自溯源批评主义。后者是一种文本分析的研究流派,旨在研究文本的形成过程,单语文本的溯源研究以前文本为核心,前文本指“作品形成之前的文本”(De Biasi 2000:30-31)。双语文本溯源翻译研究的核心是翻译前文本,翻译前文本主要包括译者手稿和其它表达译者思想的书面证据。根据译者手稿,我们可以对最终的翻译产品进行批评性分析,并分析翻译文本产生的过程。因为译者手稿中留有明显的“翻译活动的痕迹”(Munday 2013:134)。译者的信件、笔记、札记等是另一种形式的前文本,它们对翻译过程重构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溯源批评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当时的文本分析处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型期。后结构主义认为,共时语境和文本间关系的不断变化影响文本的稳定性。据此,溯源主义开始质疑已出版文本的权威性,并认为已出版文本只不过是文本形成过程连续体上的一个环节(Barthes 1971,Bellemin-No⊇l 1972)。根据溯源批评主义的观点,翻译活动是一个译作与原作者的思想、感情不断接近的过程。学者们通过“遗传记录”(dossier génétique)勾勒出翻译文本形成的不同阶段。“遗传记录”分为译者的翻译准备工作和翻译前文本(Ferrer 2010)。翻译准备工作可以细分为“外源性追溯材料”(exogenetic),即文本外的信息资料,如译者的笔记、文章、图片和书籍等,与“内生性追溯材料”(endogenetic),如手稿、草稿、校对稿等(Debray-Genette 1979),其中手稿是最重要的追溯材料。如果说英—美文本分析是通过手稿重构翻译文本(Greetham 1994),那么溯源批评主义则聚焦文本形成过程的分类、分析和图示及对文本形成过程各阶段的解读。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文本溯源的方法开始用于翻译手稿的调查和研究中(Bourjea 1995, Paret Passos 2002, Romanelli 2013,Scott 2006)。溯源翻译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两点:(1)初期旨在“揭示创作过程的复杂性”,并强调“译者也是创作者”(Stallaert 2014:370),即探究“翻译是再现还是创作”的问题;(2)描写作用于翻译过程的因素,重构翻译文本出现的各个阶段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Munday 2012, 2013)。Munday指出,“结合研究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调查”的追溯式方法拓宽描写译学的范畴(Munday 2013:134)。溯源翻译研究中译者手稿的描写对于调查翻译过程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译者手稿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临时性产品,它可以使研究者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文学翻译过程的核心,并为翻译选择机制的研究提供书面证据”(同上:126)。
根据溯源批评主义的观点,虽然译文的复杂程度低于原文,但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是针对不同语境采取相应策略的结果。虽然以溯源批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溯源翻译研究还只是一个新兴的方向,但它对探究译者能动性和创造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以溯源的方法研究翻译手稿直至译文是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范式。
3 溯源翻译研究的内容、步骤及进展
3.1 内容
溯源范式下的翻译研究者认为,翻译研究的注意力应放在对翻译过程的描写上,翻译在本质上是一个文本演变的过程。翻译手稿和某些文本外信息展现译者思考和选择的过程,通过资料和译者手稿的查阅,学者们能详细了解翻译文本在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作用。以溯源的方法研究翻译,学者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译文初稿形成之前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2)历时来看,译者手稿的修订是语言的要求还是出于翻译策略的考虑;(3)从初稿到终稿,手稿的顺序。即初期和后期的译稿分别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些变化反映出译者怎样的心理过程。根据研究主体的不同,溯源翻译研究又可以分为自译和他译研究,二者的客观性有所不同。
3.11 初稿形成前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
溯源批评主义视域下的译者心理过程研究不同于以往的翻译认知研究,它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不仅关注译文从初稿到出版的译者心理,而且对初稿形成前的译者心理进行定性、定量研究。Pijuan Vallverdú研究Manuel de Pedrolo翻译的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1932)(译文是加泰罗尼亚语),分析一段翻译草稿的语言学特征,如:拼写、句法、词汇、标点符号等,指出译者在初稿形成前进行过“不必要的修改”和“不正确的修订”(Pijuan-Vallverdú 2007:64),说明初稿形成前译者反复推敲、难以抉择的心理。
3.12 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和翻译策略
翻译必然涉及语言和策略问题。语言被认为是翻译中最主要的因素(转引自蔡毅 段京华 2000,Catford 1965),而翻译策略是不可忽略的要素,翻译策略可分为归化与异化2种(Venuti 1995:19-20)),即译者是靠近原作者还是读者(转引自黎士旺 2007)的问题。译者的修改和修订主要涉及两个方面:语言和翻译策略。根据对自译小说的研究,Bush审读1-6稿的译文后发现,虽然译文多次易稿,但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修订主要集中在姓名的翻译、近义词的替换和句子的调整等细微的语言层面。从译者自身的角度Bush提出,译文最初的修改主要为了使其更加符合语言的要求,如他将pounding the carpet 修订为 pounding the parquet,旨在强化头韵的作用 (Bush 2006:27)。随后,他又考察第6到第8稿发现,这几稿的修改集中在混合语的处理、外来词,甚至译文结构等问题上,即译文风格应该更加接近源语还是译入语,并指出手稿后期的修改大多出于翻译策略的考虑。
3.13 手稿的顺序
手稿的顺序研究可分为自译和他译两类。(1)自译研究:通过溯源的方法可以考察自译手稿的顺序,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翻译策略和翻译选择;第二,翻译选择针对的词汇、意向、节奏和韵律;第三,译稿中突出语言特征的量化分析。Jones运用多种方法对翻译手稿进行研究,并证明前期的译稿聚焦于语言问题,后期的修改则关注翻译策略。他采访过5位诗歌译者,调查他们的背景和翻译策略;运用有声思维法(TAP)研究自译Serbo-Croat诗歌4稿的翻译过程。他发现译稿特征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历时变化:第一稿的修改聚焦于词汇,第二稿注重节奏、韵律和诗歌形式,第三和第四稿则主要进行整体上、风格上的修订(Jones 2006:70)。(2)他译研究:相比自译,他译研究有更强的客观性,手稿研究往往结合译者本人的反思,能“为我们揭示翻译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常是翻译的主旨和精神所在”(Filippakopoulou 2008:34)。Filippakopoulou分析Ros Schwartz和Lulu Norman的合译本及手稿,通过对手稿的研究发现,译稿修订、校正都必须符合语言准确性的要求。她还发现,手稿修改由微观向宏观的变化,即由词序、动词、标点和连词到翻译风格的转换和顺应等。
Munday选取不同译稿中的片段,分析并重构不同翻译阶段的译者行为,推测译者行为背后的选择和决策过程。他还提出,通过分析译文终稿、手稿、译者书信、札记等因素对译者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他以Bello重译Perec作品Leschoses的翻译手稿和译文终稿的历时变化为例,分析译者最初的迟疑,后期每一稿修改的聚焦点则由微观的词汇替换、句法重构转向宏观的衔接和篇章结构。他通过对Bello的译文和3份手稿的溯源研究发现,在整个译文形成和修订过程中,词法的修改逐渐减少,而翻译策略和文化因素的选择逐渐增加(Munday 2013)。这一结果也验证Jones(2006)和Filippakopoulou (2008)的结论:手稿修改是由微观到宏观的过程。
3.2 步骤
溯源翻译研究有自己特定的步骤,从译者的第一稿开始直到译稿完成,对每一稿的修改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描写和分析,从而发现手稿修改的一般顺序和规律。例如,Munday(2013)通过分析译者的1-3稿发现,每一稿的修改都有不同的对象和目标。第一稿的修改聚焦如下问题:(1)Bello对某些词汇采取省略不译的方法,如bois clair(轻的木头);(2)Bello对仅有90单词的译文进行过10次修改,这些修改都集中在微观层面上,如词汇的替换 (glide over换成slide over; US gray换成UK grey等)、词序的调整、句法结构的变换(black-veined wood换成grainy black wood;in soft colors换成soft-hued等);(3)因为是重译,他还对Lane译文省略的部分进行补充,改变某些从句的词序,如:把cabinets, whose copper fittings would gleam改成 wooden fitted cupboards, light and gleaming with copper fittings.
第二稿的修订集中在文本层面上,反映译者的决策过程:(1)Bello用铅笔在译稿的页眉或页脚部分写大段文字,对译文第一稿进行改写和重构;(2)关注句法和结构上的变化,使用新的衔接手段。第三稿仅有一处词汇修改:将the Epsom winner 修改成the Derby winner. 这一稿其余部分的修改都集中在句法重构、衔接手段和某些信息点的反复推敲上,有些地方还显示出犹豫不定。译者的反复推敲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在选择情态动词时,译者经历would slide>could slide>would slide的过程;(2)在选择句式时,译者在施事行为句和受事行为句之间摇摆不定: What you would see first of all would be...换成 Your eye, first of all, would glide over...(3)在选择物品名称时,译者围绕corridor(走廊), cupboards(碗柜)和 fittings(家具)等名称的上位词和下位词进行修订。最终,译者选择更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和语序。
译稿修改的时间顺序是溯源翻译研究的纵向线索,溯源分析按照从第一稿到最后一稿的顺序展开;词汇、句式、衔接、翻译策略的选择是溯源研究的横向线索,研究者会在每一稿中寻找这些信息点,并按照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入挖掘。
3.3 进展
3.31 多语种和非文学文本的溯源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文本研究所(ITEM)就曾以溯源的方法研究诗人Paul Valéry的作品集以及他的翻译手稿。2010年,研究所从主要研究单语文本转向翻译文本和多语文本。如学者们通过追溯著名作家的自传、通信等资料研究他们的文学作品写作过程。溯源方法也可用于研究其它类型的文本,如文本研究所对艺术作品和建筑物、影视和摄影作品进行溯源研究。
3.32 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和溯源研究范式的推广
1995年,在法国阿尔勒召开会议并出版论文集《溯源与翻译》(Génétique&Traduction)。但溯源翻译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还是在最近的10年。2011和2014在巴西、2014和2015在法国分别举行过以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2009年布鲁塞尔欧洲文本研究协会第6届会议的主题是“超越边界的文本:多语主义和文本研究”,会后出版特刊《翻译变体》(Variants)。溯源翻译研究也成为一些学术期刊的重要论题,以此研究翻译中的作者介入案例 (Anokhina 2015:198-210)。此后,溯源翻译研究的单行本不断出版,涉及的语言有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等(Romanelli 2013; Weller, Van Hulle 2014)。
3.33 系列论文的刊出和溯源翻译研究的纵深发展
2015年,LinguisticaAntverpiensia杂志把溯源翻译研究作为主题,刊登9篇论文和1篇总论,论文涉及4个议题:(1)原文本与翻译过程:译文形成过程中译文和原文在内容接近程度上的变化(Romanelli 2015:96);原文本重构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翻译前文本是否影响译文终稿的形成(Lozano 2015);(2)文本中译者身份的显著度和主观性:译者创作的认知过程(Guan 2015,Romanelli 2015:87-104);不同译者在译文修订过程中采取的不同策略(Karpinski 2015);(3)翻译是一个多任务、互动的过程:文本外诸因素对译文的影响,包括作者、其他译者、读者、编辑以及网上社区等(Bricco 2015,Fan 2015);作者与译者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Karpinski 2015);(4)计算机技术为溯源翻译研究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Fan 2015,Scocchera 2015)。
同时该杂志以溯源的方法,通过对翻译手稿的描写,探讨译者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从多个角度分析文本视角下的翻译过程。
4 溯源翻译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如前所述,手稿反映出译者在不同阶段翻译选择的具体信息,而问卷、访谈、信件等还反映出译文出版中的权势对译者选择的影响。因此溯源方法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4.1 问题
溯源翻译研究这一新的翻译过程研究范式还存在理论和技术上函待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之所以把溯源方法用于翻译研究,是因为二者有天然的联系,但溯源批评主义最初只用于研究单语文本,而非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双语文本,所以溯源与翻译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融合,原因是:(1)溯源批评主义诞生于法国,而法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束缚,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脱离语言学、文体学和比较文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2)文本分析主义认为,翻译有偶然性,译者生活在作者的影子里,其作用被忽视;原文被看作是决定性的、永久的,译文会被不断地重新语境化(Cordingley,Montini 2015),因此是扩展的、修订和修改过的、是不稳定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者的意识形态会对结论产生影响,如何避免这一影响也是溯源翻译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技术上,溯源翻译研究需要依据大量的译者手稿,而对手稿的收集和保存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和体系。著名作家手稿的收集始于中世纪,然而要想把这类手稿用于溯源研究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溯源研究更加认同译者签名的手稿,现存译者签名的中世纪手稿还比较罕见;二是现有的收藏多为作者手稿,译者手稿的收集开始于20世纪,当时的溯源翻译只是为了研究杰出人物的文化立场,手稿还没有用于翻译过程研究,因此也没有进行过相应的技术处理和加工。
而不知名译者的手稿更是难以获得,一是因为他们很少保存自己的手稿或信件、札记等文献资料;二是他们不愿意将手上的资料提供给研究人员,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翻译过程中犹豫不决的地方和不理想的译文公布出来,而使读者怀疑自己的翻译能力。因此,无论是著名作家或是不知名的译者,手稿的获得都是溯源翻译研究的一个技术难题。
4.2 前景
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和数字技术促进溯源翻译研究的发展,使其具备良好的前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翻译是传播文学和思想观点的桥梁,当代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凸显,译者身份研究得到普遍关注,翻译实践的广泛开展引发对译者身份认同的再思考,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考和地位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译者身份研究的驱动下,一些机构开始投资收集译者手稿以供检索和查阅。目前已有多家机构开展译者手稿查询服务,如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的Lilly图书馆、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的Harry Ransom中心、英国的东英吉利亚大学、法国卡昂当代出版回忆录研究所等(Cordingley,Montini 2015)。
在技术层面上,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溯源研究,译者工作空间的数字化为手稿保存、储存、分类处理提供有效、快捷的途径:(1)数字恢复技术:从电脑或者数字存储中进行信息恢复;(2)数字信息管理:进行数字的储存和应用;(3)计算语言学,尤其是语料库语言学:从语言学层面处理大宗数据和语料;(4)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译者定期储存和记录自己的翻译内容。在网络和数据库中翻译前文本也变得触手可及,这也为溯源研究提供便利,贝克特电子手稿库(www.beckettarchive.org)就是这类数据库的典型(同上)。该数据库是首个专门用于溯源研究的数据资源,它不仅存储英法双语对照的贝克特手稿,还提供可视化对比和翻译前文本分析的相应软件工具。
5 结束语
溯源翻译研究缘起于法国的溯源批评主义,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人们发现,译者的手稿和档案库作为理解翻译过程的重要文献已经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翻译前文本为我们提供评判翻译策略和译者选择自主性的可能。溯源翻译研究关注译文的独立性,认为译文独立于原文,翻译传播译文生成的过程,同时以译文—翻译前文本—原文的顺序激活文本生成的连续统一体。
溯源翻译研究从产生到理论和技术上的发展,再到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它对翻译学科的贡献主要有3点:第一,它所采用的批评和溯源研究视角使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证明翻译是一个历时的过程;第二,它立足于文本,以翻译前文本、书信、札记作为依据的方法实质上形成翻译研究的实证模式。从文本中挖掘译者的心理过程和选择机制,并把文本描写和解释预测相结合,使翻译过程研究更加客观;第三,溯源翻译既可以结合计算机技术和语料库研究,又可以结合认知心理学的方法,使翻译过程研究有可能实现多学科、多领域的融合。
以溯源方法进行翻译过程的案例研究目前仍局限在欧洲,国内相关的研究尚未开展。但我们认为,作为立足文本的翻译过程研究范式,溯源不仅是对翻译过程研究认知模式的有效补充,也是一种通过文本激活而探究整个翻译过程的有效方法,值得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