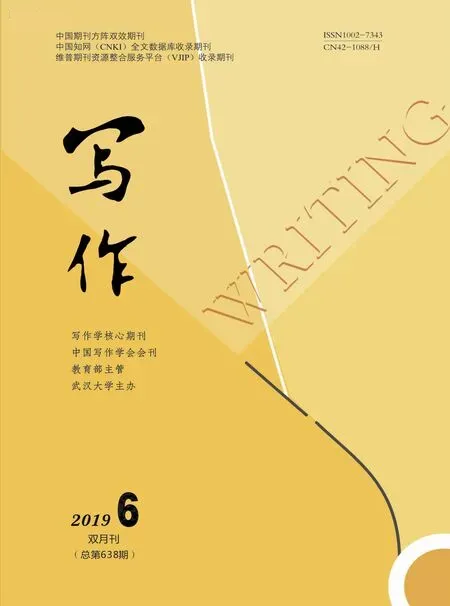“甘南”的生态语义场与“藏地”书写
——藏族诗人诺布朗杰诗歌论
2019-11-26董迎春
董迎春 覃 才
藏族青年诗人诺布朗杰的首部诗集《蓝经幡》201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五辑《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之一)。这部诗集收录了诺布朗杰近年来创作与发表的一系列以出生和成长地“勒阿”藏寨,工作地“舟曲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及青海、拉萨等藏区自然景观、雪域文化、宗教文化为审美对象的诗歌作品。他“所选诗歌对藏地的自然生态、历史现实、风物民俗等诸多藏文化内蕴进行了发掘和展示。既有诗人对生命独有的感受、思考、洞察与吟咏,也有对乡土与藏文化的精神回望”①诺布朗杰:《拉章拾句——也说新书〈蓝经幡〉》,《阿坝日报》2018年8月24日,第7版。。作为一个深受藏区自然文化、藏族宗教文化传统影响的青年诗人,诺布朗杰的诗歌创作可以说显现了藏区文学和藏族文学惯有的“藏地”书写特征。而在朝向藏族母语精神的藏语与汉语混合的写作当中,诺布朗杰的诗歌书写也相应地形成了具有“甘南”的自然、社会及精神特征的生态审美与意义表现场域。
一、“甘南”的生态语义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鲁枢元、曾繁仁、袁鼎生等为代表的生态美学研究者倡导进行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在“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①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的基础上,他们以“生态”的审美视角着重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的精神性存在。对人与环境的这种生态性存在关联与生态性审美特性,盖光指出:“‘生态’的一般意义在于显现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为人类自身搭建与自然共生互惠的居所,构筑生命灵性的‘栖居’之地。”②盖光:《文艺生态审美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这种自然、社会、精神(心灵)相融通的“生态人”审美结构,不仅暗合文学创作过程中写作主体长久以来观照自然、社会、精神,并赋予自然、社会、精神以特定生态诗性情感意义的特性,更显示了现代人在贫瘠时代对诗意栖居的期待。可以说写作者在自然、社会、精神(心灵)相融通的“生态人”审美结构中,既能够在一种程度上达到诗意的状态,又能够创造出熔铸于作品当中具有生态性审美的“语义场”。
语义场(也称意义场、词场等)是关于义素及其构成的词语的结构和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初现于索绪尔,“由德国学者易普森(G.Ipse)、特里尔(Trier)、维斯盖别尔(Weisgerber)等人提出并加以发展的”③符淮青编著:《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在这些语言学家看来,词语的意义不是单纯地由构成词语的义素来建构,而是在一个超出义素本身的更大的结构或系统中生成。相关词语的意义在这种结构或系统中的纵向聚合和横向聚合就构成了“语义场”。根据这一理论,如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写作者自觉性地运用、组合具有生态性的自然、社会及精神(心灵)等义素的审美结构,其结果无疑会生成一个意义丰富的生态语义场。对生活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具体出生地为舟曲县的“勒阿”藏寨)的藏族诗人诺布朗杰而言,他诗歌书写中表现出来的关于“甘南”藏区自然景观、社会生存状态及藏族宗教精神信仰体系的生态性审美与想象,无疑也是构成了其诗歌创作的“生态”语义场。在这一“甘南”的生态语义场中,诺布朗杰坦然地构建自身的这种自然、社会、精神(心灵)相融通的“生态栖居”和生命诗意。纵观诺布朗杰诗集《蓝经幡》而知,他本人聚焦于“甘南”藏区这一地理区域内的生态性书写与意义表达,大致表现为自然、社会及精神(心灵)相融通的“生态人”审美特征与语义场域。
(一)自然生态层面海德格尔在著作《林中路》中指出:“作品回归之处,作品在这种自身回归中让其出现的东西,我们曾称之为大地。大地乃是涌现着——庇护着的东西……作品让大地是大地。”④[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人作为生活于大地上的人,“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⑤[德]R.施贝曼:《现代的终结?》,《社会科学报》2004年11月11日,第1版。。对写作者而言,这种影响就表现在他对所生活的地域的自然性、生态性观照与思考之上。诺布朗杰出生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名为“勒阿”的藏族村寨,现工作于舟曲县城。他在“甘南”藏区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及工作生活的实际情况,会构建起一种关于地方(土地)的书写意识,在他诗歌书写的过程当中,这种意识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观照“勒阿”“舟曲”“甘南”这三个地方的自然和生态书写特性。
诺布朗杰在诗作《勒阿:第三首即兴诗》中写到了他对“勒阿”自然生态诗意性的亲和感:“把雪写得再白一点,不融化/落在我的屋顶。储藏一生的冷与热……把山的海拔继续压低/直到看见远方/看见山雾里丢失的那几只羊羔//再把溪水流动的速度调快一点/让它及早触摸海洋。”⑥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2页。在《舟曲一瞥》中他写到他对“舟曲”自然生态的危机感:“一瞥,就瞥见群山/它们舞着自己的骨头//一瞥,就瞥见龙江/枝头结着两条河//一瞥,若能瞥见飞鸟/我就跟它们学怎么用天空筑巢?”⑦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2页。而在《九行甘南》的“G”一节中,他写到了对“甘南”草原自然生态的热爱:“草原,凝固着牧人所有心跳/那个拾牛粪的人伸出祥火之手/火光中,雪后的草原开始旺盛//当我们高喊一声,云朵就会落下来/蓝天从远古蓝到现在/白云从远古白到现在。”①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5、50页。显然,诺布朗杰的这三首诗不仅表现了“勒阿 ”“舟曲”“甘南”三个地方的自然生态状况与其诗歌创作的直接性、生成性关联,更展现了他诗歌创作中自然生态审美语义场的思考维度与灵性特征。
(二)社会生态层面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指出:“自然并非‘自为地’(“in itself”)来到我们面前,而是被置于社会中加以沉思。”②[英]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页。在社会存在过程中,自然作为人的本性特征之一,不仅影响着人对社会和生命方方面面的思考,也决定了人的社会生存和生命状态具有生态的特征。对具有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身份的民族诗人而言,社会和生存层面上的生态审美似乎更加显著。因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存活动与审美活动是同一的,他们往往是“在生存中审美,在审美中生存,消融生存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分离与对立,使生存活动成为审美活动的载体,使审美活动随生存活动不间断地展开。”③袁鼎生:《袁鼎生集——生态美学论》,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版,第188、187页。诺布朗杰作为一个藏族诗人,同时也是一直生活在藏区,藏族和藏区的社会生态性生存活动必然影响着他的审美活动(即影响他的诗歌创作),他的审美活动也必然地反过来影响他的社会生态性的生存活动。在社会生存活动与审美活动的相互影响与交织的过程中,他的诗歌创作创造的生态性语义场域也得以完成。
在诗作《在勒阿,我碰见了一块石头》中诺布朗杰写道:“屋檐下,被雨水质问着的石头/跟玛尼堆上的某一块/有着相同的材质/砸我脚的,好像也来自一块石头//在勒阿,我碰见了好多这样的石头/被三轮车拉过来拉过去/后来,我在一座房子折断的脊梁上/发现了这块石头/它头顶着,岌岌可危的/家园。”④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5、50页。“玛尼堆”(藏语称“朵帮”,垒起来的石头的意思)也被称为“神堆”,指那些在藏区路口、山间、湖畔等地用石头垒起的祭坛。在这一首诗中,藏区自然界中的“石头”和玛尼堆上“石头”是自然直接物化的一种表现,“房子”和“家园”则是藏区社会生存的一种象征。我们看到,自然界中的“石头”和玛尼堆上“石头”变成“房子”和“家园”中的石头的过程,即是诺布朗杰以象征的方式将自然置于社会中思考的直接体现。可以说“石头”这种经历自然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变化状况,即是诺布朗杰作为一个生活在藏区的藏族诗人经历的社会生存活动和审美活动相互影响与交织的反映。这种影响和交织,既构成了诺布朗杰面向“甘南”藏区的诗歌书写和审美内容,又是他在社会生态层面上极力要构造的语义场。
(三)精神(心灵)生态层面对人而言,自然或社会生存的生态审美最终会上升为精神的诗意探寻与心灵的美感。因为在自然或社会性的生态感知与美感的慰藉下,人必然会萌生精神或心灵的形而上的收获与体验。“生态审美理应促合人类诗意性、生态化的生存体验,合理探寻人类生态性生存结构,澄明人类朝向未来的生存状貌,诗意性地显现为生命及其生存的‘美态’。”⑤盖光:《文艺生态审美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对藏族诗人诺布朗杰而言,民族是他进行自然和社会性生态审美的先验前提,也是他进行自然和社会的生态审美之后产生精神(心灵)生态美感的显现形式。所以,在他的诗歌书写当中,“民族审美场的生态运动,都指向生态审美场和归于生态审美场”⑥袁鼎生:《袁鼎生集——生态美学论》,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版,第188、187页。,经由自然和社会的生态审美之后的精神(心灵)生态审美也统一于他的“民族审美场”。
如在诗作《朝圣》中诺布朗杰写道:“合上双手,我要为灵魂洗浴/盘踞在腕际的念珠/是宗教里的时间。它们正在经历黑夜……//我所遇见的,将是永不凋谢的花/甚至落叶,是我怀里翩翩的蝶/把人生铺开/换取片刻宁静/再用我的湖泊,引出内心的大海。”①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藏族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这种宗教信仰也是藏族人精神或心灵世界的核心观念。在《朝圣》这首诗中,“合上双手”“灵魂洗浴”“念珠”等宗教礼仪和物件即是诺布朗杰本人宗教信仰的直接显现,对诺布朗杰而言,在“朝圣”即是在“宗教里的时间”,也即是进入精神(心灵)的生态审美境界当中。他在这一精神(心灵)的生态审美境界和美感当中,遇见“永不凋谢的花”,看见落叶似蝶翩翩起舞,感受心中静谧的湖泊和大海。显然,对诺布朗杰而言,他在这一精神(心灵)的生态审美境界和美感当中,构筑了他诗歌创作的内容和意义的场域。
综上而述,诺布朗杰作为生活于“甘南”藏区的藏族诗人,他在“勒阿”“舟曲”“甘南”生活、工作的自然、社会、精神性的生态审美既是他本人进行诗歌创作内容的直接来源,也是他以诗歌的方式理解他的出生、生活、工作之地,以及他的民族的生态性意义场域。诺布朗杰说:“万物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日月星辰镶嵌于天空,山川河流分布于大地。这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我们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挪到纸上,又重新组合它们。”②诺布朗杰:《飞鸟说——有关歌曲〈坠落的飞鸟〉的残言断句》,《阿坝日报》2018年7月13日,第7版。在这一种生态性的审美结构当中,诺布朗杰表达了他对“甘南”藏区的深深乡情、亲情,展示了他对“甘南”藏区自然、社会变化过程独特的思考与关怀。
二、“藏地”书写
对“甘南”藏区的自然、社会、精神性生态审美与观照,是诺布朗杰诗歌创作的重要维度。但作为一个藏族人,他的诗歌创作必然走出“甘南”藏区的空间局限,以进入藏区作家共有的“文学藏地”的想象与书写之中。“文学藏地”(也称“文学藏区”)是白浩、高亚斌、方亚男等学者对藏区文学和藏族文学的总概观,“指的是‘文学的藏地’,是涉藏文学的文学领地,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③方亚男:《新时期“文学藏地”视阈下的“轻游记”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而作为“文学藏区”概念的第一个命名者,白浩甚至指出“文学藏地”是“以文学为主体,不限于民族、地域,而是以藏族(民族)、藏区(地域)的相关生活、文化为对象的文学”④白浩:《当代“文学藏区”的多元融合与创生研究纲要》,《阿来研究》2015年第1期。。可以说这种具有文学地理学研究视角的概观与命名,是“借鉴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与迁徙,探讨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揭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⑤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具有整体性、空间性探求藏区文学(藏区文学或称藏地文学涵盖范围比藏族书写广泛)内涵与外延的意味与价值。
1961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行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提出以“民族成分”“语言”“题材”为界定民族文学和民族书写的三项基本要素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1984年版,第103页。,其中“民族成分”是必备要素,“语言”“题材”的要求相对宽松,即是“以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作为前提,再加上民族生活内容和民族语言文字这二者或是这二者之一”⑦中国作家协会编:《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理论评论卷1》,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0页。,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民族创作即成立。诺布朗杰是藏族人,藏族的少数民族身份决定了他的诗歌创作是一种“藏族书写”,他以身体与精神“远游”的形式跳出“甘南”藏区,以整个藏地(藏区)“雪域文化”和“宗教文化”为主要内容,也让他的诗歌具有“藏地”书写的象征意义。
应该看到,以雪山、高原、湖泊等为原型的“雪域文化”在藏地(区)作家和藏地(区)文学当中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对生活于藏地的作家、诗人而言,“在他们的周围,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有相应的神灵驻守……每一株花草,每一个生灵都有其生存的独特意义”①才旺瑙乳:《藏诗:追寻与回归——代前言》,才旺瑙乳、旺秀才丹主编:《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藏地的作家、诗人带有神性、灵性特征的诗歌审美,即是藏地“雪域文化”万物有灵论、众生平等观的哲理性显现。我们看到,在“雪域文化”这一维度上,诺布朗杰的“藏地”书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青海、拉萨等藏地自然雪域的描绘与体验;二是对藏地“地域文化”的人文性感知与思考。这两个方面的灵性探知与对话,显示了诺布朗杰“藏地”书写具有的“雪域文化”特征。
在《青海绝句》中诺布朗杰写道:“还能说什么。天太蓝/容易暴露出鹰/草太青,会撑高牛羊/朝圣的人太多/就可以磕出好同个青海湖。”②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5、46、85、15、29、28、24 页。在《德令哈》中诺布朗杰写道:“德令哈,黄金的光芒太沉/用白银的一生,换掉我满头黑发/德令哈,容我空旷/容我为不可一世的孤独加冕/德令哈,我所有的抒情终究是败笔/唯有落日的深潭高过群山。”③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5、46、85、15、29、28、24 页。在直接名为《雪域》的诗作中诺布朗杰写道:“奔跑的雪域,我愿做你胯下的马鞍/愿十指攥紧的拳头撑起你/在你茫茫白雪的纸上,怀孕十万亩花朵/用十万亩花朵收住你的心。”④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5、46、85、15、29、28、24 页。我们看到,诺布朗杰在直面青海和青海的德令哈及藏族的“雪域文化”的自然面貌的时候,表现出作为一个藏族人对雪域自然文化的崇敬与亲近之感。
而在诗作《酥油灯》中,诺布朗杰写道:“来自天界的火种,降临人间——/独守神的秘密/细小的腰上,系满沉甸甸的祷词//我看见的光/分明是铸在体内的泪//最好以盲人的身份,出现在灯下/假设一种光芒,照亮众生。”⑤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5、46、85、15、29、28、24 页。在诗作《马背上》中他写道:“马背上住着风。住着雨/住着缰绳里的远方/拴好草原的辽阔,再把马蹄下的尘世/踏响。”⑥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5、46、85、15、29、28、24 页。在诗作《蓝经幡》中写道:“一块切割好的天空,久搁人间/我们顶礼膜拜/额头上是一生的碑文//说到高,说到天空的海拔/用它扩充一颗慈悲之心的辽阔//风动似心动。摊开的腹部雕满灵魂的印经。”⑦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5、46、85、15、29、28、24 页。显然,在命名为具有藏地雪域文化特征的《酥油灯》《马背上》《蓝经幡》三首诗作当中,诺布朗杰表现了他对藏地地域文化的敬仰之情与人文性感知。
藏族诗歌有深厚的宗教书写传统,学者王沂暖、唐景福在著作《藏族文学史略》中指出:“十一世纪下半期到十三世纪上半期,藏族出现了两个有名的诗人,一个是噶举派(白教)的米拉日巴,一个是萨迦派(花教)的贡噶坚赞。这两个诗人,都有专集,这是藏族人有诗歌专集之始。”⑧王沂暖、唐景福:《藏族文学史略》,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历史地看,以米拉日巴和贡噶坚赞为代表的宗教诗人为藏族诗歌创造了史诗、叙事诗、格律诗传统。而在当下,“我们能够感受到藏族诗人背后强大的族裔、宗教文化的影响,这也成为他们区别于主流诗歌的特征”⑨徐寅:《边界的想象——试论藏族汉族诗歌的嬗变》,《名作欣赏》2017年第32期。。在朝向“藏地”宗教文化的书写维度上,诺布朗杰的诗歌创作也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以描写藏地寺庙、建筑为主体的“及物性”想象;二是以表现他本人与藏地高僧、法王、活佛的精神对话与现实意义思考。可以说正是这两个特征,建构了诺布朗杰“藏地”书写的“宗教文化”特征。
在诗作《旧句:色拉寺》中诺布朗杰写道:“可以释放出来了,胸口憋久的母语/甚至可以忽略高仿的历史/在寺的某个角落,匍匐/把缺氧的汉字收起来。履行一个藏人/应有的使命。”⑩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5、46、85、15、29、28、24 页。在诗作《旧句:哲蚌寺》中他写道:“我用粗糙的手合十。佛光滑的倒影/学着掏空自己。就好像拉住了时间之手/轮回之腕。”①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26、40、70、82 页。在诗作《旧句:羊卓雍错》中他写道:“这是高原的海。我在它的镜子里放下心底的深渊/并贡上剔除干净的心脏//弓下身子,我更要/解读这份充满玄机的信/一定要找到它前世和今生的真相。”②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26、40、70、82 页。在这三首以藏地寺庙为名称的诗歌当中,诺布朗杰以由物及人的方式,表现了他对藏地文化的朝圣之心。
在诗作《谒上师更敦群培》中诺布朗杰写道:“莲花生从遥远的喜马拉雅/运来青海湖/隔世的桑烟/斜斜地飘向热贡/静静的宗喀吉日山/沉默着一个佛陀的心事。”③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26、40、70、82 页。在诗作《使命》中他写道:“噶玛巴大师圆寂那晚/我听到所有经卷的悲鸣之声//法号沉默 海螺失泣/一条河突然在我眼前中断。”④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26、40、70、82 页。在诗作《尊者仓央嘉措辩》中他写道:“大雪封山。春天一直没有出现/备上鞍辔,还得走一趟/看不见的功德,也自会圆满/那沾满尘土的靴子,也沾满人间疾苦。”⑤诺布朗杰:《蓝经幡》,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26、40、70、82 页。我们看到,在这三首内容为他本人与藏地高僧、法王、活佛的精神对话与感悟的诗中,诺布朗杰呈现了他对藏地宗教文化的虔诚的信仰之情。
藏族诗人才旺瑙乳在《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中指出:“藏族诗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一方面他们要客观地面对青藏高原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另一方面,又生活在由于与大自然长期搏斗而形成的充满了神(诗)性的精神家园。”⑥才旺瑙乳:《藏诗:追寻与回归——代前言》,才旺瑙乳、旺秀才丹主编:《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诺布朗杰作为藏族诗人,他在面对青海、拉萨等藏区或是荒凉或是旷远亦或是纯净的雪山、高原、湖泊之时,自然地产生了与之相适合的神性、灵性精神场域,并且再加上本人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宗教文化影响,他的诗歌创作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朝向藏族地域的“雪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写作维度。我们看到,在这一比“甘南”藏区更为广泛的诗歌创作与情感表现维度内,诺布朗杰既“在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世俗纠葛错杂中,向母语致敬,向自己的民族致敬”⑦诺布朗杰:《拉章拾句——也说新书〈蓝经幡〉》,《阿坝日报》2018年8月24日,第7版。,同时又建构了具有藏族诗歌传统和他本人特征相结合的“藏地”书写。
三、审美价值
通过以上论述而知,作为具有藏族身份且出生、成长及工作生活之地也是扎根于藏区的诗人,诺布朗杰的诗歌创作反映了文学与生态、文学与地理的相互影响关系。可以说诺布朗杰正是凭借以面向“甘南”藏地的自然、社会及精神(心灵)的生态审美和以朝向青海、拉萨等藏区“雪域文化”“宗教文化”为主体的“藏地”书写建构起了个人诗歌创作的内容表达和审美意蕴。而作为一个主要以汉语为日常交流、工作用语和写作语言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虽然部分地使用藏语写作,但主体的部分还是“用藏人的思维在汉字中摸索属于自己的抒情方式”⑧李亚键:《把凌乱的人间再打扫一遍——专访藏族青年诗人诺布朗杰》,《甘南日报》2016年12月7日,第3版。。姜永琢指出:“藏族诗人的汉语非母语写作的优势和魅力在于,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使之有了超越语言和文化疆域束缚的可能性,表现出较强大的文学发展空间。”⑨姜永琢:《论当代藏族诗人非母语写作的物质》,《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2期。我们看到,在以面向“甘南”藏区的生态审美和青海、拉萨等藏区的“藏地”书写过程中,诺布朗杰具有藏族母语精神的藏语写作、汉族写作,也突显了当代藏族青年诗歌在中国青年诗坛当中的影响与意义空间。
第一,诺布朗杰面向“甘南”藏地的自然、社会及精神(心灵)的生态审美,增补了“甘南”藏地的人文灵性与诗意。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中国直接以藏族命名的十个自治州之一,它以草原文化、雪域文化、宗教文化和风俗等为其人文特色。诺布朗杰作为出生、成长及工作生活都在“甘南”藏地的少数民族诗人,“甘南”藏地久远的藏族文化、宗教体系及当下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草原、雪域等自然景观,都作为一种血脉记忆或生命经验直接显现于诺布朗杰的诗歌创作当中。我们看到,这种具有“地理感知”“地理记忆”“地理根系”及“地理思维”等特征①邹建军:《文学地理学关键词研究》,《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的诗歌创作,表现了诺布朗杰作为藏族诗人,在面对“甘南”藏地的这种人文传统和时代变化之时,相应的也自觉性、创造性地以面向“甘南”藏地的自然、社会及精神(心灵)的生态审美,建构他对这个时代的“甘南”藏地的理解与价值探求。以响应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说的“这个世纪的启示在荒野”②[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的人类普世命运呐喊。纵观诺布朗杰的诗歌,我们发现,他具有“甘南”藏地“荒野”精神与启示的生态审美,也为“甘南”藏地建构出了新的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征的人文灵性与诗意。
第二,诺布朗杰以青海、拉萨等藏区“雪域文化”“宗教文化”为主体的“藏地”书写,丰富了“文学藏地”的审美意蕴。“雪域文化”和“宗教文化”不仅是藏区文化的核心内容,更是藏地文学和藏族文学审美表现与情感表达的主要内容。藏地文学或藏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当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也正是通过这一差异性的核心文化突显出来,并受到认可。我们看到,仓央嘉措、阿旺洛桑、伊丹才让、央珍、阿来等一代代的藏地或藏族作家、诗人正是凭借他们出生、生活及工作于藏族地区,并且是以与藏地“雪域文化”和“宗教文化”相关的题材、主题进行写作,建构在中国文坛当中的地位与影响。洪堡特指出:“一个民族的人民总是以同样的独特方式理解词的一般意义,把同样的附带意义和情感色彩添加到词上。”③[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4页。诺布朗杰作为一个藏族诗人,他本人具有的藏地和藏族文化血脉也直接显现为他对与藏地“雪域文化”和“宗教文化”相关的题材、主题的诗歌写作。我们看到,诺布朗杰通过一系列的以藏地“雪域文化”和“宗教文化”为内容、题材及主题的诗歌创作,慢慢地建构起了具有他本人特征的“藏地”书写与情感表达,这种个体化的“藏地”书写经验能够丰富“文学藏地”的审美意蕴。
第三,诺布朗杰朝向“母语精神”的藏语与汉语相结合的写作,展示了当代藏地文学和藏族文学作家群体整体性的写作态势与转型特征。对现代的且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而言,他们的写作在语言上表现出混合写作的特征。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写作和审美必然徘徊于“母语”和汉语之间。如藏族诗人、作家阿来所言“我是一个藏族人,又用汉语写作”④阿来、姜广平:《“我的一个藏族人,用汉语写作”》,《西湖》2011年第6期。,“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⑤吴怀尧:《阿来:文学即宗教》,《延安文学》2009年第3期。。作为当代非常有影响的藏族作家,阿来的非母语写作自述,说明了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共生的可能。阿来具有藏族“母语”和汉语相结合的双语写作现象,不仅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巨大动因,更是他在中国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原因之一。当下,诺布朗杰作为一个藏族诗人,和阿来一样,他的诗歌创作在语言方面必然地表现出藏语与汉语相结合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他本人用藏语进行创作的诗歌也相应地发表于某些期刊上。可以说诺布朗杰这种朝向“母语精神”的藏语与汉族相结合的双语写作,“是建立在年青的语言差异和藏族地域认同上的”⑥覃才:《面向母语精神的非母语写作——关于藏族诗人诺布朗杰诗歌的一种阐释》,《格桑花》2015年第2期。,这吻合和展示了当代藏地文学和藏族文学作家群体整体性的写作态势与转型特征。
第四,作为当代藏族青年诗人代表之一,诺布朗杰关于藏族和藏地的文化书写与影响,突显了藏族青年诗歌在中国青年诗坛当中的意义。作为一个90后诗人,诺布朗杰近年来在《诗刊》《民族文学》《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等各大刊物发表一系列作品,两度获得甘肃黄河文学奖 (2015年,2016年),曾参加《中国诗歌》“新发现”诗歌夏令营(2014)、鲁迅文学院第29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2016),诗歌作品《就这样老去》入选2015年潍坊市高一语文期中考试试题。并且在2018年的9月,诺布朗杰作为甘肃省青年作家代表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①雷媛:《我省作家代表团参加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兰州晨报》2018年9月20日,第7版。。这些文本的传播与影响,及文学界或社会对其创作的肯定,建构了诺布朗杰作为当代藏族青年诗人代表之一的形象。就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本质而言,其本质无疑是关于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书写②董迎春、覃才:《民族志书写与民族志诗学——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学人类学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诺布朗杰作为一个藏族青年诗人,他以系列地反映甘南、青海、拉萨等藏区和藏族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诗歌作品和文学认可度,既表现了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书写本质,也突显了藏族青年诗歌在中国青年诗坛当中的意义。
综上而述,作为一个90后藏族青年诗人,诺布朗杰以面向“甘南”藏地的自然、社会及精神(心灵)的生态书写和反映“文学藏地”传统和特征的“雪域文化”“宗教文化”的“藏地”书写建构起了他本人诗歌创作的内容表达与审美旨趣。并且凭借这些具有民族、地域及“母语精神”等特征的诗歌创作与影响,诺布朗杰也建立起他在当代藏族青年诗坛、藏族青年文学当中的符号价值与文学地位。而作为处于成长期、上升期的青年诗人,诺布朗杰也突显了藏族青年诗歌在中国青年诗坛当中的意义。
四、结语
诺布朗杰基于“甘南”藏区和青海、拉萨等藏区“雪域文化”“宗教文化”的自然、社会、精神(心灵)性审美与思考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他作为当代具有藏族身份的青年诗人的诗歌自觉与担当。通过诺布朗杰扎根于“甘南”藏区和青海、拉萨等藏区“雪域文化”“宗教文化”的诗歌作品,我们不仅感受到了“甘南”、青海、拉萨等藏区和藏族精神信仰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的执着坚守,还感受了藏区文化和藏族文化所具有的神性和灵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精神和心灵的诗意栖居。综合而论,诺布朗杰的诗歌创作既呈现了藏区文学和藏族文学的本质意蕴与传统,又以个人主体性的审美维度表现藏族青年诗人对民族、时代的理解与意义建构。这种个人化的理解与书写在当代藏族诗坛和中国诗坛当中的价值与意义,也因诺布朗杰诗歌作品的影响与传播日益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