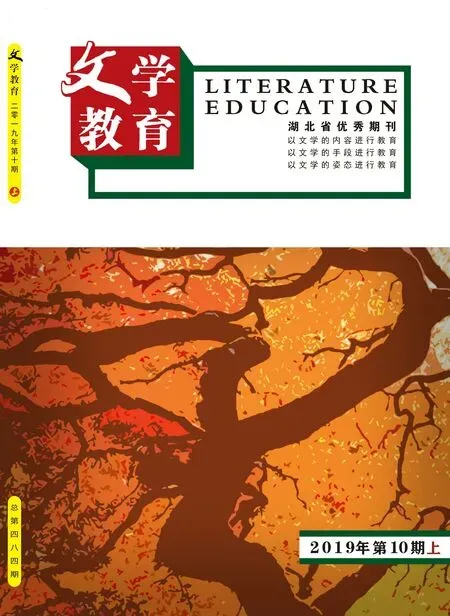从改写理论看《边城》英译的“不忠实”
2019-11-26杨洁
杨 洁
一.引言
翻译中的“信”与“忠实”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中西译论的核心议题。(谭载喜,1999)译者坚持译本要忠实于原文的同时,却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翻译策略,在某些地方对原文“不忠实”,戴乃迭英译的《边城》便是典型例子。
评论一个翻译作品“应该以具有一定水平和一定影响的译本为主要对象。”(孙致礼,1999)《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至今已有四个英译本,既有中国的本土译者,也有西方国家的汉学家积极地翻译这部作品,足以表明它在中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影响力之大。戴乃迭作为一位专业的译者,具有双重文化的身份,多年的翻译实践为她的翻译事业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在翻译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译本的接受度较高。她翻译的《边城》最初发表于《中国文学》,于1981年在“熊猫丛书”再版。2013年耿强的《“熊猫丛书”英译本的跨文化传播》提到,英美各大图书馆收录的销量较好的几个译本中就有戴乃迭的《边城及其他》,何谷理和李欧梵也评论《边城及其它》极具特色让人印象深刻,赞赏戴乃迭向外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耿强,2013)因此戴乃迭的译本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具有极强的可借鉴性。
笔者通过分析发现,戴乃迭英译的《边城》中,“不忠实”翻译现象较多,基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本文主要探讨《边城》英译本中的“不忠实”翻译现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往往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的影响,同时也指出译者的改写失误及其原因,以期为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带来一定的启示。
二.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是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指控》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从而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Lefevere,2004)他还认为,主要有两个要素在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一个是文学系统内部因素,包括翻译家、评论家、批评家、教师等专业人士,另一个则是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可以是有权利的个人或者团体,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Lefevere,2004)“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译入语文化对文学翻译的三种基本力量,”但“归纳起来,实际上控制文学翻译的因素主要是意识形态和诗学两种”。(查明建,2004)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常常会对原作在文化层面进行改写,采用省略、删减、增添、篡改等方式让译本符合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翻译拓宽了思路,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至今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介绍,以及批判性解读。何绍斌指出改写理论“对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何绍斌,2005)它“跳出了文本的樊篱,把翻译研究从纯语言转换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影响整个文学系统的宏观文化因素”。(王峰,2008)由此可见,改写理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边城》英译本的“不忠实”
戴乃迭主要在《中国文学》编辑部从事翻译工作,因此她的翻译策略必然会受到社会意识的影响,而作为一个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译者,戴乃迭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发挥其主体性,受到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外,不同的语言文化具有不同的诗学规范,为了适应英语文化的诗学规范,译者对原文做出了相应的改写。以下笔者将从社会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以及诗学规范三个方面探讨戴译本《边城》中的“不忠实”现象。
1.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戴乃迭翻译《边城》是出于“对外宣传”的政治需要,为了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原作中涉及“旧社会”的政治、军事、宗教等用语做出了调整,或凸显、或遮蔽、或模糊、或曲解原意。(谢江南、刘洪涛,2015)最明显的是译者对“顺顺”这个人物形象的处理。
例(1):
原文: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沈从文,1981:243)
译 文:The wharf-master,Shunshun,served under the Qing Dynasty banner before becoming an officer in the celebrated 49th detac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in 1911.(Gladys,1981:15)
“顺顺”是大老、二老的父亲,译者对其形象进行了“美化”。原文在描述这个人物时用到了“前清时便在”一个“便”字表明作者将“掌水码头”与“前清时”的“营伍”以及“陆军十九标”都列于同等的地位,而且从“人物”二字可以看出作者对“前清时”的“营伍”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将在里面“混过日子”视为一种荣誉。但是在译者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译者批判旧社会,颂扬新社会,因此译者有意将顺顺前清时期的经历弱化了,凸显了“四十九标”将其引申为“革命军队(revolutionary army)”,这在原文中是没有体现的。此外,原作在介绍顺顺的身份时,用了三个不同称呼:“掌水码头的”、“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船总”,这些称呼都显示了顺顺是晚晴民国时期流行于川黔湘西一带的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或称袍哥会)的地方首领。(谢江南、刘洪涛,2015)但是戴乃迭将其统一用“wharf-master”替代,为顺顺的政治身份洗白,足以看出译者的用心。
2.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
戴乃迭是一位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女性译者,在她的译本中,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挥,尤其是80年代时,翻译了一系列的女性主义作品,向西方世界展示了女性在中国当时历史情况下的生存环境和境遇。在《边城》的英译本中也是如此,译者同情女性,将原文中“妓女”的称谓都采用“these girls”、“the women”、“that particular woman”等委婉语替代。除了采用这种直接手法之外,译者也采用了间接手法,通过降低男性的形象来对比、抬高女性的形象。
例(2):
原文: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沈从文,1981:236)
译文:…and shrank from spoiling his own record as a soldier…(Gladys,1981:7)
这是原文对翠翠父亲的描述,作者是对他持赞赏态度的,作为一名军人,宁愿死去也“不便”让自己的名誉受损。但是译者却对此进行了改写,使用了“shrank”一词,将翠翠的父亲改写成为一位胆小怕事的军人,以此降低了其身份,改变其人物形象,这也会导致读者将翠翠母亲后来的自杀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父亲的胆小、畏缩。
3.诗学规范的影响
“语言不仅从形式上确保作品合乎语法,还要从语用方面总是要反映特定的文化,因此翻译也总是要将不同的文化‘自然化’即使其符合接受文化的习惯。”(何绍斌,2005)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确实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可是译者切不可将文学作品中文化全盘托出,必须考虑译入语的诗学规范,使译文符合接受文化中的读者习惯,译本才能更广泛流传,发挥其文化传播的作用。
例(3):
原文: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沈从文,1981:264)
译文:I want to eat my cake and have it.(Gladys,1981:38)
这句话出自大老之口,是他选媳妇的标准,他喜欢翠翠的摸样,但是又怕翠翠太娇弱,于是用这句古话,表示自己内心的矛盾。原句对仗工整,句尾押韵,读来朗朗上口,但是译成英文时,若要保留原文的内容与形式,就会损害译本的可读性,因此译者考虑到读者接受,将原句进行改写,使其符合译入语的诗学规范,用英文中具有同样内涵意义的表达方式代替。
例(4):
原文:下棋有下棋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沈从文,1981:278)
译文:Chess has its rules:the castles and knight have to move in different ways.(Gladys,1981:53)
大老想娶翠翠,派了人向翠翠的爷爷打探口风,爷爷用此句向此人表明凡事都要讲个规矩。“车”和“马”都是中国象棋的棋子,英语文化中没有这种象棋,译者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将“车”和“马”分别译成了国际象棋中的“castles”和“knight”,使得译文更加流畅易懂。
戴译本的《边城》中的“不忠实”现象是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影响的结果,是译者对原文的故意不忠实,译本的成功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果,也得益于译者遵守译入语诗学规范,考虑译入语读者的习惯,将原作翻译得流畅易懂。但是戴译本也同样存在一些改写失误之处。
四.《边城》英译本的改写失误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曾说:“翻译是永无止境的。”(Newmark,1982)孙致礼也曾说:“天下绝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译作,即使再好的译文也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孙致礼,1999)同样地,戴译本《边城》中也存在着改写失误。译者尽其所能让译本符合译入语诗学规范,却损害了原文的逻辑关系,不过这些错误其实可以通过分析上下文逻辑来避免。
例(5):
原文:小溪宽约二十丈。(沈从文,1981:234)
译文:…some twenty feet wide…(Gladys,1981:5)
这句话描述的是翠翠家门口的小溪。“丈”是中国的长度单位,现在不常用,英语文化中没有这种单位,常用“英尺”来衡量,但是“英尺”与“丈”是不对等的长度单位,译者不能直接套用。原文二十丈约等于67米的小溪,成了译文中二十英尺约等于6米的小溪,这差距是非常大的,损害了原文的内容。若翠翠家门口的小溪只有约6米宽,何来后文的“限于财力不能搭桥”以及“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
例(6):
原文: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沈从文,1981:243)
译文:Short-term engagement,long-term“marriages”,or a temporary retirement…(Gladys,1981:15)
这句话描述的是那个时代湘西的“妓女”的生活。译者将原句中“一时间的关门”中的“关门”理解成了“retirement”,这是不正确的。不同语境下,“关门”具有不同的意思,而在这句话当中,通过后文的总结句“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可以推断出这里的“关门”绝不是“retirement”的意思,它也是妓女们进行交易的形式之一。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对汉语的理解必须理清语境,否则就会误读,偏离原文的本意。
例(7):
原文: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沈从文,1981:253)
译文:Quiet,Brownie!Never mind him!(Gladys,1981:26)
这是翠翠第一次与傩送见面时说的话。翠翠误解了傩送,以为自己受到羞辱,于是对他说话毫不客气,借用对狗说的话继续讽刺他。这句话有两层意思,才会让傩送误以为“是她要狗莫向好人乱叫,放肆的笑着”。译者将这句话翻译为“Never mind him!”却在清楚地表明翠翠让狗不要管他,是因为他不重要,因此就不符合原文的语境了,毕竟这句译文怎么也不会让傩送听出歧义,与下文逻辑混乱,让读者摸不清头脑。
虽说没有一个译本是十全十美没有误译的,但是译者还是要尽自己所能,认真推敲上下文,不能为了适应译入语的诗学规范而损害了原文的逻辑关系,从最大程度上避免误译,保证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从中也可以看出译者之所以会忽视上下文的语境,出现改写失误,正是由于对汉语的语言文化理解得不是很透彻,才会对原文的语义理解产生偏离。
五.结语
戴乃迭英译的《边城》在国外的接受度较高,广受好评,因此对它的研究必定会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较高的借鉴性。基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本文探讨了戴乃迭《边城》英译本中的“不忠实”现象,分析得出,中国文学外译毫无疑问受到特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制约,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也在此基础上发挥着作用。此外,译入语的诗学规范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因为只有译入语读者接受的译本才能发挥其文化传播的作用,才能引起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兴趣。但是译者不能一味地为了适应读者的习惯而损害原文的逻辑关系,译者要认真推敲上下文,保证译本的流畅度,才能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