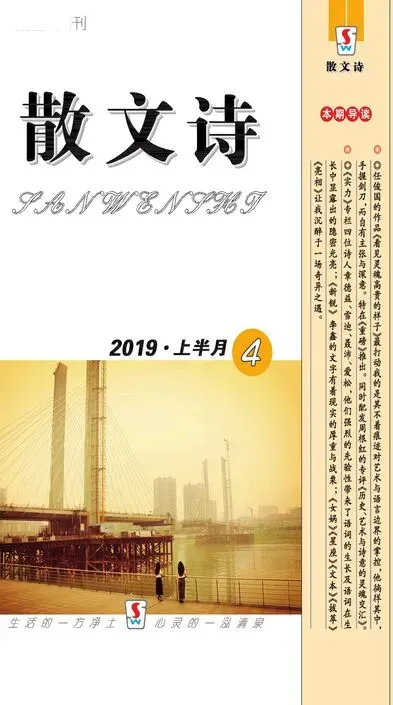蓝色之墙
2019-11-23甘肃王晓燕
甘肃◎王晓燕
粟跃资 图
之 一
纷飞倾斜,终会随同大地安宁。降下来,坠向素常、归途时的安宁。
那些草叶和树枝正在枯萎,那些行走过的路途、目光和深处的视力抚触过的柔情,正被雪覆盖。覆盖,是我铺满草叶、日月星辰、你和我脚步挪移的存在和未来。
我生活在这些事物里。我将双脚置于荒滩、沼泽,以及思想、口舌、人体的裂隙,我靠这些感知生命,靠这些活着,靠它们每天分泌出来的戈壁、风暴雨雪,还有阳光岚露而生活。并且,我还有可能会在这些事物中死去,我死去,就像被戈壁滩上的烈日一寸一寸晒死。像为爱和某种梦想而死。
当我越向内,越靠近那些困境绝望,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那些事物的诡计裂隙和风暴雨露的欢宴之中。
当我越向内,越远离人群、言论及规则,我就越存在。越是一棵孤卓之树,越能知晓风暴雨雪,越能懂得一枚石头的寒孤、一个现代人不能轻易懂得和经受的幸福。
我生活在那些事物里,我拥有的荒滩、戈壁、思想,以及我所触闻到的口舌与人体的裂隙,我所经受的这些事物,与我肌肤相亲,是我全部的浓情、爱意及等待和遇见,是我的爱情,以及梦想和欲念。
我的灵魂、我的精神于某处领域的沉淀,注定要在它们中间刷洗、刮搽,注定要在绣口锦心之外燃起激情。
我在我和那另一个我之间抗争、漂泊、游离,在思想、口舌和人体的裂隙间辨识、拒绝、回应、唾弃和向往。
穿越那蓝色的孤寂之墙。在巨大的逝去和未来的词语中间,我是如此枯贫无力。我围绕着它,围绕着它们的原始属性,经由你,它的孤独华丽的嗓音永远在那——与语言夹杂在一起不能被剥离的青春,注定要被生命的原始属性收容包藏。
注定这很艰难。书写,回忆。如若不是注定要坠向归途,如若我的眼不是因为你而流露柔情,如若不是注定有时光纠结处的距离。
风声中的戈壁。
我手指、思想甚至感情的痕迹有一部分会到达你,被留存、置放于你的时间、视线和内心,我暂存于某段时光的容颜会被你的手指和时间翻卷。
我在暗夜听见你的目光穿越那些汉字和诡计时的会心、怜憾。我咬在舌尖的话语,正在树一样盛开。未能告知你,时间被白昼和黑夜传送之中的颤音。我手指的动作、思想及感情的痕迹被你了握于心,那些被戈壁、玫瑰、烈日、雨雪以及茶水、咖啡催落了的黑发、青春和语言,你注视我走过的季节、秋日绵延的脚步。
被幻觉和此时的存在延拓而出的深情充填后的记忆愈加完美。仿佛是我们为自己重新添置了更多的温情,重新增生了另一些时间、存在,好让后来的记忆比现实完整。
雪降下来。寂静。寂静擦亮生命之晦暗。
那些向上的云朵,那些时光纠念处摇摆不定的忧愁、欲念和唤声。那些戈壁、荒滩和困境,这样安静而死心踏地地坠落和沉着,心界的传奇,无数个刹那的时光里,我仰赖于那些金色的尘埃,那些无可理喻的柔情,就如同是我对自身一种不无歉疚的柔情。
浮尘野马。那凋敝的在深色树干上发黑、发黄的高枝,终将开掘深处的视力。
正是它们:戈壁,玫瑰,手指的动作,茶水,咖啡——正是它们,催落了的黑发与浓情,绽放的生命,打开又关闭,死去又重生,不可被言说,不能被复制,一直以来,散布着孤寂,并把独孤和华丽堆砌成一道蓝色之墙。不是传奇,不是信仰。只是一股柔情、一种方式、一道深处的被宿命开掘的视力。雪降于大地的静寂,海泛起芬芳的幻觉。
之 二
茨维塔耶娃站在无尽的黄昏。我们的小镇。只因为我多回了几次头,有些声音扬起,有些语言掉落进身体里。经过茨维塔耶娃的小镇的风里,会飘散不可被摧毁的柔情。
若“窗口大朵牡丹花”,则,更让我安宁。小镇,不会是我的故乡,或许是你的故乡。我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在这里成长而不会觉得陌生和落寞。相反,她终寻到奢求了一生的安宁。“而你无声深爱着我,以生命最坦诚的方式。”
你的目光蜷曲成早在我梦中固定的姿势,我的视线终穿透我的身体,那深处的语言,说出来,与不说出来,同样妖娆芬芳。
用我们擅用的语言和文字,制造出那些布景和气味。以我们的情感,飘漫出那富有生命质感的空气、阳光、戈壁,以及靠你的力量和热爱种植而出的我们的家园和树,枯燥无力的沙漠、荒滩和烈风。我愿意相信自己的决心,像一棵树从沙漠里挺拔而出。
我也愿意相信,夏天来了,窗下的花,就开了。我为这番等待激动难安。那排除了诡计和技巧的语言和情感,一如淡花盛开。
一撮烟灰被你的目光接住,一个句子一个词语被你轻斥一声。清晨来了,黄昏逝了。
我站在这里,站在白天和黑夜,四季不那么分明,风是季节的信使,是我的忧愁欲念。我站在你和树的身旁,风、四季和我们,和树一起蓬头垢面。
属于你,也属于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我的幸福会因为听到你的唤声而终于涨满。
窗口,大朵牡丹花。我看你,和树倾斜了影子。我的长发随同烈日和无尽的黄昏,随同你的情感和欲念疯长。
我不剪掉它,如同不剪掉四季和风沙。
阳光穿透碎花棉布。慵懒之心彼此张望,彼此依赖。
那深处的语言忽然跌落。深处的视力。
始终学不会与你休戚与共。
日子不再繁复,只是一株要在季节内外长大的树,甚至没有水源,没有雨露。只是一缕风和阳光。而我的发随同无尽的黄昏和烈风、随同你的情感和欲念疯长,我不剪掉它,如同我不能剪掉属于我们的四季和风沙。
我和你一起期待。期待一个芽苞,一片叶子,一处暗处的水源;期待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进窗棂,碎花棉布的窗帘悬垂着,纯棉的质地和温柔。期待手脚、心事摊成最原始之态的你和我的无尽黄昏,我们的慵懒之心彼此对望,彼此依赖。
你的手指穿过我长及脚面的头发,你的目光穿透深处的视力,深处的语言忽然跌落,大朵,大朵。我来不及敲击,手指和思想最放松的自然的敲击,触处花开。我猜你正要说,某个不可被言说的词。那是我们不再存有目的和技巧的生息。最切近生命的抒情。
烟缸。水杯。一个小菜园。三朵,两朵,生命之花。几排被我们的手指和赞叹翻阅的书籍、阳光、青苗、风沙、稻草、还有爱。烟灰抖在你的指尖、我的目光,季节于是平复下来。有雪忽然开放。日子短暂停顿。
你看不出来,我依然不能如你般喜欢上郁金香的芬芳。我们张口争吵,却发不出声响。灵魂恒久缓慢地攀爬,不再独孤倔强,学会与你休戚与共。
只是一棵树,开出孤独芬芳花朵的树。彼此忘记赞叹和欣赏。此刻,站在窗前,以我们各自习惯中的姿势。你说,唯愿这种缓慢,能更缓慢一些,即使,你会越过我的脚步,我会,重新跌落进那切近血管的河流。
你说,想站在上帝面前,指着我说,这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
我想,即使这样,我也不会贬低自己。或者,这样,我便不会贬低自己。我也不会责怪自己,责怪这窗前的时光,因为你说,生命终于能以生命的方式和温度延续,而非它物。
那和语言夹杂在一起的涛声,切近皮肤和血管的河流。我不能停止手指敲击的动作,不能停止接纳想象和茶水的思虑,玫瑰和绝望催落的语言,是否仍会如同树的血液,被你和我的四季分泌而出,这已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