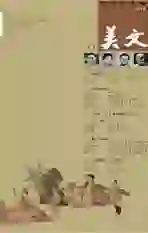我们的观念开始转变了
2019-11-21穆涛
穆涛
一
灯塔,其实也是路灯。
普通的路灯照耀眼跟前那一截子路,照寻常路。灯塔也是照耀寻常路,但当一艘远归的船处于危机和迷惘中的时候,就不寻常了。灯塔的魅力在于站位高,而且有方向感。
学问家与一般学者的区别,不在知,在识,在于清醒的认识力和洞察力,在于给人带来方向感。梁漱溟说,有主见就是学问。学问是以学的态度去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有了自己的突破和建立,就是学问家。
张华兄是学问家。
二
今天是大雪过后的第七天,距离冬至还有五天。按照中国人的老黄历,一年开始的第一天是冬至,这一天地热由地心向上升腾,古称一阳,“今日交冬至,已报一阳生”“冬至大如年,纳履添新岁”。二阳在小寒与大寒之间。三阳是立春那天,阳气突破地表,由此三阳开泰。我们中国人认识中的新年第一天,与“西历”的元旦,相差一周左右的时间,12月22日前后到1月1日。这个差异是中西方观测天象所占据的地理位置形成的,中国人的老祖宗站在黄河,确切的说是站在渭河流域观天象,察地理。西历的落脚点在欧洲,他们那个说法,还有一点人为因素,以耶稣诞辰日为一年的首日。
张华兄是治中西文学比较的专家。我试着按他的方法,比较了一下中国与西方纪年的差异。
按我们中国人的计时方法,今天距新的一年开始还有五天。
门前街面上的两排桐树,叶子都枯黄了,但并不落下来。我三十年前开始住在西安的时候,最感动的就是这座城市的这个细节,满树的叶子黄了,一枚一枚满是丰富的皱折,却不飘零。有风的日子,依旧相互欢欣着击掌而歌,等到第二年新叶萌动的时候,只几天的功夫,它们便集体告老归根。每年春天的这几天,我都会在树下慢慢地走,看这群老树叶全身而退的壮观场景。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叶子坚持着走完整个冬天呢?物候的变化是天大的科学,是硬道理,让人们探究着并费解着。而我有时就简单地认为,这些老叶子是负责任的遮羞布,不想让这条街上的树赤裸着身子呢。
我们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家们的写作是多元丰富的,但文学研究领域却单调着,也相对滞后。文学研究者们思考的东西与作家们思考的东西并不在一个层面发生碰撞,评论家们对作家的作品或解读,或诠释,或欣赏,或挑剔批评,但严重缺失着文学研究的导航功能,甚至对文学原理的一些基本认知也是错杂不整的。从这个角度讲,张华兄的这些文章,也是遮羞布吧。
三
我选取张华兄两点认知做例子:
以前学汉语的外国人少,不知道他们的母语作品翻译到了中国变成什么样,现在学汉语的多了,看到他们的母语和名著翻译成中文后,每个字都认得,但整部作品却不知所云。
……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母语是西班牙语的译者,他告诉我,以前学习英文,发现英文版的《堂吉诃德》与原文差异很大,有明显的向英语国家文化习惯靠拢的倾向。后来他学习了中文,发现无论从西班牙语版翻译来的中文《堂吉诃德》,还是从英文版翻譯来的《堂吉诃德》,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西班牙人生活的文化“味道”丧失殆尽,有的章节甚至荡然无存,最后好像只让中国读者看到一位像孔乙己一样可笑的“大战风车”的人。
……
我本人在尝试一种保持“原汁原味”的翻译,也就是说,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字、词、句和语法结构,当然是使用汉语的,要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但是语言在整体上要保留母语的风格和它自身的文学性,让读者能体会到外国人母语的“味道”,也就是写作风格。这就像音乐,让人一听就能分辨出是西班牙风格,俄罗斯风格,还是阿拉伯风格。
以上三段是说文学作品翻译现状的。他这么说文学和文化:
文学是最好的语言载体,也是最好的文化载体。
语言文字的区别实质上就是文化模式的区别,什么样的话语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文化模式。
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学作品是最好的担当。
中国饮食文化,中国酒文化,中国茶文化,中国功夫文化“走出去”,并不代表着中国的文化真正走了出去,而只有文学真正被世界所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才算是走了出去。
文化走出去,从“自信”和“信自己”开始。
这些话都是普通的,但于当下却有着穿透力。中国的新文学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发端的,基本上是全方位向外国文学,主要是向西方文学学习,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包括文学翻译,几乎学习了一百年,至今仍在矢志不渝的学习着。比如散文这个门类,分列着杂文、随笔、小品文等名目,就是向不同国家学习的“果实”。这几年,又最新进口了一个“非虚构”品种,一个文学门类,就这样分崩离析着。而在文学评论领域,西方的文学观,方法论,话语方式,占据着主导席位,乃至“几乎是在以西方的肺叶呼吸”。如果不用这样的方式写评论文章,被认为是“没有理论思维”。
一个国家的文学,没有自己的标准。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对当代文学研究界,还能说些什么呢?
四
有预感的话,叫预言。张华兄说这些话的方式有点傻,像愚公,又像挖井,一锹一锹的,也不紧不慢,但他在挖自己的井,井底有深层次的泥土,水是清亮的,且富有钙质。
他说文化品格的独立,说文学教育的疏离和偏执,说国学与汉学,说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说崇洋媚外何以发生,说文学中的“人性”和“人性化服务”的区别,说民族的和古典的。他在说到文学与多元时代关联的时候,话锋一转,“伊朗和沙特断绝外交关系的日子,也是朝鲜第一枚氢弹试验成功的日子”,话是具体的,但话外音里有视野,也有格局。
他对文学中人性的理解给我印象深刻,他傻傻地做了分类,把具有人性的放在一边,把不太具有人性的放在一边,把完全没有人性的剔除出去。这种傻的下边,藏着他的大方和大器。
这些带预感的认识,还兆示着另一种预感:我们的观念开始转变了,我们今天的文学已经在向有文学规律的那个地方在进步,虽然还有一点距离,像我今天写作这个文章的时候,距离中国时刻里新的一年到来还剩五天的时间。
五
我一下子写了这么多,核心是想对张华兄写作这本书时的严谨和达观表达敬意。严谨表现在虽然文皆不长,但观念自成体系,守自己的体统;达观则表现在对当下的文风,译文风,文法等诸多方面的认知上,满怀理想。这些文章多数是给《美文》写的,他受贾平凹总编辑之邀,担任《美文》杂志“汉风·孔子学院散文专刊”的主编,除了繁重的编辑工作,还需要每一期写一篇卷首语,积淀三年成就了这本书的大半。我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在其中凝聚着,我是他的责任编辑,是每个月第一个读到他文章的人,向张华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