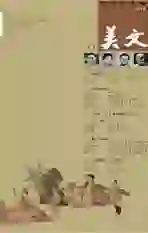初恋的回声
2019-11-21王子君
王子君
时隔十年有余,我写下这一行字。
我不再悲戚,我却依然满眼含泪。清明过后,气温下降得厉害,但午后
的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落在我的书桌上,透明耀眼。我感到异常温暖。
我的初恋,因为温暖而永恒。
——题记
2008年盛夏的那个清晨,我的电话铃声不祥地响起。电话说,他走了。
他,是友皓。因为他像极了三浦友和,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友皓”。他从来没有使用过,除了我,谁也不曾喊过他“友皓”。就像他给我取的笔名“野艾子”,无人知晓,我也从来不用。
我没有哭,我只是泪如流泉,涌流不止。自责、痛悔、悲切,像罪恶一样紧紧地缠绕住我,令我无法呼吸。就在昨天,我请年少时我们的密友去看望他,去向他承诺三天后我回家乡去见他最后一面。密友说,他幸福地笑,眼睛闪闪发光。然而今天清晨,他就死了。密友安慰我说,他一定是确认你要回来见他,安心了,又不想让你看见他形容枯槁的模样,决意永别。
但是,我无法原谅自己。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不能自拔。
两个多月前,大约是6月份,我接连收到由同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发给我的短信,短信内容充满了爱与美、善的祝福,热烈、真挚。我请问他是哪位高友,他不回复;我多次回拨电话,他始终不接。我以为是哪个好开玩笑的朋友拿我开心,事情也就过去了。到了8月,我回到家乡给母亲祝寿,宴席过后,有朋友透露说,友皓两个多月前得了绝症,医生判他只有三个月好活,如今命不延一月了。震惊的刹那,我想起那些神秘的短信,恍然大悟,是他,是友皓,是他在刚刚确诊之际给我发出的短信!他是在向我求助,也是在向我告别!
我很快镇静下来,通过密友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段联系上了他。他是那么惊喜。当他承认那些短信是他所发、十几通电话是他不接、他渴望得到我的帮助却又不愿惊吓到我的事实时,我泪如雨下。我为自己那曾引以自豪的第六感却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失去感应能力而痛心。如果我能第一時间得知他的恶讯,或许能在精神上成为他对付恶魔的一剂良药……
他在电话里笑声朗朗地安慰我说,你不要哭,我不怕,死亡不过是生命的一部分。他说,他终于听到我的声音了,这久违的、他一直渴望着的声音。他自信地说他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并正在好转,他一直以他是我的初恋而感到骄傲。现在,他更是再无恐惧,我的出现将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他不会死,他甚至怀疑是误诊了。他相信奇迹。
他说话的语气和醇厚的声气完全迷惑了我。他不是一个病人,至少,他不是一个绝症病人,他的生命不会只剩下一个月!
于是,在他的密友和我的密友的劝说下,我打消了去和他见面的念头。我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里,我不能给世俗留下流言伤害各自的家族。那些关于我和友皓初恋的传说,二十几年里像暗香一样地浮动在这座小小的山城里,眼下如果去见他,暗香或许就会成为暗雷,引动惊天的爆炸。不见,期待他康复,期待生命真的出现奇迹,期待一切安好如初。
怀着莫名的希望,也怀着一份忐忑,我结束假期,回到京城,一面工作,一面等待着我的新书《蓝色玫瑰》的出版。《蓝色玫瑰》是我以家乡为背景的一部中篇小说,讲述一个爱与生命在绝美的风景与温暖社会中神话般重生的故事,我希望友皓能读到这部作品,从中汲取到战胜病魔让生命顽强延续的力量。
接下来的几天,家乡不断传来关于友皓病情的消息,时而恶化,时而稳定。密友去看他,他说出了心中的愿望,希望见我一面。而且,为了更安静的治疗环境,他决定住到医院去。密友流着泪说,她没想到美好爱情的故事,竟发生在她的眼皮底下,发生在她最要好的朋友身上。
友皓住进了医院。我第一时间拜托密友去医院探望友皓,并转达我的决定。我计划三天后一拿到《蓝色玫瑰》样书,便启程回家乡见他最后一面。我要将书中最美的段落念给他听,以此回馈他最初的爱情。密友说,当他确认我将回去见他时,他的眼睛放出奇异的光亮,他虚弱的脸上出现幸福的笑容。
为了三天后回家乡看望我行将死去的初恋情人,为了我的决定不给双方家族带去新的矛盾,我特地给家人打电话强调我的理由:友皓是我的初恋,最宝贵的是,他没有伤害过我的情感,他将我放在他心里二十多年,这样的爱情是伪装不出来的;从文学意义上来说,友皓是我最关键的启蒙老师,没有他,或许就没有我的文学生活;我对友皓的情感已不再是一种爱情,而是出于人性的高贵与善良。如果世俗认为这是爱情要非议我,就让他们非议去吧,我只希望家人不要因此困扰;友皓在生命遭受重大打击寻求我的精神支持时我却毫无感应,这也许间接地加速了他心理的崩溃。而前些日子在家乡时又没有去见他,为此我摆脱不了自责、痛悔的深重压力。我要勇敢地挣脱世俗的捆绑,给他最后的慰藉。我也给从未谋面的他的妻子打去电话,请求她看在友皓将要逝去的生命份上理解我回去见他的行为。
我感谢我亲爱的家人,他们是明理的,是高尚的,是人道的。他们理解了我,并一致同意我回家乡看望友皓。我也感谢友皓的妻子,在长久的有名无实的婚姻即将结束时,能够容忍一个她或许怨恨了大半辈子的影子“情敌”去向她的丈夫作最后的话别。
然而,第二天清早,也就是友皓住进医院的第二天,也就是密友代我向友皓承诺回去见他面的第二天,友皓死了。通报死讯的电话是他美貌的妻子打来的。
我感到万箭穿心。我呆坐在沙发上,任泪水无声无息地涌流。那被晨阳照得温热的屋子,阴冷得像冰窖。我的眼前,漫过我和友皓的一切。
那一年,我17岁。单纯、懵懂的生命,却在不知不觉中迷上了文学。我的密友见我喜欢读诗歌小说,便将我带到她的邻居哥哥友皓住处借书。友皓是个已经参加工作的文学青年,在小城里早已小有名气。他英俊得就像正火遍中国的日本电视剧《血疑》的男主角,他的工资几乎全花在了购买文学书籍的事情上。刚刚涌进中国图书市场的外国文学书籍,如雨后春笋般的中国文学期刊,在友皓的书柜里琳琅满目。一个喜欢读书的女高中生和一个热爱文学的男青年就这样相识了,那最初的爱的种子可能就在这一瞬间种下。其后,借书,还书;再借书,再还书,循环往复,爱情的种子悄悄萌芽。夏日傍晚,我们去城边的小河边约会,躺在青青的草地上朗读那些我们认为最有诗情的诗句;冬天,我们坐在炭火不明不灭的火柜上,看他创作的文采飞扬却未曾结尾的小说。我们手握着手,头抵着头,心连着心。四目相对时,眼睛里流淌着蜜一样的爱情。然而,我们却不曾想过偷尝禁果。纯洁的爱情啊,在那些令我精神滋养丰润、文学素养节节生长的日子里,镌刻进了我的灵魂。
我从梦中醒来,为“灵魂”的真实久久震撼。然后,我的心境突然变得平静异常。我依然悲伤,但不再迷茫自责。我相信友皓是希望他留给我的永远是他最美、最美好的形象,是我初恋的那个风流倜傥的文学青年。
这一晚,我再也没有入睡。纯属个体的情感经历,在这个梦境后,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震撼、最悲情、最奇幻的一次事件,化作对“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终极哲学命题的思考。物质生命与虚幻灵魂、俗世爱情与柏拉图精神、生与死亡、终结与永恒,种种与爱、与生命关联的符号纠结在一起,让我的心灵难以承受,却又欲罢不能。
第二天清晨,我托家人按我的要求订购了鲜花花圈,送至友皓的灵前。花圈中的每一朵鲜花都富有深意,而这份深意,友皓当能切切地体会。唯有红色玫瑰,我没有配置。面对友皓的爱情,我已失去了为他献上红玫瑰的资格。在随后的出殡仪式中,我请密友代我送他上山,从我送的花圈中抽出一支粉色玫瑰掷入墓穴。密友一一照做了,然后她将电话举在空中,让我对友皓告别。我哽咽良久,深情地说:友皓,安息吧!天堂会赐给你永恒的爱,赐给你一切!
我的密友小菊,见证了我和友皓的传奇。小菊有着体操运动员般的身材,皮肤黝黑,似杏非杏的双眼、高低适中的鼻梁、欲翘非翘的嘴唇,非常有机地组合在一张圆润的脸庞上,散发出洋气十足的美感。她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专,毕业分配回县城后,遇见了她的爱情,一位白马王子式的男子。后来,小菊下海经商,开茶馆、开KTV,生意兴旺发达。每次我回家,我们必会见面掏心掏肺地畅聊,那份少女时代建立的亲密情感,从未因为生活空間的不同而有所淡化,反而因为我与友皓的初恋,早已胜过了普遍意义上的密友之情。
人的情感,最纯的莫过于初恋,最痛的莫过于死亡。友皓给了我最纯的初恋体验,也给了我最痛的死亡感受。在我放下对他的爱情时,他却将我深藏于心;在他带着对我的爱死去的时候,我对他的情感却升华为更为广阔意义的纯纯的爱。从纯粹到纯粹,从男女恋情到对人类悲悯之爱,友皓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爱里永生。
那天下午,北京的天空像火烧一样,漫天红霞。而《蓝色玫瑰》的样书到了。那梦幻般的封面,那比《廊桥遗梦》还要美丽的爱情神话,我把它献给梦境中的友皓。
今天,我的回忆是冗长的,但我的文字,已是最简练的了。我仿佛看到友皓正在至纯至美的天堂谈情说爱,那甜蜜的笑容已是全然忘记了人世间曾有过的爱与荣光、痛与绝望。我想起友皓第一次为我朗诵诗歌的模样,耳畔回荡起他饱满、激情而又温柔的声音: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友皓朗诵的是我和他都热爱的诗人北岛的《一切》。我和友皓的一切是从这一首诗开始的。如今,我觉得这首诗映照亮了我和友皓的纯真爱情。
这是我的初恋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