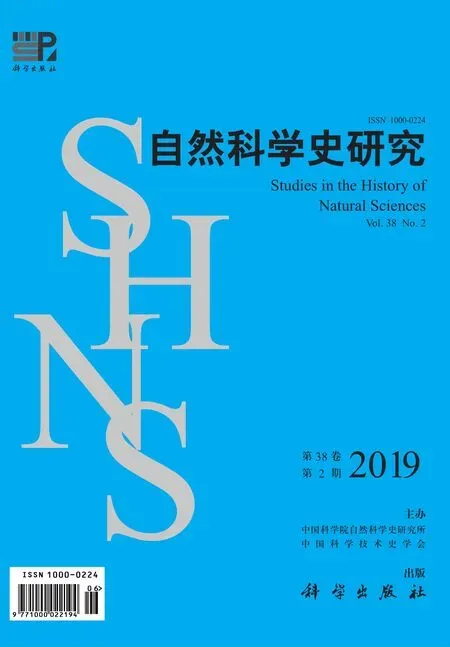陈仅《艺蕱集证》考述
——兼论清代甘薯在陕西的引种与推广
2019-11-21熊帝兵
熊帝兵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陈仅(1787~1868),字余山(亦作渔珊),号涣山,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清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自道光十三年(1833)起,先后任陕西延长、紫阳、安康、咸宁知县,宁陕厅同知等职。陈仅为官期间,关注民情,推广农业技术,颇受百姓爱戴。他的生平事迹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倪根金曾考述过陈仅的生平及著述[1],郑继猛等人编制了陈仅年谱[2],朱艳霞则在倪、郑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陈仅的家世与交游等[3]。通过分析代表性著作,揭示陈仅的学术贡献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涉及《诗诵》[4- 5]、《竹林答问》[6]、《群经质》[7]、《继雅堂诗集》等[8- 9]。在学者的努力下,陈仅的形象逐渐丰满,其为官、为学的成就也越来越清晰。然而学者在介绍陈仅《艺蕱集证》一书时却多有含混之处,恰巧,笔者发现了一些与该书有关的线索,现对之作简要考述,兼论清代陕西引种与推广甘薯的曲折历程。
1 《艺蕱集证》其书考
道光《紫阳县志》在记载当地物产“红蕱”时,提及知县陈仅曾刊有《艺蕱集证》一书,“红蕱,山间亦种以助粮,然随挖随食。邑侯陈公名仅,刻《艺蕱集证》,劝以广种储荒,其法甚备”。([10],166页)当地举人杨家坤执笔撰写的《邑侯陈公去思碑》称陈仅在紫阳知县任上,“刊《艺蕱集》,劝民种植,荒政豫也”。([10],266页)杨氏所说的《艺蕱集》应当脱一“证”字。距离紫阳不远的石泉县也知道陈仅撰有《艺蕱集证》,道光《石泉县志》记载:“安康令陈仅所以有《艺蕱集证》书,劝民广种而切晒收储,以备荒歉。”([11],18页)之所以称陈仅为“安康令”,一是《石泉县志》纂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仅正在安康任上;二是《艺蕱集证》在安康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名中的“蕱”,《说文》未录,为陕西方言,指的是甘薯。道光《紫阳县志·艺文志》录有陈仅的《紫阳书事三十二韵》,其中“冬窖蕱丝谋久蓄”句原注曰:“包谷不可久藏,余谕民收晒蕱丝为备荒计。南山人呼番薯为‘蕱’,其红者曰‘红蕱’。”([10],241页)陕西还有其他地方也将甘薯称为“蕱”。光绪《沔县志》在介绍阳芋(马铃薯)的优点时说:“胜红蕱,尤甚芋头、茨菇,亦胜山药。”[12]光绪《白河县志》记载当地“所产惟包谷、红蕱。”[13]安康人张鹏飞在《修关中水利议》中说:“薯有红白二種,陕人呼之曰‘蕱’。”([14],72页)也有史料将“蕱”写作“苕”,以四川地区较为典型[15],陕西部分地区也作“苕”,如嘉庆《汉中府志》记载:“红苕,一名薯,蔓引于地,茎微赤,叶似山药,苕生根下,状如萝卜,红色。”[16]相同内容也见于道光《三省边防备览》[17]与民国《汉南续修郡志》[18]。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载有《陈仅传》,其中提到:“(陈仅)刊《艺蕱集证》一卷,《深宁年谱》一卷。《蕱艺集证》者,以包谷不可久藏,谕民以收晒之法也。”[19]根据上下文,“蕱艺”显然是“艺蕱”的倒误。陈仅自己也提到过撰写《艺蕱集证》一事,在其《捕蝗汇编》之“论不食之物”条下,以案语的形式说明番薯的块茎在土里,为蝗虫所不能食,并注曰:“仅任紫阳,劝民种薯,著有《艺蕱集证》一书,俟续刊。”([20],3501页)但是,关于《艺蕱集证》刊行与流传的信息却一直不清晰,就笔者阅读所及,各书目对《艺蕱集证》的著录仅见一处,即《中国农业古籍目录》的著录:“《艺蕱集证》一卷,(清)陈仅撰,版本不详”,标注此书藏于南京图书馆。[21]笔者亲自到南京图书馆查阅,发现该馆实际未藏此书。
《中国古籍总目》是“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主要的成果”,首要特点是:“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二十万种。”[22]但它没有著录《艺蕱集证》。借助“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笔者依然没能检索到满意的结果。学者对此书的提及也多有模糊之处,如倪根金在同一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曾质疑此书是否刊行,后半部分又根据《中国农业古籍目录》的著录说:“看来,此书不仅刊刻过,而且还收录他书。”[1]同时,倪氏对此书与《邑侯陈公去思碑》中所说的《艺蕱集》关系也不确定,“此《艺蕱集》,可能是其最早的书名,即使是分成二部书,二者之间也有密切关系。”[1]郑继猛在相关成果中将“苕”写作“蕱”,并作简单介绍:“考虑到山民初次种苕,缺少技术与经验,随即编写了《艺苕集证》一书,散发民间,教民种植技术。”[2]
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为《艺蕱集证》的搜寻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在著录陈仅的另外一部著作《济荒必备》时它提到:“仅于道光十五年官紫阳知县时,作《艺蕱集证》,又于二十二年在安康知县任时作《济荒必备》。后并合二书为一,分子目三,曰《辟谷神方》、《代匮易知》、《艺蕱集证》各一卷。艺蕱者,种番薯也。”[23]指出了《艺蕱集证》与《济荒必备》的关系。事实上,学界对《济荒必备》的研究亦少,对该书的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晰。《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此书为一卷,不但卷数上存在差异,书名也误“济”为“救”。[24]倪根金认为卷数有误,应当为三卷。[1]但是清代浙江钱塘人吴庆坻在《蕉廊脞录》中谈及陈仅著述的时候提到:“所著《济荒必备》一卷、《捕蝗汇编》四卷、《南山保甲书》一卷……”[25]明确提到有《济荒必备》一卷本的存在。
陈仅在《济荒必备序》中说:“道光十五年,仅自延长量移紫阳,见山地硗薄,民鲜盖藏,惩壬辰癸巳之变,仿东南法,劝民种番薯以备灾,于是为《艺蕱集证》一书。既而调任安康。二十二年,春夏不雨,民心惶惶。仅急为思患预防计,又成《济荒必备》一书……岁终封篆,民事既阑,回念二书仓猝成编,其板移存紫阳东来书院中,难于就印,因取旧本重加增订,合二书为一,厘为三卷。两书均为济荒设,故仍其旧名,总颜之曰《济荒必备》”。([20],3983页)可见,的确存在《济荒必备》一卷本,且是最早的版本,其中不包含《艺蕱集证》。而《济荒必备》三卷本则收有《艺蕱集证》。《中国古籍总目》“集部”著录了《陈余山集七种》不分卷,未列子目[26];“丛书部”著录有《陈余山所著书七种》,子目列有《济荒必备》三卷,藏中科院[27]。笔者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中检索到另外三处藏有《济荒必备》,(1)济荒必备[DB/OL].[2019- 05- 24]. http://202.96.31.78/xlsworkbench/publish;jsessionid=5723E522EEA79DD6F0A5F52851F06CE3?keyWord=%E6%B5%8E%E8%8D%92%E5%BF%85%E5%A4%87&orderProperty=PU_CHA_BIAN_HAO&orderWay=asc.皆为三卷本(如表1所示)。

表1 《济荒必备》版本与馆藏(2)此表根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检索与《中国古籍总目·从书部》整理。
2 《艺蕱集证》之主要内容与特点
结合前文《济荒必备序》与民国《鄞县通志》的记载,《艺蕱集证》应当收录在三卷本的《济荒必备》中。《中国本草全书》第124卷与《中国荒政书集成》第6册都收录了三卷本《济荒必备》,前者据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影印,后者据道光二十九年刻本点校排印,第三卷的卷名都题为《艺蕱集证》。除了《济荒必备》书首的总序之外,《艺蕱集证》卷首还保留有道光十八年陈仅为此书作的“原序”,阐述了撰书的主要原因:“陕西南山居民,素以种包谷为业,即有杂粮聊以代匮,未尝为盖藏计也……虑包谷不可(入)[久]藏,因仿东南法,劝民种红薯,切丝晒贮,以备偏灾。”([20],4007页)该序还交代了撰写过程,“顷伏读《钦定(援)[授]时通考》第六十卷所辑甘薯诸条……复就群籍略采数则,以资证佐。山署携书不多,未能广集,录成付梓,颁诸斯民,以为法式,颜曰《艺蕱(音绕)集证》。”([20],4007页)
《艺蕱集证》“原序”之后,辑录了13部重要文献中关于“甘薯”的内容22则(表2),全书取材广泛,当时甘薯种植与利用的代表性文献基本上都收入其中,如《钦定授时通考》、徐光启的《甘薯疏》、王象晋的《群芳谱》、黄可润的《种薯说》等。所录内容之后,加以案语,阐释陈仅自己的见解,补充旧文未见的甘薯种植与加工技术。末附《劝谕广种红蕱晒丝备荒示》、《劝民种蕱备荒六十韵》两篇,与道光《紫阳县志》所录两文内容吻合,系陈仅亲撰。全书总计约7500字,序言、案语与附录部分约占全部文字的三分之一。从结构上看,它虽是《济荒必备》三卷中的一卷,但是该卷首有序,末有附文,显然是一部完整而独立的专著。

表2 《济荒必备》本《艺蕱集证》之主要内容表
说明: 此表根据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984~4013页《济荒必备》整理绘制。
《艺蕱集证》所辑录的文献主要涉及甘薯在各地不同的名称,气味、口感、外形、功能、加工,传入过程、生长特性、种植技术、食用方法、藏种要领、相较于其他作物的优势等。其中以录《群芳谱》的内容最多,达8则,黄可润的《种薯说》次之。全书重点辑录甘薯种植与藏种方法,创新内容主要集中在作者所加的案语以及两篇附文上。案语涉及内容较广,但更侧重于阐释甘薯的备荒优势。结合《劝谕广种红蕱晒丝备荒示》看,全书的核心内容集中于将甘薯切丝、晒干来储存以备荒上,陈仅在序言中对此就有提及,即传播东南地区的甘薯“切丝晒贮,以备偏灾”技术。([20],4007页)他介绍了浙、闽、江南、两广等省的经验,“或切如米粒,或如寸筋,不宜过粗,俗呼茹丝”,“欲久藏,则干条为胜,以藏窖中,磊叠透风,不致黦霉故也。其晒藏总以干透为度”。([20],4007~4008页)
该书的显著特征是密切结合陕西地区农业生产与生活实际,这一点在书名上就有明显体现。明清时期,诸多甘薯文献都以“甘薯”、“番薯”或“薯”为题,如徐光启的《甘薯疏》与陆耀的《甘薯录》等。陈仅不用“薯”而用“蕱”,甚至让外地人很难通过书名判断出此书的内容。对此,陈仅特别交代:“南山人呼甘薯曰蕱,从其土名,使之易晓也。”([20],4007页)书的内容也密切结合陕西地域实际,例如它在辑《群芳谱》中甘薯蔓枝饲喂牲畜的内容之后说:“陕西南山居民以喂猪为大贸易,卖之客贩,或赶趁市集。所得青蚨,以为山家终岁之用。贩者船载赴郧襄下游售之。其喂食则以包谷、构叶为主,特未知红蕱枝叶,亦中喂猪之利耳”。([20],4009页)它在录《种薯说》之内容后说:“直隶、陕西,土宜相近,可以知其利矣。因亟录之,以为吾民助。”([20],4011页)附于书末的两篇文章完全是根据紫阳县百姓生活与生产实际而撰写的。
不可否认,此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书中辑录了《南方草木》与《异物志》中的“甘薯”内容,显然不恰当。因为明代以前文献中的“甘薯”与明晚期传入的“甘薯”存在着明显区别。依据夏鼐的研究,《南方草木》与《异物志》中的“甘薯”“可能是今日学名叫作‘甜薯’(D.esculenta)的一‘种’,但也可能是普通薯蓣(D.batatas)中较为甘甜的一个品种。”今日所称的“甘薯”实际上是美洲作物“番薯”,拉丁学名为Ipomaea batatas,旋花科的双子叶植物,与明代以前的“甘薯”不同种、属,也不同纲、目[28],胡锡文[29]、戚经文等[30]也持相似观点。陈仅所推广的“蕱”是明代晚期才传入的“番薯”,而非中国本土“甘薯”。陈仅在案语中还提到:“王祯《农书》称蝗不食芋及薯。”([20],4009页)今核,王祯《农书》中所说的蝗虫不食之物为芋、桑、菱、芡,并没有提到“薯”。[31]另外,此书所辑内容大体按照原文献的年代先后作简单、机械排序,并没依据整地、种植、管理、收获、加工、藏种等生产逻辑组织材料,相关技术散布在文中各处,且有重复,略显凌乱。
3 《艺蕱集证》成书之前的陕西甘薯引种
甘薯在陕西的引种有明确的历史起点。乾隆十年(1745),陕西巡抚陈宏谋从成书不久的《钦定授时通考》中了解到甘薯栽种技术及其抗灾备荒优势,在本地还没有获得薯种的情况下,就着手布置引种的准备工作,于此年之初刊发了《劝种甘薯檄》,并提前印发了他亲自编写的“种甘薯法”。他说:“苟能觅得此种,如法栽种……特用刷印二千张,饬发该司,可酌量分发通省府厅州县并佐杂等官,及士民人等”。([32],卷20,《劝种甘薯檄》)此文的目的一方面是宣传甘薯之利,另一方面是动员官民“觅种”。同年四月,陈宏谋又发布了《劝种甘薯示》,包含了丰富的甘薯种植技术,涉及锄地法、藏种法、栽种法、收薯法、收蔓法等,再次动员各类人群四处觅种,“凡正杂各官,有闽、广、江、浙、蜀、豫之人,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缙绅商贾从闽、广、浙、江、蜀、豫等处往来者,带回布种”。([32],卷20,《劝种甘薯示》)
另据陈宏谋所刊发的《劝民领种甘薯谕》可知,截止到该年十二月,蒲城、潼关、临潼(今西安市临潼区)、兴平、略阳、甘泉等多地官员分别从江浙、河南、四川等地寻得了薯种,并从外地雇善种甘薯之人到陕西传授栽种技术。陈宏谋做了细致的部署,“谕令将薯种如法收存各该县,以待明春试种。有将薯种送到省城者,亦已发长安、咸宁二县,如法收贮。又四川李藩司将薯种送司,亦发咸、长二县,如法收贮。以上各该县所购存薯种,尽供本地种植而外,尚有多余,正可分散各该县,以为广行试种之计。”([32],卷22,《劝民领种甘薯谕》)陈宏谋以当时的省城为中心,由近及远推行甘薯试种,“谕知近省之西、凤、同、商、邠、乾六府州所属,各就附近有薯种之各县,相订于春和时乘便取种……其榆林、延安、绥德、鄜州、汉中、兴安六府州,或边地严寒,或离省较远,俟近省各处种成,由近及远,再为推广”。([32],卷22,《劝民领种甘薯谕》)
经过陈宏谋的推动,陕西的确有部分地区成功引种了甘薯,地方志对此多有肯定。乾隆《商南县志》记载:“甘薯,俗名番薯”,“乾隆十一年在河南南召购种,照陈大中丞《劝种甘薯法》,令富水关居民布种有益,今渐广。”[33]乾隆《鄠县志》记载当地土壤宜种红薯,注曰:“此抚军桂林陈公遗者。”[34]乾隆《咸阳县志》记载:“抚宪陈公条示劝导树桑”,“于前又奉发甘薯一种,质粗于山药,味脆于芋魁,犁亩分栽,如法灌溉,丛生滋长,食可耐饥。”([35],329页)民国《盩厔县志》引《恒州偶录》曰:“红薯,一名甘薯,以谓甜也,又名番薯”,“陈榕门先生抚关中日,从闽中得此种,散给各州县分种,惟盩、鄠水土相宜,所种尤多。”[36]各地方志所提到的“陈大中丞”、“抚军桂林陈公”、“抚宪陈公”和“陈榕门”指的都是陈宏谋。
有学者依据上述史实对此次引种番薯的效果做过总结,认为经过陈宏谋的推动,“番薯很快在陕西各地传播开来”。[37]何炳棣也认为自18世纪中期至太平军起义这段时间,川陕间的山地是甘薯的集中生产区域之一。[38]何氏将起点设在18世纪中期,显然是肯定了陈宏谋在陕西的甘薯引种之功。但是相对而言,对陈宏谋引种甘薯的效果持保留态度的学者较多,如陈树平认为陈宏谋引种甘薯的各县均在陕南,陕北传种较晚。[39]美国学者罗威廉论及此事时说:“据对陕西农业有着精深研究的魏丕信推测,该计划可能是个失败,当地农民对这种南方稀奇玩意的抵抗程度之强烈,很可能令一个乐观的巡抚难以克服。”[40]
笔者也认为此次引种甘薯的效果十分有限。依据前述《劝民领种甘薯谕》所引的内容可知,陈宏谋将更多的薯种集中投放到长安和咸宁,可见此二县是引种甘薯的核心区域,但是这两个县的县志中均没有甘薯的记载。陈宏谋重点推广的地区是西安、凤翔、同州、商州、邠州、乾州等六府州所属各县(厅),此六府州当时共含有47个县(厅),然而仅仅商州府的商南县,西安府的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盩厔(今周至县)、咸阳与凤翔府等三个府州的极少数县(厅)记载了陈宏谋引种甘薯的史实;同州、邠州、乾州三府未见记载。在榆林、延安、绥德、鄜州(今富县)、汉中、兴安(今安康市)等非陈宏谋重点引种甘薯的区域的地方志中,绝大多数没有陈宏谋引种甘薯的记载。另据生活于嘉道期间的张鹏飞总结,“薯有红白二种,陕人呼之曰蕱……南山近年歉收,四民恃此度岁。曩见盩、鄠有此,他邑则否……,而西、同、乾、凤不知广种,岂非坐失陆地之利耶?”([14],72页)说明即使是在陈宏谋当年重点推广的地区,直到嘉道年间依然没有完全实现甘薯的广泛种植。
或许正是因为陈宏谋的首次引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重修兴安府志》才将其功归于陈仅,“陈余山劝民艺苕,民食始足。”([41],34页)结合前文所述的道光《紫阳县志》、《石泉县志》所记载的相关内容看,兴安府之紫阳、安康等地普遍认可陈仅的劝种甘薯之功,而非陈宏谋。地方志如此记载似有不妥之处,却又在情理之中。陈宏谋在甘薯引种过程与计划中明确指出:“其榆林、延安、绥德、鄜州、汉中、兴安六府州,或边地严寒,或离省较远,俟近省各处种成,由近及远,再为推广。”([32],卷22,《劝民领种甘薯谕》)当时的兴安府并不属于严寒地区,而是属于“离省较远”的地方,不但没有被陈宏谋列在重点引种区域之内,反而被列在最后一位。
4 《艺蕱集证》对陕西甘薯种植技术的补充
甘薯引种的阻力来自多方面,但是基本可以排除“土地不宜”的影响。一是甘薯本身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雨不能侵损”([42],563页);陈宏谋也曾指出:“随剪随插,随种随生,天下易生之物,莫有胜于此者。”([32],卷20,《劝种甘薯示》)可见甘薯对土壤要求不高。另一方面,当地少数地区已经成功种植甘薯;清后期甘薯在陕西得到广泛种植的事实也从反面证明了“土地不宜”不是问题。陈宏谋当年的引种计划虽然明确强调从土宜的角度出发,但事实上,他却是从政治区划的角度做的规划,因为处于陕南的兴安府(今安康市)气候与土壤环境要比关中与陕北地区更适合甘薯生产,但是却被陈宏谋视为偏远地区,而未予以重视,这显然是推广策略存在问题。
但是从乾隆十一年(1746)至道光十八年(1838),已经历时近百年,兴安地区的确有了一定规模的甘薯种植,这很可能与陈宏谋的引种与推广有关,但是,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生产并不普遍,“查访紫邑山内薄地,小民间种红蕱以作杂粮,无关轻重。”([10],234页)老百姓对甘薯种植尚持怀疑或者是观望态度,陈仅说:“劝民种红薯,切丝晒贮,以备偏灾。申谕再三而听者寥寥,即绅士亦疑信参半。”([20],4007页)道光《石泉县志》记载:“安康令陈仅所以有《艺蕱集证》书,劝民广种而切晒收储,以备荒歉。窃谓五谷皆耐于久贮者,不独蕱也。”([11],18页)凭借笔者早年的农业生产经验,晒干了的甘薯丝或甘薯片,储藏时间的确可达数年之久,远超五谷。从道光《石泉县志》所载内容可见,该志的编纂者对甘薯干的耐久特性并不了解。
更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当地居民并没有完全掌握甘薯的特性,甘薯的功能没有被清晰地揭示出来,而相关技术也没有得到熟练运用。陈仅就曾说:“一人之私言,未易为浅见寡闻道也”,所以他才辑了诸多知名著作中的甘薯信息。考察《艺蕱集证》所辑录文献的编排,笔者发现,这些材料不光在总体上表现出时间先后的顺序,同时还有影响力由强到弱的顺序,显然是为了增强说服力,希望把更多的甘薯信息与技术传播给当地民众。陕西的地方志就不止一次提到技术因素对甘薯种植的制约,乾隆《咸阳县志》在介绍陈宏谋引种甘薯之功时明确指出,当地存在“愚民初试,未善栽培”的客观情况([35],329页);《重续兴安府志》也曾提及技术问题,“红苕:前志未载……故虽易生之物,苟不得其法,终不免于卤莽报也。”([41],35页)
客观地说,甘薯在当时虽然是引进不久的异域作物,但是其种植过程中的整地、播种、施肥、管理、收获等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旱地作物生产以及蔬菜栽培技术区别并不大,由于甘薯的生命力较强,某些技术操作甚至比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更简单,所以这些常规技术对甘薯种植的制约性不大。相对而言,藏种才是甘薯种植过程中的核心技术。薯种保存对温度要求较高,但是在西北地区,冬季的温度远远低于南方,无疑增加了藏种的难度。乾隆初期,福建籍官员黄可润将甘薯引种至河北,就曾遇到藏种技术的困扰。他由家乡寄种至无极县试种,种植、生长、结实都很成功,但是,“不久即寒冬,亟收取之,仍如南方法藏藤为苗,至次年春,皆冻干不可用矣。”([43],457页)几乎与此同时,方观承在努力将浙江甘薯种植技术传往直隶地区,也遇到同样问题,“购种雇觅宁、台能种薯者二十人来直,将番薯分配津属各州县,生活者甚众。”([43],457页)但是浙江师父在秋后用浙江的方法,开窖藏薯,“然闻坏者尚半”。([43],457页)
通过黄氏与方氏向河北引种甘薯的实践可知,由于气候环境的差异,即使是福建、浙江等地的专业种薯人员,在北方地区也不能很好地完成甘薯藏种越冬工作,足见“南方藏种法”并不适合北方。乾隆十六年,黄氏丁忧归里,路过山东德州,发现当地广泛种植甘薯,“叩以藏种之法。曰:本年冬十月收起,于冬至前掘窖,如藏菜之式,将薯择其小不中食者带藤藏于内,口用土坯封固,仍用泥涂,至次年清明后,将土坯先拆二三块令出气,阅数日,再拆开,恐骤见风易坏,将薯拉去藤,勿用力割。”([43],458页)黄氏服阙复职以后,将山东藏种技术引入河北,方才克服了这一技术难题。
陈宏谋引种甘薯入陕的过程中,虽然也介绍了几种藏种法,但是其法取自《授时通考》,而《授时通考》的藏种法又来自《群芳谱》和《农政全书》,皆属于“南方藏种法”。结合前述黄可润与方观承藏种失败的教训,可以推知陈宏谋的藏种法很可能也不适用于陕西地区,乾隆《咸阳县志》就明确提到了低温导致当地甘薯藏种困难,“咸地冱寒,收种不易”。([35],329页)而就《艺蕱集证》所辑录的内容来看,藏种恰恰是陈仅关注的重点,全书辑《群芳谱》8则,涉及五种藏种法,陈仅案曰:“藏种法不一,备载之,俟农家采取焉。”([20],4009页)尤其是他辑录了黄可润从山东引入河北的“北方藏种法”,显然弥补了陈宏谋“南方藏种法”的不足。
甘薯是较具代表性的高产作物,亩产可达数千斤,史书对此多有记载。但是鲜薯又具有畏冻、不耐储存的缺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南土到冬至,北土到霜降,须尽掘之,不则烂败矣。”([42],561页)陈宏谋也说:“五六月种晚薯,九十月可以取食,始生尚小,冬至则更大,务于冬至前掘出,若在地则朽烂矣。”([32],卷20,《劝种甘薯示》)依据现代测量数据,薯块贮藏的温度要求在10℃~15℃之间。即使按时收获,如法收藏,亦难克服鲜薯不耐久贮的局限,清代福建人陈云在《金薯论》中指出:“(甘薯)惟敛藏有不及乎谷者,谷积数载,陈而不腐。”[44]就连当时南方甘薯产地的鲜薯保存技术也不是十分成熟,乾隆《福宁府志》记载:“虽有地瓜一种,堪作饔飨,而易致腐烂,不堪收贮。”[45]此处所说的地瓜就是甘薯。储存技术如果不解决,大量甘薯在越冬期间就会腐烂变质,不能够被充分利用,丰收和丰产所带来的现实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第二年开春依然会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
《艺蕱集证》恰恰解决了陕西甘薯储存的技术难题,即将鲜薯加工成薯干储藏。陈仅将其家乡浙江的经验介绍到陕西,“冬至前后藤枯实老,掘负室内,切成细丝,勿沾水气,晒极干透,收藏柜桶中。至春夏,每遇晴和,倾出竹席或木板上晒过,仍贮于桶中。年年出晒一二次,即收藏十年亦不至霉烂,非如包谷之不可久藏。”([10],234页)《劝谕广种红蕱晒丝备荒示》系统阐释了甘薯切丝、晒干技术。陈宏谋在甘薯引种的文件中也提及储存技术,但是介绍的是蒸干法,用此法加工而成的薯干还含有一定量的水分,储存时间虽较鲜薯略久,但是工作量巨大,效果也远不及晒干法。尽管南方地区很早就有切丝、晒干储存法,但是在《艺蕱集证》之前,陕西地区对这一方法的确了解不多,不仅前文所述的道光《石泉县志》对此有充分反映([11],18页),而且几乎与陈仅同时期的张鹏飞也曾谈过当地人对晒干法的陌生,“不知此物可切片晒干,贮之竹囷,每夏晒一次,永不生虫。以之御饥,不亚于谷。”([14],72页)可见,陈仅所引进的甘薯切晒技术是对陕西已有储存技术的重要补充。
5 结 语
《艺蕱集证》是陈仅任紫阳知县时为推广甘薯的种植与切丝、晒干储存的技术而编撰的著作,它密切联系紫阳实际,对陕南地区甘薯的推广起到重要作用。陈宏谋曾在乾隆十一年(1746)大力引种甘薯入陕,取得重要成就,受到当地普遍认可,但是其引种甘薯的重点区域是“近省”之地,对偏远地区影响较小。就现有的史料来看,至少到道光年间,甘薯在兴安府等地依然没有得到普遍种植,其原因应当与当地居民未能掌握藏种与储藏两项关键技术有关。《艺蕱集证》恰恰注重了上述两项技术的引进,致力于改变当地甘薯的种植状况,为紫阳、安康等地百姓所肯定。如果评价陈宏谋与陈仅对陕西甘薯种植的贡献,陈宏谋当居“引种”之首功,陈仅则居关键技术“推广”之要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