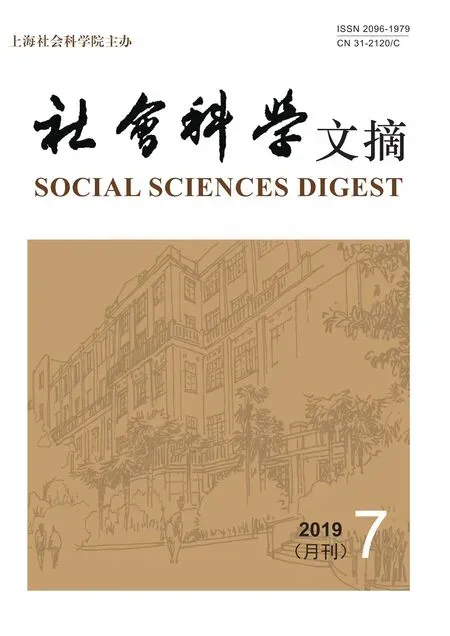学术争鸣与中国学术话语的构建
——对“汉学主义”研究现状的评析与思考
2019-11-19
“汉学主义”(sinologism)通过重新解析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非合理化运用,揭开了中国研究中隐形逻辑的面纱,强调政治和学术的分野,提倡学术的公平客观,以期避免全球化过程中学术研究的单一性和压抑性,并为催生原创性学术提出范式性思考。目前国内“汉学热”方兴未艾,“汉学主义”概念与西方的“汉学”相关但并不相同,引起了一定的概念混乱,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狭义汉学是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知性思想以及艺术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广义汉学泛指西方产生的有关中国的一切知识。顾明栋认为汉学主义理论涉及的汉学是广义的中国学,包含两大方面:汉学主义现象和汉学主义理论。前者指“汉学和知识生产的一种异化形式,它以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涵盖了中西学术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后者则是一套理论体系,对受西方权力和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知识进行批判性审视,深入到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内核,梳理文化无意识形成的靶点和路径,反省学术背后的政治与文化逻辑。
汉学主义理论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较为热烈的反响,但毁誉不一,评论中不乏溢美之词和苛责之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学主义”论争集萃》(以下简称《集萃》)问世。该书并没有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而是站在客观的学术视角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景。本文以《集萃》收集的文章为主要参考资料,通过评析众多学者对汉学主义理论的观察、分析、阐释和评论,从多个视角和多个层面对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发展及现状做一个整体性的评介和思考,并试图对如何超越研究现状、促进汉学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提出新的看法。
理论的提出——探索、发展及完善
汉学主义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厦门大学韩振华于1956年对汉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可以说是开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先河。时隔近50年后,厦门大学的周宁通过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在“西方文化他者的话语”的汉学研究表象下隐蔽的是一种“学术殖民”,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学人须“警惕汉学与汉学译介研究中的‘汉学主义’”。50多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但并未真正摆脱西方思想和理论的控制,对“汉学主义”现象的警惕正逢其时,有必要给学人敲响警钟,再次强调中国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客观性。温儒敏反思了文学研究的现状,提醒当代学者,尤其是国内的汉学研究者建立学术自信,在进行文学研究时注意文本背后的产生机制,避免照单全收的“汉学心态”。
“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都牵涉到后殖民的概念,极易引起混淆。作为“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者,顾明栋认为“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研究方向、研究对象、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存在差异,当前语言研究领域、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汉学主义”是一种认识论殖民,概念运作逻辑实际上是一系列偏颇的观念所构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结合,使“汉学”研究异化。为构建公平客观的学术话语秩序,顾明栋呼吁从后殖民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心态应超越“汉学主义”。在此基础上,他从“汉学主义”的研究范围、内在逻辑、工作原理和功能等方面阐明了“汉学主义”既是认识论、方法论,又是意识形态的定义及范围,并界定了汉学主义理论的目标和反思范式。对此,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各自的见解。比如,程章灿指出“汉学主义”是汉学“对国学所代表的那一套中国知识与学术传统的解构”之后的再解构,耿幼壮认为“汉学主义”存在民族主义的藩篱,钱林森认为汉学为一种研究方法和途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的学术态度,方维规不赞同硬性区分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做法,认为“汉学”和“中国学”本就是一个概念,虽然“汉学”与“东方学”两者有相通之处,但“汉学”在学科意义上不属于“东方学”,对汉学知识的“运用”不应囊括于广义汉学的范畴,并反对将所有汉学都看作是“汉学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产物。
“汉学主义”的初始阶段主要侧重于由“东方主义”引发的对汉学研究中后殖民意识形态的批判。之后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后期的汉学主义理论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均有所拓展,其涵盖的内容不但包括“文化无意识”的概念梳理和形成路径的解析,还涉及意识形态无意识导致的汉学和中西方研究中的“知识的异化”,更重要的是,理论还对如何重新建构西方国家和中国本土对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知识生产方式提出了建议,这对促进中国研究范式的变革意义重大。“汉学主义”作为一种包含了概念、理论、方法及范式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得到了以上众多学者的支持和补充。这些学者眼光敏锐,他们把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清晰化,为汉学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翰墨留馨。
理论的评价——集思广益、博采众长
汉学主义理论提出后备受学界关注,多位学者各抒己见、见解多样。季进在分析海外汉学的基础上,解读了“汉学主义”的渊源、学理、实效和发展,并认同“汉学主义”的方法和机制。周云龙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存在诸多缺陷,而“汉学主义”具有清晰的文化定位和知识立场,其对话性和建设性的目标是不偏不倚的学术伦理诉求。任增强和陈军从身份焦虑的视角切入,指出“汉学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是华裔学者建立一种超越地域和身份的精神归宿之诉求,正是这种特殊身份让理论创始者在经历了东西方文化和学术熏陶之后,深刻体会到中立与客观才是学术文化研究的指导原则,才能以科学多元的跨学科视角放眼世界,利用自身身处于多重文化圈的优势批判性反思跨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建构“以自觉反思为导向的构建式研究”新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汉学主义理论从广度和深度上有别于其他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理论,因其内在逻辑是从认识论无意识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无意识,这一理论揭示了权力与知识在他者殖民和自我殖民的形成过程中的显性和隐性作用。周宪认为汉学研究提倡的“政治正确”并不是撇开政治不谈,而是“回到正确的学术政治和文化政治上来”。有感于汉学主义理论去政治化的困囿,不少学者担忧不受政治形态影响的知识生产是否能够实现,对此,刘勇刚指出,虽然“纯粹学术”难以实现,但学术研究需要有这样的目标指导才能克服西方霸权主义等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来维护学术的尊严。这一看法得到了叶隽的支持,他评价“汉学主义”超越“东方主义”,在学理上的成就及提出者横贯中西的知识容量和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正体现出这种理想主义的诉求,但与此同时,“汉学主义”可能会受到“东方主义”的限制;陈晓明和龚自强认为“汉学主义”理论创造人从中西文化学术交流的不对等现状中突破重围创建出汉学主义理论的知识体系,为中西比较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批判视野,但认为其立足点值得商榷,并提醒学人要保持拨乱返正后的理性,以免过犹不及。各位学者对汉学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及批判性特色则基本持肯定态度,同时也从学理、架构、研究范围等方面提出建议,为汉学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理论的争论——百家争鸣、相得益彰
诸多学者对“汉学主义”的关注还引发了不小的学术之争,其中既有充满了针锋相对的学术争鸣,也不乏因争论而迸发的思想火花。张博认为“汉学主义”是“萨义德理论的变体”,存在先天性缺陷。他指出萨义德的观念不具有普世性,这个理论侧重一个文化内部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导致视角逼仄而忽视了作品人性和美学的意义。因而,他建议“汉学主义”应区分西方学者的治学态度,并借助“异域之眼”来反躬自省。严绍璗认为汉学主义理论构建缺乏支撑,相关研究者缺乏文本阅读和“原典实例”的能力,仅仅是靠“灵感”泛泛空谈,理论表述者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以及“局部”与“整体”方面思维逻辑混乱。对此,顾明栋认为两位学者对汉学主义理论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和初期,并未触及汉学主义理论的内核和发展。首先,张博对一些理论的梳理虽“有助于深入理解汉学主义理论的价值和不足”,但他落入到以偏概全的窠臼:将后期汉学主义理论混淆为“早期的东方主义翻版的汉学主义理论批判”,而且批评往往是自立靶标,无的放矢,其阐述的思维模式正是汉学主义理论所反对的“知性殖民”的典型体现;而严绍璗仅通过汉学主义理论的二手文章就对此理论严加苛责,实在有违其提倡的“原典实证”科研方法,也忽视了重新建构的汉学主义理论对前期的厘正和扩展,以蠡测海,误判汉学主义理论逻辑不清。由于国内学者较少接触到西方对中华文明刻意丑化的实例,就容易误认为汉学主义理论是针对国内所有相关研究,进而得出汉学主义理论抹杀了有些研究的客观性的结论。实际上,这是对汉学主义理论指向和指导价值的不折不扣的误读。
诸多学者的观点中,赵稀方直抵争论的核心所在。赵稀方肯定了汉学主义理论对海外汉学的态度及“文化无意识”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但质疑东方对西方知识的接受路径、中西文化交融的阐释以及理论的根本诉求,就“汉学主义”对“东方”界定的合理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学主义”忽视了“东方主义”中被殖民者参与的意见。顾明栋通过Orientalism(《东方主义》)(Said 1978)英文原文的内容回应了这一批评,确认了“东方主义完全是西方人的单边建构”的结论,而“汉学主义”的多边建构正是它有别于“东方主义”的根本之处。对此,顾明栋解释释道,“汉学主义”是对相关研究的反思,东方对西方知识的接受路径不在研究范围之列,建议学者结合“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来深度理解和探讨“汉学主义”。对于顾明栋的反馈,赵稀方查阅英文原著,引用原文就当代东方是否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再次反驳顾明栋对以上问题的阐释,他认为“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一样具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特征,论据是顾明栋在理论阐释的过程中对西方的“汉学主义”及中国的自我汉学主义化重点着笔。之后,顾明栋澄清,早期的汉学主义理论可能存在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但后期的理论克服了这一范式的局限,希冀通过反思尽可能做到客观地生产知识。对于赵稀方认为“汉学主义”否认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的结论,顾明栋先是对翻译偏差和编辑处理的疏漏作了补充,并就“被动参与”和“主动建构”两个不同的视角以及“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树”的指向解答了阿拉伯和中国的自我殖民这两者的差异,由此对东方是否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释疑解惑,阐明“东方主义”与“汉学主义”在“人力资源、理论关注和研究对象等方面”截然不同,并且“汉学主义”正是对“东方主义”二元对立缺陷的弥补。而对于赵稀方反对“汉学主义”理论认为萨义德没有考虑被殖民者声音的观点,顾明栋认为是因为他并未认识到“汉学主义”的另一个核心概念——“知识的异化”。不过,虽然两位学者研究路径不同,但都认同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的研究范式。
张西平肯定“汉学主义”批判反思精神的启发意义,但他更多的是对其理论架构和学术基础的质疑,质疑“汉学主义”提出的知识合法性问题,认为“汉学主义”沿袭了“东方主义”的套路,依葫芦画瓢,只是将东方主义批评的对象换为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他依据Orientalism的译本《东方学》指出萨义德理论的局限,认为“汉学主义”套用了“东方主义”,缺乏创新性,无视中国学术界众多学者在治学时对后殖民主义的警惕。除此之外,《东方学》在纯粹知识与意识形态和想象之间的关系存在谬误,因而,建立在此理论基础之上的“汉学主义”对西方汉学研究的缺乏客观性,过于片面,倡导者忽略了中国文明和知识系统的解释主体是中国学者本身,并错误地“将西方汉学发展的复杂历史简单化、概念化”。最后,他指出“汉学主义”理论倡导者用西方汉学一个时期的特征来覆盖各个时期的特点是以偏概全且缺乏论据的,由此得出“汉学主义”将学术与政治等量齐观,将中国学术与汉学对立看待,是对《东方学》扭曲运用的结论。除了从后殖民视角批判汉学主义理论之外,张西平还从哲学和后现代理论的角度批评了汉学主义理论。他指出“汉学主义”缺乏跨文化理论的运用,并混淆了汉学作为知识和作为思想史这两个不同的层面,无视后现代主义哲学层面的弊端,必然导致理论的片面性。韩振华声援了张西平的观点,认为“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相似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其构建不足、论证牵强,有以偏概全、陷于文化本质主义的泥潭、忽视跨文化立场的缺陷。对以上批判和质疑,顾明栋通过个案例证,说明政治和学术存在相斥相融的辩证关系,张西平对理论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东方学》文本的误读之上,孤立地择取原文中的几段,并采用了错误的译文,从而曲解了萨义德原著的本意并得出“汉学主义”的理论基础有问题的偏颇结论。他进一步在厘清“汉学主义”概念的八个方面及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指出,意识形态的概念理解过于狭隘才会产生上述学者的质疑,认为“汉学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断论是管中窥豹。此外,顾明栋还从哲学层面追根溯源,指出对汉学主义理论的上述误解是因为对后现代理论了解不够全面而导致的,并以二手的资料对新历史主义等理论进行了误读。他强调,汉学主义理论的概念性基础不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而是以“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为核心构建的反思理论。
有关“汉学主义”的争鸣刷新了国内争鸣的记录,参与争论的学者们从理性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评论者和争鸣者都乐于倾听并勇于表达,通过多维度的视角陈述各自的观点。围绕“汉学主义”的争辩逻辑思路环环相扣、争论的指向和力度也非比以往,这对汉学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中西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对“汉学主义”论争的反思
学术需要争鸣,通过论辩,汉学主义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得以厘清,汉学主义理论前期的主体思想和理论后期的发展与突破点得以呈现和阐明,“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异同也更加清晰。在对“汉学主义”论争的评介与思考中,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及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的哲学观点得到了多维度的深层阐释,更新了以往学术争论涉猎面的阈值,为中国学术争鸣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笔者认为,反思有关“汉学主义”的论争对汉学研究、跨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研究有着较为深远的意义。
首先,论争对汉学的学科认识和建设有一定的意义。有关汉学的研究绵延百年,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然而,作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产物,汉学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特征,其异质性、多样性和倾向性使得一些汉学研究成果带有隐形或显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当随之而来的杂糅特征上升为具有生命力的政治性阐释话语时,汉学的部分学术研究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西方霸权的衍生物,从而演变为过于政治化的汉学认知。客观性是汉学研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一知识生产的问题,使汉学在世界文化研究的共性中更突出个性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汉学主义”理论的初衷即是推动尽可能客观中立的汉学研究,让科研领域成为神圣的一方净土。虽然完全去政治化是理想主义的奢求,但这种纯粹的学术信仰应该是每一位学术研究者追求的目标。关于“汉学主义”的争论是对汉学主义理论解构之后的再建构,同时也对汉学研究所应具备的学术态度进行解析和补正,有助于汉学研究者以开放和中立的心态对中国文化加以展示并共享,促进汉学这一学科在全球文化融汇中稳步健康地发展。
其次,论争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争鸣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围绕“汉学主义”展开的争论对学术研究的启发首先体现在争鸣的方式上。国内的众多争鸣大多不愠不火,亦或充满着溢美之词,亦或非愚则诬,甚至对簿公堂。这种争鸣并不健康,对学术的发展也无促进。而这次争论针锋相对,甚至言辞犀利,虽然观点的碰撞很激烈,但争论的方式文明理性,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是秉持积极健康的态度,遵守文明理性的学术争鸣原则,摆事实、讲道理,这正是汉学主义理论所秉持的学术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编“汉学主义”论争的《集萃》一书是这种纯粹的学术精神的体现。首先,编者并不会因为反对意见而诛锄异己,反而高度肯定反对意见,希望通过争鸣来澄清问题,再达到共识。这样的编辑姿态在国内学术界创建了良好健康的学术争鸣的范例。第二,围绕汉学主义理论的阐释和争论层层展开、步步推进,逻辑缜密,解析透彻,有助于培养读者的批判性思维,并帮助现代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学习如何思辨,以及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文化批判意识和能力。第三,围绕“汉学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代表着当中国学术遇上西方研究范式引发的内省和批判,这种学术争鸣的意义不但体现在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反思,而且对如何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原创学术话语体系,展示中国本土话语权,以及树立文化自觉,加强学术自信也有启发性意义。
汉学主义不同于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扬弃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批判路径,在对汉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种种偏颇现象进行批判的同时,要深入挖掘造成扭曲中国文化现象的内在逻辑,即后期汉学主义理论所说的“文化无意识”。笔者认为,汉学主义的“文化无意识”理论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有待于学者们去发掘和发展。首先,汉学主义的文化无意识理论不仅对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具有意义,而且对超出中国研究的其他领域也有一定的跨学科和跨文化价值,不仅可以揭示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发展的隐形逻辑,也可揭示第三世界知识界思想意识的隐形逻辑。近代以来,第三世界的社会和学界普遍存在着对自我信心不足、对西方“他者”盲目崇拜的意识,而且由于西方持久的霸权和东方的积弱不振,这种意识已经深深地侵入人们的无意识之中,以人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因此,第三世界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心态和做法,而且,往往还对此并无自我察觉,这些无意识心态严重阻碍了第三世界人民和学者的原创性。
此外,根据笔者观察,“文化无意识”的隐形逻辑不仅适用于人文社科,也适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我们不难注意到,中国科技领域中凡是西方向我们开放的领域,中国科技人员很少能做出原创性的工作和成就,而在西方对我们加以封锁的领域,中国科学家们却作出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原创性成果。比如于敏的氢弹设计模式完全不同于英美苏俄的设计,可以使氢弹的维护保养简便可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保留氢弹的国家。为什么会如此呢?在量子信息这一个全新的学科中做出令世人瞩目成就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曾说过这样的话:“过去,我们在科研领域,常常扮演追随者和模仿者的角色,研究方向的选定、科研项目的设立,都要先看看国际上有没有人做过。”潘先生的话确实把住了科技工作者的文化无意识之脉,由于文化无意识的缘故,不少中国科技人员认为,西方是科技的领跑者和引领者,中国人只能跟在后面跑,由于文化无意识导致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心态,有时即使作出了原创的发现,也不敢相信,结果是被他人利用,为他人作嫁衣裳。有鉴于此,“汉学主义”的研究应该继续深入发展“文化无意识”理论,促使其扩展到人文社科以外的科技领域,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方向,而且是大有可为的领域。
围绕“汉学主义”展开的论争在广度、深度、力度方面拓宽了中国学术争鸣的内容,开创了学术争鸣的新典范。然而,任何理论的形成都要经过筚路蓝缕的过程,汉学主义理论也不一例外,从初期到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汉学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在多重视角中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在对“汉学主义”理论的众多解读中,观点的变化和融合持续进行。诚然,诸多学者所呈现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全然规避主观与客观的局限,但正是通过不断的分辨和批判,科研工作者才能在从后殖民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秉持汉学主义理论提出的目标进行学术研究,在尽可能中立客观公正的学术之路上越走越远,在探索中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