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江边
2019-11-18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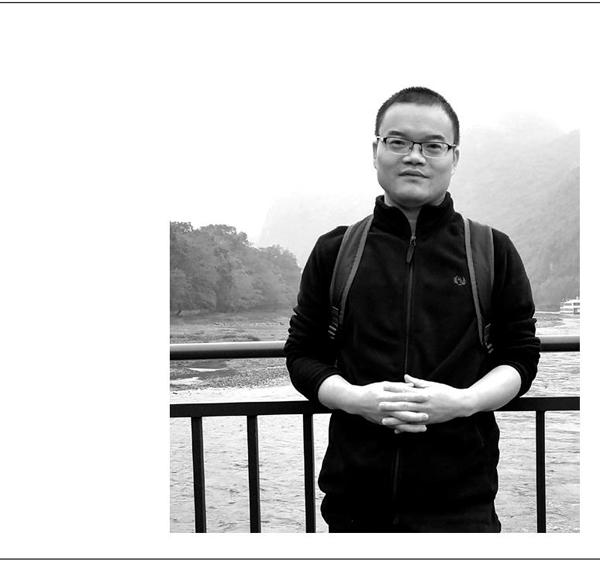
半文,本名钱金利,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曾在《散文》等刊发表文字,有作品收入《中国散文年选》等选本。
1
早晨四点多,云雀远远地叫了一声。叫声并不响亮,有些犹疑。天还很黑,江对面,天只微微一丝白色,白不过江边的路灯。我不清楚这只云雀是做了一个不太美妙的梦,被惊醒了?还是身体里那一口钟突然出走神,走岔了路?突然的一声叫,投进了黑暗里,立马沉了下去。没有听到回声。
过一会,又有一声。然后,是两声。三声。仿佛对黑夜的试探。
我住的小区,在江边,叫江景房。站在阳台上,白天,可以看见钱塘江的潮水,万马奔腾地跑过,又悄无声息地跑回去,“人生长恨水长东”的说法,在钱塘江,是不合适的。这里的江水,会向西跑,那么多的浪花,跑得很齐整,跑成一条白线,叫一线潮。晚上,看不清潮水,可以用耳朵听,听着潮水向西奔跑的声音,叫“夜潮”。小区和钱塘江之间,有路、有堤、有坡,有花、有草、有树。树上有鸟。很多鸟。我喊不出它们的名字。在绝大多数时候,看见一只鸟飞过,我只能喊:“喏!一只鸟!”或者说“一只大鸟”,“一只小鸟”,“一只黑白的鸟”,“一只彩色的鸟”。如果是人,虽然叫不出名字,我还可以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小孩、一个老人;但鸟不行,我分不清男女老幼,我只认识它是一只鸟,只能分辨它的大小和色彩。所以,我只能说:“喏!一只鸟!”
有时候,我常常为自己的不认识一只鸟而感觉惭愧,像看见一个经常遇见却叫不上名字的人,觉得尴尬。虽然这鸟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但我责怪我自己。
偶尔看见一只鸟,能叫上名字,就很兴奋。云雀是我少数叫得上名的鸟之一。短冠,白尾,不大,总有四只麻雀大。站在树上的时候,很端庄。不像麻雀,总跳来跳去。鸟的大小其实是很难描述。我们描述一个人的身高,只说一米七八,有点壮,大概就知道了。鸟的大小,说十五厘米,就很难想象。所以,我常拿麻雀做计量单位,说云雀,不大,就四个麻雀大小。白头翁感觉小一些,两只麻雀大小。绣眼鸟和棕头鸦雀更小一些,只有半只麻雀大小。乌鸫要大些,有八至十只麻雀大小。如果白鹭,我说有二十只麻雀大。江边还有一种鸟,彩冠,锦羽,比鹌鹑大一圈,走路很慢,在江堤上很从容地走,看上去很肥美的樣子。要等汽车开到身边,才会突然消失。没看清楚它怎么飞,就是不见了。我至今不清楚它叫什么,沙地人叫“野鸡”,主要是样子像鸡。看上去,有三四十只麻雀大。
江边的云雀,据说是小云雀,鸣声婉转。高兴时“唧唧唧——啾啾啾——”的声音,短而劲,拿瓷碗打蛋一样,能把天上的黑色打碎。这只叫一声,那只叫一声,同一片林子里,很有规矩。一只叫完,另一只才叫。另一只叫完,别一只再叫。站在林下,听叫声忽近忽远,忽高忽低。有时情绪高,几只一起叫,也不乱,有点合唱的味道。清晨五点多的时候,云雀叫得最欢。太阳从江对面出来之前,天色泛白,云雀们的情绪就很高,几只一起,轮着叫,合着唱,很少有停下。夏天,知了在林子里叫,感觉乱,感觉杂,感觉躁。春天,清晨,在林下听云雀叫,只觉得欢喜。
五点多的时候,江边没什么人。有一个老人,在练太极,或许是道家的吐纳。我不懂,只感觉他站在那里,像一棵树桩,黑魆魆的一团,就不去打扰他。我立在那里,静静地听云雀们欢叫,也跟一棵树桩样。或许站久了,等脚下生出根来,便也成了一棵树。
没有人声,就感觉安静。
江边,是清晨最安静。云雀叫得欢的时候,白头翁也会插几句嘴。白头翁头很白,却不老,叫声“啾啾”,短促,有力,有时连着“啾啾啾啾”,好似两人相对聊天。聊的是家常。插在云雀的欢叫声里,也没感觉乱。分得清是谁跟谁在说话。
我站在林下,听它们欢叫笑谈,常常感觉纳闷:在我听来,云雀和白头翁的叫声,有不同。绣眼鸟与云雀,也不同。但云雀A和云雀B,它们如何分辨?云雀欢叫时,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粗粗细细,在我听来,也略有不同,大约是要表达不同的情绪和意思,和我们说今天天气很好今天心情也不错今天适合去外面走走等大概一个意思。但这话谁说的?怎么说?
或者?这句话谁说的并不重要。但这只云雀是谁?是云雀A还是云雀B?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半文。即便没见着我的脸,说两句话,便知道,是半文来了。再熟悉一点的,听见我的脚步声,就知道是半文来了。因为半文的声音是半文的,半文的相貌是半文的,而不是全文的。云雀A和云雀B声音不一样?相貌不一样?我连云雀和小云雀都分不清,两只小云雀,怎么分?
云雀们应该分得清,谁云雀A,谁云雀B,谁男、谁女、谁老、谁少、谁亲、谁远,不然,走错了窝,把别人的老公当了老公,别人的老婆当了老婆,别人的孩子当了孩子,就有点乱。贾平凹写商州,写到老街上的人,经常走错门,半夜出去撒了泡尿,回来就进了别人的家,抱了别人的娘子。人家知道,或不知道,也不说,只当是自己家老公,睡了再说,反正也不吃亏。结果,就有些乱了。
人与人,本来也都很像。如果叫一只鸟来分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也应该是分不清的。连插在田里的稻草人,一只鸟也分不清。如此说来,人与人应该和鸟与鸟一样,都很像,都应该是一家人。可惜人与人设的防太多。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市与市、省与省、国与国,都有界线,都有防备。不像鸟与鸟,都是一家鸟。出个国,也不用办出境手续。翅膀一抬,就去了。翅膀一抬,又回了。过个界,出个境,也不用付费。自然而然。
到了他国,也没有隔阂,没有语言的障碍,讲的都是鸟语。我在网上听过法国的云雀叫声、听过美国的云雀叫声、听过日本的云雀叫声,和在江边听到的差不多。或许带点方言,是美国腔的云雀叫,或是日本味的云雀叫,总体上,都是云雀叫。不像英语和汉语,差太远。就一个中国,如果不经学习,让越地的人听粤语,如听外语。不说远的,我在杭州,听温州话也只懂十之一二。听英语、法语、德语,便如听外星人说话。听叙利亚一盲童站在大马士革的废墟上,和一群孩子唱“重生”,我听不懂。好在音乐没有国界。我能听到歌声里的伤痛和废墟,也能听到歌声外的希望和憧憬。
鸟语也没有国界。在江边的林子下,我能听到云雀们的欢欣和舒畅,云雀们好像没有什么理由会不高兴。云雀们不用承担高房价,不必担心会有战争,连日常的争吵都没有。只有下雨的时候,云雀们兴致不高。没有日出的清晨,我在林下,只能听到雨打樟叶的声响,雨滴打在花岗岩上的声响。我不清楚云雀们在落雨的清晨,都去了哪里。云雀们的被窝,挡不住雨,也盛不住风。它们在哪一片树叶下躲雨?
我有伞。我撑着伞,想象睡在热被窝里的人们,梦境里,肯定没有一只被雨淋湿的云雀。
天气好的时候,在太阳跳出江面之前,我把手机的录音功能打开,把高高低低的云雀的欢唱和笑谈,收藏进手机。晚上,睡在床上,可以循环着听。梦里,清脆的鸟鸣声和钱塘江的夜潮声,就混在了一起。
没有人声,梦境也不会杂乱。
2
江边,适合晨跑。江堤上,一面是涛声,一面是鸟声,两个不同的世界。
山鹡鸰飞得很低。有时就站在草坡上吃虫,跑过去时,它会突然飞起来,吓人一跳。还好,鹡鸰很低调,飞得很低,贴着地面飞行。翅膀上有白色,很亮,一纵一纵,好像波浪,在水里游泳一样。鸟在天上飞,如果把空气当成水,或者把水稀释成空气,可不就是在天上游泳?空气足够稠的话,人也可以在天上游。不过,空气里的水太薄,不适合人来游。
谷雨前后,布谷鸟来喊“布谷、布谷”,白天黑夜都能听到。布谷鸟从天上飞过的样子,很是平稳,不像游泳,像是一条大船,稳稳地在水上航行,几乎是一条直线。原来江边,还有一种苍鹰,在天上飞,却不像飞,倒像是浮在上面,一动不动,也不会掉下来。可惜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能看到的鹡鸰,以山鹡鸰和白鹡鸰居多,白鹡鸰在沙地叫“青丝麻雀”,比麻雀略大,一个半麻雀大小。但瘦。身材比麻雀要好。
白鹡鸰飞的时候,一纵一纵的感觉更加明显,好似游泳没学好,要费力气地用双腿去蹬,若不用力蹬,便很容易就沉下去。看白鹡鸰,走路的时候很多,在鱼鳞瓦的屋脊上,快速地行走,两条腿换得比人类跑动时要快。麻雀不太走,总是一跳一跳地。以此来看,麻雀的性子比鹡鸰要急一些。
我不会一跳一跳地走。一跳一跳走着的,是年轻的学生妹。年轻的学生妹要夜跑时才见到。晚上,很多学生妹,有很五四的,也有很后现代的,一律都带着保镖,坐在江堤边的石凳子上,或者倚在栏杆上。也有在江堤的斜坡垫一块防潮垫,搭一个帐篷,或擺开POSE拍照。很少见到走着的学生妹,跑着的学生妹。不过,从她们身边跑过去的时候,我仍可闻到一股春天的气息。和一只麻雀一样年轻。
年轻是好事情。年轻人,可以装成很成熟的样子,坐在那里谈论爱情。像我这样年长的,就不能装年轻,混在那里谈论爱情。我只是跑步,一步一步地跑,不是一跳一跳地跑。我没有翅膀,也不能鹡鸰一样一纵一纵地跑。一步一步地跑,一呼一吸地吐纳,然后一滴一滴地流汗,据说这样,可以把身体里陈年的东西吐出去一些。这叫“排毒”。人体里,是有很多毒的,都是陈年的毒。
山鹡鸰的叫声“刮油刮油刮油”,和我跑步的目的是一样的。这些年,坐得太多,动得太少,收入就超过支出了。在江边跑步,可以把身上的油刮去一些。鸟们是不会肥的。一只鸟要是肥了,离死期就不远了。鸡很肥、鸭很肥,都是鸟,都飞不高,都跑不出一把刀。鸬鹚也是鸟,也飞不动。飞不动的鸟,就不是一只真正的鸟了。
是只鸟,就该飞。既然飞,就不会肥。我不会飞,所以我肥。不过,在江边晨跑,江风浩荡的时候,展开双臂,两胁生风,也有类似飞翔的感觉。
现在四月,春正浓。学生妹们谈论爱情,鸟们也在谈论爱情。只是谈论的方式有些不同。学生妹们坐在江堤边,草坡上,帐篷里谈,鸟们坐在枝头上谈。
喜鹊喜欢栖得很高。栖得高,便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在那里谈论爱情,便旁若无人。一般鸟儿酒足饭饱、混圆了肚子后,都会拿喙给自己梳理羽毛。鸟们都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鸟的羽毛被淋湿,就很不幸了。要是没有羽毛,就更不幸,不像一只鸟。我们看鸵鸟不像鸟,也还是留了几根羽毛的。鸟们除了吃,就是穿。也不必买新衣服。这一身毛,就很好。所以,吃饱了梳理打扮一下,显得十分重要。我看见过喜鹊梳理羽毛。两只喜鹊歇在我家阳台外的栾树上,一只给另一只梳理,一边梳理,一边聊天,和人类谈论爱情是一个模样的。梳理完了,换过来,另一只给这一只梳理,然后,继续谈论爱情。
在江边,不太看得到鸟们谈论爱情的样子,主要是树太高,叶太密。只听见它们说话的声音。听不懂鸟语,不清楚它们具体谈论些什么。冬天的时候,落了叶子,在江堤上跑步,会看清楚一些鸟。远远地停着,像中国画里谁没画好,多出了一个墨点。最好看的是那些鸟巢,硕大,粗犷,被枝枝杈杈高擎在半空中。
江边,是杨树居多,很是高大。冬天脱了衣服,杨树们粗砺的身子,便很有些雄性的味道,和钱塘江很般配。那些硕大的鸟巢,更像是杨树结出的果实,被举在天上。我所居住的高层公寓,也像是钢筋混凝浇筑的大树上,一个硕大的鸟巢。树叶,是鸟窝的窗帘。这几天,鸟们在鸟巢里谈论爱情或者亲情,已经十分私密,不容易窥探。倒是学生妹们不怕被青鸟探看,用很是开放的姿势谈论着爱情。我偶尔傍晚出去跑步,一对,又一对,旁若无人。
杨树林往里走,是一条河。原来围垦的时候,是把一条河里的泥,翻过来,成了一条堤。所以,原本平地上,多了一条江堤,也多了一条河流。河边杂在杨树下的,是柳树。沙地人原来叫柳树为杨柳树。现在看起来,杨树和柳树,是两种不同的树。柳树在吐春天的絮,白色,比蒲公英大,比棉花轻,一朵一朵在天上飞,比雪花好看。久了,河面上可以看见密密的一层。宋时苏轼写诗:“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四月,江边正是开花的季节。除了满城的柳絮,还有桃红梨白,还有榆叶梅、紫叶李、樱花、丁香、海棠、柑橘、蒲公英,红的粉的白的绿的黄的紫的,空气中散漫着各种颜色的香味。
有些树也开花,刺槐,鸟卵形的叶,开一串一串的白花,像金蚕豆的花。长出的果子是荚果,很是芳香,是那种纯白色的芳香。栾树开小黄花,和桂花一个模样,但花香不同。到九月十月,结红色蒴果,形似红叶。举在树梢,分不清是果是叶。泡桐树的花是繁华的,一整树,紫色,喇叭状。朝着天,热热闹闹地吹。好似有一天的喜事好事需要庆贺。那些开花的树,总感觉有些不正经。好像一个正直的人,没干正经事。明明一棵树,学着人家开花。不过开着一树花,得了一树鸟鸣,真是一件好事情。远远看着,可以得一日好心情。
柳絮据说不是花,是种子。人家开花的时候,它来撒种子。有些像人家谈恋爱的時候,它来炫孩子。也不正经。有些娇弱的女子,柳絮过敏。也有些,花粉过敏。春天,便不敢到江堤上来谈论爱情。或者,要戴个很严实的口罩,谈论爱情的时候,便口有遮拦,谈得十分不畅。这些对春天过敏的人,人生的春天,便也会来得迟些。
不过,柳絮不管这些,随着风,就飞了。风是媒人。我喜欢风这个媒人。风吹着吹着,云就开了。风吹着吹着,花就开了。像云雀叫着叫着,天就亮了。
在江边,天是被鸟们喊亮的。我一边跑步,天一边就慢慢地亮起来。太阳出来的时候,江面上,有很多个太阳。白鹭伫立在浅滩上。潮水未至,江面平静,白鹭发呆,只有风在轻轻发颤。江的对面,是美女山、是乌龟山、是白虎山,在那里站了不知道几万年。江这边,早起的,都是老人,上年纪的人,像我这样,睡不着又醒得早的人。
一个老人面对着许多个太阳,在练习什么功夫。双臂高举,两手伸展,像一只鸟起飞的样子。太阳跃出江面的刹那,正好在他的两臂之间,像是他把太阳举了出来。
3
江边最多的是芦苇鸟。沙地人的“芦苇鸟”,学名叫“苇莺”,体型和白头翁差不多,两只麻雀大小。儿时用弹弓射,麻雀和苇莺最容易。麻雀喜欢停歇在电线上,一长串,像是电线长出的一串果实。
麻雀停在电线上,视线极好,本来“叽叽喳喳”聊天,看有人走近,便突然安静下来。再近一些,便哄一下飞走。我若举起手瞄下,即便手上没有弹弓,麻雀们也远远地逃走了。麻雀的胆小,是出了名的。沙地人说一个人“就麻雀那么大点苦胆”,就说这人的胆子小到不能再小了。麻雀胆子是小,智商却是不低。它们认识我,也认识我手中的枪。现在,鸟枪收了。弹弓也锈了。在江边,草地上,围垦广场上,麻雀便不怕人。常常一跳一跳在人的帐篷边、防潮垫旁找东西吃。我跑过它们身边,它们已不认得我,只把我当一股风。只低头找东西吃,旁若无人。
苇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好似中国的文人,讲一些气节。苇莺通常停在芦苇的顶梢上,很像旧时在岗亭上放哨的哨兵,随着风,一摆一摆地,和着韵律的样子,那韵律,我不清楚是一首诗,一阙词,或只是一首乡间的歌。坐在芦苇头上,视线大概极好。不过,只看远处。我沿着芦苇丛,小心不发出声,可以靠到很近,它仍在望着远处。远处应该有很好的风景。我不能像苇莺一样站在一棵芦苇上,所以,我看不到那些风景。
苇莺的巢也做得很好。等到五月初,芦芽在水边长起来,苇莺就开始做巢。我喜欢说做巢,好像做一个手工艺品。与喜鹊不同,喜鹊只是把一些树枝混乱地搭放在杨树的枝杈间,所以叫搭巢。苇莺的巢是要做的。要想办法找寻一些很细很韧的草茎来,把三根四根芦苇捆扎在一起。在离开水面一米左右的高度,一圈一圈地捆起来。捆数百上千转。我是十分佩服苇莺的,不是巢有多完美,是做巢本身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难以想象,苇莺没有手,没有绳索,就靠一张嘴,如何把这三根四根芦苇捆在一起?水边风大,芦苇摆动时,难度会更大。我几次去找,都没有窥见苇莺做巢的手艺。我所寻找到的,都是成品的巢。向着天空,仿佛神人举起的酒杯。
苇岸说:这世界神造的东西正在减少,而人造的东西越来越多。这苇莺的巢,就是神造的东西。这是一项微小而伟大的工程。一个巢,数千上万根草的茎和根,细细密密地织着,织成一个酒杯的样子,从下往上看,正是要和天空干杯的样子。
发现巢中有卵。大人会告诫孩子:鸟卵是不能随便摸的,摸了要长雀斑。苇莺的卵上,雀斑更大,比麻雀的大。好像祖父脸上的老年斑。后来,我知道鸟雀有人所未知的智慧,一经人手抚摸,鸟妈妈回巢时,从遗留的温度便可判断出事实的真相。鸟妈妈会把被人摸过的卵扔出巢外。像是神性的东西,经了人手,被玷污了。
四月,春天还不深。河边还只有芦苇的尖芽,苇莺们应该在江南之南,更南的南方过冬。芦苇们的边上,蹲着很多戴鸭舌帽或撑太阳伞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他们有的是时间,能在那里蹲一天。这人,不是鸟,但蹲在那里的样子,和苇莺抓在芦苇的枝头,是一个模样。
同住一个小区的老宗,退休了没事情,就蹲在河边钓鱼。最多的是鲫鱼,一天能钓一百多条。不喜欢吃,就喜欢钓。钓多了家里鱼缸浴缸养不下,就放生。鲫鱼太多了,就改饵料,钓鲤鱼。鲤鱼不多。有时能钓到汪刺,身上无鳞,两边长刺那种。鱼在水里游,本自由自在,和鸟在天上飞一个模样,被钓线牵了,像风筝,跑不掉了。
我去钓过,江边的河,鱼多。原来能用电触鱼,开着小船,用柴油机发电,把河里大大小小的鱼用电一锅端了。原来也有用游丝网粘鱼,凡粘上网的,都被卡在网眼里,进不得,出不得。现在,都不允许了。钓原本也不允许,但钓的人多了,被默许了。钓鱼,不爱吃,就又放生。总不可能把鱼子鱼孙都钓完了。老宗去钓,钓大,放小。边上有人看着惊呼:那么大的鱼,怎么放了?结果,老宗钓了二三十条,那人一条都没钓到。
我在江边的河里,钓到过乌龟。鱼漂一直往下沉,又沉,一直沉到水面之下了,还在往下沉。我从没遇见过这么奇妙的事情。往上一提钩,鱼竿也沉下去了。一直往上提,再提,竟然提出来一个乌龟。这是我第一次钓上乌龟。提到草地上,一放竿,乌龟竟然就脱了钩,“叭叭”地往河里跑。此时,我诅咒那个写龟兔赛跑的人。我从来不知道乌龟四条小短腿竟然能跑得那么利索。快入水了,终于追到。我穿着凉鞋,也是豁出去了,一伸脚,把乌龟背踩住了。还好,它把头缩回去了,没有放嘴咬我。
以后,谁要是再说乌龟跑不快,我要跟谁急:乌龟不是跑不快,是没到拼命的时候。
4
在江边,燕子是不多的。
这些年,没了枪,没了弹弓,也没有网,鸟们活得自在许多。在江边,鸟的品种也是越来越多。我倒是不在乎多,反正都不认识,多几个少几个,也不在乎。沙地人叫做“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小时候,若看到这么多鸟,高兴坏了。那时候看到眼睛里的鸟,都被拔了毛,好似一团肉,可以射下来,可以放进嘴里嚼,可以嚼出肉的香味来。飞得很高的苍鹰,射不到,据说也可以骗下来:在道地上拴一只小鸡仔,令它嫩嫩地叫。旁边放一摊类似臭柏油一样的黏液。苍鹰本来浮在高高的天上,看见小鸡,便突然直线冲下来,像急速坠落的风筝。接近道地时,忽然一个转弯,用爪子捞了小鸡,展翅一拍,便重又急速上升,回到空中去。在这个下和上的急转弯中,它要很用力地拍打翅膀,才能急转弯,结果,翅膀被粘在臭柏油上,再飞不起来。
想起那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現在,苍鹰见不着了。这个见不着,起码有廿年了。江边,麻雀、白头翁、喜鹊、白鹭之类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鸟很多,大的小的各种形状各种色彩的。苍鹰没有,燕子不多。
燕子和其他鸟雀有些不同。称“家燕”。不是“家禽”。不算鸡鸭鹅,鸟类中,只有燕子可以登堂入室,进家中做窠。我家老屋堂前的木门之上,留有一个扇形洞口,专供家燕进出,即便家人出了远门,也不影响家燕回家、出门、哺育幼燕。
燕子搭的是泥窠,若搭树上,一朝落雨,全部跌落。搭在家中,很牢靠。我家老屋堂前,柱上、梁上,有燕子窠十余个。燕子很念旧,去年做了窠,来年春天从南方回来,还住那家。原来搭的窝,也不舍弃,稍作修葺、翻新,又住一年。我不清楚其他鸟们,是否这样。
在沙地,燕子是有神性的。燕子来一户人家搭窝,是看得起这户人家,说明这户人家不错。有很多对燕子来做窠,那就是很不错了。我的父亲,父亲的父亲,常以此自慰。以此自傲。
燕子窠不能损坏,如拿竹竿敲打,要肚子痛的。燕子不能射,若拿弹弓射,要眼睛痛,厉害的,眼睛是要瞎掉的。我儿时射鸟无数,却不敢射燕子。更不敢吃燕子。远远看见燕子五线谱一样停在电线上,便仿佛看见头上的神明。据说:把所有色彩都放在一起,便是黑。把所有色彩都拿走,便是白。燕子一身,只穿黑白,只用神性的色彩。大概是得了神性,燕子胆子也大,我们从电线下走过,即便是一大群人,燕子也不动声色,该叫的继续叫,该沉默的继续沉默。不像麻雀,早跑得不见影子了。
燕子的叫声也很有特点:“不吃你家一口饭不喝你家一口水只想借你家住——”,用沙地话翻译过来,是这样子很长的一个句子,且燕子一旦开叫,就要把整句话说完,特别最后一声“住”字,拉得很长,仿佛演讲时最后强调一下,等待与会者鼓掌。不像麻雀,“叽”一下,“喳”一下。
现在江边,很少见到燕子。江景房造得很高,越来越高,但没有一间是为燕子建的,没有一间留着门或洞。那些屋檐很薄,容不下燕子小小的身子。我不清楚家燕们现在在哪里做窠。现在,春意正浓。燕子们该从南方回来了罢。
从江堤上跑过,看见一只黑色的鸟,原来是八哥,全身黑得不像样子。也像燕子一样,浑身冒着神性。现在,鸟们身上的神性,开始慢慢发出光来。苇岸说这些是神造的东西,我开始相信。神造的东西身上,是有些神性的。人造的东西虽然不够好,但也要有些人性。只可惜,现在没有神性,也没有人性的东西,不少。
我怀念燕子,像怀念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虽然,它不会把我当朋友。这些年,我是把很多鸟很多花很多鱼很多虫当朋友的。见不到活的,看书、看图片、看视频也行。虽然我清楚我这是一厢情愿。住江边,除人之外,还能一厢情愿地认识一些新朋友,一些带着神性的新朋友,真是幸运。
常交一些带神性的朋友,说不定,自己也会带上神性。带不了神性,能多点人性,也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