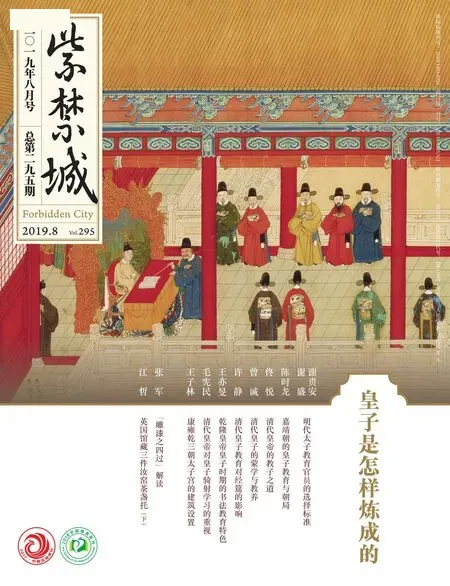流转与鉴藏(下)英国馆藏三件汝窑茶盏托
2019-11-18江哲
江 哲
(接上期)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汝窑瓷器
收藏概况及溯源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目前藏中国器物约一万八千余件,同大英博物馆一样,也以陶瓷最多最精。(马丁·罗特《序言》,吕章申编《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卷》,安徽美术出版社,二〇一四年)藏品来源包括博物馆购买,以及藏家、艺术品商贩不间断地捐赠。
一八五七年正式建成的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前身。与大英博物馆不同的是,南肯辛顿博物馆开办的主旨是收藏优良的艺术品而非古物。因此在其成立之初的十年中,中国工艺品藏品多为十八世纪的物件。(柯玫瑰《中国外销瓷》,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一四年,页一九)
一八八二年二月,南肯辛顿博物馆支出五百镑请居住在中国的史蒂芬·布绍尔(Stephen W.Bushell,一八四四年~一九〇八年)代购「造工优良的物品」,一年后获得各门类的藏品共二百五十三件(组),其中不乏官窑、哥窑、钧窑等精品瓷器,甚至还买到了宫廷旧藏(一件有底款的清乾隆官窑茶叶末釉长颈瓶)—推测很可能是二十余年前因鸦片战争从圆明园流散出来的。(刘明倩《从丝绸到瓷器——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页四八)布绍尔是英国驻北京使馆的专业医生,在京城居住了三十年,精通中文,还翻译了《陶说》(由清乾隆年间的进士朱琰所撰写,是首部综合整理、记述中国陶瓷史的作品,在海内外影响广泛)。一八九八年,在布绍尔退休前,他被英国教育部委任撰写了《中国艺术》(Chinese Art),其中记录了一件布绍尔自认为是「汝窑观音尊」的藏品,但如今据图片来看这不过是一件仿出土墓葬品的赝品(刘明倩《中国文物和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吕章申编《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卷》,安徽美术出版社,二〇一四年,页五),而这也印证了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宫廷文物还没有大量外流之前,西方收藏家对「汝窑」这一御用品接触了解甚少的事实。
一八九九年,南肯辛顿博物馆正式更名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一九〇九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得到了乔治·素廷(George Salting,一八三五年~一九〇九年)的四千五百件遗赠,其中中国艺术品约占其遗赠的三分之一。斐西瓦尔·大维德爵士也随即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建立了重要关系:通过一位老藏家引荐,捐献了三件中国瓷器,开启了博物馆捐助人的生涯。(当时的英国藏家必须通过捐款和捐物来培养与博物馆的关系,以获取博物馆的相关信息)
乔治·尤莫霍浦路斯(George Eumorfopoulos一八六三年~一九三九年)本是希腊裔造船业大亨,曾任东方陶瓷学会主席,不幸受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市影响陷入财务危机,只得在一九三四年提出将自己大部分藏品以约市价四分之一的价格出让给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Helen Long,The Unobtrusive Collector,The Antique Collector,1991,p.88-91)一九三五年,傅振伦先生赴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展,返回中国前受尤莫霍浦路斯夫妻邀请共进午餐,并参观其私藏,见到了汝窑瓷器。(傅振伦《伦敦中国艺展始末·十一》,《紫禁城》,二〇一四年第十一期,页一五〇)最终,尤莫霍浦路斯的大部分私藏被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于一九三六年正式完成收购并入藏,其中两件带乾隆皇帝御题诗的汝窑盘(编号1936,1012.150;1936,1012.178)均入藏大英博物馆。在他去世后,最后一批遗物先后于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四年拍卖,现存大英九十五号展厅一只镶铜扣汝窑圆颈瓶(编号PDF.61)就是一九四〇年伦敦苏富比拍卖时被大维德爵士买走,后来一直存于大维德基金会。(Yorke Hardy,Ex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Catalogue,Vol.VI,No.E368,1953,p.75)除了收藏与捐赠,尤莫霍浦路斯氏曾于一九二三年发表过关于汝窑的文章,臆测「汝窑即影青」。(George Eumorfopoulos,Ying-Ching,Ju and Ch’ai Yao,T.O.C.S II,1922-1923,p.24-38)由此可见,因为当时缺乏考古实证,从布绍尔医生的误判到尤莫霍浦路斯以及其他学者的论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的英国收藏界存在着各种对汝窑的粗浅认知及误判。(Hetherington A.L.,The Early Ceramic wares of China,London:Benn,1922,p.69-70;Hobson R.L.,The Catalogue of the George Eumorfopoulus Collection of Chinese,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London:Benn,vol II,1926,p.3-5)
原哈里·加纳爵士旧藏汝窑茶盏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经济繁荣发展,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于一九八七年开放了中国外销展厅。一九八八年,徐展堂先生(一九四一年~二〇一〇年,香港著名商人、慈善家、艺术文物收藏家)资助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建立中国展厅,并于一九九一年正式开放。本文将要介绍的第三件汝窑茶盏托便是展厅展品之一,并从此一直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四十四号厅(即中国展厅)向公众展示。
这两件汝窑盘原属尤莫霍浦路斯的私藏,均带有乾隆皇帝御题诗。
此件为本文介绍的第三件收藏于英国的汝窑茶盏托。
此件盏托造型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汝窑茶盏托的造型几乎一样。
这件汝窑茶盏托与上篇大英博物馆所藏两件汝窑茶盏托的相似之处是:盏托都由上部分碗杯、中间托碟和底部撇口圈足三部分组成,且都是中空的{Rose Kerr(柯玫瑰),Song Dynasty Ceramics,London,V&A Publications,2004,p.30,pic.18a};表面均有冰裂纹,开片稍大的线纹颜色较深。与大英博物馆所藏两件汝窑茶盏托的明显差别在于:此件盏托的托碟非五瓣花形而是简约的圆形(与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北宋官窑青釉盏托造型几乎一样)。此外,该盏托托碟边缘较薄的釉层处因再氧化,使得天青釉呈现出一种略偏粉红的色调。该盏托口缘经琢磨并镶铜,撇足也因被削而露胎。
这件汝窑茶盏托最特别之处还在其铭款——足内里边缘处镌刻「寿成殿」三字款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寿成殿」这三个字是在茶盏托烧成后经人为錾刻上的,字的缝隙里还涂有红色颜料。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从字体判断认为这三字「近似那个爱好为开封宫殿命名题字的宋徽宗的笔法」。(《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页一〇九)据考证,「寿成殿」可能是南宋孝宗成肃皇后谢氏的居所,刻此铭文的器物当与此宫殿有渊源。(吕成龙、韩倩、徐巍《附:「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导读》,《紫禁城》,二〇一五年第十一期,页三六~页三八)刻有同样字样的存世古器物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定窑盘(台北故宫博物院《定窑白瓷特展图录》,一九八七年,页一六);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汝窑盘上亦錾刻有「寿成殿皇后阁」六字,但未加红色颜料。
阅读链接
加纳爵士给约翰·艾尔斯信件原文节选
◎“The bowl-stand has been bequeathed to the Museum for more than 7 years……I may mention here that my associations with Museum go back over 40 years,when I used to bring pieces of Chinese blue-and-white to Honey and Leigh Ashton for their opinion.Since then Arthur Lane and,of course,yourself,have always been most helpful.The gift can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a sign of appreciation to the Museum.”
◎注:信中所言“The bowl-stand”即加纳爵士捐赠的汝窑茶盏托,“the Museum”特指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信中还说明了捐赠这件汝窑茶盏托是为了感谢四十年来诸位友人在加纳爵士藏品方面(如中国青花瓷)的帮助。这件汝窑茶盏托见证了加纳爵士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之间的情谊。
此件汝窑茶盏托也是哈里·加纳爵士的旧藏——目前英国仅存的三件汝窑茶盏托中,竟有两件为加纳爵士所捐赠。此件汝窑茶盏托是一九七〇年由加纳爵士赠予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加纳爵士在一九七〇年四月十日给朋友约翰·艾尔斯(John Ayers)的信中,感谢在博物馆任职的诸位友人这些年来的勉励及情谊,并以捐赠此件盏托作为谢礼。同时这也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入藏的第一件器物,时间比大英博物馆入藏加纳爵士旧藏另一件汝窑盏托还要早一年。
关于此件汝窑盏托更为传奇的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相关资料显示,它是哈里·加纳爵士以不可思议的低价「捡漏」得来——这件珍贵的汝窑瓷器是从伦敦露天市场(street market)买来的;(同前引柯玫瑰二〇〇四年之文)还有一说是加纳爵士在逛英国「卖二手的慈善店」时淘到的。(同前引刘明倩二〇〇八年之文)
这件汝窑茶盏托是否真的经历过被人舍弃在「露天市场」或「二手慈善店」的沉浮现无法考证,不过这件御用品上明显留下了经过磕碰并被人修补的痕迹——盏托托碟口缘被磨并镶有铜扣、撇口足被整体削掉了一截,且至今边缘还有一些小豁口,豁口上填充了一点「青蓝色的合成物」,修补精细。根据柯玫瑰女士记录,以上这些修复肯定是一九七〇年此件茶盏进驻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之前就完成了的,而且「这件器物明显曾被珍视,因为其修补是通过很大的努力完成的」(同前引柯玫瑰二〇〇四年之文)。到底何时、在何处完成修补?谢明良先生认为,两岸故宫均藏有许多镶铜扣的传世宋瓷,这些铜扣多出自清宫造办处之手。(谢明良《金银扣陶瓷及其相关问题》,《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石头出版,二〇〇八年,页一七四)而从所呈现的「打磨」、「镶铜扣(并做旧处理)」、「随色」等几个修补的关键步骤来看,结合纪东歌在二〇一三年两岸故宫研讨会论述并发表的《乾隆时期宫廷瓷器修补》(纪东歌《乾隆时期宫廷瓷器修补》,《南方文物》,二〇一四年第四期,页一三九~页一四七)来分析,笔者认为这几个修补特征皆契合清宫造办处修复旧藏宫廷瓷器的关键步骤和方法:此件茶盏很可能先经过玉作,经「好手玉匠」打磨破碎的底足和托碟口缘;接着在铜作「镶铜扣」并做旧「烧古色」,以起装饰或延长使用寿命之效;最后再找画师,在足部边缘打磨所遗留的小缺口处「找补颜色」——即补上近天青色的填充物。至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这件汝窑茶盏托到底是否曾为清宫旧藏、修复时间地点到底是不是在清宫造办处,除前文根据修复特征和目前学术界修复研究的粗略对比推断之外,还有待科学研究给予更多的证据支持。
本文所述三件汝窑茶盏及其所涉及的人物、机构和事件,恰好反映了二十世纪御用及传世精品文物外流后,英国逐步建立「中国式」鉴赏的过程和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影响。汝窑是中国陶瓷艺术的精粹,其含蓄内敛、静谧的特征下,蕴蓄着无穷的生命力,凝聚着庄严、崇高的美,这种美超越了时代和地域,从南宋流传至清朝,更流向域外到达欧洲,至今被世界所珍视。对美的追寻、对中国陶瓷艺术的纯粹鉴赏也是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无法停止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