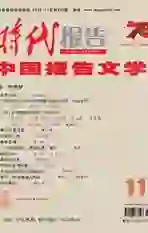一览众山小
2019-11-17阿莹
阿莹
我知晓长安画派已经是上世纪的80年代了,那时候由于社会氛围和资讯的落后,人们对这个艺术流派的形成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可是随着市场经济铺天盖地的冲刷,各种“画派”脱颖而出,几乎让人目不暇接,也就渐渐减弱了我对长安画派的热情。然而,最近我阅读了几册中国美术史后,不由得萌生了研究这一艺术现象的念头,进而阅读了长安画派领军人物赵望云、石鲁等人的档案,瞅着那一个个蝇头般大小的钢笔字,眼前便浮现出画家们孤傲而坦荡的身影,便想到他们坎坷而又执着的一生,不由得被这些卓越艺术家对美术事业的不懈追求所激励。尽管他们已经相继辞世三四十年了,但他们的笔墨精神依然活跃在当今画坛,他们所铸炼的人格力量,已不是一句“高山仰止”就能概括的。
随后我又仔细阅读了近年面世的赵望云、石鲁等人的画论画集,又与依然热衷美术创作的画家后人们进行探讨,忽然发现,由于种种浮躁的因由,人们对長安画派的研究始终处于一种简单疏浅的状态,这不能不让人为这个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成长起来的这一珍贵的艺术现象感到遗憾,于是我开始梳理有关长安画派的形成与成就,似乎对我国今天美术事业的发展不无裨益。
一
世界上任何一个艺术流派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天,我们讨论长安画派的艺术成就,首先要把握这个流派核心成员的创作实践,准确把握他们所取得的艺术风貌。我们知道长安画派是上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学术概念,今天回顾和审视这个艺术现象,首先应该对这个艺术流派的画家状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便从容把握和理解长安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位置。令人欣慰的是没有人质疑长安画派是以赵望云、石鲁为核心的,而品读有关长安画派的作品和评论,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杰出的画家在汇聚西安以前艺术主张和学术抱负是基本一致的。
赵望云从23岁步入画坛的那天起,就立志要创立中国画的“民族形式”和“中国气派”。他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瞄准现实的艺术创作,举办了三十多次的个人画展,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表现劳苦大众疾苦的作品,申明要抛掉清代“四王”的范式,将笔墨和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在中国画坛刮起一股赵氏画风,引起了中国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从此这一风格再也没有发生过动摇和偏离。而石鲁是从20岁就走进红色延安的,他致力于创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新画风,开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此他还将自己的姓名也由冯亚珩改为石鲁,取国画大师石涛和文学巨匠鲁迅的姓氏组和而成。那清代的石涛以强调笔墨的时代性而著名,那现代的鲁迅始终将文学作为投枪匕首,所以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传统与现实的结合,极其鲜明地概括了他的思想和艺术追求,数年之后这个名字果真响彻中国画坛。也许,这就是命运的绝妙安排,那时候他们两人一个在“国统区”,一个在革命圣地,却殊途同归西安,为长安画派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长安画派的形成过程,发生过三次极其重要的“事件”,从而汇聚了一批国内顶级的美术人才,构成了这个艺术流派的智慧核心。
一是1949年7月,来自“国统区”的左派画家赵望云与来自红色延安的石鲁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文代会上相见。这应该是长安画派形成过程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两人的档案记载得很清楚,尽管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当时两位极具才华和抱负的美术家在京见面时的情形,但可以推断两位美术家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当时赵望云43岁,大大小小的画作上报刊进画展,与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合作更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吸引了国内众多文艺大家的关注,郭沫若就曾为此写过颂诗,周恩来也曾慕名买过画作,叶浅予、黄苗子等一批享誉中国画坛的艺术家对赵望云的创作实践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扬。而此时的石鲁刚刚进入而立之年,年轻的石鲁在延安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熏陶,其艺术才华已在根据地展露风采,尽管如今保留下来的资料很少,但我们依然可以从那有限的版画和速写稿中看到他卓然超群的天赋。我注意到延安时期的所有鉴定材料,都对石鲁的艺术水平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所以,我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个对后来的中国画坛产生深刻影响的会晤,无意中为长安画派的最终形成做了一个“未经批准”的准备,在长安画派的发展史上应该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
二是1950年9月,陕西以赵望云、石鲁为主成立新的国画研究会,吸收了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等一批颇有艺术底蕴的优秀画家,在西安形成了一个高扬革命现实主义旗帜的艺术群体。从此这些画家便在两位大师的带领下,一次次地上陕南下陕北写生素描,一次次地汇聚在美协小院的某个小屋讨论画稿,几乎每位画家都有代表自己最高水平的代表作当期问世。按说作为赵望云入室弟子的黄胄和徐庶之也属于这个范畴,只是他们刚刚聚合不久就奔赴自己倾慕的地方,但他俩的创作始终没有冲出长安画派的窠臼。的确在中国美术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画派能集聚这么多顶级的艺术家,为日后创立长安画派奠定了组织和艺术的基础。
三是1961年10月,西安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班习作展”,整个艺术团队在京整体亮相。这些作品以精湛的笔墨描绘了西北风貌和新社会的新生活。其中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各有二十余幅,石鲁有五十幅,李梓盛有近十幅。这一百五十余幅画作,犹如猛烈刮来的一股西北风,新的构图,新的色彩,让中国画坛为之一振,标志着中国画在现代意义上取得一个可喜收获。虽然当时他们谦卑地把展出的作品统称为“习作”,但还是让沉寂已久的中国画坛轰动起来,评论家们毫不犹豫地将这一群画家创作的这一种风格的作品,概括为“长安画派”。从此这些画家、这个画派再没有离开过评论家们的视线,至今还让人感到振奋和骄傲!
这里,我们厘清了长安画派的发展过程,有必要对这一艺术流派核心成员的人生状态有个清醒认识,以便准确把握长安画派的艺术特性。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大家都认为赵望云和石鲁是长安画派的核心,没有他们便没有长安画派。是的,自从两人在西安汇合,命运便把他俩紧紧扭结到一起,也把他们的艺术实践和友谊带到生命的终点,使得两个耀眼的名字深深嵌进长安画派再也无法分开。如今,由于各种原因,在坊间时常会有长安画派的流言溢出,其实这些杰出艺术家的胸怀之博大,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难以理解的。由于赵望云与石鲁的人格力量与长安画派的形成息息相关,我试图对两位杰出艺术家的艺术与感情状态做些分析:
一方面,长安画派注重反映百姓的现实生活。我注意到长安画派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都秉承着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描写火热的现实生活,而没有把笔墨浪费在反映古人诗意和闲情逸致上。赵望云应该是那个时期最清醒的国画家了,而用中国笔墨来系统反映农民的生活他应该是第一人。这位眼力独到的大师创新了中国画的表现方式,他始终强调:“国画如果要有前途,就必须从芥子园的框框里跳出来与现实结合,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加倍关心。”大师对百姓的挚爱是深入骨髓的,他始终将笔墨瞄准现实生活中的百姓。新中国成立前,画家不避风险游历大江南北,穿越“国统区”和沦陷区,用画笔将人民的呐喊和苦难表现得动人魂魄。新中国成立后,画家笔下依然充满对底层百姓的关注和热情,一大批精品力作应运而生。那一套《桑蚕组画》就是新农村史诗般的写照,有的画面是郁郁葱葱的桑树,姑娘们在树林间若隐若现,桑叶的清香微微飘出;有的画面姑娘们在清洗蚕具,圆圆的簸箕舞蹈般在溪水里起起伏伏;有的画面是养蚕小屋,密密麻麻的蚕宝宝带给人丰收的畅想,幸福也都全印到蚕农们的脸上了。选择这个角度来概括新社会,显示了杰出艺术家的智慧和表现力。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后有外贸部门专请赵望云绘制一批仕女骚客的画作,画家依旧固执己见上交了一批农村题材的作品,执着的艺术追求令人闻之动容。
另一方面,长安画派注重提炼创作对象内在精神。石鲁也注重反映现实生活,但要求更深入。他有段谈论华山的论述极为精辟:“大家都在画华山,可那古人眼里的华山是修行炼道的地方,而我们看到的华山则是祖国壮丽河山,蕴含着民族的精神。”所以这位激情澎湃的大师努力使创作更集中更纯粹,以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石鲁笔下的华山巍峨挺拔,透出一股凛然正气,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岸。笔者特别要强调的是,石鲁坚持艺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尤其是用笔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最著名的就是那幅《转战陕北》了。今天我们平静地欣赏这部旷世之作,依然会被作品所传达出的豪邁所感染,苍苍茫茫的山峦之间,一位背着斗笠的小战士将战马拴住歇息,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屹立在浩瀚深邃的群山之上,显示出运筹帷幄的自信和淡定,使人想起伟大领袖气势磅礴的诗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幅作品之所以令人震撼,之所以能成为长安画派的扛鼎之作,就是画家将伟大领袖置于壮阔的山河怀抱之间,领袖与人民与时代与祖国山河的关系把握得生动而又准确。后来画家谈到这幅作品的创作,正是由于他经历了转战陕北的过程,从而精妙地驾驭和艺术再现了这一重大革命题材,任何时候去品读都会感觉到作品昂扬的张力,而这恰恰在中国传统绘画里难见其踪,被视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毫不为过。
第二、创新了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从中国画的发展看,传统绘画基本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山水、花鸟只是为了衬托人物氛围而存在着,后来三种类型分野以后,愈发强化了各自门类的独立性,从此似乎互不搭界了。而长安画派却是将山水、花鸟重又与人物融为一体,互为背景来表现创作者的主题,从而把中国画的表现形式朝现代思维推进了一大步。
首先,是将人物置于山水之间,人物是作品的点睛之笔。传统的山水画也有饮茶抚琴的隐士和山坳里的樵夫,也有市井的卖家和游历的商客,这应该是这种表现形式的滥觞,但那些人物只是山水风貌的点缀,仅仅是画面的陪衬而已,起到的是渲染山水主题的作用。而长安画派是将人物纳入作品的核心,使风景与人物融为一体,取舍哪一部分都难成佳作。比如赵望云那幅《集场归来》,我们看到一群农家男女簇着骑着毛驴马车,提着背着集市购买的货物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边一棵棵参天的老树似张开的翅膀,抚慰着经过的农家儿女,其中的景色和人物互为补充,生动地描写了那个激情燃烧岁月的典型场面。而且画家没有直接描写集市,仅仅抓住了返家归途的瞬间,巧妙地展示了劳动者生活富足的风貌。这种构图延续了画家始终不渝的艺术主张,画面人物与风景互补,洋溢着轻松与自然,新中国的新面貌也由此可见矣。
这种创作风格与石鲁的艺术实践也大体一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石鲁的创作风格明显在向这方面靠拢,同时他又大胆进行创新,达到了一种更加集中更加强烈的震撼效果。比如那幅代表作《东渡》,汹涌的黄河浪花四溅,一群赤露上身的战士奋力驾驭着小船向着胜利的彼岸,而毛泽东站在小船中央气定神闲成竹在胸,把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风度生动展现在读者面前,那河水的汹涌和危岩的狰狞,都是为衬托船上人物的气场,谁见到那幅饱蘸着创作者才情的作品,都会感到运筹帷幄的豪迈席卷而来。
其次,是将山水融于人物情怀,山水尽显意境之美。人们欣赏山水画所能传达的意境闲逸,所以古时的山水画总能看到茅屋、亭阁、板桥、山径,里面也常有小小人物半遮半隐,让看惯了神道仙姑的达官闲士找到了进入逸情的通道,成了居室附庸风雅的象征。而长安画派的作品,山水是他们描写的主要背景,但这个背景是为画面中的人物服务的,你阅读这些作品一方面会为壮美的山河所感染,另一方面会为山河里的人物所牵挂,似乎在石涛、黄宾虹等山水大师的画作里较少这样的范例。赵望云画的那幅《万山丛中》,众多人们在山崖下,辛勤劳作,英姿飒爽,把山的壮阔与人的潇洒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最为经典的就是赵望云那幅《深入祁连山》了,层峦叠嶂的山峰与深深浅浅的沟壑挤压着,让人可见山的壮阔和沟的深邃,而那行进在山间的骑马人盘旋于群山之巅,且不知何时才能到达终点,不由得为跋涉者不避艰险的壮举肃然起敬,也为画家选取这样一个角度表现山与人的壮美而赞叹不已。
而石鲁在这方面也进行着积极探索,他创作的山水画同样引入了人物形象,但他更深一步提出“要把山水当作人来画,有的是高大的,有的是坚强的,有的是优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水画就是人物画”。这种“形而上”的画论,至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令人沉思。为此他进行了卓越的实践,那幅《逆流过禹门》,气势磅礴,惊涛拍岸,群山似被激流劈开,江水顺势而下,只见一位船夫奋力驾驭着小船,汹涌的波浪更将小船掀得快要侧立起来,其浪也高,其势也险,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让读者几乎感到身体都禁不住剧烈摇晃。那幅《延河饮马》却把山的壮阔与晚霞的恬静拉到面前,巍 巍宝塔迎面而立,一群马儿欢快地扑向延河岸边,两位牧马人紧随其后,潇洒自如。整个山河都沐浴在红灿灿的霞光里,牧马人的幸福也就跃然纸上了。所以,这幅杰作如果没有牧马人的点睛,就难以由纯粹的山水来实现意境的升华,如果没有山水创造的意境,那牧马人就会显得单薄无力,二者缺一不可矣。
第三、创新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有人曾经追问长安画派的特点,老画家概括了四个字“不断探索”。的确,“不断探索”应该是长安画派的精神所在,而画家们所竭力推崇的“民族形式”和“中国气派”就是长安画派的不懈追求。我们注意到赵望云和石鲁都有大量的作品没有题款,那可不是他们的疏忽,而是他们对自己的创作不甚满意的表现。一生注重诗、书、画、印和谐的石鲁,甚至到晚年磨平了印章,喜欢在作品上画印,让人感觉怪异,其实大师直言是他感觉那些传统钤印已不符合创新的笔墨意境了!
一是将写生带入笔墨。我们知道中国画的笔墨讲究写意,甫一面世就将写意作为这个艺术品类的风格顽强地延续下来,所以中国古代画家讲究看山读水,喜欢游历江河湖泊,寻觅能感动自己的神韵。但这种阅历更多地是一种寻找美感的过程,而很少会将阅读对象真实地收入尺幅,所以中国画不论是山水、人物、花鸟,写意的成分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几乎可以说基本拒绝写生。但赵望云认为中国画创新的突破口在于写生,在于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所以画家身体力行,走南闯北,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月,依然将看到的山水人物凝聚到笔端,通过写生去采撷创作灵感,此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获得了艺术界的满堂彩。那幅《秦岭林区》画的是掩映在山间的帐篷里的人们,神态之生动,劳作之忙碌,令人不由得为之感慨。而且赵望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大都具有写生笔墨的鲜明特征。那《初探三门峡》就是这一创作方法的代表之作。站在这幅巨作前,尽管山势狂野危石林立,尽管江水湍流涛声拍岸,但你感觉不到大自然的压迫,反而会被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所感染,在这些激情万丈的劳动者面前,必然高山低头、江河让路,这就是优秀艺术作品给人的感受。而且赵望云不但身体力行,还要求入室弟子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白天到街上去写生,晚上将写生稿改绘成水墨画,这些画家后来也都能够成为了美术大家,这与当时苦练的创作方式不无关系。后来赵望云担任西北美协领导后更把这种心得无保留地与同道们分享,一次次带领大家看山望水写生采风,一次次读画阅书体验传统,使得中国画艺术从象牙塔里走到了十字街头,这在今天看来依然需要弘扬。
同时,画家们还竭力给写生注入感情。我们知道写生强调的是真实描绘目视物状,而石鲁直将写生提到创作的高度。他有一篇专论写生的文章,对写什么、如何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写生能发现真正活泼的东西,这是创作代替不了的,好的写生就是创作,但不能将写生直接搬进画幅。”石鲁的经典之作,似乎也与赵望云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幅《古长城外》应是画家不多的几幅早期的写实之作,生动而自然。而那幅《春播图》更把农民喜播粮种的欢悦直接挥洒到脸上,那赶牛的老农、扶犁的青年、等待收获幸福的女人们多姿多彩,使翻身农民的兴奋一览无遗。而且这幅作品只在上角画了一牛四人,大面积的留白裸露着土色,你会发现这是一群土改后的农民在给自己的地里播种,杰出的艺术品实在是太有概括力了,不能不伸出大拇指。
这里笔者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创作思维已经渗入画家骨髓了,石鲁不但努力写生现实世界,还瞄向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阅读画家在精神发病时创作的十余幅似乎充满呓语的怪诞作品常常会感到震撼,也会感到莫名深奥,似乎谁也道不清那些画作的意蕴,其实这是一位杰出艺术家完成艺术实践和人格塑造的巅峰之作。那些作品大多是在他十年前访印作品上的二度创作。当时石鲁人虽病了,但思想绝对没有病,艺术状态依然完整,所以没有一幅是涂鸦,也没有一笔是多余。你看那些印度老人和少女衣皱上绘满了似乎谁也无法解读的字符,那可不是精神错乱的涂抹,而是艺术家精神苦恼在艺术上寻求解脱,是试图用这种神秘的线条与笔墨表达对迫害的反抗和不满,当是画家精神世界的写生素描,是画家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卓越的艺术品质在作品上的升华。而且,令人敬佩的是画家即使在病中依然在追求美,那幅迷人的《美典神》,双眸微闭,圆润恬静,安详地斜倚在浓浓的红色里,中间露出的点点留白,还绘有篆刻般的提示字符,衬托着女神的热情和美丽。这幅杰作哪里是病人所为,翻遍石鲁所有的画作再没见过如此迷人的形象,所以这幅作品实质上是画家对美的真情告白,也是画家心灵的写生,是画家对美的追求登峰造极的表达。可能大师明白美的最高境界是残缺,而这幅作品太完美了,所以大师完成创作后竟将画作一撕为二,郑重地交给儿女一人一半,也许就是寓意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完美!
二是将赭黄融进笔墨。如果我们有兴趣翻开厚厚的中国美术史稿,就会发现中国的山水人物画追求的是雅逸和恬淡,近代也会有画家把笔墨浓重地挥洒到宣纸上,却依然是在表现逸情呈现悠远。而长安画派却旗帜鲜明地将赭黄大面积涂到画面上,在中国画创作领域可谓独树一帜。赵望云提出:“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基本色彩,不论历史怎样变化,文化形态怎样演进,而民族间的个性色彩是始终存在的。”
为此,长安画派的经典作家经过对西北风貌的长期观察和揣摩,提炼出了“沥沥搓搓的笔墨”,一种苍茫浑厚的色泽基调,与国内各地画家的风貌都拉开了距离。具体到作品上,就是彩与墨混同,多种皴法并用,其色泽浑厚,一展大西北韵味,又内隐筋骨,藏匿大西北的倔强,形成了一种接近黄土高原的美术色彩,把西北高原的苍凉与厚重透过色彩呈现出来。这种方法在赵望云解放前的作品中多有表现,解放后又加以精进,更加符合大西北的风情物貌,后经长安画派的进一步锤炼而更加生动自然。可以说长安画派经典画家创作的多数作品都喜用这种色调,其实这也就是美术作品时代精神的体现。赵望云特别喜欢描写祁连山风情,总能把这方水土的神韵描绘得活灵活现,与他把握了这种色调不无关系。那幅《陕北秋收写景》,山脊被一道道的梯田托起来,一孔孔窑洞高低错落在山峁间,喜获丰收的农民与毛驴拖着辘轴在麦场上脱粒,还隐约可见从窑洞出来的老乡和孩子,整个画面几被赭黄所笼罩,隐隐透出沉甸甸的喜悦。那幅《禹门渡口》,山势迎面逼仄而来,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几家门口的农人骡马与几间茅屋校舍隐隐若若,赭黄的山坡蜿蜒而来,场景幽静而又甜美,好一幅春光无限的幸福写照。
同时,石鲁也抓住了这种西北风貌的色调,创作了一批这种风貌的绘画作品,但是他对色彩的运用更浓重更热烈,似乎没有任何顾忌,直将人的感官逼得气喘,这当然是优秀艺术作品的魅力使然。那幅《山腰修梯田》,在层层叠叠的山腰上,密密麻麻的农民兄弟挥锄大干,一块梯田依次而上,且把劳动者汗水浇过的梯田染得一片赭黄,与那黑黝黝的山崖形成对照,凸显了今日农民的创造力。还有那幅《高原铁路到我家》,更把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用笔墨精致地刻画出来,尽管山顶白雪皑皑,山下却是热浪扑面,鳞次栉比的帐篷依山而列,运料的马队络绎不绝,直把山脚下的山坳闹得热热哄哄,横贯画面的赭黄冲击着人的视觉,相信很快就有天路铺到藏胞帐前。作品所以能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就是画家把握住了大西北的风土基调,使得画面充满朝气而又十分自然。
综上所述,赵望云上世纪40年代以创新中国画表现方式名载画坛,50年代以反映百姓幸福为己任,60年代则以提炼笔墨韵律为追求。而石鲁上世纪50年代以歌頌新生活为目标,60年代以重大题材突破而著名,70年代以创新笔墨入史册。长安画派的确为中国画的创新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在中国画坛上高高扬起了长安的旗帜,随着历史的演进,随着各种复杂因素的荡涤,我们将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创作实践给中国画坛带来的持久影响力。
伟哉,长安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