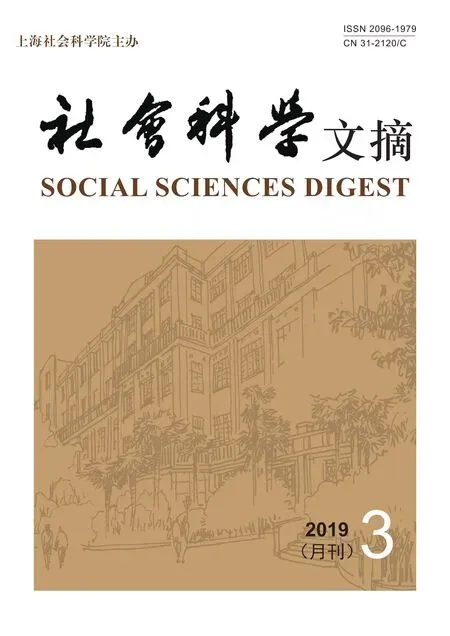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何一再遭到质疑
——基于哈佛大学学生罢课的分析
2019-11-17
引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使用自然科学的分析思维和方法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不仅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发展,而且也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日益相脱离。这样,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种缺陷在实践中的暴露,就出现了一轮接一轮的反思和批判思潮;同时,这种思潮也逐渐扩散到青年学子之中,一个典型事件是2011年11月哈佛学生的罢课事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垄断以及对其他竞争思维的排斥,造成了经济学界的单向度状态以及对现实问题的集体沉默;同时,这种沉默所换来的除了偶尔的抱怨外,最终将导致矛盾的集中爆发。因此,哈佛罢课事件根本上具有学术和现实两方面的深刻根源,它是30多年来经济学界反思运动的延续,也是无法根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之内在缺陷在教学上的周期性爆发。
然而,与经济学革新运动如火如荼的国际形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面貌和青年学子的态度: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对欧美高校发生的经济学革新毫不了解,也根本不愿了解,而只是一味地追随着所谓的“主流”。更为甚者,对学术反思和批判持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只有那些做不了真正的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去从事所谓的方法论探究,进而,他们也就将那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视为没有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而能力低下者,甚至当成非理智的愤青。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一群知识狭隘而无力反思的经济学人占据了重要的学术岗位,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限制经济学的多元化思维。
现代主流经济学何以遭受挑战
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深化对人类现实行为的认知并逐渐解决现实社会中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此,经济学理论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解释层面,而是要深入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同时,遵循从现象揭示本质以及由本质来审视现象的双向逻辑,这就为构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双重要求:(1)不能脱离日常经验;(2)又要把基于经验的认识与逻辑化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进而,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济理论体系要得到广泛的接受和传播,还必须经受这样的双重检验:(1)理论逻辑自恰的内在一致性检验;(2)理论与事实相符的外在一致性检验。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局限于对市场表象的关注,并基于先验的理性假说来构建逻辑化市场,进而为现实市场种种现象进行辩护,从而无法真正剖析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进而也就无法满足上述两大一致性的检验。
具体而言,一方面,就外在一致性而言,经济理论根本上要解决现实问题,从而需要与社会环境的演化保持一种历史逻辑的一致性。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理论与历史之间共同演化的逻辑关系,而日益被打造成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的抽象理论,从而导致理论体系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另一方面,就内在一致性而言,经济理论体系必须建立在自洽性的逻辑之上,各具体理论的内在逻辑基础也必须具有一致性。但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以及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却存在差异巨大乃至截然对立的前提假设,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往往采取不同的分析逻辑。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现代经济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但问题是,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存在根本性差异:(1)社会经济现象本身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演化的;(2)型塑社会经济现象的人类行为也具有明显的意向性,由此产生出不同的社会行为。同时,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根本性不同,使得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逻辑自洽性上也存在巨大差异:自然科学注重的是物理或数理的形式逻辑,而社会科学注重的是人的行为逻辑。这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简单地蜕化为静态的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关系,经济学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和“客观”的程度。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向自然科学攀亲,而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则不断拉大距离;相应地,它积极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进而致力于数理模型的构建和数学工具的使用,并由此以“科学性”而跻身于诺贝尔奖的殿堂。问题是,尽管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会捧出一两个“著名”经济学家,但这些经济学家在提高社会认知和促进社会发展上究竟提供了多少帮助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片面地向自然科学攀亲,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论文也越来越注重模型的优美,以致经济学研究蜕变成向他人展示智力水平的一种游戏,而非探究事物内在本质及其因果关系的一门科学,甚至经济理论也越来越成为与人类社会无关的“普适公理”。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课程所提供的也只是与任何具体问题都没有联系的“想象世界”,而且,它还借助数学工具极力排斥其他思想的挑战,进而对学生的思想和理解力造成了严重的压制。
其实,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根本上应该是问题导向的,应该关注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熟视无睹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具有强烈的方法导向,热衷于在既定范式下进行抽象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而忽视这些分析工具在真实世界的运用;相应地,现代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黑板化,经济学界的思想则犹如一潭死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黑板经济学”把青年经济学子训练成了一个个建模高手,却不具有有关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常识。这就如自闭症患者,他们往往具有特异的才能,在适当场合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由此获得大量收益,例如,具有超强记忆力的自闭症患者甚至可以被培养成赌圣,由此获得的收益甚至可以雇佣多个正常人为之服务。问题是,如果社会充斥了自闭症患者,那么,社会就会被割裂成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就不再有热情和欢笑,也形成不了良好的合作秩序,从而也就会导致社会的解体。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正处于这种处境,它正在培养出一个个自闭症患者,而这最终又将会解体整个经济学。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和反思,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新学科也逐渐兴起,它们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自闭病症。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还在极力维系它的正统支配地位,还在坚持理性+均衡的分析范畴,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死亡,我们也不能再用新古典标签来描述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了。实际上,任何现实主义经济学者都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现代盛行的那种经济学的弊端,有社会实践经历的学者更是如此。例如,斯蒂格利茨早年主要热衷于不对称信息下的保险、信贷、租佃、失业等抽象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探索,但自2006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后,他就加强了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同样,以开发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撰写主流宏观经济学高级教材闻名的保罗·罗默在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也发生了很大的认知转变,他指出,宏观经济学研究利率、经济衰退、失业、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等大事件,但显然,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预测经济大萧条,因为迄今为止的宏观经济学本身就是胡说八道。
有鉴于此,一批众多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以及非主流经济学家也起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说进行严厉抨击,进而也引起了不少主流经济学家的共鸣和反思。例如,“后我向思考”网站的扉页上就刊登了索德鲍姆、基恩、金迪斯、劳森、霍奇逊、本尼科特、吉列斯、布劳格、纳尔逊、阿克曼、张夏准、奥默罗德以及弗里德曼、斯蒂格利茨、科斯、诺思、里昂惕夫、缪尔达尔、索洛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批判。同时,正是深受主流经济学教材之害,进入21世纪后,由欧美高校学生发展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革新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兴盛起来了,它呼吁对现代经济学做根本性的改革。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教材却依旧阐发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智慧,整个经济学依旧深陷于没有思想、缺乏反思的单向度状态,这一情势最终酝酿出了哈佛学生的大罢课。
中国经济学界为何如此沉闷
面对欧美经济学界出现的轰轰烈烈的经济学反思运动,中国经济学界却呈现出截然背反的一种图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化取向越来越强烈,乃至绝大多数青年学子都投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事实上,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已经在西方社会遭到了激烈批判并处于快速的衰落之中,但是,中国经济学人却将之捧若至宝而大肆引进。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一方面热衷于社会热点和应用政策的研究,另一方面又热衷于照搬主流经济学教材中的方法导向研究而偏重于抽象的数理模型和计量实证,这就导致“黑板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以及社会实践所造成的恶果更为严重。
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的那些经济研究论文根本上是无意义的:(1)从事计量实证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对现实社会环境作正确的理解,从而那些实证分析往往非常牵强附会而根本无助于预测或指导实践,从而表现为“下不着地”;(2)从事数理经济学的那些人士根本无力在数理逻辑或模型构建上有所创新,而往往是机械地搬用(最多是对变量做些调整)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从而表现为“上不入天”。当然,随着“黑板经济学”缺陷的逐渐暴露,中国一些经济学人也提出了反思,并倡导“上天着地”式研究。问题在于,流行的所谓“上天着地”式研究往往被扭曲为:搬用教材中的一些理论来对具体问题进行解释或解决,结果,这反而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更严重的恶果。
其实,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发展根本上应该走知识契合的道路,但这一研究取向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却遇到极大的阻碍。究其原因,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往往简单地基于“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学术,从而也就缺乏起码的学术交流、对话和尊重。结果,基于知识反思和契合的研究路向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1)它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往往不能被当前甚嚣尘上的“主流”们所青睐;(2)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往往又不能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尤其是,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青年学子们更是迷恋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而对那些反思的声音要么是故作不理不睬,要么就是竭尽嘲讽之能事。因此,即使笼罩在2008年经济危机下的哈佛大学学生罢课事件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报道,但中国经济学界却依旧像一潭死水,青年学子依然毫无反应。
由此,我们就需要思考:中国经济学界为何如此沉闷?这大致可从四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崇洋心态:对国外经济学者往往采取一种仰视的态度,称之为“大师”或“泰斗”;相反,对中国经济学人则采取犬儒主义态度,把任何批判和质疑都视为是一种“自傲”和“不自量力”。
第二,中国社会还缺乏独立的人文思想这一“道统”:那些与政治需要不符的思想往往会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压制,甚至根本就无法发表;相反,承袭西方的主流范式尤其是数理范式则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学术压制,因为这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前沿研究,数学逻辑更显中立。
第三,中国经济还处于增长周期,较好的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抵消了人们对其理论基础的批判,而稍纵即逝的经济机会也使得大多数经济学人热衷于去把握现实机会而不是理论批判;相反,西方经济学子之所以起来反对主流经济学,因为这种理论指导下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明显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第四,中国的市场经济远远不是完全竞争的,不同岗位的收益相差极大,而进入具有高收益的财经岗位往往依赖于文凭之类的“敲门砖”,因此,经济学专业的学子往往热衷于获得这样的“敲门砖”,而不在乎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认知。
很大程度上,前两者反映了崇洋主义、媚俗主义的学术精神,而后两者则反映了功利主义和务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显然,正是两者的共同作用和强化,使得中国经济学人热衷于追随主流学术,热衷于模仿数理经济学的形式,而鲜有时间和精力对这种流行范式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和质疑。
事实上,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很少有经济学人能够且愿意对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经济学众流派的学说进行系统梳理以及对相关知识进行契合,并由此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展开系统审视和批判。这些经济学人往往会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各类学术宗派所排挤,从而就只能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学界当然也就难以有真正的学术探究,相反,盛行的大多是那些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学术规则以牟取私利的学术蟑螂。特别是,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基本上都为一些功利主义的海归经济学人所掌控,他们倾向于制定一系列的学术奖惩制度来推行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只有那些遵循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思维和分析范式的数理文章才能得到认可,乃至形成了居绝对支配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中心观。在这种游戏规则下,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热衷于撰写为主流认可的形式文章。
结语
马歇尔很早就指出,经济学必须遵循日常生活的实践,经济学的理论也必须用大家所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使用大家所不熟悉的术语名词和数学符号,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进入经济学的门槛,其结果就是,经济学与社会大众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日益相割裂,最终蜕变成一种“我向思考”的经济学。同时,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经济预测和社会实践中遭遇越来越多的失败,西方社会就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起来寻求改变,以致每一次重要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类似哈佛罢课的事件。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人却依旧在大肆照搬这种新古典的主流范式。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学人深受功利主义和传统智慧的双重束缚,而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传统智慧都促使中国经济学人追慕西方的主流,与主流一致才会带来认可,才会带来利益。显然,正是这种学术取向导致了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化和一元化,从而严重窒息新思想的出现和成长,严重制约学说理论的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学的僵化和形式化,很大程度上又与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精神有关。正是由于缺乏学术反思和批判精神,大多数经济学人热衷于学术的“照搬主义”,乃至整个经济学界日益陷入一种缺乏否定的单向度状态,进而造成了如此沉闷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