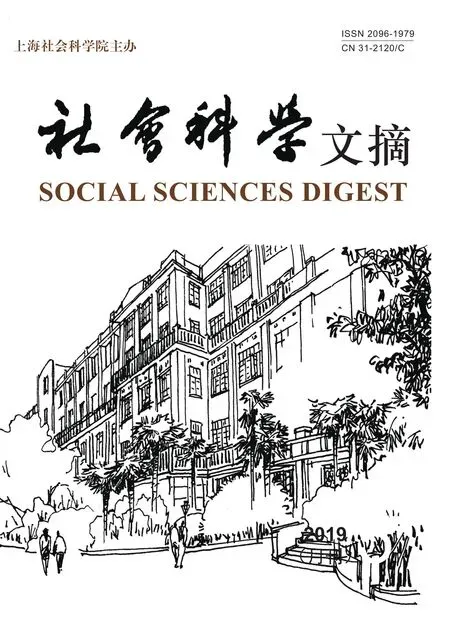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019-11-17
诞生于1919年,为了防止一战这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重演而开启的国际关系学,今年迎来了百岁诞辰,而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前景的争论也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国际关系学依然是大学中的一个热门专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她能在日趋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指点迷津,但这个被形容为“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先是沉湎于理论的构建和范式的争论,接着又在范式的争论之后消沉下来。有学者甚至围绕“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然,也有西方学者早就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五大弊端”,并就重构国际关系学进行尝试,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设方案;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也在通过不同路径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所有这些反思、批判、构建和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之中,“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成为重要的发展取向,同时与国际关系演变的历史和现实更为直接地联系起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遭遇如此尴尬局面的重要原因,是1919年以来世界的发展变化“撑破”了原来人们对解读国际关系所设计的框架,其内涵和外延的“野蛮”生长早已超越了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界限,而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拓展或将是其重获生命力的必由之路。
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
首先,所谓的“国际关系”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许多历史学家的经典著作也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著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国际关系学的产生也和历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出现这样一种情形的重要原因是,历史学一直把人类共同体的演进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种共同体包括部落、城邦、帝国,当然也包括帝国之后的“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是“越界”,而是其学科发展的传统,只不过历史学家研究国际关系的视角和方法与政治学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而已。其次,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经历了一个“去历史化”的过程,但迄今为止,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与政治学中(在中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都是政治学的“二级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依然有许多重叠之处。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研究和大战略研究方面,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更是难分彼此。许多杰出的地缘政治学家和战略学家既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也是在历史学领域中享有盛誉的学者。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对比1919年,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严重地”重新塑造过了:整个世界已经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组织起来,新兴的“主权国家”几乎蔓延到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些“类似单位”表象的背后是传统的种族、族群、部落、宗教和教派利益的重新组合,是新兴政党的生死博弈,是血与火的“洗礼”。幸运的国家,这一过程绵延数千载;不幸的国家,几十年过去,依然在国家建设的路上踯躅前行。一战和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都没有能够消解掉这些国家的“前现代遗产”,而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新的国家、区域和全球治理模式,以及新的世界秩序,又在探索、过渡乃至重构之中。如何解读这一被重塑的过程,既是历史学的责任,也是其他学科包括国际关系学的需求,更有可能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新的出发点。
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可能性
历史学的特点决定了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可能性。当然,关于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学界有诸多争论,也有诸多误解。对于许多其他学科的人来讲,历史或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把历史的“真相”挖掘出来。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和历史学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学的突出特点是她的双重特性:它一方面研究人类所有“过去”的活动,有着独立的研究对象、领域及理论和方法,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另一方面,其研究领域又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相关学科的“历史”研究部分相交集。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种交集不仅仅涉及他学科的“专门史”,而且还涉及他学科的“学科史”。这种“交集”为国际关系学“历史路径”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当然,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在考察同一历史现象时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历史学家往往倾向于把历史事件都作为个案考察,努力挖掘出它的特殊性;国际关系学家则倾向于把历史的分析简约化,为理论抽象创造空间。在这方面,法国学派的研究呈现了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时间变量的多元性和空间维度的多层性。历史理解离不开时间、空间、记忆、过程等范畴。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常常将这些因素默认为常量,而历史研究则将其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变量来考量。这或许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陷入“僵局”的原因所在,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优势和价值所在。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双边关系”不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在过去百年的演化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内涵和外延都“无休止地扩大了”。历史学已经不再仅仅专注于政治史,而是深入拓展到文化史、社会史、观念史以及环境史等领域,历史人类学和历史社会学更是已经各成体系,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历史学也不再仅仅在国别史和区域史方面下功夫,而是在跨国史和全球史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国际关系学也已经超出了“一个传统学科的想象”,不仅把非国家行为体纳入研究范围,而且也把目光投向资源、环境、人口和气候等领域,“国际”的范畴被大大拓展了。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都在向学科群的方向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化,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重新匡正学科视角,跨越“国界”的束缚,而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最新“拓展”的领域有高度重合性,这也为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拓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选题
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选题有许多。首先是对“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探究。尽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经蔓延到全世界,但传统的种族、族群、部落、宗教和教派等所谓“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顽固地生存下来,并且在许多新兴国家的构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东、中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区。在这些“构建中国家”中,种族、族群、部落、宗教和教派等历史的演进已逾千百年,而“民族国家”是一种新鲜事物,许多国家的边界都是西方殖民者人为制造出来的。当一个新兴国家的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一直不能取代或超越其他社会组织认同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聚合的力量就难以平衡和战胜分裂的力量,国家建设的任务就依然没有完成。
其次,国家的历史类型学分析。关于国家的类型学分析,政治学已经有大量优秀作品问世,但大多没有把足够的历史背景纳入其中。面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学者已经放弃对国家的专注,转而把目光投向族群研究。当然,被纳入国家体系的族群、部落和宗教或教派等社会组织,也已经与原初不一样了,进入了一个新的演化过程。国家的历史类型学分析,就是要把这种演进过程的取向分析出来,以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前景有一个明确的把握。笔者曾经以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为线索,把当今国家分成“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并试图对“构建中国家”再行细分。这样一种分法也是初步的,期待学界同仁有更为精致的划分方法。
最后,人类共同体演进的逻辑。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我者”与“他者”之间分化与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共同体演进的过程。比如在古埃及,“我者”指的就是居住在古埃及疆域内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群体,反之即是“他者”。“我者”与“他者”的关系还有三个递进层次:相互对立;“我者”的构建以承认“他者”的存在为前提;二者非此即彼的关系也可以发生转化,并最终走向认同。古埃及文明中“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我者”的聚合便是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关于共同体的定义有许多,一般指的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聚合在一起生活的群体、组织或团队”的含义,既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也包括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民族。实际上,当今世界并不仅仅是由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构成的,而是由千百个共同体聚合而成的世界,其中既包括在主权国家之内或跨国界存在的族群、部落、宗教或教派组织,也包括以超越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区域共同体等。
我者与他者的转换,人类共同体演进逻辑的研究,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弹性”发展指明一个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不应该“僵化”在国家身上,因为现实的“国际”已经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互动,而国家也只是人类共同体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主导单位而已。如果要想消除国家之间的“零和”游戏,扩大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消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负面”作用,就必须逐渐推进“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转换,构建更大的超越国家边界的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似乎已经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初衷,但它与当初创建国际关系学科的目标相一致,这就是消弭战争,实现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