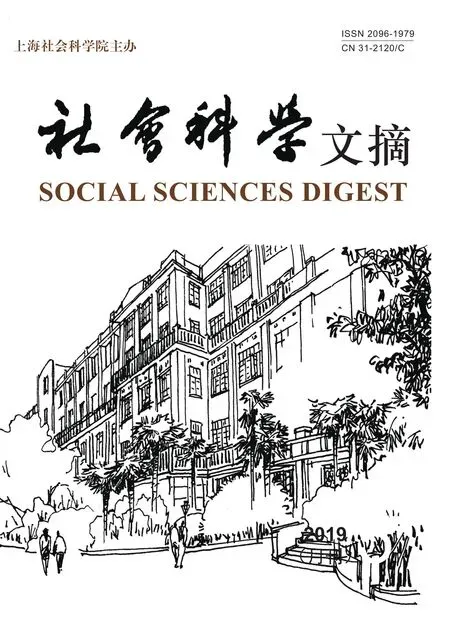关于“去鲁迅化”现象的思考
2019-11-17
何为“去鲁迅化”?
“去鲁迅化”,也被称为“鲁迅大撤退”,是21世纪以来人们对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逐渐减少的一种现象的概称。这两种称呼法,前者更为恰适。因为前者“鲁迅”是作为被动名词,后者“鲁迅”是作主动名词,而在语文教材的调整中,鲁迅作品是被调整,带着一点无可奈何。相对于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被动状态,现实中人们的话语状态则更为主动。这种主动的话语状态让本只属于语文教育域场上的简单教材调整,逐渐演变成公共文化域场上群雄舌战的文化大讨论。而且,此讨论不是热议过后便归为平静,而是成了一种“间隔性爆发的癔症”。
“去鲁迅化”进入公众讨论视线,至少可追溯到2007年。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语文教材删减鲁迅作品的新闻是在2007年8月16日,人民网杨卓发文质疑中学语文教材放弃鲁迅作品而选择金庸作品,这是否让中学语文课本变味儿了。但人们当时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对金庸作品《雪山飞狐》进入北京版语文教材的争议上。“去鲁迅化”成功撩起公众讨论欲望得从2009年说起。这主要是由于,湖北省进行高中课改,在准备使用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文章相较于之前少了两篇。2009年7月17日,许多网站转载《长江日报》关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新闻称,“梁实秋文章首次入选语文教材,鲁迅作品明显减少”。此文章一投入公众视线,便激起了千层浪。新闻报纸、社交媒体纷纷对此发表评说,鲁迅的作品成为了“鸡肋”、与时代有隔膜、被踢出中学语文教材等字眼刺激着人们的眼球与神经。虽然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老师表示,人教版选录篇目在调整,鲁迅被剔出中学课本是一个伪话题,教材已经在一些省市用好几年了。然而,人教社的澄清早已被网络难以控制的流言淹没。
2010年9月6号,一位编剧的微博牢骚,竟将“去鲁迅化”的热议推向了高潮。编剧刘毅发微博称语文经典大换血,“鲁迅大撤退”。“鲁迅大撤退”一词便来源于此。此言论火速在网络上传播,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看客们”你一言我一语,主要形成三种态度:第一种是看到鲁迅文章终于减少了,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第二种是强烈批评中学语文教材删减鲁迅文章,认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立人”之根本;第三种是认为鲁迅文章调整是语文课本改革的正常变化。
“去鲁迅化”热议过后,亦慢慢有冷却的趋势。但在余论还未偃旗息鼓之际,2013年,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风筝》一文“飞”走了,这一引火线导致关于“去鲁迅化”的讨论再一次席卷而来。在此次讨论中,人们逐渐反思表象之下的更深刻的问题,如教材改革只是教学的一部分,如若教学方式不改革,单调无味的课堂将赶走任何一篇被选入的“鲁迅”。另外,“去鲁迅化”大讨论犹如单士兵所言,形成了一个轮回:一旦讨论形成新闻,很多人就会运用鲁迅的批判精神对其他风花雪月的文章指责一番;出版社会跳出来肯定鲁迅的文坛地位与教材地位安抚人心;文坛的专家学者则搬出“鲁迅论”,高呼他不能被抛弃;不少逻辑混乱的知识分子也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以搏一回眼球。然而这样的争论是偏离了教材的受众(学生)的讨论,仅仅是一场空谈。此后,每逢开学季、鲁迅逝世纪念日、鲁迅的诞辰纪念日等与教材、鲁迅有关的日子,与“去鲁迅化”类似的新闻标题都会出来露个面。在2017年秋季全国推行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之时,有关“去鲁迅化”的新闻又卷土重来了。总体来说,虽然公众对此的讨论影响广泛,但是很多讨论并不是平心静气的对话,并不是有理有据的辨析,并不能作较为全面的分析,甚至还有以讹传讹等不负责任的言论出现。
为何“去鲁迅化”?
调整鲁迅作品的第一施事者为语文教材的编者,我们不该忽视编者的声音而随波逐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曾呼吁大家应“理性审视教材对于鲁迅作品的选编”。事实上,“去鲁迅化”是为积极落实语文课标要求作出的适应学生认知规律的合理调整,是教材编写不断自我改进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过往经典与当下时代激烈碰撞的必然取舍。
一是积极落实语文课标要求而作出的适应学生认知规律的合理调整。语文课标对教材编制应该依据学生生理、心理以及语言能力的阶段发展规律已作明确要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教材编写应依据课程标准,全面有序地安排教学内容”,“教材应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水平”,“各种类别配置适当,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然而众所周知,鲁迅作品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其思想深刻性更是令很多成年读者读后都陷入云里雾里,而要使中小学生充分了解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进而分析理解这样有难度的作品,可能是一项艰巨而枯燥的任务。即使优秀的老师能将鲁迅文章讲得形象生动,多数学生仍难以对其感兴趣。正如语文课堂教学那句为人熟知的、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的玩笑话所言,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常常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所以,为了让中小学课堂教学能够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做到适时而教,教材的编选有必要对过分深刻的作品作适当调整。
二是教材编写不断自我改进的必经之路。教材的编写是一件众口难调的艰巨任务,有关鲁迅作品在中小学教科书中的数量、位置等问题,最终的教科书成品也必然经历多方争论的妥协与和解。大众在轻而易举地提出对教科书编写的不满时,往往容易忽视教科书编写的每一步自我改进的艰苦尝试。语文教科书的课文容量是有限的,如果因为鲁迅文章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伟大,而使得教材必须永远将其置于重要位置,不能作丝毫改动,那么,这可能是对鲁迅作品的最大讽刺。鲁迅的怀疑批判精神是我们向高度精神文明社会迈进的基石。“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一经典之问对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同样受用,对于大众如何看待“去鲁迅化”现象依然会有所启发。
教材的“去鲁迅化”现象,乃至“类鲁迅”作家选文的减少现象,是教材改革进程的一部分。教材编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朝着科学合理的编写机制不断尝试的过程。不得不说,鲁迅的某些文章在必修课本中被删除,是整个教材编制系统中的一个小部分。虽然这一部分很重要,但是依然要服从整个系统的协调安排。
三是反复衡量过往经典与当代精品的必然选择。在语文教材的课文编选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矛盾选项,比如在有限的容量下如何能够既强调过往的经典作品,又强调丰富的时代气息,与学生的经验世界保持紧密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也可以回答为什么语文教材会出现“去鲁迅化”的现象。但遗憾的是,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答案。过往经典与当代精品在中小学的教材中,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端。语文教材应该把握好度,让矛盾的两面相互协调,形成最大的合力,共同为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而铺设好语言文字之路。而且,语文教材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丰富性。教材内容的丰富性特征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学生阅读各样文本、掌握多种学习方法的需要。由此观之,鲁迅先生的作品篇数在教材中的调整,是综合考量教材编选经典性、时代性与丰富性等要求的结果。
“去鲁迅化”为何会引发社会间隔性“癔症”?
“癔症”,又叫“歇斯底里病”,是医学范围内的一种神经障碍。这里是指人们听闻语文教材“去鲁迅化”时,表现出的一种兴奋性情感状态,或欢呼庆贺,或赤面相批,或悲愤无奈。这使得各种情绪化表达充斥网络之中,而理性化的分析屈指可数。那么,究竟“去鲁迅化”为什么会引发社会间隔性的歇斯底里呢?我们可以抓住关键词“间隔性”“去鲁迅化”“社会”几个关键词,逐步抽丝剥茧,探其缘故。
在发生时间上,语文教材“去鲁迅化”事件有一个明显特点,它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的未终结事件。它主要是随教材变动而出现。由于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篇目调整时间不一样、同一版本不同地区使用时间不一样,“去鲁迅化”讨论便呈现出一种间隔性。而随着语文教材的调整完善,“去鲁迅化”这个事件可能依旧会持续间隔发生着。
事件的发生和大众的知晓中间是依靠媒介来联系的。在“去鲁迅化”由社会大众传播并引发讨论这个事件中,媒体发挥着巨大的信息传递和价值导向功能。然而,在此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媒体缺乏事件报道的真实性,存在着炒作嫌疑,部分为博眼球的炒作行为让鲁迅作品调整的讨论事态升级;而且,部分新闻媒体对旧事重提的偏爱也是“去鲁迅化”引发社会间隔性爆发歇斯底里的原因之一,如在和鲁迅有关的重大日子里,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减少的新闻常会再次浮出水面。
媒体在“去鲁迅化”大讨论现象中其实只处于“助攻”地位,中学语文调整鲁迅作品之所以会让社会歇斯底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鲁迅作品本身的争议性。其实,教材进行的篇目调整并不是只针对鲁迅作品,但只有鲁迅作品被删减引起了如此轩然大波。对于“去鲁迅化”,一方面,人教社本着从学生认知出发,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对中学语文教材进行篇目调整;另一方面,诸多研究鲁迅和爱好鲁迅文章的知识分子,把鲁迅供奉于神坛地位,大有动谁都不能动“鲁迅”之势。还有部分一线教师单一从自己的角度,以鲁迅作品难读、难教为由,站在删除鲁迅作品的赞同面,这对于评价鲁迅作品也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因此,“去鲁迅化”呈现间隔性的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鲁迅作品理解的差异性。
从“社会”方面分析,鲁迅作品减少引发群众“歇斯底里”的情感宣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由于中华民族向来的保守性生成了一种新不如旧的习惯性思维,在“去鲁迅化”现象中,则演化为一种“鲁迅情怀”。这种情怀源自儿时对“三味书屋”的好奇,源自曾受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问题的搅扰,源自对《山海经》的遐想,源自将“早”字刻在桌上的模仿行为。当这样一种情怀遭到破坏的时候,群众将对学生时代的记忆统统化为了歇斯底里的表现。这实则是对鲁迅文章的怀念,并且包含着一种怀念学生时代的复杂情绪。其二,在对“去鲁迅化”的歇斯底里的争议中,不乏有人是借讨论鲁迅作品调整之名,行指责中学语文教改之实。这主要体现在人们表达对鲁迅作品被删减的情绪中,既有对语文教材变动的不解,又有对语文教学弊端的反感,还有对中国教育的批判。当这些情绪纷纷融入对“去鲁迅化”事件的看法中时,自然而然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爆发。因此,“去鲁迅化”引发的社会癔症是民众复杂性情感的综合爆发。
对“去鲁迅化”现象的反思
从2007年到如今,“去鲁迅化”讨论仍在继续,热闹一阵,沉寂一阵,而且讨论的过程十分相似。这样的讨论很像是在原地打转,如鲁迅曾在《在酒楼上》形容的那只苍蝇一样,被人一吓,飞走了,绕了个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去鲁迅化”现象产生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我们需要认真辨别,并且反思如何继续保持有利影响,减少甚至去除弊端。
这种全民参与的大讨论,实际上体现的是全民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和重视。以往,民众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多是和高考有关,如高考语文分数调整、高考作文题难易等。这次“去鲁迅化”的大讨论,涉及的群众包含各个知识阶层。它无疑成为了人们关注语文教育的一个新的突破口。人们的关注其实也是现代公民意识的体现,他们不再一味地服从上级安排,而是有一种平等意识,借助网络媒体平台发出自己对事件看法的声音,与教材编者大胆对话。在这种全民关注语文的氛围中,语文教育改革者将会更加慎重地完善语文教育,促进语文教学改革稳步前进。
然而,“去鲁迅化”的讨论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试图探寻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减少甚至避免类似“去鲁迅化”中极端社会歇斯底里的舆论爆发。首先,从语文教材选编的角度来看,教材选编“鲁迅式”作品不仅应该做到经典性与可感性的统一,而且要加强宣传力度,提升教材编选过程透明度,增进公众对语文教材调整的理解,让群众既明白每一篇教材选文的重要性,又明白并不是所有经典作品都能进入语文教材,这其中还要从学生的接受能力等方面考虑其成为教学文本的可能性。当然,为了减少学生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隔膜,语文教材也可以让学生从别人笔下的鲁迅形象中了解鲁迅其人,从别人对鲁迅作品的评价,增进对其文本的阅读兴趣。另外,现行教材编写机制可多加创新,设置大众参与机制,集思广益。同时,亦可考虑让学生拥有阅读选择权,从而达到经典性与学生可感性的调和,编选出优秀的语文教材。其次,在语文教材试行或正式使用阶段,媒体应做到全面调查、真实报道,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为人民群众报道语文教改的进程,而不是以增加关注率、点击率为主要目的,创造新闻噱头,引导大众展开歇斯底里的争辩。同时,鲁迅研究专家和爱好鲁迅文学作品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去鲁迅化”的教材改革事实下,应选择理性表达自己的见解,维护鲁迅地位的神经不要太过敏感,要明白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择不能单单从鲁迅的文章之伟大的角度来论证,更应该从中国语文教育的实际情况、中小学生的接受情况来研究。
“去鲁迅化”歇斯底里的情绪爆发也暴露了很多人浅表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当看到北京版教材金庸作品《雪山飞狐》入选教材,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被删减,则立马想到金庸顶替鲁迅,并将二人做一番比较;当看到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入选人教版教材,鲁迅的《药》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被删,则又联想到了梁实秋顶替了鲁迅。这种浅表性的思维是缺乏深入思考能力的表现,是中国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的体现。公众对于语文新教改,应该多一份宽容,在保持现代公民意识的同时,以应有的理性去看待、思考和评价身边的社会事件。
结语
回顾“去鲁迅化”间隔性大讨论的始末,或者说这是一个仍未完结的过程,随着语文教材的变化,讨论依旧会间隔性爆发。但是,通过反思讨论的整个发生过程,剖析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希望未来的讨论不再引发社会的极端癔症,不再沦为文化讨论的泡沫,不再依旧轮回、停滞不前。未来的讨论,应是在公众对语文教学的了解下,对教育现状的熟知下,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与信任下,展开的一场多元的、平等的、文明的深度思考与自由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