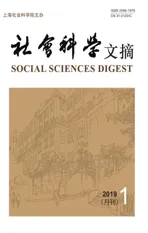如何理解“法理”
——法学理论角度的一个分析
2019-11-17
张文显教授在《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中,凝练了“法理”的概念,主张法理学应是“法理”之学,“法理”应当成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面对“法理”这个全新的法理学范畴,首先需要思考的两个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就是:一方面,“法理”概念有何必要?“法理”概念针对的是何种问题?另一方面,“法理”如何能够成为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如何回应其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法理”为何能够发挥和承载其所设定的理论功能和实践意义?
自觉和反思:法理学的为学标志
自觉和反思之于一门学问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哲学和法学在西方诞生的历史逻辑中得到印证。古希腊,尤其是苏格拉底之前的西方并非不存在对于世界的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巴门尼德对于“存在”的提问已经表征了西方人对于宇宙根本问题的形而上学思考。但是,人们往往把苏格拉底视为西方“哲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性人物。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古希腊直到苏格拉底方才把“美”“善”“正义”“幸福”等概念作为思考的对象。概念本身是人类认识的结晶,因而对于概念的考察意味着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认识,属于对于思想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自觉意识和反思色彩。而且,苏格拉底对于概念的自觉意识和反身思考借助了智慧的“助产术”——理性主义的“辩证法”,由此形成了进行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的专门方法,具备了较为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借由“认识你自己”的德尔菲神谕,自觉反省了人类进行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的理性限度,人类被认为只是具有“爱智”的性质,至于“智慧”本身则被归诸于神灵。正是对于概念作为哲学的认识对象、理性主义辩证法作为哲学的认识方法和爱智作为哲学的认知限度的自觉和反思,这使得西方的哲思追问活动和哲理求学实践成为了一种“哲学”。
同理,人类自从产生法律以后,就有了对于法律现象和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就有了相应的法律意识和观念。古罗马之前的西方并非不存在对于法律现象和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就已出现了对于法律现象的哲学式反思。例如,《米诺斯》中对于“法是什么”的追问,已经不再是对于各种具体“法”现象的思考,而是对于抽象大写的“法”本身是什么的形而上学式追问。但是,人们往往把西方法学的诞生归之于古罗马,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古罗马人已经初步形成了观察法律现象和思考法律问题的自觉。这种自觉意识突出表现在乌尔比安的如下论断之中:“法学是有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它集中展现了古罗马人对于法学的问学对象(神和人的事物、正义和非正义)和学问属性(知识和科学)的明确自觉,这是古罗马人对于自我法律意识的意识,是对法律观察活动的二阶观察和反身思考。而且,古罗马人使用“jurisprudentia”(法律实践智慧)指称“法学”,更是表明其已经意识到了自身认知法律的必然限度。这种自觉和反思使得古罗马人观察和思考法律现象和问题的实践活动得以成为一门“法学”。
因此,对于法学自身研究对象、方法及其限度的自觉意识和反身思考,是法学之为法学的重要标志。
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检视和批判
上述只是一般性地阐释了法(理)学为何需要对其研究对象、方法和限度进行自我觉解和反身思考,聚焦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具体问题。古今中外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论述形成了源远流长、复杂艰深的学术脉络。针对域外部分有关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阐释,本文将其主要分为对象直陈式和问题论域式两种模式。
(一)对象直陈式
“对象直陈式”的理论模式主要是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或是特殊限定的“法(律)”,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直接地论说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方式。这种理论模式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简单地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显然无法区分法理学与其他法学科目,诸如法教义学、法史学,因为其他法学科目同样也是以“法(律)”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诸多论者,例如普佛尔滕当然知晓简单地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显然无法区分法理学与法学的其他分支科目,因而提出了以认知角度或方法作为划分法理学与法学其他科目的标准。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哲学本身就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没有本体论的方法论,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方法论的本体论,这些区分提法只不过是对哲学的人为分割和分类。一方面,“对象决定方法。就法而言,这意味着:法提出了哪些问题以及应以何种思考方法回答这些问题都取决于法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另一方面,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决定了研究的“视界”,“视界”决定了研究者所能“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世界”,亦即研究对象,同样也决定了研究者能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所谓在研究对象之外增加研究方法的标准,实际上只不过是借助于视角或方法进一步澄清和厘定了其所研究的真正对象而已。
第二,众多学者俨然知晓简单地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远不足以把法理学与其他法学科目区分开来,因而各自基于对于法理学问学方式和学问特质的理解,针对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予以进一步方式各异的特殊规定或限定。例如霍布斯、霍兰德等人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实证法”“实在法”,康德、考夫曼等人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自然法”“正当法”。但是,这种界定法理学的方式使得本应属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被人为预先排除出了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但是我们并不能通过定义的方式将学科所要讨论的问题预先地排除出去。同样,格雷、埃利希等人对于法理学及其研究对象的界定,也是以其对于“法律”的特定前见作为立场和基础,通过预先定义的方式人为地排除了部分本应属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对象直陈式”的理论模式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部分学者为了进一步区分法理学与法学其他分支科目,对其增加了其他限定,由此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诸如“实证法”“自然法”,或是“一般法”“普遍法”及其“一般原则”“根本原理”等特定的法律形态或要素。但是这些限定方式除了上述论及的缺陷之外,共同存在的问题在于,它们基本上忽视了法理学的另一重要研究对象——法学。法理学不仅研究作为规范的法律,而且应当研究作为学问的法学本身,这也是作为整个法学之方法论的法理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二)问题论域式
“问题论域式”的理论模式并不直接明确表述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或通过列举的方式把法理学界定为研究某些特定问题的学问,或通过概括的方式把法理学界定为研究基础问题、一般问题的学问。以此阐述法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或主题论域,进而间接表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通过法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或其所触及的主题论域揭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能够较为直观地表达法理学的问题意识,是表征法理学的学问特征和问学方式的重要方式。但是,对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论域式界定,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通过问题论域的方式阐述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混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仍未阐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因为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反之,即使是使用相同表述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可能探究的内容也会存在差别。
第二,由于法理学的问题论域本身处于不断开放之中,因而始终无法穷尽所有的法理学问题,因此我们无法从“论题”“主题”“问题”的角度来界定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实际上所有的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都可以从法理学的层面和角度予以追问和探究,这使得以问题论域式的方式来界定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难免陷入挂一漏万的窘境,终究会不当限缩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第三,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不同论著对于法理学“一般性”“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的不同理解和主题设定,除了部分共同问题之外,仍然存在明显差异。这就使得在貌似相同的话语表述背后实际上隐含了其各自相异的理论立场,这种表面上的相似回答实际上遮蔽或回避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个仍然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既有域外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两种主要理论模式——“对象直陈式”和“问题论域式”——要么简单笼统地界定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因而未能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区别于法学其他科目,无法彰显法理学的问学方式和学问特质(比如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或“法律”的理论);要么因为各自既有的理论立场和前提预设,不合理地预先排除了本应属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因而不适当地限缩了法理学的研究范围(比如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实证法”或“自然法”的理论);要么因为混淆了研究对象和其他问题,因而实际上并未真正回答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比如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研究问题论域的理论)。因此,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自觉和反思的问题。
“法理”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和证成
(一)“法理”的内涵要素
“法理”具有丰富深邃的内涵,“法理”包含了“法之道理”“法之原理”“法之条理”“法之公理”“法之原则”“法之美德”“法之价值”“法理之学”等构成性内容,使得“法理”成为了一个具有“丰富”而且“深邃”内涵要素的概念。“法理”虽然源于或关于“法律”,但又不等同于“法律”,突显了法理学与法学其他科目,尤其是法教义学、法律史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法理”概念的“丰富”使得“法理”具有了“泛在”的存在形态,使得以“法理”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同样具有了相较于上述既有理论模式的诸多优势。
(二)“法理”的论域范围
“法理”概念不仅具有上述丰富的内涵要素,而且这些内涵要素分别触及了性质不同、类型有别的主题和领域,这使得“法理”概念具有广泛的论域范围。
一方面,“法理”既包含了从经验角度描述和总结法律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起源、演进、发展、变革之内在机理和客观规律的“法之道理”“法之是理”“法之条理”。“法理”也包含了从逻辑角度归纳和提炼法律规范体系内部的逻辑结构、效力位阶、解释方法、推理模式、论证方式等问题的“法之条理”“法之机理”“法之事理”“法之道理”。“法理”还涵盖了从价值角度表征和体现法律的价值标准、价值追求和价值体系的“法之原理”“法之公理”“法之美德”“法之价值”。这使得“法理”概念涵括了法律所触及的三个主要论域,亦即法律的经验—事实领域、逻辑—规范领域和价值—评价领域。
另一方面,“法理”既涵盖了表征“法学”历史演进规律、内在结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法学之理”。“法理”也包含了“法律之理”。“法理”还涵括了有关“法治”基本问题的“法治之理”。通过包容了“法学之理”“法律之理”“法治之理”的“法理”概念,法学、法律和法治都成为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
(三)“法理”的层次结构
“法理”不仅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要素和广泛论域范围的概念,而且是由不同层面、领域的法理构成,由此形成了一个复杂融贯的“法理体系”。根据“法理”的抽象程度、指涉广狭及其在整个法理体系的层次结构关系,可以将“法理”分为三种密切关联但又大体可分的主要类型:基本法理、一般法理和具体法理。
基本法理,意指作为整个法理体系基础和根本的法理。一般法理,意指统摄各个部门法领域的一般性、普遍性法理。具体法理,意指相对于基本法理和一般法理而言,抽象程度较低、涵盖范围较狭,主要涉及特定法律部门和法律个案的法理。
由于“法理”具有多样的结构层次,这使得把“法理”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更为清晰地表征了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层次和结构;避免了人为割裂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及其他法学科目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法理体系内部的结构关联,更好地建立起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及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关联。
(四)“法理”的维度属性
“法理”同时具有不同的维度,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多重属性进行分析,“法理”至少具有“本体”“方法”和“价值”三重基本维度属性。
1. 作为本体/实体的“法理”。作为本体或实体对象意义的“法理”,主要旨在回答或侧重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法理”?“法理”的内涵要素、外延范围、特质属性为何?存在哪些“法理”?存在何种类型的“法理”?等等。
2. 作为方法/视角的“法理”。我们可以从方法或视角的意义上,针对“法理”提出这样的问题:“法理”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维度或方法?如何才可以称之为“法理”分析、“法理”解读?如何才是一种“法理化”或“法理性”的思维方式?等等。
3.作为价值的“法理”。“法理”还具有“价值”的维度,它主要试图回应、解决的是依据“法理”“应当如何”的问题。例如我们常常在以下语境中使用“法理”一词:“……的法理证成”“……的法理基础”“按照法理”“根据法理”“法理中国”,等等。
正是由于“法理”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要素、广泛的论域范围、复杂的结构层次和多重的维度属性,“法理”具有“泛在”的存在形态,这使得以“法理”来界定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克服了上述“对象直陈式”和“问题论域式”两种模式的诸多缺陷,使其更为准确、全面地澄清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更为合适地表征了法理学的问学方式和学问特质。因而,以“法理”概念来统摄和指称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成为一种更为合适的理论。
结语
“法理”概念的提出,是对法理学问学方式和学问特质的自觉和反思,是对法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澄清和厘定,相较于既有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式,把“法理”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具有更大的理论优势。借由“法理”的问题化和概念化,法理学将其研究的中心主题聚焦于“法理”之上,更多的法理学问题将被开放出来,这无疑是有助于推动法理学转变成为真正的“法理”之学。